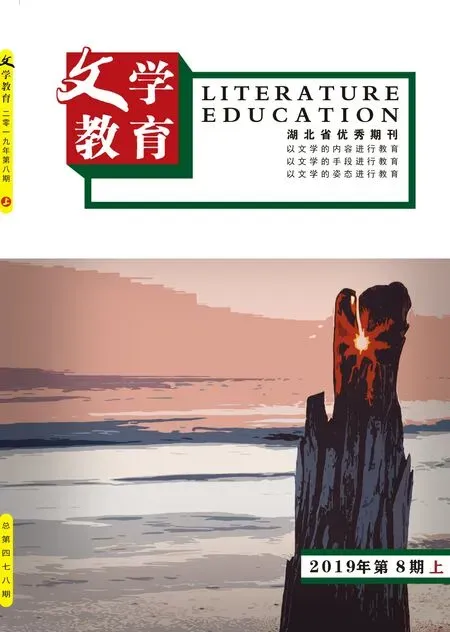羅伯特·弗羅斯特詩歌的“不確定性”解讀
汪 虹
一.引言
羅伯特·弗羅斯特是美國當現代文壇唯一一位獲過四次普利策優秀詩歌獎的詩人,他,連同艾略特、龐德、威廉斯和史蒂文斯一起,被譽為20世紀美國詩壇五巨擎。較艾略特、龐德詩歌之浮華張揚,威廉斯詩歌之獨辟蹊徑,史蒂文斯詩歌之隱晦艱澀,弗羅斯特詩歌別具風情,其詩多以新英格蘭鄉村為背景,田園氣息濃郁,使人讀來清新流暢、通俗易懂,然而,如弗羅斯特自己所說:“我是一個十分難以捉摸的人……當我想要講真話的時候,我的話語往往最具有欺騙性。”[1]其詩雖多采用傳統格律,看似簡單直白,卻極具不確定性。詩中精妙難斷的隱喻意象、似是而非的文本悖論、懸而未決的多元結局,不僅賦予了讀者不確定的多元解讀可能,也彰顯了詩歌簡約而不簡單的深邃內涵。“他的詩具有一種不確定性,既嚴肅又活潑,既實在又空靈,既穩定又飄忽,既明白易懂又富于暗示;讀者初讀時感到簡單明白了,可再讀幾遍便會發覺它們的寓意深刻。”[2]在此不確定性創作理念下,讀者亦能積極地投入詩歌解讀之中,全方位、多角度地探尋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復雜關系。
二.隱喻意象
隱喻是“將兩個差異性‘不一定是對立’的事物并置并形成‘甲是乙’這樣一種陳述”[3]。“利科把隱喻過程看成是認知、想象、感觸。”[3]可見,基于認知方式、想象空間和感觸行為的差異,不同讀者對同一隱喻的理解將呈現不同視角、不同方法、不同領悟的不確定多元解讀。
“湯普森認為弗羅斯特詩歌藝術的核心是隱喻的使用。”[4]雪、樹林、河流、山巒、路、村莊、農場……,各意象以隱喻形式在弗羅斯特詩歌里層出不窮,在不同讀者的不同領悟下,詩歌的隱喻內涵往往變得不再確定。
《進入自我》為弗羅斯特第一部詩集《少年心愿》(1913年)的開篇之作,“樹林”是此詩的主要隱喻意象。“我的一個心愿是那片黝黯的樹林,/那片古老蒼勁而微風難進的樹林,”[4]那么“樹林”意喻何在?“開篇第一首詩歌《進入我的自己》(“Into My Own”)是一首十四行詩,其題目便直截了當地告訴讀者詩中人是要躲避他人和逃離社會”[4]。“我”如何避開塵世的紛擾、遠離他人,進入我的自己?唯有走進心愿中那片“樹林”,它是遠離喧囂生活的棲居之所。在標題“躲避”意義的聯想下,隱喻意象——“黝黯的樹林”“古老蒼勁而微風難進的樹林”應順理成章地意指為“離群索居的隱世生活”。
然而,將詩歌創作背景帶入解讀,隱喻意象“樹林”卻另有他解。收入《少年的心愿》詩集前,《進入自我》已于1909年5月在《新英格蘭雜志》發表過,“也是在那一年,弗羅斯特曾攜家人野營旅行,一路上觀察野生植物,那是一次長途的旅行,他們一直走到佛蒙特州的威洛比湖才停下來。像這樣將身心都放置于大自然之中的旅行在弗羅斯特的一生中是經常進行的事。當然,《進入自我》這首詩并不是在那一年的旅行中寫下的,但卻一定是在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中有所感觸才寫出來的。”[5]此創作背景下,詩與大自然間的緊密關聯不可忽視,正如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的名篇《我好似一朵流云獨自漫游》:“水仙花在我的心靈閃現,/使我在幽獨中感到欣然”[6],詩歌常被解讀為“人不僅能從自然中尋求安慰和寧靜,也能從中凈化靈魂和情感”,詩中“水仙花”被認為是“大自然”的隱喻,如此一來,與“水仙花”同屬性的“樹林”亦可認定為“大自然”之隱喻,“我”將投入大自然懷抱,在大自然中尋求人生真諦,成就真實自我:“他們將發現我依然是從前的自己——/只不過更堅信我所想的都是真理。”[4]
作為弗羅斯特熟為人知的名詩——《雪夜林邊》,“樹林”是此詩的主要隱喻意象。“這是誰的樹林我想我清楚,/他家就在那邊村子里邊住;/他不會看見我在這里停下來,/觀賞白雪覆蓋住他的林木。”[7]詩歌講述作為旅人的“我”為觀賞大雪覆蓋的樹林美景而停下腳步,不再趕路前行之事。從詩意解讀,“樹林”隱喻意象可理解為“大自然”,為一睹大自然的無窮魅力,“我”寧愿“在這一年最黑的一個夜晚,/在這樹林和封凍的湖泊之間,/停在近處不見農舍的野外。”[7]“大自然”之美雖讓“我”流連忘返,然世俗瑣事纏繞,“我”終歸不得不放棄自然之美景,重回塵世喧囂之中,“這樹林可愛,陰暗,幽深,/但是我還有許諾的事要完成,/臨睡前還要再趕幾里路程,/臨睡前還要再趕幾里路程。”[7]
然而,“最黑的一個夜晚”“封凍的湖泊”“不見農舍的野外”“白絮般飄飄落下的雪片”“陰暗”“幽深”等多種凄涼意象的出現,給詩歌籠罩上了濃郁的恐怖氛圍,不同視角下的“樹林”解讀應運而生:“樹林”即“死亡”。白雪覆蓋的樹林美景——“死亡”引誘著“我”,“我”亦被其深深吸引,欲放下一切投入其懷抱,然而馬兒及時讓“我”醒悟,“他抖了抖挽具上的鈴串,/像問,是否有了差錯出現。”[7]“但是我還有許諾的事要完成,”[7]“我”終究逃脫了“樹林”——“死亡”的誘惑,回到了現實中,在“死亡”到臨之前繼續完成未了之事。
此外,“另一部分評論家認為,‘樹林’是詩人既不熟悉卻又必須面對的潛伏危險的景物,而詩人卻依然冒險走進樹林,以尋找創作靈感。”[8]“樹林”即作者的“創作源泉”。“我”不顧嚴寒,奔赴白雪皚皚的樹林,只為從中尋得創作靈感,最終在這片幽深樹林中,“我”覓得所求,并對其難舍,但想到未完之創作,“我”馬不停蹄地回趕,“臨睡前還要再趕幾里路程,/臨睡前還要再趕幾里路程。”[7]
在《永恒的象征》中,弗羅斯特宣稱“詩歌就是比喻,說一事而指另一事,或說另一事而指這件事,因而具有一種隱晦之樂,詩歌簡直就是由比喻組成的,……每一首詩內部都是一個新的比喻,否則這首詩就毫無意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有的詩歌運用的總是那種相同的、古老的比喻。”[9]弗羅斯特詩作除了“樹林”這一帶給讀者無限遐想的常見隱喻意象,其他隱喻意象在其詩作中也比比皆是。如詩歌《牧場》,在僅兩節八行的簡短詩行中就出現了“泉流”“落葉”“小牛仔”“母牛”四個隱喻意象,它們極大豐富了詩歌內涵,賦予了此首田園小詩不確定的多元解讀可能。“我要去清理牧場的泉流,/我只是停下腳步把落葉耙開”,“我要去抱回那小牛仔,/它站在母親身旁,幼小的身軀”[8],詩中對比出現的“泉流”—“落葉”,“小牛仔”—“母牛”隱喻意象使人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新舊交替、生死循環之自然法則,讓人從蕭條無望中看到了勃勃生機。
“這首詩(《牧場》)幾乎被排印在他所有的集子的扉頁或首頁,成了他詩作的族徽或牌標,事實上也是他大部分詩篇適當的樣品。”[7]弗羅斯特將《牧場》當作其詩作之榜樣,此詩與詩人的創作理念必然息息相關。如此,隱喻意象“泉流”“落葉”“小牛仔 ”“母牛”是否另有他解?對此,黃宗英教授認為:“在第一節中,詩中人所要清理的‘枯葉殘枝’暗示著詩人要放棄十九世紀陳舊的詩歌創作手法;第二節中那只掙扎著要自己站起來的牛犢似乎象征著詩人所追求的新的詩歌創作風格。”[4]不言而喻,“泉流”—“落葉”,“小牛仔”—“母牛”是詩人在詩歌創作上將推陳出新的意愿暗示。
弗羅斯特詩歌看似簡單易懂,但詩中各隱喻意象的不確定性解讀,卻使詩歌張力無限,讀者往往被帶入廣闊的思索空間,在不確定的多元解讀中探尋詩與人、人與自然間的深邃關系。
三.悖論文本
“悖論在古希臘時期是一個哲學詞匯,指的是愛麗亞學派的芝諾用兩論相反的方法提出的諸多詭辯。”[10]傳統觀念看來,悖論邏輯混亂,互相矛盾,充其量只是一種詭辯術。現代評論家卻認為,“在悖論中發現真理是人的最優天賦。”[11]悖論往往包含自相矛盾甚至荒謬的兩種意思,讓人感到似是而非,難以確定,然而“‘不確定性’本來就是因為這個社會到處充滿著不確定性;換句話說,‘不確定性’到真成為本社會中唯一最確定的事物”[12],在似是而非的悖論中,人們反能覓得本質與真理所在。
美國“新批評”代表人物克林思·布魯克斯認為悖論出自詩人語言的本質,偉大作品中必然出現悖論特質。作為美國當現代最偉大詩人之一的弗羅斯特,其詩作中的悖論特質不容置疑,如詩歌《收集落葉》,此首六節小詩中的悖論可謂隨處可見,它們的出現讓詩歌既矛盾難斷又意蘊深厚。
“用鐵锨收集落葉/不比用調羹順手,”[7]詩歌伊始,“鐵锨”—“調羹”此對悖論事物即讓讀者頗感費解。雖同屬用具,“鐵锨”為清掃工具,“調羹”則是餐具,此對用具無論用途上,或容量上都相差甚遠,實屬風馬牛不相及,那么,“調羹”真能用作落葉收集?且比專業收集工具“鐵锨”還用來順手?此外,“裝滿落葉的口袋,/輕得就像是氣球”[7],滿的口袋,卻輕如氣球,同一詩節,再次出現的悖論讓讀者又一次陷入難解矛盾中,可謂舊惑未解,新疑又生。
然而悖論未止于此,“我整天忙著弄出/沙沙響的嘈雜聲,/像小兔也像小鹿/奔逃在叢林之中。”[7]第二節中,“我”每天忙于收集落葉,辛勤勞作,“我”的辛勞卻與第三節的“收獲”構成悖論,“我捧起一座小山,/卻無法把它抱攏,/總留出我的臂彎,/總泄向我的面孔。”[7]與“我”而言,一切豐厚收獲都宛若浮云,無法真正擁有。
“我”似乎也意識到了此悖論的矛盾性,于是“我”在第四節追問自己“我可以裝了又卸,/千遍、萬遍重復,/直到填滿了小屋,可我又有了什么?”[7]答案卻又是悖論一組。“論分量聊剩于無,/由于接觸過泥土,/一片片逐漸發烏,/論顏色聊剩于無。”[7]“論用處聊勝于無,/而收獲總是收獲,/又有誰能對我說,/收獲該止于何處。”[7]事實上,我什么都沒得到。這些辛苦收集而來的落葉看似數量眾多,堆積如山,最終卻是毫無價值可言的一堆廢物,但矛盾的是,它們雖是無用之物,但終歸是辛勤勞動所得的收獲,詩歌最后兩句“又有誰能對我說,/收獲該止于何處”將詩歌悖論推向高潮,反映了“收獲”又“無獲”的悖論困惑。整首詩歌可謂悖論重重,各種矛盾讓讀者陷入了難以決斷的困境,也使讀者不得不反問自己:整日忙忙碌碌的我們到底收獲了什么?這些所謂的“收獲”真是我們想要的有益收獲嗎?
再如,詩歌《五十自述》,全詩由兩節八行構成,兩詩節中對照出現的悖論讓此詩成為渾然一體的悖論整體。詩歌第一節回顧年少時“我”的求學生涯。“我年輕時,我的老師們年長,/學規矩,消火氣,直到心涼。/忍受煎熬,如金屬接受鍛造,/向長輩學習以往,我進學校。”[7]第二節則講述年長時我的再次求學經歷。“如今我老了,老師們卻年輕。/難以成型,一定會坼裂破損。/我努力用功,試圖彌合裂縫,/向青年學習未來,我進學校。”[7]回顧過往,年輕的“我”向年長的人習禮教,礪性情,變得成熟而冷靜。如今,年長的“我”則向年輕人習新知,彌代溝,迎接未來。“年輕”—“年長”、“以往”—“未來”、“金屬接受鍛造”—“坼裂破損”,讀者在難解矛盾的同時,也必對詩人“學無止境”“與時俱進”的深邃學習觀深感贊同。
四.多元結局
“開放式的結尾是弗羅斯特詩歌創作的一大特色。”[4]讀者雖不能從開放式結尾中獲得確定結論與結局,卻在不經意間有了更廣闊的自由解讀空間,這正是弗羅斯特詩歌的深邃魅力所在。
《一條沒有走的路》是當現代英語詩壇中一首熟為人知的經典名作,也是一首典型的開放式結尾詩作。詩歌一開始便講述了“我”偶遇林中岔路卻抉擇難做的困頓,“金黃色林中有兩條路各奔一方,/可惜,我是一個人獨自旅行/不能兩條都走,我站在岔道上/向其中一條,長時間凝神眺望/直到它彎進灌木叢失去影蹤。”[7]抉擇雖不易,路卻得走下去,比較權衡后,“我”選了人跡罕至的那條路繼續往下走。選擇雖已定,結局卻未定,“我將會在很久很久以后的某處,/一聲嘆息,重把這事提起。/樹林中曾經有兩條歧路,當初——/我選擇了其中人跡少的一途,/這就造成了以后的全部差異。”[7]“差異”到底何在?“我”是否后悔選擇了這條“行人較少的路”?若選擇了“較多人走的路”,“我”又會發出何種感嘆?詩歌的開放式結尾著實讓人讀來意猶未盡,來自讀者的不確定性多元結局也隨之而來。
“一聲嘆息,重把這事提起。”[7]這“一聲嘆息”將“我”的無奈盡顯無遺,它暗含了“我”對當初選擇之悔意。“鮮有人走”之路必布滿荊棘,充滿險阻,“我”在經歷大量磨難后感嘆道:“我選擇了其中人跡少的一途,/這就造成了以后的全部差異”。[7]此開放式結尾是對未選路的遺憾和對已選路的懊悔的省略。然而心態不同,解讀也有差異。相同的情境,在樂觀主義者眼中,此結尾可解讀為“我”欣慰于自己所選,若不是選了較為艱辛的路,“我”就不會在經歷大量歷練后,獲得挑戰艱難困苦的勇氣。
而聯系此詩創作背景,結局又有他解。此詩非弗羅斯特的偶然之作,它的問世實屬詩人的有感而發。1914年秋,弗羅斯特和其家人搬到了一個叫做“加洛斯”的小農莊,也在那時,愛德華·托馬斯成了其為數不多的密友之一。兩人親密無間,常去林間小路散步,每當遇到小路岔道,托馬斯總詢問弗羅斯特該如何取道。有一次,弗羅斯特告訴托馬斯,無論他選擇哪條道,最終都會留有遺憾。后來,托馬斯參軍,戰死沙場,而托馬斯在岔道口前猶豫不決的形象讓弗羅斯特實難忘懷,于是以此事為原型,詩歌得以成形。結合詩歌創作背景及詩中暗示兩條道路并無差別的描述:“然后走上絲毫也不差的另一條”“已踐踏得兩條道路難分上下”“而在那一天早晨,那兩條道路/曾同樣覆蓋落葉,未經步履”,可見,此開放式結尾的可能性結局當是弗羅斯特曾向托馬斯點明的深邃思想:“無論選擇哪條道,最終都會留有遺憾。”
“詩人的用意是讓讀者自己去體味詩中的含意,包括那些連詩人本人也不清楚的含意,他一般不在詩的結尾下明確的結論,因為這樣會限制讀者的想象力、損傷詩歌的深度。”[2]在難以確定的開放式結尾中,詩歌被賦予了更深邃的意蘊,弗羅斯特詩歌的魅力也在讀者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讀中展露無遺。
五.結語
弗羅斯特詩歌多取材于新英格蘭的農家生活,詩歌質樸的措辭、自然的表述,常讓讀者感到簡單易讀。然而,這是詩人所布迷陣,看似直白簡單的詩歌表述下卻隱含著精妙難斷的隱喻意象、似是而非的文本悖論、懸而未決的多元結局,它們讓詩歌的解讀不再確定,讀者需要在更廣闊的思索空間探索詩歌的深邃內涵。“在文學作品文本的不確定性結構中,詮釋者應擅長于運用作品文字中的各種修辭結構的松散性,盡量運用詞語表達中各種比喻和象征性多重結構,使本身對于文本的理解成為一種思想的漫游,盡可能延長地逗留在文本的含糊性結構之中進行多層次的反思。”[13]最終,在讀者多角度、全方位的不確定性解讀下,弗羅斯特詩歌的獨特魅力得以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