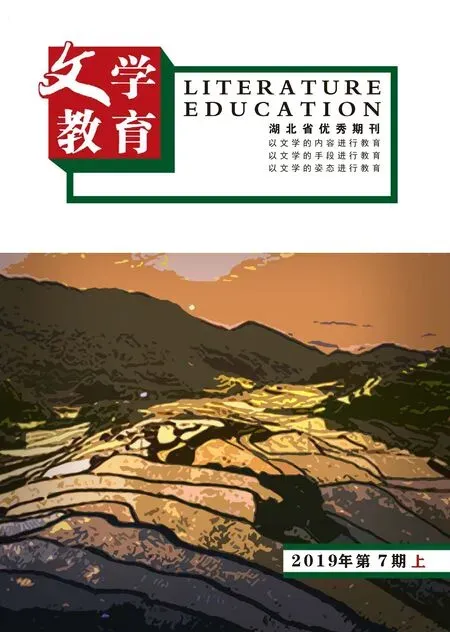查良錚研究綜述
余彥迪
查良錚(1918~1977),我國(guó)著名愛(ài)國(guó)詩(shī)人、翻譯家,曾用筆名梁真、穆旦等。查良錚作為“九葉詩(shī)派”的代表詩(shī)人之一,將西方的浪漫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與中國(guó)的傳統(tǒng)詩(shī)歌相結(jié)合,他的詩(shī)歌充滿了深刻的哲理思辨和豐富的象征寓意,為我國(guó)的新詩(shī)創(chuàng)作留下了寶貴的經(jīng)驗(yàn)。作為詩(shī)歌翻譯家,查良錚通過(guò)他的詩(shī)歌譯作,使更多中國(guó)詩(shī)歌愛(ài)好者和西方文學(xué)愛(ài)好者了解并熟悉西方浪漫派、現(xiàn)代派詩(shī)人普希金、拜倫、雪菜、濟(jì)慈、艾略特、奧登等的詩(shī)作,尤其是查良錚翻譯拜倫的《唐璜》、艾略特的《荒原》被譽(yù)為詩(shī)歌翻譯的典范,查良錚“在詩(shī)歌方面創(chuàng)造了一種健康硬朗的語(yǔ)言……在那個(gè)語(yǔ)言貧乏的時(shí)代,對(duì)整整一代人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王宏印,2007)
研究查良錚的“以詩(shī)譯詩(shī)”這一現(xiàn)象是因?yàn)椴榱煎P有作為譯者有其特殊性,他的譯作并不是為了出版,他的翻譯活動(dòng)是詩(shī)歌的延續(xù)而不是單純的翻譯工作,所以他的譯本就摻雜了很多自已復(fù)雜的感情,因此查譯本詩(shī)歌就不僅僅是語(yǔ)言符號(hào)的轉(zhuǎn)換,而是詩(shī)人與譯者的共同“作品”,研究查良錚的詩(shī)歌翻譯不僅為了英語(yǔ)詩(shī)歌翻譯做努力,也是為了中國(guó)詩(shī)歌的進(jìn)步做貢獻(xiàn)。
1.查良錚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
查良錚(筆名穆旦)早在20世紀(jì)40年代就在詩(shī)壇引起了強(qiáng)烈震撼。當(dāng)時(shí)詩(shī)壇宿將聞一多在編選《現(xiàn)代詩(shī)鈔》時(shí),就選入了穆旦的詩(shī)作十一首,數(shù)量之多僅次于徐志摩,穆旦其人在當(dāng)時(shí)詩(shī)壇的影響可見(jiàn)一斑。王佐良1946年寫的《一個(gè)中國(guó)詩(shī)人》對(duì)穆旦詩(shī)歌的意義作出了精辟的分析。王佐良認(rèn)為,穆旦以純粹的抒情著稱,而好的抒情是不大容易見(jiàn)到的,尤其在中國(guó);穆旦所創(chuàng)作的《詩(shī)八首》則是現(xiàn)代中國(guó)最好的情詩(shī)之一;穆旦的努力表明了當(dāng)時(shí)詩(shī)歌藝術(shù)的進(jìn)展,即“去爬靈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一件在中國(guó)幾乎完全是新的事。”(王佐良,1947:105)王佐良還就穆旦與西南聯(lián)大的關(guān)系、穆旦詩(shī)作與中西方文學(xué)關(guān)系、穆旦詩(shī)作與西方宗教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論述。1947年7月周玨良在天津《益世報(bào)·文學(xué)周刊》上發(fā)表《讀穆旦的詩(shī)》對(duì)穆旦同樣評(píng)價(jià)很高。在周玨良看來(lái),穆旦的詩(shī)歌并不是對(duì)西方的模仿,他在擺脫西方詩(shī)人的影響后已形成了個(gè)人的風(fēng)格,那就是“情思的深度,敏感的廣度,同表現(xiàn)的飽滿的綜合。”他認(rèn)為:“穆旦永遠(yuǎn)是強(qiáng)烈的感受,加勁的思想,拼命的感覺(jué),而毫不惜力的表現(xiàn)。……而這里要著重的更是以上各項(xiàng)的綜合性。”其他評(píng)論文章包括唐湜的《詩(shī)的新生代》、袁可嘉的《詩(shī)的新方向》等都從不同側(cè)面揭示了穆旦詩(shī)歌的意義。
由于政治因素,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三十年間,穆旦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幾乎被人們淡忘了。直至20世紀(jì)80年代,穆旦才重新進(jìn)入人們的視野,成為人們關(guān)注和研究的焦點(diǎn)。杜運(yùn)燮等人在1987年和1997年分別編纂了論文集《一個(gè)民族已經(jīng)起來(lái)》和《豐富和豐富的痛苦》。這兩本以穆旦為主題的紀(jì)念論文集豐富了讀者對(duì)穆旦的認(rèn)識(shí)。1966年,李方編輯了作為“20世紀(jì)桂冠詩(shī)叢”之一的《穆旦詩(shī)全集》。緊接著,1997年,曹元勇編纂了穆旦詩(shī)文集《蛇的誘惑》,其中第二輯“文論書(shū)信”收錄了穆旦生前發(fā)表和未發(fā)表的論文、譯序以及書(shū)信多篇。2004年,陳伯良撰寫的《穆旦傳》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shí)。1988年5月25日,在北京召開(kāi)了“穆旦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
隨著穆旦研究資料的不斷完善,越來(lái)越多的人開(kāi)始關(guān)注并研究穆旦,傾聽(tīng)起詩(shī)歌所發(fā)出的獨(dú)特聲音,并對(duì)之作出高度評(píng)價(jià)。評(píng)論界或者關(guān)注穆旦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時(shí)代語(yǔ)境,或者細(xì)讀穆旦的詩(shī)作,或者梳理穆旦與古典文學(xué)的關(guān)系,有的還把研究視野延伸到穆旦與整個(gè)西方文學(xué)傳統(tǒng)的淵源。比如王毅的《圍困與突圍:關(guān)于穆旦詩(shī)歌的文化闡釋》、陳林的《通向上帝之路——穆旦對(duì)艾略特詩(shī)意的接受等》。盡管研究方向存在很大差異,但人們普遍對(duì)穆旦的詩(shī)作給予了較高的評(píng)價(jià)。1994年,在王一川、張同道主編的“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大師叢書(shū)”中,穆旦名列詩(shī)歌之首。2000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將《穆旦詩(shī)集(1939-1945)》評(píng)為“百年百種優(yōu)秀中國(guó)文學(xué)圖書(shū)”之一。2001年,穆旦早期的詩(shī)作《贊美》和《春》被選入中學(xué)語(yǔ)文課本。正如鄭敏這樣評(píng)價(jià)穆旦,他是“一個(gè)抹去了‘詩(shī)’和‘生命’的界限的詩(shī)人。”(鄭敏,1996:38)
2.查良錚的詩(shī)歌翻譯
從某種意義上來(lái)說(shuō),談穆旦的詩(shī)而不談他的譯詩(shī)是不全面的。自1953年回國(guó)后,“穆旦”為另一個(gè)名字所取代,那就是翻譯家“查良錚”,其詩(shī)歌翻譯具有很高的文學(xué)價(jià)值。王佐良認(rèn)為穆旦和戴望舒是“最成功的兩位詩(shī)譯家”。香港學(xué)者馬文通稱穆旦是“一個(gè)杰出的詩(shī)歌翻譯家,迄今為止中國(guó)詩(shī)歌翻譯史成就最大的一人”(馬文通,1987:78)。非議過(guò)穆旦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當(dāng)代詩(shī)人公劉也對(duì)其譯詩(shī)給予很高的評(píng)價(jià)。他認(rèn)為,穆旦作為詩(shī)歌翻譯家——另一種意義上的詩(shī)人,是不朽的,他的許多譯詩(shī)都堪稱一流。1981年,周玨良和杜運(yùn)燮先后分別在《讀書(shū)》上發(fā)文,研究探討查良錚的翻譯藝術(shù) (陳 林 ,2001:68)。杜運(yùn)燮(1987:116-118)將自己著作——《穆旦著譯的背后》的第四部分用來(lái)探討穆旦詩(shī)歌翻譯的原則。當(dāng)代作家王小波在談到穆旦的譯詩(shī)時(shí)也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他們(穆旦和王道乾)的作品是比鞭子還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現(xiàn)在的年輕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讀他們的譯書(shū),是我的責(zé)任。”(陳伯良,2004:180)直至現(xiàn)在,學(xué)者們對(duì)穆旦的研究依舊是有熱情的,而且是從更加系統(tǒng)更加全面的角度來(lái)進(jìn)行的。宋炳輝(2000:85)在他的作品——《新中國(guó)的穆旦》中提道,“查良錚的詩(shī)歌翻譯正在尋找新的方法來(lái)表達(dá)沉默。劍平(2007:53)在《國(guó)外文學(xué)》上發(fā)文《查良錚先生的詩(shī)歌翻譯藝術(shù)——紀(jì)念查良錚先生逝世30周年》,他以詩(shī)體長(zhǎng)篇小說(shuō)《歐根·奧涅金》為例,他、將查良錚的詩(shī)歌翻譯概括為:富有詩(shī)味、文字流暢、語(yǔ)言灑脫。易彬著作的《穆旦與中國(guó)新詩(shī)的歷史建構(gòu)》(2010)、《穆旦年譜》《穆旦評(píng)述》等,傾向于向讀者展現(xiàn)一個(gè)更加完整的穆旦。除此之外,翻譯家“查良錚”的一面也開(kāi)始被提及,就目前研究而言,對(duì)于翻譯家查良錚的研究多是出自于論文,而鮮少有系統(tǒng)的著作來(lái)全面的展示查先生的譯者風(fēng)采,僅僅出現(xiàn)了兩本著作即高秀芹與徐立錢合著的《穆旦苦難與憂思鑄就的詩(shī)魂》(2007)與商瑞芹的《詩(shī)魂的再生:查良錚英詩(shī)漢譯研究》(2007)。“研究者和出版者所發(fā)出的‘應(yīng)重新評(píng)價(jià)詩(shī)人譯詩(shī)的成就’的感嘆,顯示出穆旦(查譯著作)研究的新態(tài)勢(shì)”(易彬,2010:388)。
詩(shī)人譯詩(shī),翻譯史上很早便有學(xué)者關(guān)注,但研究者甚少。西方譯界早在17世紀(jì)就意識(shí)到詩(shī)歌譯者的身份問(wèn)題,英國(guó)詩(shī)人、翻譯家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就曾表示優(yōu)秀的譯詩(shī)者必須是一名優(yōu)秀的詩(shī)人 (John Dryden,2006:173),而與他同時(shí)代的翻譯家、詩(shī)人羅斯康芒伯爵(Wentworth Dillon, Earl of Roscommon)(Wentworth Dillon,2006:176-179)也認(rèn)為譯詩(shī)不僅必須由詩(shī)人完成,并且譯詩(shī)者本身必須有寫出所譯類型詩(shī)歌的能力。因此,譚載喜認(rèn)為:“伊麗莎白時(shí)代詩(shī)歌的翻譯在質(zhì)量上比不上散文翻譯,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翻譯家是學(xué)者而不是詩(shī)人,譯詩(shī)卻必須本人也是詩(shī)人。”(譚載喜,2004:78)
穆旦停止詩(shī)歌創(chuàng)作,以查良錚的身份潛心進(jìn)行詩(shī)歌翻譯。其主要作品有英國(guó)雪萊的《云雀》、《雪萊抒情詩(shī)選》,英國(guó)拜倫的《唐璜》、《拜倫抒情詩(shī)選》、《拜倫詩(shī)選》,《波爾塔瓦》、《青銅騎士》、《普希金抒情詩(shī)集》、《普希金抒情詩(shī)二集》、《歐根.奧涅金》、《高加索的俘虜》、《加甫利頌》,英國(guó)《布萊克詩(shī)選》、《濟(jì)慈詩(shī)選》。所譯的文藝?yán)碚撝饔刑K聯(lián)季摩菲耶夫的《文學(xué)原理 (文學(xué)的科學(xué)基礎(chǔ))》、《文學(xué)概論》(《文學(xué)原理》第一部)、《文學(xué)發(fā)展過(guò)程》、《別林斯基論文學(xué)》和《怎樣分析文學(xué)作品》,這些譯本均有較大的影響。王佐良在對(duì)《荒原》的前后三個(gè)中譯本加以比較后,發(fā)現(xiàn)穆旦翻譯得最好。至于拜倫《唐璜》的翻譯,卞之琳在《譯詩(shī)藝術(shù)的成年》中同樣對(duì)它評(píng)價(jià)很高。
盡管經(jīng)過(guò)學(xué)術(shù)界眾多專家學(xué)者的不斷努力,迄今為止的穆旦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主要表現(xiàn)在創(chuàng)作內(nèi)容、創(chuàng)作風(fēng)格與技巧、意識(shí)形態(tài)趨向、文學(xué)價(jià)值等,但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還有待提高,尤其缺乏對(duì)翻譯作品細(xì)讀式的批評(píng),如將穆旦詩(shī)歌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shī)歌作對(duì)比研究,將穆旦詩(shī)歌創(chuàng)作與其詩(shī)歌翻譯風(fēng)格作對(duì)比研究等,而這恰好也給穆旦詩(shī)歌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