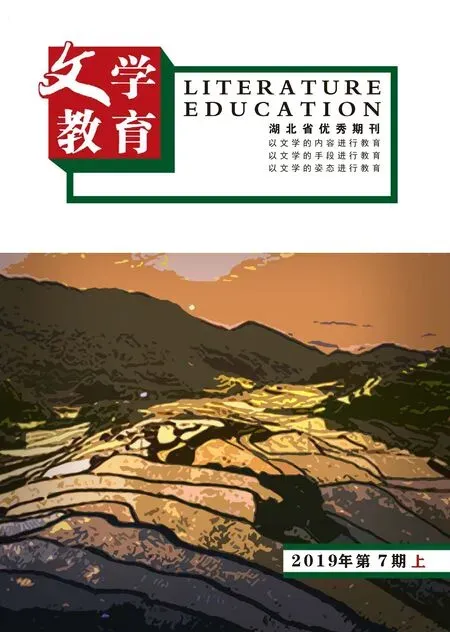從《第二十二條軍規》解讀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說創作
劉 偉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文學里出現了一種明顯的歷史斷裂感。在歐洲,大戰前后,許多主要的現代派作家去世了。美國文學也大同小異,也有好幾位蜚聲世界文壇的作家謝世。到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小說的現實主義思潮雖仍有余波,但其最顯著的特點是從邊緣到中心的移動。猶太文學異軍突起,黑人文學的新繁榮,以及華裔小說名家輩出,與此同時,黑色幽默小說與之共存。1961年,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的長篇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發表,震動了沉悶的美國文壇,使美國小說走進了“黑色幽默(Black Humor)的新時代,走出20世紀60年代初的困境,繼續向前發展。
一.概念簡述
“黑色幽默”的概念是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布勒東在1937年的一次演講中提出的,最初源于法國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黑色幽默作家的思想基礎是存在主義,他們“強調世界的荒謬、混亂、神秘莫測以及人與環境的不協調,并以夸張到荒謬程度的幽默手法嘲諷社會、人生以及人類的災難、痛苦和不幸,將快樂與痛苦、冷漠與荒唐、大笑與悲劇并列在一起,讓生活中一切為之沮喪、為之悲嘆的事物在逗笑和嘲諷中暴露無遺。”[1]黑色幽默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反英雄”的形象。他們生活在變態的社會里,命運坎坷,任憑權威力量的支配,身心備受無理的折磨,變成言行古怪、人性扭曲的“荒誕人”。這些人物在現實環境無情的壓迫下無可奈何,既無法改變現狀,有沒有能力逃避。他們只能用黑色幽默的笑聲,來忍受一切說不出的痛苦。他們的遭遇和不幸令人同情,但他們用虛無主義代替了激進的社會理想,提不出代替他們所冷嘲熱諷的世界的可行藍圖。
二.作家及創作背景
約瑟夫·海勒出生于紐約布魯克要區柯尼島,家境貧寒,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他于1942年應征入伍,在美國第十二飛行大隊服役,成為一名空軍投彈手,并曾任中尉,在歐洲戰場駕駛轟炸機執行了60次任務。這段空軍服役的經歷對他創作《第二十二條軍規》提供了真實的素材。戰后他退役進入紐約大學獲學士學位,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學位,之后又到英國牛津大學深造一年。海勒從小喜愛文學創作,早起在雜志社任職期間曾發布過短篇,但并受到文壇的重視。直到1961年,他的長篇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問世,揭開了20世紀60年代黑色幽默時代的序幕。他本人也因這部小說一舉成名。
三.小說人物形象的塑造
1.反英雄角色約瑟連的成功塑造
《第二十二條軍規》描寫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期,美國第256空軍轟炸機中隊內部發生的故事。整個部隊由指揮官卡斯卡特上校掌管,為了能升官發財,他不顧士兵的死活,無限度的增加他們的飛行任務。由于經歷了太多的轟炸任務,這些飛行員最后都變得瘋癲。主人公約瑟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已經按照命令飛往法國和意大利執行了規定次數的轟炸任務,此時,卡斯卡特上校要求飛行員不斷增加飛行次數。約瑟連很生氣,決定抵抗。他想裝成瘋子,以為空軍內部有個二十二條軍規,規定瘋子可以停止飛行,但他不得不問清楚才有依據,可是一旦去問,又恰恰證明他頭腦正常,還要繼續執行任務。小說里寫道:“第二十二條軍規并不存在,這一點他可以肯定,但這也無濟于事。問題是每個人都認為它存在。這就更糟糕了。因為這樣就沒有具體的對象或條文,可以任人對它嘲弄、駁斥、控告、批評、修正、憎恨、辱罵、唾棄、撕毀、踐踏或燒掉。”此時,約瑟連領悟到了,第二十二條軍規表面上看是一條約束每個官兵的軍規,但軍官可以對它做任意的解釋,其愚蠢的推理更是十分荒唐可笑。
2.掌權者和被主宰者的成功塑造
在《第二十二條軍規》中,海勒描寫了一個沒有理智和希望的世界,在這個世界當中,發生了一系列荒誕離奇的事情,通過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表現出來。小說中的人物大體可分為兩類,及掌權者和被主宰者。掌權者代表人物是飛行大隊的指揮官卡斯卡特上校。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權欲狂,一心只想往上爬。他常因自己36歲就當上上校而洋洋得意,但是,當他一想到還有年輕人已經當上了將軍,就會垂頭喪氣、痛苦不堪。為了能夠當上將軍,他不擇手段,對上級言聽計從,唯唯諾諾,對下級卻打著“第二十二條軍規”的幌子,專橫武斷,不斷增加飛行員的飛行次數,用士兵的生命來換取自己的升遷。被主宰者代表人物就是約瑟連。他本來是一個富有愛國精神、樂觀向上的軍人,將保衛祖國當成是自己神圣的使命。他每次執行任務都會出色的完成,但是,當他發現自己周圍的人都十分可恥,上級也只是把部下的生命當成自己升官發財的工具后,對自己的行為感到了無意義。更可悲的是,他無論采用什么辦法,都始終無法逃出“第二十二條軍規”這一陷井,于是他成了一個厭戰者和怕死鬼,最后還做了逃兵。在約瑟連的身上,沒有傳統的英雄具有的出類拔萃的品格以及崇高壯烈的行為,但是,他是這個荒謬的世界中唯一清醒的人,看清了現實的混亂和丑惡,不愿與無恥之徒同流合污或被其控制,敢于公然予以反抗。因此,約瑟連最后的逃跑行為可以看成是一種積極的行為。所以,約瑟連既沒有陷入道德含混的泥潭,又不屈服于陳腔濫調的誘惑,因此他扮演了一個反英雄的角色。
四.小說創作的藝術手法
《第二十二條軍規》在藝術上頗有特點,突出體現了黑色幽默小說的主要特征。首先,這部小說運用了獨特的“反小說”的敘事結構,故意用外觀散亂的解構、松散凌亂的情節、龐雜的內容、眾多的人物來顯示其所描述的現實世界的混亂和荒謬。其次,海勒以一種“絕望、沉郁、玩世不恭的幽默將內心無形的恐懼變為有形的大笑,借以表示對現實世界的不滿與反抗”。[2]再次,海勒善于運用象征、夸張等手法,對世界的荒誕思考,整部作品中最成功的象征便是“第二十二條軍規”,對官僚體制的混亂、專橫和冷酷進行了高度的概括,表達了現代人的災難感和困惑感;運用夸張手段將人物和事件極度變形,使人物和環境極端地不協調,從而描繪出一幅幅荒誕不經的圖像,讓人們在苦笑中回味和思索。最后,這部小說的語言有著顯著的反諷特點,或是用插科打諢的文字來表述嚴肅深邃的哲理,或是用故作莊重的語調來描述怪誕滑稽的事物,或是用冷漠戲謔的口氣來講述痛苦悲慘的事件,或是用幽默嘲諷的語言來述說沉重絕望的境遇,在不經意的調侃之中露出了銳利的諷刺鋒芒,直指荒誕的要害。
《第二十二條軍規》有力地影射了美國所謂的法制社會,法律都像第二十二條軍規一樣,變成政府官員可隨心所欲地解釋,以壓制普通老百姓的強大而無形的圈套。海勒抓住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的本質,以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親身經歷,從新穎的角度對美國的法制和民主提出質疑。黑色幽默就是用怪誕的喜劇手法來表現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的悲劇性事件,揭示社會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這種幽默,有些評論家稱它是“荒誕的幽默、變態的幽默、病態的幽默”或“絞刑架下的幽默”“大難臨頭的幽默”。它與傳統的幽默并不對立,反而常常糅合在一起,以辛辣的諷刺、古怪的挖苦、哭與笑的反常結合等手法,在小說里形成一個可恨、可怕和可笑的世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作家采用黑色幽默的藝術手法進行創作,評論家就將黑色幽默小說乘坐后現代拍的,而海勒則是這個流派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