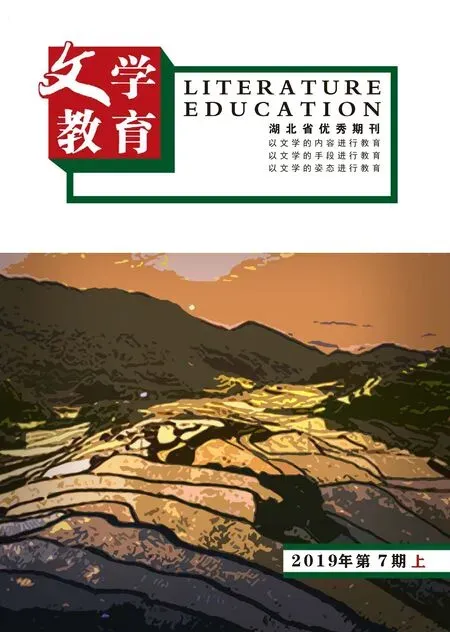從美學角度看“吝嗇鬼”形象
張睿思
從“吝嗇鬼”這一帶有明顯諷刺意味的綽號上,我們可以輕易的抓住這類形象的典型特點:吝嗇。但今天,我們要從美學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這類形象尋找這種吝嗇之中的美的體現,以及這樣的形象中的美學價值。
1.“吝嗇鬼”形象中的丑之美:“丑”,作為給人以厭惡為主的復雜情感刺激的審美類型,它首先是一種客觀存在。其次,它體現著一種消極、否定的生活內容,是對人生命價值的抵觸與毀滅。這種丑在“吝嗇鬼”這一典型形象中可以看到。葛朗臺作為一個瘋狂的金錢愛好者,他愛財如命,見錢眼開。他眼中根本沒有家庭、道德、情感的觀念,妻子一死,他便為遺產的繼承權發愁。直到女兒放棄繼承財產,他才平生第一次擁抱、贊美了女兒。而嚴監生的形象也如葛朗臺一般極具丑的一面,他有錢卻又極為吝嗇。他生了重病,卻舍不得人參等物,在趙氏提起送舅爺趕考盤纏時,他一腳將貓踢開。這些細節都體現形象中吝嗇的一面。從審美角度來看,我們所說的“美”的內涵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蔣孔陽)。那么,“丑”是不是“美”的一種?如果是,對這種非主流美的審視意義在哪里?我們審視“吝嗇鬼”形象的丑之美,其真實目的不是來探究它的產生,更多的是去批判。探討從人類最本質的力量中產生的這種“丑”,是為了從根本上對其進行深刻批判。因而,這種丑之美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它存在的意義就是以這種給人帶來不適的刺激感,來引起人們更深刻的思考,從而通過這種批判來警醒、啟發人們。
2.“吝嗇鬼”形象中的荒誕:“荒誕作為丑的極端化形式,是理性協調的顛倒,表現為極度的不合理、不正常,給人以無可奈何、哭笑不得的痛苦感受。”換句話說,荒誕不僅是一種丑的極端,也是一種悲劇性與喜劇性的混合,它將痛苦與詼諧的兩種情緒復雜的融合。“吝嗇鬼”形象的刻畫中存在著這種荒誕性。葛朗臺在臨死前聽見神父讓他親吻鍍金的十字架,他便瞬間清醒,瞪大了雙眼,那雙仿佛死了幾個小時的雙眼又突然活了過來,他做出駭人的掙扎姿勢,想把十字架抓在手中,最后一句遺言沒有提起親人,而是“把一切看好,到天國來向我交賬。”嚴監生的荒誕性體現的更加精彩。他的生命已到盡頭,卻又如何都不肯咽了自己最后一口氣,只是伸出兩根手指示意家人,家人紛紛猜測。最后趙氏的話揭開了謎底:遲遲不肯咽氣竟只是為了油燈里燃著兩根油繩,恐廢了燈油,只待趙氏挑斷一根,他便闔眼離去。這樣令人覺得不可思議、違背常理的情節進一步圓滿了吝嗇鬼的形象。這種荒誕既有著喜劇般令人捧腹的效果,又有著悲劇般將人刺痛的能力。這樣荒誕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無意義,但從這種無意義中恰恰令人體味出一種特定意味來。“吝嗇鬼們”死時的情節給人以劇烈的荒誕感受。這兩種同樣無意義的行為舉止在他們臨死前的、人生結束的重要時刻出現了,又給這樣無意義的行為加上了一種特別的意味。
3.“吝嗇鬼”形象中的喜劇性:喜劇的主要特征是不協調性、矛盾性,其最突出的審美效果是“笑”。這種喜劇性是指在審美者未深入思考之前,得出的最直接最自然的笑的效果。在初讀這兩個“吝嗇鬼”形象的時候,大部分的人表現一定是笑。怎么能不去笑呢?當你知道天下竟然還有如葛朗臺和嚴監生這樣愚蠢、吝嗇的人的時候,你自然會帶著一種高高的優越感對不如你的人進行嘲笑。在嘲笑之中,仿佛你的榮譽突然出現了,你的能干和智慧都要顯現出來了。從而,你在面對這兩個吝嗇鬼時自然是輕松的,你心想:反正他們做出什么蠢事都是正常的。但,當你面對的是具有崇高感的悲劇主人公時,你自然會為他捏一把汗。為他從緊張到痛苦。喜劇性的“吝嗇鬼”形象的確不需要人們的關切和掛念,他們的形象只會在你突然頓悟時給你狠狠一劍。你會發現他們可能是被作者夸大了的現實生活中的你我他。或者,在嘲笑他們的你的身上就帶著這種深思后會顯露的喜劇性。
我們從美學角度來看“吝嗇鬼”形象,是因為這種文學上的典型形象具有自己獨一無二的美學價值。從這種丑和荒誕的角度來說,這樣的“丑”與丑到極致而產生的荒誕勢必會給人以更加強烈的刺激。這樣強烈的刺激勢必會引起人們更強烈的反感和對主流美的渴望與追求。也因此,我們審“丑”是為了進一步對“丑”進行批判,進一步表達對“美”的渴望和追求。也就是說“吝嗇鬼”這樣丑的形象之所以存在幾百年而光彩依舊,正是因為他們足夠丑,也足夠激發人們厭惡,進而來反感“丑”、追求“美”。而從喜劇的角度說,“吝嗇鬼”這樣的形象的存在反而可以更好的帶來一種反思后的陣痛,更有利于培養人的豁達樂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