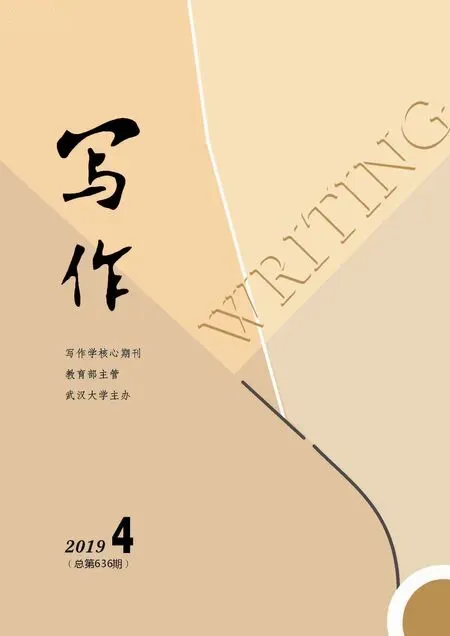寫作者的文體意識
邱華棟
一
先談談詩。30多年里,我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寫詩,截止到2019年,我一共出版了六部個人詩集。詩歌對于我來說,就是母語的黃金,必須要在寫詩和讀詩中保持對語言的敏感。詩的文體特點,在于其高度的濃縮性,詩就是人與世界萬物相遇的瞬間的語言呈現。
除去中國古代詩歌對我的影響,最早影響我的現代詩人是“新邊塞詩派”的昌耀、楊牧、周濤等詩人。我當時還在新疆上中學,每天,我面對天山雪峰的身影讀著西部詩人的作品,感覺他們距離我很近。接著,我讀到了“朦朧詩”,非常喜歡北島、楊煉、顧城、舒婷、江河。到武漢大學就讀之后,我繼續寫詩。當時大學校園詩歌活動非常多,武大也有出詩人的傳統,像早年的聞一多、孫大雨、曉雪、韋其麟,一直到后來的王家新、高伐林、洪燭、陳勇、李少君、吳曉、方書華等,都是我關注的對象。我還廣泛閱讀了胡適、卞之琳、馮至、聞一多、郭沫若、朱湘、李金發、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王獨清、艾青等詩人的作品。在大學里,我開始接觸到更多的翻譯詩,我最喜歡的還是“超現實主義”詩歌。“詩是不能被翻譯的東西”這句話,我覺得是錯誤的——假如你有一顆敏感的詩心,讀翻譯詩你也可以還原原詩的表達。
近年我在寫一些計劃中的專題詩集,我不再像過去那樣,感覺到什么就立即拿起筆來寫。比如,我寫了一本關于石油的詩集《石油史》,我還寫了一本禪詩集《碰到茶喝茶 遇到飯吃飯》,都是短詩,正在寫一本詩集《飛機》,嘗試將詩歌的敘事性結合飛機這種交通工具演繹出詩意。
比方說,有人會問我,你為什么寫起禪詩來了呢?那是因為,多年以來我訪過不少禪寺,偶有所見,就記錄下來。后來讀了不少禪宗的書,如《壇經》《景德傳燈錄》《祖堂集》《五燈會元》《宗鏡錄》《碧巖錄》《禪宗無門關》等等,看到很多禪師故事、禪宗公案,偶有頓悟,就記錄下來。心境變化了,安靜的時候內心里會忽然如同泉涌一樣蹦出來一些句子。我就這么寫下了《碰到茶喝茶 遇到飯吃飯》,這本詩集將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其實那些禪詩不是我寫的,是歷代禪師寫下來的。只不過我是提煉了、會心了、共鳴了、重述了和偶得了。歷代禪師有那么多的公案、故事、事跡、行狀、蹤跡,從我的這些詩里面都可以看到回響。這恰恰就是禪詩的魅力——作者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能和這些禪詩會心,你就能和禪師與禪宗相遇。
我還參與了小說家、詩人蔣一談發起的截句詩歌活動,出版了一本截句集《閃電》。截句沒有題目,只有句子。在詩歌的長河里,短詩的文體和形式感最強。古代中國有五絕、七絕,波斯有魯拜,日本有俳句。“我夢見黃金在天上舞蹈”,這一句詩我拿來作為我寫詩的座右銘,表達我冶煉語言黃金的心境。
二
再來說說小說的文體意識。我覺得短篇小說在于它的鋒利和短小精悍。我一直喜歡寫短篇小說,30年來,我已經寫了160多篇了。
我小時候在業余體校武術隊訓練了6年。練武術的人常說:“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說的是長有長的好處,短有短的優勢。短篇小說,因其短,就很“險”。險是驚險、險峻、天險、險峰、險棋、險要、險勝等等。短篇小說篇幅有限,但卻可以做到出奇制勝,做到以短勝長。
我最早的一個短篇小說《永遠的記憶》寫于1984年,那年我14歲,寫的是一種感覺和心理狀態。上大學之后,寫了一些少年記憶的短篇,這個系列的小說每篇大都在六、七千字,一般都有一個符號和象征物作為小說的核心,比如《風車之鄉》里一定有個風車,《雪災之年》里一定有一場大雪,《塔》里也一定會有一座象征神秘性的塔。表達的都是關于青春期成長和窺探世界的那種惶惑、煩惱和神秘感。
每次寫短篇小說,我都把結尾想好了,短篇小說的寫作很像是百米沖刺——向著預先設定好的結尾狂奔。語調、語速、故事和人物的糾葛都需要緊密、簡單和迅速。我大學里畢業后寫的短篇小說,有詩意的追尋、城市異態帶來的變形,小說故事本身不是寫實的,是寫意的,寫感覺、象征和異樣。我寫短篇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圖譜式的多重、多角度、多次地進行某個主題或者對象的書寫。
2000年之后,我寫了《社區人》系列短篇,分為《來自生活的威脅》與《可供消費的人生》兩個集子出版,一共60個短篇。這個系列的短篇小說將視線放在中產階層,都有完整的故事和相對多面的人物,少了很多意象、象征、詩意,多了寫實、人物、故事、場景等等。
近年寫了小說集《十一種想象》和《十三種情態》。《十三種情態》是13篇與當代情感、婚姻、家庭、外遇、戀愛有關的短篇小說。這些小說的題目都只有兩個字:《降落》《龍袍》《云柜》《墨脫》《入迷》《禪修》等等。
對于我來說,如何寫短篇小說,一直有一個“多”和“少”的問題。15000字的短篇,時間的跨度,人物的命運跌宕,都有很大的空間感。比如,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說,是“少”的勝利。我覺得他的簡約和“少”,是將一條魚變成了魚骨頭端了上來,讓你在閱讀的時候,通過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想象力,去恢復魚骨頭身上的肉——去自行還原其省略的部分,增添他的作品的“多”。這對讀者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此,顯得非常風格化。寫短篇小說就應該在其篇幅短的地方做長文章,在多和少之間多加體悟。
我寫短篇不是主題先行,是模糊的,是寫的過程中逐漸清晰的。起先是題目先涌出來,然后一點點的,內容出現了,是小說的題目召喚來的故事。
最近,我在寫短篇俠客小說系列,以中國歷史上若隱若現的刺客和俠客為主角,醞釀了幾年了,沒有下筆。2016年上海書展期間,我去滬上探望了我上中學時期的語文老師兼武術教練黃家震先生,我從初一到高三,在黃家震擔任總教練的地區業余體校武術隊里練了6年武術,每天早晚高強度訓練4個小時,從蹲馬步開始,再到長拳南拳通背拳大成拳形意拳,刀槍劍戟斧鉞鉤叉短刃繩鏢,拳擊散打摔跤等全都練過。黃家震老師又教了我三年高中語文,擔任班主任,把我送到上大學。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他調回到了老家上海,繼續在中學任教。我去看望他的時候,他已經80高齡了。有這么一個文武雙全的老師,我也勉強算是文武雙全吧。
2016年夏天,我帶著上海小說家陳倉一起去看黃老師。陳倉給我們拍照。黃家震老師見到我這個徒弟很高興,他早就穿好了對襟練功服,將他珍藏多年的武術器械全部拿出來,擺滿了一屋子。長刀短刃明器暗器上百件,令我目不暇接,令陳倉興奮不已。后來,師徒二人來到樓下花園,他一個弓步,將關羽當年耍的那種青龍偃月刀一橫,單手將大刀舉在頭頂呈45度——這是很難的,大刀非常重,接下來讓我練,我一個弓步,將青龍偃月刀一舉,幾秒鐘后那大刀就咔嚓落了下來,砸到地上了——我這40多歲的徒弟和80歲的師父比,還是差了很遠。這些都以陳倉拍的照片為證。
所以,我想寫一個俠客中短篇小說系列,紀念我的武術訓練時期,也獻給我的老師黃家震。我先寫了三篇,《聽功》取材于《舊唐書》,寫的是唐代唐太宗換立太子時期發生在宮內宮外的事情:《劍笈》,取材于《古今怪異集成》,背景是乾隆修《四庫全書》;《擊衣》寫的是春秋時期晉國刺客豫讓的故事,屬于故事新編了。其余的幾篇我慢慢寫。我的俠客小說的寫法,是一種對大歷史情景的重新想象和結構。這就是我理解的武俠小說的一種新可能吧。
再說說中篇小說。中篇小說從文體上來說,不長不短。我比較喜歡三、四萬字的篇幅。最近我在寫一個當代題材的中篇系列小說,每一篇都是獨立的,但都是中國人、華人在海外的故事。
我喜歡看地圖,各種地圖。每到一處,一定要找到當地的地圖,按圖索驥,找到所在的位置,以及要去的地方,然后把地圖留存下來。這樣就有了很多幅地圖。有了地圖,就很難迷路。我也愛看地圖集,這些年,我搜集了不少有關地圖的書。比如《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古代世界歷史地圖集》《改變世界歷史的一百幅地圖》《地圖之王——追溯世界的原貌》《誰在地球的另一面:從古代海圖看世界》《中外古地圖中的東海和南海》《失落的疆域——清代邊界變遷條約地圖》等等,有幾十種。這些地圖能夠把我帶到很遠的地方,帶到時間和歷史的深處,讓我發現、揣摩、想象到一般人很難體會的關于歷史地理、時空交錯的那種有趣和生動的場景。我還喜歡擺弄地球儀。地球儀有大的,也有小的,有三維的,還有通電后通體發亮的。把玩地球儀有一種“小小寰球,盡在手中”的踏實感,一球在前,地球全覽,地球儀真是個好東西。
我常常把玩地球儀,把地球儀使勁一點,它就開始轉動起來,我的手指又一戳,停!地球儀停下來了,我看看我指的是哪個地方。我一看,這幾個地方,在地球儀上顯示的是太平洋、澳大利亞、中亞、古巴、巴西、俄羅斯、中非、法國、冰島。于是,我就想,我能寫寫這些地方的中國人的故事嗎?在這些地方,我碰見了一些有趣的外籍華人或中國人,他們早就擁有了自己獨特的故事。我應該可以寫寫來到這些地方的人的精彩故事。現代世界交通工具的發達,幾乎能夠讓人到達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包括那人跡罕至的生物圈之外。大洋之下,冰原之上,沼澤之中,大河之里,江湖之內,雪峰之頂,人都能夠抵達。只要是你想去,物質條件具備,各類交通手段就能幫助你到達那里。
于是,我先寫了這本書里的《唯有大海不悲傷》。寫這篇小說也有一些動因。近些年,我也常常聽到認識的朋友中間,有些人生活中發生了不幸事件。每個人的生活中,總是有大大小小的缺損和缺失。比如,有一個朋友的獨子,留學歸來正待結婚,卻因病忽然去世,黑發人送黑發人,何其悲傷!還有一個朋友的孩子,年僅10歲,不慎溺水死亡。朋友痛失自己的孩子,夫妻倆陷入了困頓和悲傷,婚姻關系也岌岌可危。常常是,突發的生活變故造成的痛苦在一個人、一個家庭里難以承受和化解,那么,他們如何承擔這悲傷,重新獲得生活的勇氣和信心呢?如何獲得自我救贖,繼續生活下去?我常常站在這些朋友的角度,去想象他們面對的境遇,以及內心里要承受的沉重。化解痛苦,這是任何豪言壯語無法起作用的,只能是一個個的個體生命,去承受生活的突如其來的變故。
在《唯有大海不悲傷》中,小說的主人公就遭遇了喪子之痛,最后他通過在太平洋幾個地點、在幾個夏季的潛水運動,逐漸獲得了救贖和生活下去的力量。
這篇小說發表之后,有朋友問我,你啥時候學會了自由潛水啊?其實,我頂多玩過簡單的浮潛。我是不會自由潛水的。但我特別愛看關于海洋的紀錄片。這些年,中央電視臺第九頻道播放了多部關于海洋的紀錄片,如《海洋》《藍色星球》《加拉帕戈斯群島》等等,我都看了好幾遍,對海洋里的各種生物了解了很多,常常是一邊看,一邊用文學語言去描述我看到的片段。此外,《美國國家地理》和《中國國家地理》中也有很多關于海洋的文章,都成為了我寫作這篇小說的材料支撐。
我也常常想,作為一個小說家,必須對讀者尊重、友好和負責。人家花自己寶貴的時間來閱讀你寫的一篇小說,你又能給他們帶來什么?因此,我要在小說里增加一些材料,比如潛水和大海的方方面面的知識,這就使得小說本身帶有著新穎感和知識化的效果。畢竟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陸地上,很難去太平洋上進行孤絕的自由潛水。小說也就變得有趣和好看起來。
而《鱷魚獵人》的寫作,這個創作的念頭在很多年以前就萌發了。我曾經去過幾次澳大利亞,也接觸了一些在澳大利亞生活的華人。他們各有各的精彩故事。華人在澳大利亞的歷史和現實的處境,也有很大的變化。比如,前去淘金的近代華人、改革開放之后前往澳大利亞的80年代的華人,和21世紀去澳洲的新華人的生存景象,就都不一樣,一代代華人演繹出了各自精彩的故事,促使我寫成了這篇抓鱷魚的小說。但對如何在小說里呈現抓捕一條鱷魚的情景,我自己也頗傷腦筋,沒有把握。好在小說家都有想象力,再說了,我也見過鱷魚,有一次,在廣東還喝過養殖的鱷魚做的湯。那么,如何抓捕一條鱷魚?我也咨詢過一些我認為可能會有見地的友人。但大家都沒有干過這個危險的事情。最后說,“你就自己想唄。”抓捕一條白化鱷魚,與主人公幫助澳大利亞警方抓獲強奸并殺害了中國姑娘的白人罪犯,有著某種象征和同構的關系。小說中,兩個夏天,同時進行兩條時間線索的并置,取得了對照的效果。
小說《鷹的陰影》,則講述了兩個登山愛好者在中亞的雪峰上攀登的故事。我出生在天山腳下,小時候出了家門,往遠處一望,就能看見海拔5445米高的天山主峰博格達峰,那冰雪覆蓋的巍峨的樣子。我還跟著父親的筑路工程隊,到達過塔什庫爾干,在那座石頭城里眺望過附近那些高大的群峰,受到很大的震撼。后來坐飛機,飛越了不少雪山。現在,最頂級的登山家,要有“14+7+2”的履歷才是最完美的。什么是“14+7+2?”那就是,登頂地球上一共14座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高峰,然后,再登頂地球上七大洲的最高峰,最后是抵達南極和北極兩個地球上的極點。這就是“14+7+2”的意思。中國深圳一位叫作張梁的普通人,就完成了這一壯舉。關于他的情況,《中國國家地理》2018年第8期有專門的報道。全世界完成“14+7+2”的人只有幾十個,可見這一極限運動的實現之難。我也曾拜訪過詩人、登山家黃怒波先生。他是完成了“7+2”的少數登山家之一。在他的辦公室的走廊里,我看到了他歷次登山過程中,保留下的各種用具,琳瑯滿目,蔚為大觀。
寫這篇小說中,靈感、材料就這么以我曾經取得的知識點,見到的人和事,看到的一則新聞報道——幾年前,有中國登山家在新疆西南部登山過程中,被武裝分子綁架襲擊死亡的事件——這些就構成了我的小說壯麗、豐厚、有趣的架構和內容了。
再來說說長篇小說。寫長篇小說,從文體上說,就是蓋大樓大廈,就是攀登高峻的山峰,就是一次長跑。我先后寫了12部長篇小說,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在結構上是巴爾加斯·略薩的結構現實主義小說,在當代都市題材上,是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羅斯和索爾·貝婁,在歷史小說題材上,是翁貝托·埃科、尤瑟納爾和薩爾曼·魯西迪。長篇小說是時間敘事的藝術,文體上要有鮮明的結構意識,沒有結構,房子就搭不起來。
我的長篇小說分為當代題材和歷史題材。當代題材大都以北京為背景,有《夜晚的諾言》《白晝的喘息》《正午的供詞》《花兒與黎明》《教授的黃昏》五部。這五部小說,都是我的“與生命共時空”的寫作,是我對當代社會的書寫。
我寫的歷史小說,是在尋找一種他者的眼光和內心的聲音,描繪出小說主人公的聲音的肖像,使他們活起來。如我的長篇小說《賈奈達之城》《單筒望遠鏡》《騎飛魚的人》《時間的囚徒》,就是以近現代史上外國人在中國的生活經歷,結構而成的。我讓這幾部小說的外國人在中國近代史上出現,像鑲嵌畫一樣展現在中國的屏風上,與中國發生了難忘的愛恨情仇。我試圖找到更高的坐標系,在全球化語境中,展示文明和文化間的沖突與交融。而從西方人心理體驗東方世界,從西方人的角度反觀中國,我這幾部小說沖破了視野狹窄的藩籬,在歷史驚人的一瞥中,看到了世界的真實裂縫。
三
再說說非虛構這種文體。
“非虛構”在漢語里面是兩個字詞構成,一個是“非”字,一個是“虛構”。國外的書店里面,關于文學類的,我們會看到兩種書,一種虛構、一種就是非虛構。非虛構作品的書架上擺放著傳記、日記、游記、調查報告,以及一些難以歸類的東西,非虛構寫作在西方文學里非常廣泛。非虛構寫作和非虛構文學寫作,這之間有一些不同,比如,非虛構寫作的作品有一部分不完全是非虛構文學的寫作,非虛構寫作包含了非虛構文學寫作。因為非虛構文學寫作,要求有很強的文學性和文學技巧,同時,還需要作家有行動能力。行動能力和寫作能力缺一不可。
1960年代,美國有一批杰出作家,他們每人都寫了幾部非虛構文學的代表作。于是,美國大學里研究這種文學現象的教授,取了一個名字叫作“非虛構文學作品”。比如,有一個作家叫杜魯門·卡波特,他是一個同性戀作家,他的書在我們國內翻譯出版了不少,我受到他的影響很大。杜魯門·卡波特的非虛構文學代表作是《冷血》,我手里大概有三四個譯本,譯本的名字都不一樣,分別叫作《殘殺》《蓄謀》《冷血》,這個作品寫的是美國中部的肯塔基州,有一個家庭全家被流竄的兇手殺害了,它是一篇20多萬字的長篇作品,我對此印象深刻。這個作品一開始是這樣描寫的:在美國中部一個平原,當風吹過來的時候,齊腰深的草慢慢的倒伏下去,這個時候,有個房子就像島嶼一樣地從草地中間浮現出來,那是約翰某某家,有一天,有一個人路過這個地方,進入這個房子,把他們全家都給殺了。前面一大段都是景色描寫,他一下子告訴你,這一家的主人被殺害了。這個世界上每天都在發生各種各樣的暴力事件,但是杜魯門·卡波特通過《冷血》這一部書,把美國社會中某種本質給提煉、概括了出來,這也是我會談到中國的非虛構寫作,應該有哪些可能性,很多社會事件、案件都可以拿來作為寫作的素材。
杜魯門·卡波蒂為了寫這本書,一共采訪了6年多的時間,一直等到殺人的罪犯被處以絞刑才把這本書出版。所以說有的時候,寫一部作品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一個積累的過程。前年有一部電影叫《杜魯門·卡波特》,這個電影詳細記錄了杜魯門·卡波特寫《冷血》的整個過程,以及他的生活習性。所以,《冷血》這部作品從1960年代出版到現在,仍是非虛構文學寫作中的一個經典作品。
還有一個美國猶太作家叫諾曼·梅勒,他寫過很多小說,一共出版了30多部長篇作品,他有好幾部作品都是非虛構文學寫作,而且,他的題材都非常大。比如,他有一本專門寫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歷史的非虛構作品。他還寫了一部非虛構《夜幕下的大軍》,記錄了1967年到1968年之間,美國人進行的一次反越戰的大示威大游行,當時,集聚了幾十萬人,從紐約和其它地方出發,直奔首都華盛頓,那些人走了幾十公里夜路,所以,叫作《夜幕下的大軍》,這個作品是諾曼·梅勒非虛構寫作里最有名的代表作。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作家在處理非虛構題材的時候,有大有小,像杜魯門·卡波特寫的《冷血》,題材不大,只是一個兇殺案,但是透露出社會的一些本質來。
諾曼·梅勒的長篇小說兩部曲也是根據兇殺案寫的,叫作《劊子手之歌》,寫的是美國殺人犯加里怎么樣殺害了別人。另外,湯姆·沃爾夫的非虛構名作《名利場大火》,寫的是美國上層社交界里面的事情,美國當代作家多克托羅的《大進軍》也很不錯。因此,非虛構文學寫作這個文體在1960年的美國,是一種強有力的文體,也影響了世界文學的格局。
新聞結束的地方,就是文學出發的地方。這是非虛構文學的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另外,非虛構文學和散文的區別在哪里?我覺得,非虛構重在寫事件,而散文重在寫體驗。
非虛構文學中是否可以有適度的虛構?我覺得,事件是不能虛構的,事實本身是剛性存在的。但是寫作技巧是需要你調動多種文體的功能的。非虛構文學寫作,一定要借助虛構文學寫作的各種手段,比如對話、潛對話,心理活動等等,才能寫好非虛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