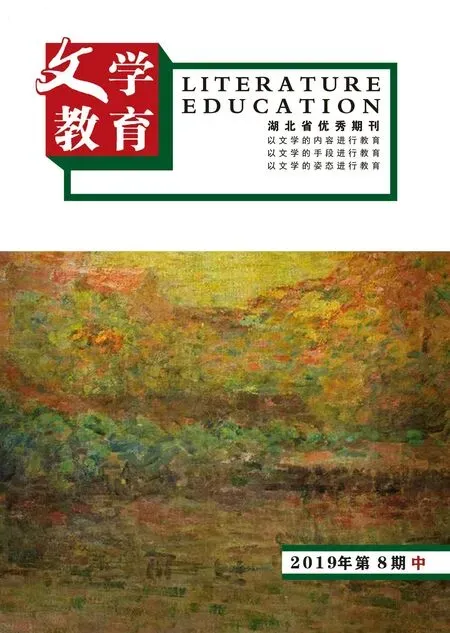從道家靈性哲學看“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
王 寧
《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時,警幻仙子命眾仙姬為寶玉演奏的曲子中有一支《終身誤》:“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即道出了“木石前盟”、“金玉良緣”兩種關系的矛盾統一。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創設了幻境與現實兩重世界,“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來自不同世界,存在前世與今世的時間差異,卻因人物的相遇、關系的發展而發生碰撞。
所謂“木石前盟”,是指林黛玉本為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絳珠仙草,追隨赤瑕宮神瑛侍者下凡,用自己一世的眼淚回報他的灌溉之恩。而賈寶玉既是神瑛侍者在凡界的化身又是女蝸補天剩下的五色靈石變化為“通靈寶玉”的肉身寄托,寶玉之玉上所刻“莫失莫忘,仙壽恒昌”,與寶釵金項圈所刻“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兩句正好成對,成就眾人眼中美好婚配的“金玉良緣”。
書中描寫了此對關系由萌芽、發展、高潮至悲劇結局的全過程,第一階段為第三回至第十八回,黛玉、寶釵相繼來到賈府,第五回提到黛玉、寶釵的判詞“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里埋。”暗示人物命運與關系走向。第二階段為從十九回至二十六回,寶黛二人隨著年齡增長,思想趨向一致,愛情也不斷發展,黛玉與寶釵接觸增多、摩擦加大。第三階段為二十七回至八十三回,寶釵、黛玉裂隙加深,“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對比性大大增強,在各自軌道上迅速向前發展又彼此牽絆,第三十六回寫寶玉隨便睡在床上,寶釵坐在身邊代襲人刺“鴛鴦戲蓮”,不久寶玉昏昏入夢,在夢中罵道:“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寶釵聽聞不覺怔忪近乎直白地說明了“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的沖突走向尖銳化、激烈化;第四階段為第四階段八十四回至九十八回,黛玉抱憾辭世,寶玉與寶釵成婚后癡傻更加乃至出家,隨著人物走向結局,“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的關系也走到終點。
從上述木、石、金、玉關系發展的脈絡來看,“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處于對立統一、相互成全又相互毀滅的悖謬狀態,抽象概括了人生無可奈何的悲劇,暗示了出路。
1.悖謬關系
《道德經》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恒也。”道出了萬事萬物悖謬統一的存在,“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的關系亦是如此。
若無“木石前盟”的存在,也不會有“金玉良緣”的相逢;若無“金玉良緣”的阻隔,絳珠仙草也不會流盡一生眼淚,“木石前盟”也難以達成。賈寶玉、薛寶釵大婚完成“金玉良緣”,林黛玉懷著無限悲傷離開塵世,重新回歸太虛幻境,寶玉出家之后也復其本來面目,依舊回歸于三生石畔呵護那令人“心動神怡,魂消魄喪”的絳珠仙草,再續前盟。“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相生相和、相互成全,但又相互毀滅,從事件的發展經過來看,兩種關系的存在直接造成了彼此的悲劇。寶黛二人一片深情,心心相印,卻備受金玉之論的困擾。寶釵的出現轉移了寶玉部分注意力,也讓賈府長輩們看到了更合適的兒媳人選,使得“木石因緣”的實現被重重現實壓力圍困,日久天長難逃破滅之殤;另一方面,寶玉、寶釵大婚看似實現了眾人眼中“金玉良緣”的圓滿,但寶玉出家斬斷俗世牽累,順應“木石前盟”的呼喚,隨同茫茫大士渺渺真人飄然離去,留下那“勘探停機德”的寶釵過著“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的生活,不能不說是“金玉良緣”的荒唐。小說到結尾,有盟的未能成為眷屬,卻帶走了對方的心;有緣的雖成了眷屬,卻永遠也找不到精神的歸宿。“木石前盟”是沒有婚姻的愛情,可傷可悼;“金玉良緣”是沒有愛情的婚姻,可悲可嘆。
從人物來看,寶釵是現實中的勝利者,又是精神上的失敗者;黛玉是現實中的失敗者,卻是精神上的勝利者。而寶玉神瑛侍者與通靈寶玉的雙重身份造成了他在“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兩重世界張力之下的尷尬,他既傾心于黛玉的靈慧與氣質,又迷戀寶釵的雍容與風度,追求心靈的慰藉與追求現實的家庭生活兩種不同的愛情與生活模式相互沖突,相互補充,無論是心甘情愿還是身不由己,寶玉始終在悖謬的關系中掙扎,最終順應本心、回歸自然。
2.悲劇實質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薛寶釵出閨成大禮”是“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對立沖突的高潮。“洞房花燭夜”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生離死別又是人生大不幸大悲哀,大喜與大悲兩種極致的情感交織一起,生死榮華鋪陳一處,形成悖謬性的雙峰對峙。曹雪芹通過極端冷靜的敘事,探討了客觀真實與個人意志之間的沖突,即存在與能動的矛盾。這種悲悲喜喜的交織融合其實超越了一般的悖謬存在,直指人生存在的悲劇性與人性掙扎的復雜性。
這種復雜性首先表現為自然性與社會性的對立,玉石沖突是人的自然本性與社會屬性沖突的變形。《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既可釋為“道從自然,自然為大”又可釋為“道性自然,無所法也”,前者突出了道的自然性,后者突出了道的本源性。
“木石前盟”是神瑛侍者與絳珠仙草的自然關系,“金玉良緣”是通靈寶玉與辟邪金鎖的人飾關系。石乃自然之物,草亦自然生長;玉乃人飾之寶,金也需費人力雕琢。“木石前盟”順應了自然法則,“金玉良緣”迎合了人世倫理。“木石前盟”象征人性的自由浪漫,是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兩情相悅;“金玉良緣”則是合乎禮法的門當戶對,代表了世俗的理想規范,不可避免會有對本性的約束與擠壓。“木石前盟”象征的自然性與“金玉良緣”象征的社會性隨人物命運的不同也有不同的發展,黛玉這個象征自由浪漫的個體被現實社會排斥與驅逐乃至走向毀滅,表現了自然性在社會性的發展中易被破壞、易遭摧殘的柔弱一面,而寶玉的出家遁世,象征了自然性的回歸,暗示了順從本心、順其自然乃是人生的最終出路,表現了自然之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道德經》第四十三章)。”而“木石前盟”之“盟”與“金玉良緣”之“緣”的區別,表現了本源與偶發的差距。“盟”即“盟約”,產生于主觀能動性的作用,是一種發于內心、根深蒂固且刻骨銘心的精神認同,“緣”則是“緣分”,是一種決定于外部條件、隨機的人生遇合。道的本源性強調“無所法”、“無所恃”,“金玉良緣”成長于外在世界,當外部條件被摧毀(四大家族凋亡)自身也難以存在,而發自本源、生于自然的“木石前盟”卻能在彼岸世界精神長存。
其二是內在追求與外在環境的對立,主客觀的二律背反永恒存在。《道德經》中有諸多關于自然中兩種運動此消彼長、此長彼消、相背相反規律的闡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第二十四章)”“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圣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二十二章)。”不單空空道人的至理名言:“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好了歌》)”和太虛幻境牌坊兩邊的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體現了這種樸素的辯證法精神,“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的對立沖突,也是這樣永恒存在于宇宙人生的二律背反。就“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本身來看,作為悖謬存在的兩方,此消彼長、此長彼消。而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正如王國維所言:“金石以之合,木石以之離,又豈有蛇蝎人物,非常之變故行于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而這“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當是主體與社會交融互攝,外在環境對內在追求的通常反應。當社會文化強調倫理本位、規范意識,便會擠占個體的生存空間,個體在抗爭的過程中自我壓縮直至自我意識犧牲,伴隨自我消失社會也趨向崩潰。主觀與客觀的相互選擇時刻進行,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身處的社會無法為青春的生命提供更多成長和發展的空間,個體生命與環境的沖突碰撞中一同粉碎、破滅。
3.永恒轉化,歸于自然
賈寶玉在“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兩處掙扎,其命運軌跡也昭示著悖謬關系的發展。《紅樓夢》初名《石頭記》,其實展示了由“石”變形為“玉”再回歸為“石”的三部曲,演繹人世的悲歡離合和生命的陰陽消長。寶玉本是頑石,“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歷塵世十九年終于頓悟,小說結尾交代了寶玉的歸宿:“那僧道仍攜了玉到青埂峰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云游而去。”寶玉的人間游歷之路如一條拋物線,行至最高點之后,開始向相反的方向回落,這一回落也是向“心頭無喜無悲”的本真生存狀態的回歸,靜嘯齋主人在《西游補問答》中對此有過精辟分析:“四萬八千年俱是情根團結,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后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這來于自然又歸于自然的過程顯現出道家循環理論的文化內涵,“反者道之動(第四十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第十六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第二十八章)。”如何從“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的悖謬關系中脫身?道家靈性哲學回答返歸自然、恢復本初乃是人生出路,《紅樓夢》以家族悲劇和個人悲劇的雙重書寫警醒世人與“情天孽海”保持距離,勿忘自然之心才是主客觀二律背反永恒斗爭的長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