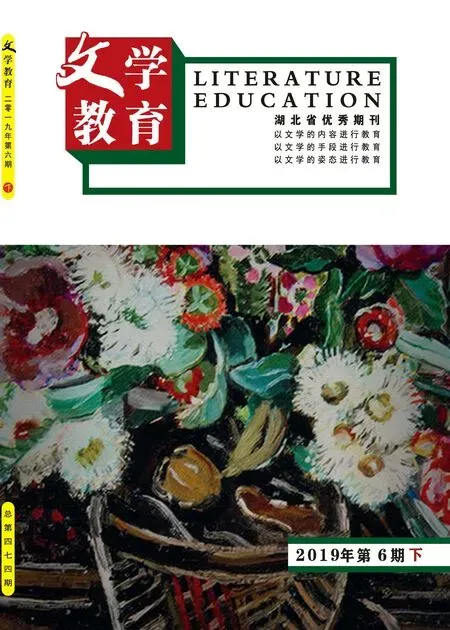蘇北方言文化衰退原因分析和解決對策
王夢茹 胡明錦
一.蘇北方言文化概況
蘇北地區包括徐州、連云港、宿遷、淮安、鹽城五個地級市,主要以平原為主,轄江臨海,扼淮控湖,這也就使得蘇北文化受海洋與農業文化的雙重影響,更具開放性與多樣性。曹志耘教授指出:“方言文化是指用特殊方言形式表達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現象,包括地方名物、民俗活動、口彩禁忌、俗語諺語、民間文藝等。”[1]蘇北五市方言文化豐富鮮明,極具特色,這些民俗文化現象集中反映了蘇北人民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積累的經驗與智慧。
蘇北方言文化具有豐富的多樣性。如“膝蓋”:鹽城人說腿節彎子;宿遷人說骼拜子;徐州人說胳了拜子;連云港人說磕腿拜;淮安人說磕幾頭子。還有“灶神”“走運”“去世”等詞語,在不同的地級市有不同的說法,這生動鮮明地反映了蘇北地區方言文化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地方歌謠能展現一個地方的地域特色和人民的生活特色,蘇北地區有許多這樣的歌謠。如“花鼓花鼓,打鑼敲鼓。女頂彩球,男跨花鼓。蹦蹦跳跳,有文有武。”,這是徐州地區農民在務農閑暇之余創作的“段子書”。打花鼓展現出徐州人民的生活、勞作、情調,是一種精神化的宣泄方式。連云港因瀕臨黃海,所以方言民俗中有反映連云港海邊人民生活的歌謠。如“大海螺,小海螺,一跑跑到大鹽坨……煮螃蟹,剝蝦婆,就是不煮大海螺。大海螺里住著我,煮了海螺疼死我。”
諺語和歇后語能反映人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經驗,蘇北五市有許多這樣的民俗文化。如:當家要儉,做事要勤;身教重于言教,亂教不如不教;麻子不多,點子不少;從小不成人,到大驢駒貨;天黃有雨,人黃有痞(病);該熱不熱,五谷不結。歇后語如:鹽城人嫁女兒——摸黑進門;瞎子吃螃蟹——只只好;滿臉冰糖渣子——甜不爍的;拾麥打燒餅——盡是利;大年五更死驢——不好還說好。
蘇北地區還有許多戲曲,淮劇是其中之一。它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蘇北方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淮劇語言是以建湖方言為基調,兼顧淮安、鹽阜等地的方言,進而戲曲化的一種舞臺藝術形式,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這反映了蘇北人民的樸實淳厚,勤勞勇敢。例如淮劇《買油條》:全家數我起得早,家務由我一人包。客堂間勤打掃,天井內我把花澆,后門口我把痰盂子倒,廚房內把熱水燒,煤爐子煽得火直冒,我再淘米下鍋把粥熬,蘿卜干子切切好,抽空檔上街排隊買油條。老太婆還在睡懶覺,家務事都由我把心來操。
二.蘇北方言文化現狀及原因分析
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副會長戴慶廈在采訪中曾經提到,一個物種的消失,只讓我們失去一種動人的風景;一種語言的消失,卻讓我們永久失去一種美麗的文化。蘇北方言文化以其特有的、豐富的文化內涵受到眾多文史學者的追捧,但是其傳承發展卻仍然面臨著巨大的時代性難題。為了更好地了解蘇北五市方言文化的發展現況,以及人們對方言文化保護及傳承的看法和態度,筆者做了一份調查問卷來對此進行分析。從結果來看:就青少年而言,相比于現下時興的各色各樣的網絡快餐文化,人們對于諸如諺語、歌謠、民間傳說、戲曲等方言文化知之甚少。就父輩而言,大部分的長輩不支持孩子學習民間藝術,只有少部分的人支持孩子學習民間藝術。由此可以看出,方言文化還沒有成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蘇北五市的方言文化的發展呈現出逐漸萎縮的趨勢,與其相關的方言文化也正面臨逐步消亡的危險,戲曲等民間藝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關于蘇北方言文化式微的現狀,我們總結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不斷地沖擊著蘇北地區的方言文化。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城鎮現代化的步伐越來越快,客觀上造成了方言文化逐漸流失,方言的使用范圍越來越小。現如今,除了當地土生土長的老年人,越來越少有人使用當地方言,“無方言”群體逐漸流行開來,“鄉音”成了一種奢侈的聲音。其次,普通話的推廣也對方言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自上世紀50年代普通話的推廣開始,到2010年的初步普及,普通話逐漸取代方言成為最為主要的交際工具,方言文化也由此被人們漸漸丟棄。再次,地方政府部門對方言文化的保護意識較為薄弱,鮮有相應的方言文化保護政策和專門的保護機構。作為我國的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方言文化可以說是呈現地方文化、民俗、風俗的一種活化石,是展現地方文化建設和發展的一個重要窗口,是呈現地方文化的一種“軟實力”。然而從事這方面保護和研究的人員較少,隊伍建設較為薄弱。
三.蘇北方言文化振興的對策
方言文化承載著地域文化的基因,反映著當地人的生活、工作、情感的需要,是一個民族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基礎,需要得到保護和傳承。然而如今方言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劇,越來越少的人使用方言,以方言為載體的地域文化也面臨著逐漸消亡的趨勢。因此,我們更應該行動起來,去搶救那即將消失的方言文化。所以,我們從國家語言政策、現代科學技術、學校教育三個層面提出了一些對策,以供參考。
首先,適當調整國家語言政策,給方言一定的地位。《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107號協議》第23條第3項規定:“必須盡可能去采取適當的措施去保存母語或是方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三十四條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由此可見,保護公民的語言權都是我國應該承擔的一項義務。方言文化作為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果法律上得到一定的保證,便更容易得到制度上的保護。國家可以適當調整現行的語言政策,比如提倡雙語或多語生活方式,使得方言不至于處于消亡的趨勢。政府還可以采取其它有效措施來保護方言文化。比如加大對方言文化的保護力度,培養方言文化繼承人;建立方言文化博物館和方言文化數據庫;設立方言文化推廣周等。在寬松的語言政策和政府的扶持下,方言文化的保護一定會發生質的改變。
其次,利用現代科技化手段保護方言。時下,方言傳播被當作一種媒介創新的大手筆在各個省市媒體中廣泛興起[2]。比如湖南的《重慶新聞》、重慶的《霧都夜話》、揚州的《今日生活》等,方言已經逐漸滲透到新聞節目中。蘇北五市也可以加大對本地電視方言節目的建設,發揚當地方言文化特色,讓更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了解當地的方言文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相比電視、報紙等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新媒體更受廣大年輕人的歡迎。基于智能手機的普及,年輕人更樂于通過手機來獲取想要的信息。這樣一來,方言文化類APP的優勢便能體現出來。經過調查,已有少量的方言文化類APP平臺,比如《學說廣東話》《學講粵語》《上海話3000句》等,平臺的流動數量在幾萬到幾十萬之間不等。方言文化類APP的發展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蘇北五市完全可以打造自己的方言文化類APP并進行推廣,通過闖關、金幣獎勵等方式讓人們更有興趣去了解當地的方言文化。方言文化類APP上除了要有當地方言的發音,還需要有當地的民俗特色、神話傳說、戲曲等諸多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文化。用戶可以在APP上通過留言的方式相互討論、交流與分享。這樣一來,年輕人也更有樂趣了解當地的方言文化,方言文化出現斷層的現象也能得以緩解。
最后,發揮學校教育在方言文化保護中的作用。在基礎教育中,絕大多數學校實行普通話教學,方言甚至不被允許進入校園,這導致越來越多的中小學生不會使用甚至聽不懂方言。在我們看來,中小學課程中完全可以開設一些具有地方方言文化特色的課程。老師可以用方言給同學授課,通過PPT等形式介紹當地的方言文化。在校園中,除了普通話,同學之間通過方言交流也不應當被歧視。而在高等教育中,高校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可以看作是方言文化的集散地。同學們都來自全國各地,把各自的方言帶到學校,為高校方言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高校中開展關于方言文化的保護活動,對方言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有著其不可磨滅的價值。高校學生的年齡大多集中在18到30之間,通過他們的了解、交流與傳承,方言文化必定能夠得到高質量的繼承。在高校中開展方言文化保護工作可以從這兩個方面入手:一為組織學生建立與方言文化有關的社團。“鄉音社”在有些高校中已經開展,但還遠沒有普及。高校應積極鼓勵學生參加相關社團,在社團中,同學們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學習。二為高校主動開設方言文化選修課。高校的語言工作者作為方言文化保護的主要力量,可以開設方言文化選修課,向同學們傳授與方言文化有關的專業知識,培養同學們對方言文化的興趣。通過多方合作,方言文化的保護工作便能順利開展并達到預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