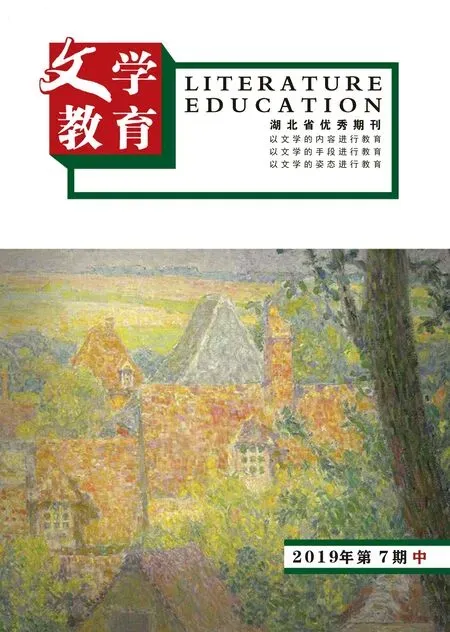《毒木圣經》:被征服的從未被征服
梁衛星
1.《毒木圣經》是對上帝的撥亂反正
女性在史詩里的角色通常是尷尬的,她們會引發男性之間的戰爭。但在形上層面,她們只是這些征服者們榮譽與尊嚴的象征;在形下層面,她們只是這些征服者們雄性力量的明證。因為男性們需要她們存在,她們才得以存在。海倫引發了特洛伊戰爭,特洛伊戰爭與海倫沒有關系。烏蘇拉甚至成為了馬貢多的守護者,但馬貢多的歷史興衰與烏蘇拉沒有關系;馬貢多的歷史不是烏蘇拉的歷史,而是奧雷良諾家族的歷史。這么說來,史詩并不令人肅人起敬,它的所謂崇高偉大是歷史事實而非道德事實;是權力話語而非真理話語。
史詩的客觀性由此而來——它是征服者的最高文體。一切史詩,都是權力與恐懼的雙重書寫。男人對女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權力里深藏著男人不可測度的無意識恐懼,對女人;文明對自然擁有壟斷未來的權力,這權力里潛隱著文明如地母般厚黑的恐懼,對自然。權力在人世間恣意行走,恐懼在人心里潛伏。男人與文明重合,是權力與榮耀的疊加;女人與自然一體,是征服與幻象的書寫。而男人與文明在當代的最大權威,以西方之名書寫;女人與自然在當代的最大屈辱,以非洲之名承受。
史詩行走至近現代,為權力加冕的,據說均為上帝之手。這是難以置疑的,因為權力前所未有地仁慈博愛,《圣經》取代了檄文,教堂取代了子彈,牧師取代了軍人……在文明的福音與自然的野蠻之間,所謂選擇難道不是不言自明嗎?懲誡與掠奪,凌辱與壓榨,控制與規劃就此隱匿不現。西方對非洲的權力壓抑,并非眾所周知;西方對非洲的恐懼,更是諱莫如深——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因此,再沒有比用史詩來稱贊《毒木圣經》更大的誤解了。《毒木圣經》不是史詩,而是關于史詩的“史詩”;或者說,《毒木圣經》是以地球自有文明以來一切史詩為素材的“史詩”。
這是最高的創作律令,芭芭拉要還原權力與文明的真相,訴說被剝奪者的苦痛與追求。《毒木圣經》必然是女性視角的,也是自然視角的,因而還是非洲視角的。在被征服者的視角下,源遠流長的史詩話語光鮮輝煌的文明面具被剝離侵蝕,權力作為歷史事實失去了道德合法性,征服者話語偏離了真理的道路。西方與男人們高舉《圣經》不斷擴展馬蹄的邊界,《圣經》所到之處,人世間有無數基督自我加冕,人心深處有無數天堂坍塌。如果《圣經》只是文明的《圣經》而非自然的《圣經》,如果《圣經》只是征服者的《圣經》而非無辜被征服者們的《圣經》,那么《圣經》何以圣?何以經?如果上帝不是任何膚色而只是白色,不是任何性別而只是男性,上帝何以成為上帝?
《毒木圣經》的女性視角顯而易見,芭芭拉·金索沃的女權傾向昭然若揭。但《毒木圣經》遠遠超越了女權主義,她以女性特有的細膩、瑣碎、溫柔、感性、堅韌、包容抵達了真正的而非僅僅是史詩性的宏闊、悠遠、深邃、理性與綜合。《毒木圣經》的女性視角不是女權主義的,包容了女權;不是自然主義的,包容了自然;不是文明主義的,包容了文明;不是權力主義的,包容了權力。“毒木圣經”不是對“圣經”的反諷,而是對“圣經”的還原;不是對上帝的褻瀆,而是對上帝的撥亂反正。它多有怨刺與幽恨,它竭力清算與控訴,卻最終在絕對平等與尊嚴的律令下選擇了寬容。
事情就是這樣,如果真理只是一部分人的真理,真理就只是權力話語;如果權力只是一部分人的權力,權力就只是剝奪的工具。要么,一部分人的權力僭越了《圣經》;要么,《圣經》只是一部分人的《圣經》——芭芭拉·金索沃的結論直接有力,即使她是瀆神的,她瀆之神也只是一部分人的神;這樣的神,不可能是全能的,更不可能是博愛的,因為它只是偶像,與金牛犢并無區別。并非人類需要一部《毒木圣經》,而是一部全人類的《圣經》,需要《毒木圣經》對文明與權力高舉之《圣經》的鏡照與還原。
2.《毒木圣經》就是女人們的《出埃及記》
顯然,《毒木圣經》只能由女性們來書寫,而且還只能是西方女性來書寫;至于西方女性,則再也沒有比牧師家的女人們更合適的了。只有出入兩間,方知兩間各自的殘損與光影。非亞女性固然能有被征服者的痛楚與自覺,卻易為立場裹協,淪為復仇的工具。西方牧師家的女性是三重的被征服者,她們作為女性,被男性征服;作為自然,皈依了文明;作為人類被征服的那一半,被《圣經》馴化。如果《毒木圣經》不得不在女性、自然、人類的一半三個層面對《圣經》進行清理鏡照,那么,其書寫者就只能是西方牧師家的女人們。更何況,也只有牧師家的女人們才能洞悉牧師最大的隱秘:牧師拿單的傳教狂熱源于戰爭創傷,確切地說,是源于征服創傷。
這一洞悉,具有真理性的意義,是全人類道德意識的隱秘起點。牧師拿單何以如此狂熱地傳教?因為他在征服的戰場上不曾榮耀上帝,那么就只能在人心的戰場上榮耀上帝。他來非洲,不是來播種愛的,而是來發動戰爭的,他要用文明消滅非洲人心的荒蕪,而他的文明,永遠有著強有力的暴力后盾。他預定了戰場,那么戰場就只能是荒蕪的。盡管這戰場是人心,有著亙古的信仰傳承與存在智慧。他企圖以此榮耀他的上帝,修復他在戰場上的創傷:膽怯與恐懼,緲小與脆弱,無力與無能。他的修復之戰早在來非洲之前就已經打響,他對家里女人們的征服即是非洲之戰的預演。
從根本上說,牧師也是被征服者,盡管他是西方白人,盡管他是牧師,但當他要在人心的戰場上發動戰爭,他就不是站在全人類的有限根基上認識圣經與上帝,他就背離了普遍的人性,因而也就背離了真正的《圣經》,他就成為了被征服的征服者,與剛來非洲時的他的女人們的身份沒有任何區別。這就是最深的隱秘:一切征服者都首先是被征服者,他們首先被權力與狂熱、偶像與觀念征服,而后才分享了權力與觀念,成為征服者。他們的狂熱無非瘋狂。他們的文明,永遠也擺脫不了區別的夢魘——人類的一部分,始終是他們征服的對象,他們的文明,陷入了野蠻的等級鏈條里,無力自拔。
然而,人心不是戰場,任何把人心異化成戰場的企圖,注定了失敗。當然,他們會留下巨大的難以言喻的創傷。對于牧師來說,對于任何人來說,真正的《圣經》,永遠不是武器而是安慰。拿單不明白這一點,所以,他的戰爭一敗涂地。他的失敗從一開始就顯露了征象:作為他的文明武器,他的圣經話語,在非洲話語面前,徹底啞火,既沒有上帝的威嚴,也沒有基督的慈悲,有的,是滑稽可笑與語無倫次,是裝腔作勢與莫名其妙,是不可思議與空洞無當……拿單永遠不明白,如果上帝要變亂巴別塔,那么,圣經話語雖然不是非洲語,但也不會是英語。每一種語言都是那種語言里的生活的合法性來源,非洲語言傳承千萬年,有著自己的價值信仰系統,又怎么可能完全為英語生活取代?拿單以為語言是可以翻譯的,卻不知道,沒有任何語言可以完全譯成另一種語言,因為生活是不可譯的。當然,語言是可以融合的,但那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安慰里;只能源于雙方的慈悲,而非一方的狂熱。而這,正是《毒木圣經》的追求。
拿單的失敗,從他踏上非洲開始,就注定了。他不僅會一無所得,還將失去已有。拿單不明白的,被他征服的女人們會慢慢明白。拿單生來不是為了生而是為了死,不是為了成長而是為了毀滅;因為他的榮耀之路不是通過和解而是通過征服。作為牧師,行等級之事,與上帝背道而馳,上帝又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如果上帝不磨滅他的黑暗之心,就會讓他的黑暗之心瘋狂。所以,拿單從無理解接納融合非洲語言的意愿,他的傲慢阻止了他也最終毀滅了他。但他的女人們不同,他的女人們在非洲生活中反觀到了自身生活與非洲生活的同構性:她們同為被征服者,她們的心一直以來都淪落于一顆黑暗之心的掌控,許多莫名其妙的東西為此凌駕于她們的生命與生活之上,她們作為祭獻者,沒有自己可以追求的人生。
這是啟示錄式的時刻,當普菜斯家的女人們發現了自己與非洲命運的同構性,發現了自己命運的荒謬性——作為被征服者卻幫助征服者以上帝的名義作惡,發現了自己作為女人、自然與弱勢人類的三重悲劇,她們怎么可能不覺醒。原來,一直以來,她們崇敬的拿單,這個男人,她們的父親與丈夫;她們自豪的西方文明,美國,歐洲,她們的文明祖國,都不過是她們人生的埃及,她們必須走出。沒有摩西,她們是自己的摩西,她們發現了自己的埃及,她們必須走出。《毒木圣經》首先就是她們的《出埃及記》。同樣,她們也沒有自己的迦南——那流奶與蜜之地;但她們還是要出走。她們那創痕累累的心修復之日,就是她們徹底回歸之時。她們可能永遠也無法回歸,但她們卻已經絕然走出了她們的埃及。
3.《毒木圣經》反對征服,但并不反征服
《毒木圣經》首先當然是所有被征服者的《圣經》,它反對征服,但并不反征服。它的書寫者們各各以自身的偏執,突現了她們作為人類的根本局限。這種突現甚至可以說是刻意的,盡管其突現的對象是客觀存在的。芭芭拉這么做,目的是明顯的,她要鏡照出《圣經》書寫者們被上帝的語言之光遮蔽的人性局限。她要示現的是,女人們有多偏執,男人們就有多狂熱;女人們有多瑣碎,男人們就有多空疏;女人們有多自卑,男人們就有多狂傲;女人們有多麻木,男人們就有多殘忍……他們還有著一樣的軟弱、無能、絕望……因此,為了追求屬于自己的生活,大姐蕾切爾可以理直氣壯地以自身為武器;為了追求一種更合理的生活,二姐莉亞竭盡全力要洗去自己的白色……沒有人有權利指責他們自私利己或矯枉過正,她們的自由意志展開之處,必有人類的局限呈現。
《毒木圣經》的敘事結構是《圣經》式的,但沒有自己的福音書,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全新的福音——當女人們發現了自己的埃及并走出自己的埃及,誰能說這不是人類聆聽到的全新福音呢?然而,女人們出埃及是難的,因為她們沒有自己的摩西,因為她們發現自己置身埃及就要洞悉自身的三重悲哀。所以,《毒木圣經》的敘事,在創世紀之后,出埃及記之前,女人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她們的覺醒與成長之路伴隨著無盡的傷害與震驚。她們被扔在非洲,就再也不能離開非洲。多年后,她們將會發現,她們的美國伊甸園,建立在謊言與征服之上;她們被拋離這個伊甸園,也是因為要陪伴征服與謊言。
然而,非洲并非本質上的墮落之地,而是被命名的墮落之地。被命名即被征服,有征服就有臣服與反抗,在如此大的背景下,女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宏大的被操控的歷史裹協沖擊,經歷了自身的啟示錄、士師記,在神與蛇的較量中,受盡無邊傷害與凌辱,在女人們的小基督蕾絲·梅死亡之后,終于徹底覺醒:她們一直在人生的埃及,她們在母親的帶領下走出。不像《圣經》里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時候總是不舍猶疑,拖家帶口,不愿丟掉一點點東西,他們不愿與埃及告別,他們的靈魂并不愿出走埃及,而奧莉安娜不同,她是決絕的,她把所有的生活用具全部拉出屋外,讓非洲人拿走,她以此在良心上向非洲人懺悔,也以此與自己的過去人生徹底告別。她和女兒們一無所有地出走,女人們的出埃及,遠遠比男人們的出埃及徹底悲壯。
這甚至在她們的敘事腔調上都表現得淋漓盡致。《毒木圣經》是流暢清新的,她刻意地遠離《圣經》式的格言警句,就好像她害怕權力的傷害。《毒木圣經》是喃喃自語的,女人們絕望的呼號也只是訴之內心的神靈而非大地江河之上的全能君主,女人們本能地娓娓道來如清水細流,而不若《圣經》敘事汪洋經地——她們執守著自身的清淺細澤,無意匯成宏大深闊。金索沃堅信,女人們的雞零狗碎本身就擁有屬于自身的宏大深闊。任何生活,其本來的面相自有不為他人所知的宏大深闊,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毒木圣經》的敘事是反歷史的,因而也是反宏大敘事的。《毒木圣經》的最高教義是:生活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個體生命的倫理敘事高于一切宏大敘事,即使上帝的預言,圣經的理想,也必須為此讓路。母親奧利安娜的出埃及自白,從失去摯愛的哀痛說到離開丈夫的決絕,從出走非洲的跋涉講到承受征服的歷史,揭示出一切既有歷史都是征服者歷史。其傾訴罕見地如高崖懸瀑江河行地,具有無與倫比的壯美。因為,女人們要走出自己的埃及了,她們從未被征服,只是默默承擔著自己的命運,在各種被強加的痛苦和歡樂中堅韌執著地活著。
奧利安娜說:不管他們占領的是妻子還是國家,他們的錯誤始終如出一轍。華盛頓橫渡特拉華河。美軍攻占沖繩。他們的心底渴求著江山萬代。但他們做不到。沖繩對自己的陷落還記得什么呢?偉大的特拉華河滾滾向前,而華盛頓先生連一抔有用的堆肥都算不上。非洲吞噬了征服者的音樂,唱出了一曲她自己的新歌。
二女兒利婭則一遍遍講述著非洲大地上,由白人和西方文明以拯救和幫扶為名肆意降下的無盡苦難。被地雷炸斷手腳的黑人兒童,集市上奇缺的蛋白質、肥皂和衛生紙,十一歲就要去當雛妓的皮包骨小女孩,叢林被毀后人們栽植的玉米、甘薯和大豆……這只是因為沒有什么悲哀重過個體的悲哀;沒有什么苦痛實過日常人生的苦痛。如果文明與自由民主要犧牲女人孩子們的日常生活,那么,這文明就是野蠻,這自由民主就是暴力與獨裁。如果歷史的潮流要淹沒兒童的尸骨,那么這歷史的潮流便缺乏正義。
《毒木圣經》是這樣一本書:她從男權“圣經”話語下發現了人類的一部分——他們因為歷史、膚色、性別、信仰而被剝奪了自主的生活,她堅決捍衛他們的生活,以女人的溫柔但不局限于以女人的名義。她悲傷而不自憐,痛苦而不沉淪;她否認了上帝是男性與白色的,但并不強加給上帝以女性與黑色。她把人類長久以來被凌辱的那一部分的人的歷史唱成了哀婉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