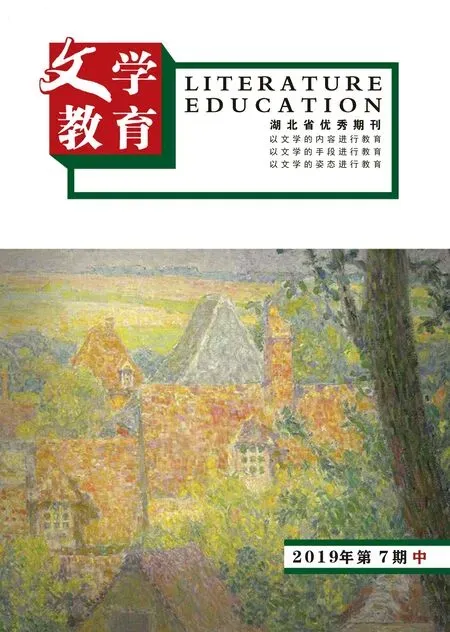當代社會道統的失語現狀:《風雅頌》知識分子研究
朱莎莎
一.中國傳統士大夫“道統”內蘊分析
道統的內蘊,自古眾說紛陳,這是因為其在歷史流變過程中,不斷被灌注于新的內涵。此處援引錢穆先生在其著作中對道統的闡釋。在錢先生的詮釋中,大約有四層意思。第一層,它是社會大群人生的大道,并不是某狹隘的利益集團所獨占封隔的,即道具有普遍共通性、社會性。由第一層詮釋,又給出第二層意思,即道有宗教意涵,有超越性。蓋中國文化所重的“道是人本位的、人文的,但道之大原出于天”①。“天生于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這類孔子的言論都體現了中國人講道德中的“仁義禮智信”中的“信”,表現出一種近乎宗教的超越性的傾向。第三,道內在于人心,有內在性。錢先生認為,中國人所謂道,即是文化中有價值意義者,“而此項意義與價值,則往往不表現在外面而只蘊藏在人生之內部”②。此亦即謂道是精神性的,而人文理想自亦可說是一人文精神。第四層意思,有現實性、實踐性。道或人文理想不是懸空高標無著落的、與世相隔的,它不是一邏輯概念,“通于時代而有切于身世之用者,中國傳統謂之道’。”③“道既存有即活動,對人生整體有效用,是現實社會人生的動源,就此自可說道具有現實的實踐的性格,即必然亦須要通過修、齊、治、平的人生實踐和社會實踐來表現與實現。”④
二.《風雅頌》:管窺當代社會“道統”的失語現狀
(一)知識分子生存境遇的畸形
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成為重頭戲,生產力成為第一要義,唯發展論使中國進入了一個遠比當初的預想復雜得多的狀態:一方面,市場活力使得中國經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又進人了一個問題頻發的時期,融入全球化帶來的文化倫理多元化問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激烈博弈問題等,都由潛在轉向公開。在這一社會轉變過程中,許多桎梏不僅沒被有效打破,反過來利用自己對社會資源和市場資源的支配權,假借“市場化”、“世俗化”、“消費時代”甚至“后現代”的名義,竭力營造一種泯滅人精神自由與理性反思空間的物質化意識形態。中國當代文化體制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相應的病癥,即一種被規則化和制度化的時代病癥——它在強大的工具主義實用原則的驅動下,使知識分子得不接受被現實制度扭曲了的命運。“事實上,藝術和學術活動的獨特和有價值之處,正是它沒有直接受控于工具主義風氣。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不是著手生產顧客需要的東西,而是追求實現更高遠的目標。”⑤而在實際生活中,實利化的求知和無私的真理性的求知之間的界限卻被模糊了,它導致了缺乏實用價值的人文知識分子越來越走向邊緣,也越來越失去精英化的角色。
在《風雅頌》這部小說中,主人公楊科所任職的清燕大學作為中國大學的縮影,呈現了一副高校整體墮落的荒誕圖景:里邊是非混亂,價值顛倒,完全失去了大學應有的品格,人性也極端麻木、蠻橫和虛偽。楊科妻子茹萍的從教之路便極其反諷的反映了這一現狀:專科畢業的她在新設立的影視藝術系憑借兩年的函授學習和她教授父親的關系,輕松地成為大學系里的講師,再一年,她憑借自己出版的抄襲的論文被評為清燕大學擁有重要論著的副教授,其后成為副校長情婦的她在剽竊楊科的《風雅之頌》發表之后,竟一躍成為系里舉足經重的對國家有特殊貢獻的專家教授。不可不謂荒誕可笑。楊科無意中做率領學生抗擊沙塵暴的英雄這一情節則可看出高校的虛偽與麻木。這次行動影響了國家推薦學校進入“國際教聯會”的提名。事后,學校并沒有正視學生發起這場運動背后的訴求,而是學校自身的利益。因為這場運動受到了國際媒體的注意,而學校這樣受到國際媒體關注是和中國改革開放給環境帶來的污染和破壞的背景連在一起的,這必然要驚動教育部和國家的領導人,進而影響到學校的利益。為了保證學校的既得利益,學校領導們不惜軟硬兼施,威脅利誘,將楊科這個在他們眼里無足輕重的副教授送進了精神病院。
美國學者曾指出今天的大學校園里充斥著一種反精英式的平庸主義文化思潮:“今天的反精英主義很少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權力上。相反,它的攻擊目標是各種常被錯誤地與精英聯系在一起的行為、文化和教育。繁復的語言、復雜的思想、挑戰性的教育,以及高難度的形式,如今都被貼上精英化的標簽,因此被認為是件壞事”⑥在這種體制化的影響之下,那些大學里的知識分子們,幾乎不可避免地開始以反精英主義的面貌出現,并以現代文化精英的身份自居。由此而帶來的結果,便是“所有將學術常規化的熱心都被當代文化精英們視為應當受到一致嘲笑”,而“那些充滿熱情地追求自己愛好的個別學者越來越面臨著被貼上‘不切實際’、‘精英’、‘脫離社會’和‘邊緣化’的標簽的危險。”⑦它導致了大量的教師在教學中不再堅持以獨立的思考和前沿性的探索來開啟學生的智慧,而是不得不選擇一些迎合學生興趣和平庸思維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取悅于學生。在小說中茹萍被樹為教學樣板的影視藝術課教師,其擅長的做學術的功夫就是把別人的論文取長補短,其講課的內容是羅列一些明星生活的小道消息來嘩眾取寵,而她的課往往被來上課聽講的學生擠得水泄不通。可見教師的授課質量和效果,不再取決于教師的思想能力和教學能力,而是取決于學生歡迎的程度。學問、對卓越和真理的追求,不斷被描繪為古怪的、任性的和不切實際的,在小說中楊科開授《詩經》解讀課,前來聽課的學生卻是鳳毛麟角,他們在課堂走神,耳語,睡覺。唯一一次座無虛席,竟是因為李廣智因給他帶了綠帽子心懷愧疚,特地下發的文件勒令學生去上課的。但即便是這樣,在講到形而上知識點的時候,學生們也紛紛退出了教室。
(二)知識分子自身人格的分裂
對當下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他們身上延續著中國士大夫文人中綿延幾千年的道統,意味著他們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方式不僅是對自身的精神性要求,也是追求社會大群人生的大道,真理、追求知識的現代文明價值體系,也是在社會實踐中傳道,行道。在《風雅頌》中,我們可以看到楊科身上仍然留存著中國士階層的道統精神。他潛心于自己的學術領域,在那塊自己的園地里執著地耕耘,有著很強的獨立意識。在曾經居住過幾位國學大師和現代著名作家的一間窄小的辦公室埋頭苦讀與《詩經》有關的論著資料,殫精竭慮地完成專著《風雅之頌——關于〈詩經〉精神的本根探究》。同時他把講臺這塊見方之地看的極其重要,流淌在他血脈中的“道統”使傳授知識學問真知變成其本能。在面對滿教室的學生,他沒有在意這件事本身帶給他的屈辱,他心里的念頭是應當機立斷,抓住時機,扛起教學這把大旗,把《詩經》研究最精髓的部分傳授給他們。可見在楊科身上仍然體現著傳統道統中的仁義。
遺憾的是,在當下許多知識分子那里,“成長的畸形環境本來就使他們的高層次人格追求帶有動力不足的先天陰影,現實的生活環境更無法為其人格系統提供出在本能需求和高層次需求之間維系平衡的必要土壤。這一切導致了他們的人格內部各層次之間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其對高層次人格內容的勉強堅持往往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撐,最終無法抵御本能的反噬,造成系統失衡、人格潰敗。”⑧他們渴望重返精英地位,卻又不斷被社會體制所鉗制;他們努力重建理想的價值,卻又常常被實用主義所嘲弄;他們試圖通過忍辱負重的方式,尋找漸漸失落的人文精神,但利益化的現實卻迫使他們最終逃離自我的生存角色。因此,自我的分裂,幾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無法擺脫的命運。
小說中,從農村社會走出來的楊科的心理邏輯和思維邏輯殘留大量的低級生存本能誘因,而另一方面《詩經》研究方面的杰出才能,又造就了他作為大學內優秀學者的自尊、自負。他表層自尊,內在自卑。在整個社會趨向功利化的時代背景下,發文章和出版專著需要交錢,校園的學風變得浮躁不堪,不學無術的妻子也評了職稱并有了看不起他之意,本來就缺乏安全感的他自尊受到嚴重威脅。這時他想維護自己人格尊嚴的方式已不再不食人間煙火,而是企圖寫一個有學術分量的專著以通過學校的教授職稱評定,企圖通過追求一種更高的職稱身份來維護所謂“尊嚴”。回家卻遇到妻子和副校長通奸,貌不驚人的副校長對妻子的吸引力無疑來自權力,妻子毫無愧疚地站在副校長的一邊。面對權力對自身權利的僭越與侵犯,楊科的反應也只是“淚流滿面”地以“一個知識分子的名義”求他們“下不為例”在與權力的抗爭中,楊科并沒有進行控訴,以揭示其丑惡的面目。面對權力的攫取,他閹割了自身的精神追求,成為了一個失去了“自我”的偽知識分子。
注 釋
①轉引自羅義俊:《論士與中國傳統文化——錢穆的中國知識分子觀》,《史林》,1997年第1期,第5頁.
②錢穆:《中國歷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0頁.
③轉引自羅義俊:《論士與中國傳統文化——錢穆的中國知識分子觀》,《史林》,1997年第1期,第5頁.
④羅義俊:《論士與中國傳統文化——錢穆的中國知識分子觀》,《史林》,1997年第1期,第6頁.
⑤[英]弗蘭克·富里迪:《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頁.
⑥同上.
⑦同上,第138頁.
⑧姚曉雷:《何處是歸程——由〈風雅頌〉看當下知識分子的精神之瘍》,《文學評論》,2009年第1期,第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