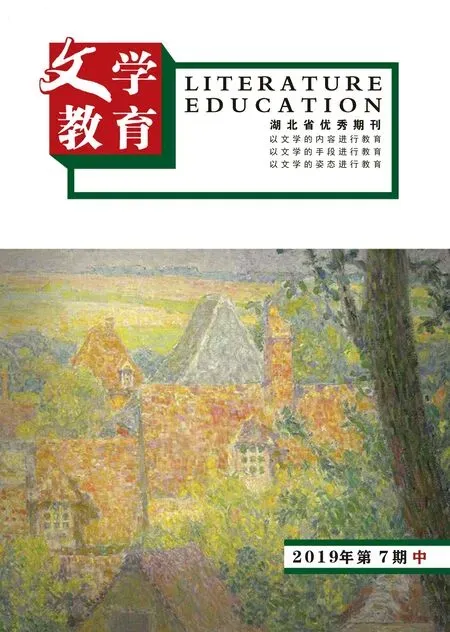創客教育:杜威“做中學”教學理論的當代發展
周澍云
一.杜威“做中學”的教學理論
杜威是南北戰爭的災后重建時間歐美各種思潮的集大成者,在批判繼承各種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張。根植于進化論的實用主義哲學,其強調真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動態發展、不斷被檢驗和修正的思想深深影響了杜威。由此結合機能心理學、民主主義,杜威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本質論——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的不斷改造和重組,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教學方法論——“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做中學”也就是“從活動中學”、“從經驗中學”,是在考慮了兒童身心發展特點基礎上強調聯系社會實際生活和動手實踐的一種學習方式。杜威認為“人們最初的知識,最根深蒂固地保持的知識,是關于怎樣做的知識”,“初生兒童就秉賦愛好活動的性能,并能夠依憑活動結果帶來的苦樂而調整其活動和控制其活動,借以適應環境的需要”[1]。他充分肯定兒童的天性和潛能,認為兒童期最富有可塑性,并且蘊含著能使他們進行復雜而高深的學習的可貴潛能。通過從實際社會生活中移植出來的活動,讓兒童發現學習的需要和興趣,產生學習的自主性和自覺性,并且由于“從做中學”是從興趣出發的,兒童會更加主動地進行探索,在實際動手操作中自然地收獲知識。
首先,在“從做中學”時,必須排除按照外部明確的指示和命令進行的機械性、重復性行動。類似這樣的活動也許能鍛煉靈巧的肌肉,但并不能使得兒童獲得必要的思維方法,反而會禁錮兒童的創造和好奇的天性,過早地框定孩子的自由發展,使其喪失活力。
其次,“從做中學”要根據不同年齡兒童的特點和能力,從社會實際生活中選取和引入合適的情景,由此設計需要孩子實踐的活動內容,確保其能夠根據已有經驗進行自主的個性化的探索,從中體會到一定的困難和樂趣,而不是一籌莫展、喪失信心。
此外,杜威還批判了福祿貝爾式的幼兒園、蒙臺梭利式的幼兒之家,認為其“不自覺地猜疑學生本來的經驗,因而過分使用外部的控制”[2],為兒童提供的教具都是精心設計和準備過的,害怕把原材料提供給學生。也就是說,杜威認為兒童所接觸的活動應該是簡單的、貼近生活的,只有通過自己將粗糙的原材料組合、制作成作品,兒童才能真正學習到蘊含在其中的知識。
二.創客教育的提出與發展
(一)創客教育的提出
根據中國電子學會現代教育技術分會創客教育專委會的定義:創客教育是創客文化與教育的結合,是基于學生興趣,以項目學習為方式,使用數字化工具,提倡造物,鼓勵分享,培養跨學科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寫作能力和創新能力的一種素質教育。[3]
發端于21世紀初麻省理工學院和歐盟先后發起的“Living Labs”計劃,創客運動在美國戴爾·多爾蒂(DaleDougherty)等人發起的“創客行動”、奧巴馬促成的首屆“白宮創客大會”等活動的推動下,迅速在世界各地流行起來。[4]2014年,美國率先啟動“創客教育”計劃,“美國中小學創客教育旨在為所有中小學學生提供宜于創造的環境、資源與機會,尤其是借助技術工具與資源讓學生將學習過程融于創造過程,實現基于創造的學習”[5],美國各高校也積極響應,挖掘創客教育潛力,開展創客教育實踐。
這種基于創新實踐的教育為我國陷入困境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創客教育成為了我國教育界中的熱點問題。2015年1月,李克強總理參觀深圳柴火創客空間。隨后,李克強總理又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大力發展眾創空間,創客就這樣從小眾走向大眾,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目前,清華大學等高校正在積極建設創客空間,國內一些中小學,如浙江省溫州中學等也已籌建創客空間并開展了創客教育的實踐。
(二)創客教育與“做中學”
在杜威“從做中學”思想的影響下,學生和活動逐漸成為了課堂的主體,越來越多的教育家開始重視學生的學習理論和心理發展,轉變以教材和老師講授為中心的課堂模式,通過綜合性活動、研究性活動激發學生的自主性和創造性,以期最大程度地發揮學生的潛能。并且,在如今的信息化、數字化時代,隨著機械化、自動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人的創新思維和創新實踐能力顯得越發重要。
創客的核心理念是基于興趣的創新或創造,由此引申出的創客教育核心也在于從興趣出發,通過多學科融合的項目型實踐活動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最終達成創新型人才的培養目標,與“做中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首先,兩者都重視發展學生的興趣。“做中學”通過從社會實際生活中尋找適當情境,并將其轉變為符合兒童發展特點的活動,順應兒童的興趣,調動兒童的積極性;創客教育則通過讓學生通過觀察平時生活形成自己的創意,進行創意驅動型項目化學習,以興趣作為學生行動的出發點,更加強調學生的自主性。
其次,兩者都強調通過實踐活動進行學習,但兩者所提倡的活動有所不同。以學科為單位的理論知識學習往往強調識記,所謂的理解與應用也不過是會做題,紙上談兵罷了,由此導致學生普遍缺乏動手能力,高分低能也就不難理解了。“做中學”和創客教育的出現正是為了解決此類問題,兩者都強調學生進行實際動手操作,在實踐中進行有目的地學習,這樣學習到的知識才能真正為自己所用。
最后,兩者都重視學校教育與社會的聯系。杜威曾指出,“學校各種形式的實際活動的目的,主要的不是在于它們的本身,或者在于廚工、縫紉工、木工和水泥工的專門技能,而是在于它們在社會方面能與外部生活相聯系。”創客教育也是如此,且由于互聯網時代開放包容的特點,學生更加方便與社會建立聯系,社會不僅可以為學生提供專業知識方面的指導,而且可以通過購買、點贊等激勵行為提升學生的成就感,促使其在某個領域繼續進行深入的探究。
此外,與杜威提倡的藝術創作、手工活動、科學探究三類活動相比,創客教育活動具有更高的整合性,強調合作學習和項目化思想,不僅要在活動中培養學生互動溝通、分工合作等團隊協作能力,而且重視讓學生體會項目化解決問題的過程(提出問題—設計方案—具體實施—評價反饋),培養適應在高速發展的信息時代發展的綜合性人才。
杜威的“做中學”是創客教育的淵源之一[6],而創客教育又擺脫了杜威相對僵化的學習三層次理論,創造性地解決了從手工活動到科學教育過渡難的問題。創客教育不再將實踐活動與理論學習階段分離開來,而是在理論學習的基礎上強調跨學科的實踐活動,幫助學生將理論應用于實踐活動中,并在此過程中尋找自己的興趣點,培養自己的科學精神和創造精神。此外,創客教育在新時代下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要求,即創客精神——自強進取,個性開放;協作分享、融合創新;重工尚器、民智國強[7]的培養。
三.結語
創客教育就是“做中學”與21世紀以來的社會與教育需求結合的產物之一。我國教育偏重理論知識的學習和知識體系的養成,在基礎教育階段僅僅進行知識學習和應試訓練,而將培養創新實踐能力和精神的重擔推給高等教育階段。在應試教育的大背景下,填鴨式教育一再被人詬病,卻只得緩慢地發生轉變,學生的實踐能力低下,高分低能的所謂“人才”層出不窮。作為“做中學”理論的發展與延伸,創客教育保留了“做中學”思想的精髓,同時又在項目學習法、創新教育、DIY理念的綜合影響下獲得了新的內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