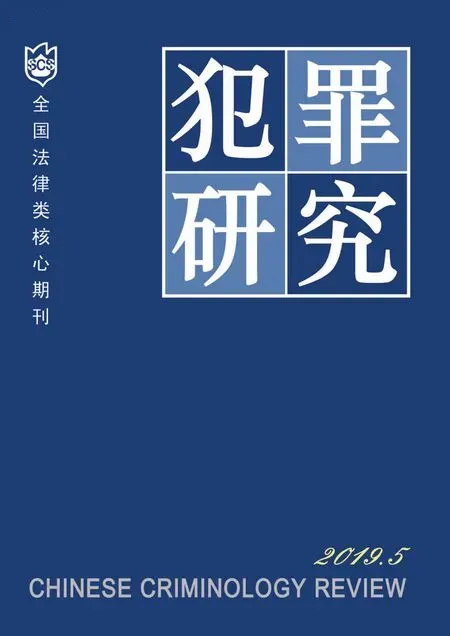我國反黑刑法立法四十年回顧與展望
姚建龍 羅建武
中國進行有計劃地、階段性地、集中式反黑始于1983年開始的“嚴打”斗爭。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作為有組織犯罪的一種重要形態,可追溯至我國近代以來的幫會問題。[1]“黑社會性質組織”“有組織犯罪”“惡勢力犯罪集團”“幫會組織”等術語都是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所出現的市民社會的異化形態,因文章寫作方向是刑法立法角度,故不對這幾種形態的“組織”進行詳細區分。同時,如無特殊說明,文中的“反黑”一詞均將“嚴打”“打黑除惡”“掃黑除惡”包含在內。幫會組織是在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后空前發展起來的,解放戰爭時期走向沒落,新中國成立后幫會組織遭受到毀滅性打擊。[2]參見周育民、邵雍著:《中國幫會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1—4頁。十年文革期間,無政府主義盛行,法制蕩然無存,各種造反組織打、砸、搶、燒、抄(家),社會處于嚴重混亂狀態。到1976年文革結束后,社會治安并未得到迅速、根本地扭轉,其后幾年里嚴重刑事犯罪頻發,黨和國家亟待重建社會秩序。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第一部刑法于1979年制定出臺,并于次年元旦起實施,結束了我國沒有刑法典的歷史。
十年文革結束后迎來第三次犯罪高潮,刑事案件尤其是惡性案件態勢嚴峻。鄧小平在1983年7月19日同當時公安部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在非常狀態,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嚴才能治住……”,[3]參見鄧小平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4頁。從此“嚴打”成為我國刑事政策的重要內容,并深刻影響著刑法立法與刑事司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我國已集中開展三次反黑斗爭,重特大惡性刑事犯罪迅速減少,社會治安狀況得到根本改善,這主要得益于刑法立法的不斷發展完善提供法治化指引。進入新時代,反黑斗爭面臨新的挑戰,回顧我國反黑刑法立法的歷史變遷,反思存在的不足并進一步提出相應的完善建議,對于進一步完善反黑法律體系,提升依法、正確、高效反黑能力,均具有重要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指導意義。
一、反黑刑法立法四十年之變遷歷程
1978年后我國迎來經濟社會的重要轉型發展期,加之十年文革的遺毒尚未根除,嚴重刑事犯罪依然高發,社會治安形勢不容樂觀,緊急制定的1979年刑法已無法滿足當時社會治理(控制)的客觀需求。與此同時,從1983年開始我國進入集中式強力反黑時期,為避免陷入弊端諸多的“運動式”反黑,對刑法立法的修訂與完善提出更高要求。刑法立法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我國的反黑刑法規范體系逐漸完善,法治化水平得到極大提高。我們可以從刑法修訂的時間、模式、內容等視角來看我國反黑刑法立法的發展進程。
(一)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專門立法活躍階段
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制定于1979年,其中也涉及諸多反黑可以適用的罪名,但實際上正式的反黑刑法立法是以1983年“嚴打”為標志。[1]“反黑”一詞始于1983年開始的“嚴打”,因而,反黑刑法立法的起始并非1979年刑法典的制定。而且,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并未對黑社會性質組織進行法律界定,所以,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罪名適用沒有嚴格標準,但從理論上以及當時的反黑實踐而言,一般包括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破壞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等四類罪名。針對嚴重的犯罪狀況和惡劣的社會治安狀況,倉促頒行的刑法典已不能適應“嚴打”提出后國家依法從嚴從快從重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司法實際。因此,大量的單行刑法出臺,從1983年“嚴打”到1995年10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累計出臺20部單行刑法,[2]參見陳興良:《回顧與展望:中國刑法立法四十年》,載《法學》2018年06期。陳興良教授在文章中論述為24個,但實際上1981年6月10日通過的《關于死刑案件核準問題的決定》和1983年9月2日通過的《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不屬于單行刑法,而屬于刑訴法的內容,因此,1979年刑法制定后我國一共出臺了22個單行刑法。同時由于筆者的視角是反黑刑法立法,故1983年之前的2個單行刑法不包括在內,文中統一使用20個單行刑法的提法。其中直接涉及反黑的規范共有5部。[3]具體包括1983年9月2日《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1990年12月28日《關于懲治走私、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于禁毒的決定》、1991年9月4日《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當然,在當時其余的單行刑法對于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過梳理單行刑法立法時期的時間要素,可以發現以下特征:(1)出臺時間間隔短、頻率高。從1983年第一個“嚴打”的單行刑法規范出臺后的12年間,我國一共出臺20部單行刑法規范,平均7.2個月就制定一部,其中間隔最短的僅為2個月零3天,同一天出臺2部的也不在少數。(2)通過時間、頒布時間和生效實施時間幾乎都為同一天,多直接表述為“自公布之日起實施”,即采取即時生效模式。這一方面是由于規范內容較少,另則也是為了能夠及時填補司法適用的需求。從以上兩個方面的時間要素特征可以看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反黑刑法立法處于相當活躍時期,呈現出有針對性地頻繁立法現象。
從立法內容來看,根據與反黑直接相關的5個單行刑法規范也可以明確該階段刑法立法的特點。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要求對于流氓犯罪、故意傷害、打擊報復行兇、販賣人口、涉槍涉爆、反革命活動、引誘、容留、強迫婦女賣淫等犯罪,要在法定最高刑以上判處刑罰,直至死刑。其后更是針對涉淫穢物品犯罪、毒品犯罪、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門出臺單行刑法。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盡管1983年開始的“嚴打”對象范圍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刑事案件,但已經明確提出了將流氓團伙或者其他犯罪團伙作為打擊的重點。至1986年底為期三年的“嚴打”斗爭結束,全國共查獲各種犯罪團伙197000個,查處的團伙成員876000人。[4]何秉松著:《中國有組織犯罪研究》(第一卷),群眾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頁。從整體上來看,不僅重視對嚴重刑事犯罪的立法完善,也極其重視對社會風氣的重塑。可以看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的反黑刑法立法呈現出活躍、精準、異常嚴厲等多重特點。
(二)二十世紀末期:體系化修訂完善階段
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我國逐漸形成由一部刑法典、22部單行刑法構成的刑法規范體系,反黑刑法規范的總體格局也保持著相對的一致性。由于1979年刑法出臺倉促而存在的諸多不完善之處以及單行刑法紛繁復雜帶來的刑法規范適用不統一、缺乏權威性等問題,對舊刑法進行全面的系統性修訂已迫在眉睫。鑒于此,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于1997年3月14日表決通過對刑法典的全面修訂。在保留1979年刑法基本框架的基礎上,對其實施以來頒布的22個單行刑法進行合理吸收,章節結構更加合理,罪名體系更加完善。就反黑刑法立法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取消了刑法典總則中關于“指導思想”的表述,其中包括“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以及“反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表述,使我國刑法祛除了明顯的“嚴打”刑事政策色彩,弱化了刑法立法的階級斗爭屬性,為我國刑法立法的不斷完善提供了廣闊空間,也符合刑法現代化的發展趨勢。
二是在刑法典總則中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三個刑法基本原則。前者對反黑刑法立法的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即反黑斗爭必須在依法的前提下進行。后二者對于反黑刑事司法也提出要求,不論誰只要屬于黑惡勢力,從事黑惡勢力犯罪活動,都應當予以打擊。同時,在刑罰的適用上,也不能突破現有有效刑法規定予以嚴厲打擊,應當通過刑法立法科學、合理地對疏漏之處予以完善。
三是在刑法典分則當中,一方面,將類罪名“反革命罪”修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罪名減為12個,罪狀表述更加與時俱進,符合實踐需求;另一方面,擴大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分解“流氓罪”,對1997年之前頒布的單行刑法的內容進行移植吸收。[1]參見劉守芬:《關于“79刑法”與“97刑法”若干問題的比較》,載《中外法學》1997年第3期。至此,我國的反黑刑法罪名體系更加的科學、完善,對于反黑刑事司法尤其是罪名的正確理解與高效適用都起到重要的依據和指導的作用。
此次刑法典的全面修訂是一次整體性、結構性、系統性的全面完善,我國的刑法立法從根本結構和理念上趨于穩定。我國反黑刑法立法也隨著統一和相對完備的刑法典的生效實施而逐漸走向統一、穩定階段。此后的反黑刑法立法,將不會再出現大規模的全面修訂完善,更加不會出現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嚴打”時期反黑刑法立法極度活躍的現象,犯罪化趨勢也將逐步實現相對穩定,這也是我國刑法發展逐漸理性與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及其當然結果。
(三)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全面穩定發展階段
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迅速,前期的反黑斗爭效果顯著。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也呈現出隱蔽性特征,如違法犯罪手段網絡化與信息化、披上合法外衣——“漂白身份”、拉攏政權中的腐敗分子充當“保護傘”、極端惡性暴力犯罪活動下降以及黑惡勢力犯罪“軟暴力”傾向等等,這些突出的新問題對反黑刑法立法提出新的嚴峻挑戰。與此同時,經歷了對1997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訂,我國的刑法體系總體上也趨于完善,刑法完善方式以刑法修正案模式為主導,進入成熟穩定發展階段。對刑法規范進行司法適用解釋也成為刑事司法正確、高效開展的重要前提。在此種背景下,我國反黑刑法立法的完善也進入了修正案與司法解釋相結合的時期。從1997年刑法實施至今,我國總共通過10個刑法修正案,其中與反黑直接關聯的主要涉及4個刑法修正案:
其一,《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6月29日實施)。涉及的內容主要包括:在刑法第303條新增一款,增設開設賭場罪;完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主要是增加行為對象、兜底性行為方式條款以及情節嚴重的法定刑;完善洗錢罪的上游犯罪,新增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詐騙犯罪等三類上游犯罪。
其二,《刑法修正案(七)》(2009年2月28日實施)。涉及的內容主要是完善綁架罪,增加綁架致人死亡、殺害被綁架人的行為方式及絕對確定的死刑法定刑,并且增加罰金刑。綁架殺人犯罪曾經是黑惡勢力犯罪集團滿足其非法要求的重要途徑,完善綁架罪的客觀行為方式并加重刑罰,有利于增強打擊懲治綁架犯罪活動的刑法力度。
其三,《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5月1日實施)。涉及的內容主要是在總則當中新設限制減刑制度,將“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新增為不適用緩刑的對象,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納入特殊累犯范圍,將符合一定宣告刑的“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適用不得假釋的規定;在分則中主要是完善走私罪、強迫交易罪、敲詐勒索罪、尋釁滋事罪,提高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法定刑并明確其法律特征,[1]我國首次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特征進行明確界定是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完善協助組織賣淫罪以及完善傳授犯罪方法罪的法定刑。
其四,《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11月1日實施)。涉及的內容包括:完善危險駕駛罪(飆車入刑)、搶奪罪(多次搶奪)、妨害公務罪(暴力襲警入刑)、綁架罪(故意傷害被綁架人),新增擾亂國家機關秩序罪和組織、資助非法聚集罪,完善破壞法律實施罪的法定刑及數罪并罰規定,完善毒品犯罪行為方式規定及其法定刑,完善組織賣淫罪、強迫賣淫罪、協助組織賣淫罪。
通過以上系列刑法修正涉及的反黑刑法規范修改來看,犯罪罪名體系的完善主要是增加行為方式,提高法定刑,新增罪名極少。在修改的頻率上,最短間隔2年2個月,最長間隔4年6個月;在通過及生效實施時間上,前兩者為公布之日起生效實施,后兩者由于修改條文較多,為隔時生效實施。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我國刑法現代化進程中的理性犯罪化的趨勢。另一方面,伴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開展,在刑法依據尤其是罪名體系及刑罰制度已經相對完善的情形下,如何正確理解、高效適用相關刑事政策文件與刑法規范成為新時代反黑刑法立法的重要內容。為了提高“掃黑除惡”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實現預定目標和成效,兩高兩部于2018年1月出臺《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總體上強調依法、準確、高效、有力懲處黑惡勢力犯罪,要求寬嚴相濟、寬嚴有據、罰當其罪。具體而言,一方面,更加深入、全面對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行為方式的認定作出更加明確、細致的規定;另一方面對惡勢力及其犯罪集團、利用軟暴力實施犯罪、非法放貸討債、“保護傘”等突出問題提出意見。此外,還提出依法處置涉案財產,徹底鏟除黑惡勢力的經濟基礎。為進一步扎實開展“掃黑除惡”斗爭,2019年4月兩高兩部連續出臺四個聯合司法解釋,[2]詳細內容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簡稱《意見一》)、《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簡稱《意見二》)、《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簡稱《意見三》)以及《關于辦理黑惡勢力刑事案件中財產處置若干問題的意見》(簡稱《意見四》)。細化2018年的《指導意見》的要求,加強“掃黑除惡”斗爭的法律理解與適用,防止人為降低或拔高黑惡勢力犯罪的認定標準。
從1983年“嚴打”到“掃黑除惡”,我國反黑刑法立法發展歷時四十載,經歷了立法政策從單一從嚴到寬嚴相濟、立法態勢從應急活躍到常態穩定、立法內容從服務于精準打擊到全面完善與加強司法適用并重的歷史變遷。這表明我國的反黑刑法立法不僅在提供反黑刑法依據上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并且也更加在順應、促進我國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產生著積極影響。
二、反黑刑法立法四十年之基本內容
反黑刑法立法發展變化的四十年是我國總體刑法立法發展的縮影,是在反黑社會治理實踐及反黑刑事政策影響下反黑刑法立法的自我完善,反黑斗爭得到法治化保障,依法反黑成效顯著。在這一過程當中,每一個重要階段的反黑刑法立法都有其特定背景下的突出貢獻,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初步形成反黑刑法立法罪名體系及刑罰結構
我國1979年制定的刑法典是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下的緊急立法。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其在權威性和統一性上的積極作用不言而喻。但內容上的不完善在司法實踐當中很快凸顯,這也是促使其后頻繁制定通過單行刑法規范的重要原因。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反黑刑法立法完善的方向也應當是著眼于罪名體系和刑罰體系的不斷完善。
一是罪名體系問題。1979年刑法分則部分共有8章,104個條文,而在罪名數量上,根據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的《關于適用刑法分則罪名的初步意見》,刑法分則有罪名8類,共128個具體罪名,[1]參見徐偉:《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刑法結構的動態走勢和變化規律》,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03期。具體罪名數量分布為:反革命罪20個、危害公共安全罪20個、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15個、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23個、侵犯財產罪9個、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26個、妨害婚姻、家庭罪6個以及瀆職罪9個。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反黑罪名適用標準及體系。但我們認為,初期反黑罪名體系適宜以作為反黑開始標志的1983年“嚴打”為判斷標準。具體而言,根據1983年9月2日通過的《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當時反黑涉及條文包括第一章反革命罪中第99條、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第112條、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中第134條、第140條、第141條以及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第160條、第169條。同時,還新增1個條文,即傳授犯罪方法罪,共計8個條文、9個罪名。打擊對象涵蓋流氓犯罪、涉槍涉爆犯罪、拐賣人口犯罪、故意傷害犯罪、利用會道門、封建迷信反革命犯罪、引誘、容留、強迫婦女賣淫以及傳授犯罪方法,這些犯罪的共同特征是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擾亂社會秩序。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反黑并非僅僅適用前述9個罪名,只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需要重點治理這幾類犯罪。在1983年之后,由單行刑法新增的罪名共101個,其中直接涉及反黑的罪名新增21個,[2]參見劉仁文主編:《廢止勞動教養后的刑法結構完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版,第266—267頁。文中指出1979年通過單行刑法的刑法罪名新增情況:1983年新增罪名1個,1988年新增罪名13個,1990年新增罪名15個,1991年新增罪名8個,1992年新增罪名5個,1993年新增罪名12個,1994年新增罪名9個,1995年新增罪名39個。其中,1990年3個單行刑法中與反黑沒有直接關聯的罪名1個(侮辱國旗、國徽罪)、1991年3個單行刑法中與反黑沒有直接關聯的罪名1個(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罪)。反黑的內容主要包括涉淫穢物品犯罪、毒品犯罪、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犯罪以及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犯罪。至1997年全面修訂刑法,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反黑司法適用罪名體系。
二是刑罰體系問題。這里主要是指刑罰的輕重結構。1979年刑法頒行后的單行刑法尤其是直接與反黑相關的,其總體趨勢體現“嚴打”精神,大幅提高有關犯罪的刑罰幅度,以符合從嚴從重的嚴懲要求。尤其是作為1983年開始“嚴打”的標志——《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其內容主要是對于突出的9種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明確要求可以在法定最高刑以上判處刑罰,直至死刑。也就是說可以突破當時刑法典總則規定的有期徒刑最高15年的法定刑罰幅度。在其后直接與反黑相關的5個單行刑法中所涉及的罪名,與1979年的相關或相同罪名相比,也大幅提高了刑罰的幅度,如刑法第170條的罪名及行為方式得到豐富,并將最高法定刑提高至死刑(原最高刑為3年有期徒刑),還增加刑罰幅度(10年有期徒刑)、刑罰種類(沒收財產)以及從重處罰的情形;刑法第171條的罪名及行為方式得到豐富,并提高其最高法定刑至死刑(原最高刑為5年有期徒刑),增加有關毒品罪名的刑罰幅度(7年有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刑法第141條的罪名及行為方式得到豐富,并提高其最高法定刑至死刑,嚴懲拐賣婦女、兒童過程中的犯罪行為,包括收買行為、強奸行為、故意傷害行為等以及國家工作人員解救過程中的失職行為;刑法第140條、第169條的罪名及行為方式得到豐富,并提高其最高法定刑至死刑。此外,還嚴懲相關的協助行為、單位犯罪行為。[1]詳細內容參見:1983年9月2日《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1990年12月28日《關于懲治走私、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于禁毒的決定》、1991年9月4日《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通過這一系列的刑法立法完善,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刑法典罪名及行為方式單一、刑罰輕重結構失衡(普遍過輕)的問題,滿足了當時反黑刑事司法實踐對于法律依據的迫切需要,保證了“嚴打”在法治化的軌道上進行。
概言之,我國反黑刑法立法四十年第一階段的的貢獻性發展就是完善了罪名體系、豐富了行為方式、調整了刑罰輕重結構,使反黑刑法規范適用依據更加符合司法實踐要求,為將來反黑刑法立法的繼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實際上,在其他類型犯罪的刑法立法上,也經歷著同樣的根本性改變,總體上使得我國的刑法規范體系更加科學、合理、全面,化解了1979年刑法結構和內容不完善帶來的司法適用困境,為后來1997年刑法典的全面修改做好了理論與實踐上的準備。
(二)明確界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法律特征
至1997年刑法典進行全面修訂前,我國的反黑刑法立法及司法已歷時近十五年,但并未對反黑中的核心要素“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法律界定,而是以具體犯罪行為的嚴重危害性——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為衡量標準開展反黑司法。在1997年對刑法典進行全面修訂時,首次使用了“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概念,在罪狀描述中將其表述為“……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但并沒有明確界定其法律特征。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反黑當中對于涉黑犯罪活動的犯罪主體的判斷,影響反黑罪名適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2年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明確界定,要求在對其進行認定時必須同時滿足四個條件:其一,組織形式特征。即人數眾多,骨干成員基本固定,組織者、領導者明確。對于人數眾多的理解,由于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本質上是一種犯罪集團,根據刑法總則對犯罪集團的相關規定,應當是三人及以上。其二,犯罪動機特征。一方面是經濟性犯罪動機。即通過違法犯罪活動獲取經濟利益,謀取非法經濟利益也成為維持組織運作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是非經濟性犯罪動機。即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這二者之間往往是有交叉的,但也不排除僅僅存在非經濟性目的。其三,危害性特征。即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本質乃是對市民社會內部秩序的嚴重破壞,其本身也是市民社會的一種異化形態。需要強調指出的是,2018年1月兩高兩部出臺了《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進一步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本身及其相關罪名的認定標準做出了更加明確的界定。
界定“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法律特征,對于防止和減少人為降低或拔高認定涉黑犯罪的標準意義重大。在進行法律界定前,反黑司法實際上更多的依賴“嚴打”刑事政策以及單行刑法對于個別化犯罪類型的規定。因而,極易陷入“運動式”反黑司法,將不符合反黑本質的罪名進行“反黑化”適用,從而擴大了嚴懲的打擊面。所以,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法律界定,不僅可以明確其判斷標準,更加能夠理解涉黑集團的本質,以區別于其他類型的集團犯罪。這是反黑刑法立法取得的第二個階段性的重要發展,在反黑罪名體系及刑罰輕重結構完善的基礎上,為反黑司法的開展進一步加強了法治化保障。同時,也為后來對“惡勢力、惡勢力犯罪集團”的法律界定提供了指引和寶貴經驗。
(三)統一“惡勢力違法犯罪組織”的認定標準
二十一世紀初以來,“打黑除惡”專項斗爭持續進行,成效顯著。同時,反黑也面臨著新情況、新問題,如黑社會性質組織及犯罪隱蔽性增強、惡勢力及其犯罪集團活躍、犯罪手段“軟暴力”化等等。隨著“掃黑除惡”斗爭的開展,實現壓倒性勝利已成為新時代反黑的根本任務。為了確保依法、全面、深入開展“掃黑除惡”,兩高兩部出臺聯合司法解釋規范惡勢力及其犯罪集團的認定標準。將惡勢力內涵及特征法定化也是反黑刑法立法發展過程中取得的重要進展。
根據兩高兩部頒布的《指導意見》以及《意見一》,惡勢力犯罪組織應當同時符合下列特征:(1)組織形式特征。三人以上,經常糾集在一起,糾集者和成員都相對固定。(2)犯罪動機特征。惡勢力實施犯罪活動的動機往往是為非作惡、欺壓百姓,但并不排除其中摻雜了謀取經濟利益的動機。(3)客觀行為特征。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區域或行業內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違法行為不能因為量的積累而認定為犯罪行為。(4)社會危害性特征。擾亂經濟秩序、社會生活秩序,造成較為惡劣的社會影響。在認定過程中對于這四個特征的把握,應當首先考察組織形式特征,再結合其他三個特征,以避免將無組織的單個行為人實施的相關違法犯罪活動認定為惡勢力違法犯罪。
同時,《指導意見》還明確列舉惡勢力主要從事的違法犯罪活動類型,主要包括強迫交易、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敲詐勒索、故意毀壞財物、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同時還可能伴隨實施開設賭場、組織賣淫、強迫賣淫、販賣毒品、運輸毒品、制造毒品、搶劫、搶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以及聚眾“打砸搶”。當然,要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還需要同時滿足犯罪集團的法定條件。此外,《意見三》還對當前頻繁發生的“軟暴力”進行法律界定。可見,新時代的反黑刑法立法更加強調認定標準的細化、可操作性,與時俱進,以更好的服務于反黑刑事司法實踐。此外,還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雖然統一“惡勢力違法犯罪組織”是我國反黑刑法立法過程當中的重要發展,但并不贊同以司法解釋的方式來對相關概念“立法”,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將在本文下一部分詳細開展論述。
三、反黑刑法立法之反思與完善建議
反黑刑法立法四十年的發展是我國1983年以來反黑斗爭持續法治化的重要體現。這四十年我國反黑刑法立法經歷了不同時期的歷史變遷,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發展成就,反黑的法治化水平不斷提高。但也應當看到,反黑刑法立法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需要我們去正視并加以完善,以確保新時代反黑斗爭贏得壓倒性勝利。
(一)明確反黑立法權限并豐富立法模式
反黑刑法立法涉及犯罪與刑罰問題,屬于國家立法權的范疇,在立法權限的劃分上,我國《憲法》做了詳細規定。其中,第62條第(三)項規定,制定和修改包括刑事法律在內的基本法律是全國人大的法定職權。而根據第67條(二)、(三)、(四)項的規定,在法律制定和修改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定職權是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限對基本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解釋法律(也稱立法解釋)。1979年刑法制定時并未規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含義、認定標準及相關罪名,全國人大1997年對其進行全面修訂時,在第294條第1款當中對“黑社會性質組織”進行了界定,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又于2002年以立法解釋的形式對其特征加以更加明確、具體的解釋。可見,我國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犯罪的刑法立法符合憲法關于立法權限的規定。
但是,在“惡勢力”“惡勢力犯罪集團”等概念界定的立法問題上則出現了不同的走向。盡管從“嚴打”開始,惡勢力及其違法犯罪就是懲治的重點,卻并沒有對其概念進行法律標準上的界定。直到2018年初“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以來,兩高兩部先后在《指導意見》《意見一》中對“惡勢力”“惡勢力犯罪集團”的特征進行了詳細的法律標準規范。從法律性質上而言,這兩份文件屬于聯合司法解釋。但是從內容上來看,“惡勢力”“惡勢力犯罪集團”在刑法立法當中并無規定,作為對審判工作、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進行解釋的司法解釋,[1]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1年通過《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其中明確了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的解釋內容、解釋主體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其本質是在尊重上位法基本原則和規定的前提下對已有法律的適用進行解釋和細化。顯然,以聯合司法解釋的方式來界定“惡勢力”“惡勢力犯罪集團”的含義及特征,存在著司法解釋立法化,僭越立法權,架空刑法立法的根本缺陷。此外,刑法立法完善方式單一的問題,也存在于反黑立法之中。
由此看來,明確立法權限,豐富立法模式是未來我國反黑刑法立法應當重點完善的方向之一。具體而言,在立法權限上,應當明確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及兩高兩部在反黑刑法立法及司法當中的角色與權限職能定位,從根本上理順反黑刑法立法中各主體的權限范圍,以利于整個刑法體系的發展完善。在立法模式上,至少應該采取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其制定主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僅法律位階高,具有權威性,也能夠相對保持刑法典的穩定性和統一性、靈活性。但同樣也存在著架空全國人大立法權的根本缺陷,盡管這種缺陷在短期內所造成的不利影響還不明顯,還會帶來刑法適用的混亂。因此,最佳立法模式應當是單行刑法。其優點在于單行刑法可以分擔刑法典罪名,減輕刑法典壓力,從整體上有利于刑法典階段性完善(全面修訂),符合刑法淵源多樣化的刑法現代化的世界潮流。此外,單行刑法的立法主體宜改為全國人大。[1]參見姚建龍、林需需:《多樣化刑法淵源之再提倡——對以修正案為修改刑法唯一方式的反思》,載《河南警察學院學報》2018年06期。
(二)統一涉黑惡犯罪的罪名適用標準
反黑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及刑事政策用語,在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領域主要表現為反黑罪名體系的完善與適用。其中,重中之重又是從立法上如何確立反黑罪名適用標準,即哪些犯罪可以被認定為黑惡犯罪活動從而加以從嚴懲處。其目的是確保反黑在司法實踐當中不被人為擴大化,這乃是新時代反黑刑法立法的重要使命。
在“嚴打”及“打黑除惡”階段,并沒有對反黑罪名的適用確立相對統一的標準,從實踐來看,反黑打擊的對象包括流氓惡勢力團伙犯罪、故意傷害、故意殺人、販賣人口(或者拐賣婦女兒童)、涉槍涉爆犯罪、搶劫、毒品犯罪、反革命活動、黑社會性質組織集團犯罪、引誘、容留、強迫婦女賣淫、電信詐騙等犯罪。[2]“嚴打”時期《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重點列舉了“嚴打”打擊的對象,但當時并沒有“黑社會性質組織”以及“惡勢力犯罪集團”等概念;“打黑除惡”時期雖然在1997年刑法以及2002年的立法解釋中明確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概念及特征,但并沒有正式文件統一明確哪些犯罪屬于黑惡勢力犯罪。“掃黑除惡”階段,兩高兩部則明確在《意見一》當中列舉了惡勢力主要從事的違法犯罪活動以及可能附隨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盡管并不贊同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來予以明確,但為了防止司法過程中人為降低或抬高認定標準而相對統一標準的做法值得提倡。
為何要統一涉黑惡犯罪的罪名適用標準,實際上是將反黑罪名與普通罪名加以區別而對黑惡勢力犯罪從嚴懲處。對于適用于黑惡勢力犯罪的罪名有哪些?其認定標準是什么?我們認為應當從兩個層面去探討:一是反黑對象本身的罪名適用。就黑社會性質組織而言,其本身已經被犯罪化,在刑法分則中共涉及三個罪名,其中主要是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而惡勢力犯罪集團本身并沒有被犯罪化,相應地反黑的內容主要則是從嚴懲惡勢力所從事的一系列犯罪活動。二是反黑對象所從事的犯罪活動。也就是黑社會性質組織以及惡勢力犯罪集團所從事的犯罪活動。只要是這些組織所從事的犯罪都應當加以從嚴懲處,并不需要區分其犯罪目的是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還是單純的謀取經濟利益。在這一問題上的區分標準有別于個體行為人所從事的犯罪活動應當嚴格分辨犯罪動機,但同時又存在一個悖論:獨立個體行為人能否被認定為黑惡勢力?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此,反黑的對象不僅包括組織,還包括個體,反黑刑事司法過程中對此必須要嚴格區分。
此外,在未來反黑刑法立法發展過程中,還應當注意以下三個問題:其一,反黑范圍的確定標準問題。是以主體是否屬于黑惡勢力,還是以犯罪行為本身。對此,應當以主體標準為主,犯罪行為本身為輔。若以犯罪行為本身是否屬于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進行判斷,則反黑的范圍相當狹窄,不利于打擊黑惡勢力犯罪集團。實際上,只要是能夠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或者是惡勢力犯罪集團,那么,其實施的一系列犯罪活動都應當作為反黑的范圍。其二,“口袋罪”問題。“口袋罪”被詬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內涵模糊,對認定罪與非罪產生困擾,在反黑當中最為突出的“口袋罪”罪名便是尋釁滋事罪。我國刑法將尋釁滋事罪置于章罪名“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下的“擾亂公共秩序罪”之下,第293條第1款第(三)項將其客觀行為方式之一描述為:“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其中,對于“起哄鬧事”的界定標準是尋釁滋事罪成為“口袋罪”的癥結所在。因此,在反黑司法實踐中應當嚴格區分事出有因的打鬧行為與無事生非的尋釁滋事。其三,黑社會性質組織與惡勢力犯罪集團的區分問題。刑法第294條第5款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特征描述與《意見一》對“惡勢力犯罪集團”的特征描述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犯罪動機、行為手段等,將后者認定為前者形成前的發展階段,也即區別主要在社會危害的嚴重性程度上。但是,這一區別的把握也存在很大的主觀性。因此,從刑法立法或者司法解釋層面對二者進行區分標準的統一規范也有極大意義。
(三)完善懲治惡黑勢力犯罪的刑罰制度
正確認定罪名,合理運用刑罰是反黑的兩個重要環節,反黑刑法立法的任務就是要為此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對于反黑刑罰制度的立法完善方向主要是從總則刑罰運用制度和分則相關罪名的刑罰配置。
黑社會性質組織有相關的獨立罪名,在刑罰制度的完善上較之惡勢力犯罪集團更加的容易操作。早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就對懲治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犯罪行為的刑罰進行完善,主要包括對有組織暴力性犯罪限制減刑、將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納入特殊累犯范疇、對累犯、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適用減刑、對累犯、有組織暴力性犯罪不適用假釋以及對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配置罰金刑。同時,還在分則中對黑社會性質組織慣常性從事的犯罪進行了立法完善,如走私、強迫交易、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等。
隨著新時代“掃黑除惡”斗爭的開展,在完善并正確適用罪名的前提下,科學、合理配刑及刑罰運用是反黑的重點。兩高兩部在《指導意見》中重申了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懲處的刑罰裁量規定,并且強調對于惡勢力犯罪案件要充分運用共同犯罪和犯罪集團有關刑法規定,依法從嚴懲處。在《意見一》中進一步指出,要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指導下,正確運用法律規定加大懲處力度,嚴格掌握緩刑、減刑、假釋,嚴格掌握保外就醫適用條件,充分利用資格刑、財產刑、職業禁止等法律手段。由此可見,對于惡勢力犯罪集團的刑罰運用基本上與黑社會性質組織一致。但存在的根本不足是,“惡勢力犯罪集團”這一概念并沒有刑法化。因此,未來刑法應當將“惡勢力犯罪集團”的概念納入刑法典,不僅有利于體系性完善反黑的刑罰制度,也有利于反黑的長效機制建立。當然,就目前而言,并沒有必要將惡勢力違法犯罪組織本身予以犯罪化,較為合理的做法是以司法解釋的方式對黑社會性質組織與惡勢力犯罪集團二者進行明確區分,以更好指導司法實踐。
由于惡勢力犯罪集團并未得到刑法的確認,并且兩高兩部在《意見一》中明確指出,惡勢力犯罪集團主要從事的犯罪是強迫交易罪、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敲詐勒索罪、故意毀壞財物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因此,對于其刑罰制度的完善,主要應當從刑法分則中的上述罪名入手。具體而言,運用資格刑、財產剝奪惡勢力犯罪集團的犯罪能力和影響范圍。通過梳理發現,在《意見一》列舉的7個主要犯罪罪名當中,配置罰金刑的有4個,并且,存在質疑的是尋釁滋事罪配置了罰金刑,而聚眾斗毆罪卻沒有配置。對于資格刑而言,刑法第56條規定了應當剝奪政治權利與可以剝奪政治權利兩種類型,前者的配刑對象是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后者的配刑對象是故意殺人、強奸、放火、爆炸、投毒、搶劫等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分子,而前述罪名均未配置資格刑。而在實踐當中,惡勢力犯罪集團已經滲透到基層政權組織,對惡勢力犯罪集團適用資格刑將是未來反黑刑法立法完善的重要方向之一。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單純對《意見一》中列舉的系列罪名單獨配置資格刑不具有可行性,亦會造成刑法體系的冗雜、混亂,相對合理的選擇還是將“惡勢力犯罪集團”刑法化之后,在總則當中明確對其資格刑的配置。
結語
刑法立法的發展取決于不同階段經濟社會狀況,也離不開立法理念、立法技術的進步。我國反黑刑法立法歷經四十年,誕生于“嚴打”時期,發展于“打黑除惡”時期,尤其是新時代的“掃黑除惡”時期,盡管是以準立法性質的司法解釋形式。面對新時代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逐步深入,刑法立法應當有所作為,為“掃黑除惡”以及今后還可能的反黑斗爭提供更加完善的刑法依據及刑罰手段。當然,這并非是要提倡大范圍地擴大犯罪圈亦或是嚴苛刑罰,其目的乃是要以刑法立法為根本依托建立法治化反黑的長效機制。
需要強調的是,反黑并非圄于懲治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以及惡勢力組織犯罪,更要治理相關犯罪,加強社會綜合治理,提升市民社會自治能力。其中,就刑法立法而言,應當進一步完善懲治及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依據,以嚴懲黑惡勢力“保護傘”,鏟除黑惡勢力滋生壯大的溫床。當然,也包括完善對行賄犯罪的立法。就當前的刑法立法而言,基本上能夠滿足依法反黑的需要。對于未來的反黑刑法立法,一方面,應當考慮反黑刑法體系自身的進一步精細化、系統化;另則,需要兼顧我國整體刑法體系的協調性,順應刑法現代化的發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