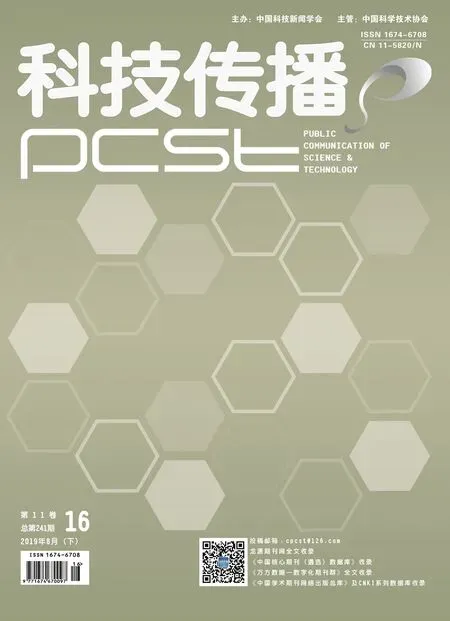新媒體功能拓展:中老年媒介素養的價值重構
曲洪圓
根據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8 年12 月,我國網民規模達8.29 億,手機網民規模達8.17 億[1]。隨著互聯網應用的持續滲透以及中國人口老齡化步伐的加快,中老年用戶的數量也在不斷攀升。但由于傳統媒體在中老年受眾群中根基穩固以及對新媒介接觸的滯后性造成傳受雙方的信息鴻溝也日趨明顯,重構媒介融合時期的中老年的媒介素養對于當前新媒體功能的拓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1 中老年新媒體媒介素養問題的提出
媒介素養的定義是伴隨著媒介自身發展而不斷完善充實的,一般指人對媒介的認知能力。由于新媒介的交互性、即時性、海量性等性質和特點,對用戶的媒介素養提出了更深刻的要求。從年齡結構來看,截至2018 年底,40 ~49 歲中年網民群體占比15.6%;50 歲及以上網民比例為12.5%[2],未來中老年網民占比還會持續增長。由于中老年媒介認知的局限,很容易誤讀或者曲解碎片化的信息,這就導致中老年用戶群成為推動網絡詐騙、網絡謠言等信息流通的主要陣地。同時,新媒體虛擬社交方式也打破了傳統社交的局限,“一鍵轉發”的即時性功能在提升傳播效率的同時也給更多的不實信息帶來生存空間,基于中老年用戶市場的巨大潛力以及新媒體語境下價值觀念的滯后,重新建構新媒體環境下中老年用戶媒介素養概念迫在眉睫。
2 新媒體語境下中老年媒介素養現狀
媒介融合驅動下的視聽傳播效率之高、普及程度之深,使中老年媒介素養在逐年提升,但仍未達到理想水平。
2.1 互聯網使用時間相對較少,傳統媒介地位依然占優勢
統計數據顯示中老年使用互聯網時間的分配比例仍然很低,僅有約1/5 的中老年人會在閑暇時間使用新媒體[3]。從客觀角度來看,中老年每天接觸新媒介的時間有限,體育鍛煉、打掃家務等繁雜的事情壓縮了其使用互聯網的時間。而且在城市中有48.2%的中老年人由于難度太大而沒有使用互聯網。從主觀角度來看,中老年群體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遠不及青年一代,封閉的思想使中老年人對新媒體產生陌生感與戒備心理,這就導致新媒體很難在中老年群體普及。相對于新媒體而言,傳統媒體更容易獲得中老年人的青睞。由于中老年人身體機能的退化,對于可視聽化的要求更高。新媒介輸出內容大多以小屏的方式呈現,對于中老年人視聽體驗而言并不具有優勢,中老年人成為傳統媒體受眾主力軍也就不足為奇。另外民生新聞、天氣情況、養生講座等,而這些內容都是新媒體的視野盲區。傳統媒體在中老年群體中的貼近性、普適性是當前新媒體無法取代的。
2.2 智能媒介應用單一,認知能力相對薄弱
當前,中老年使用移動智能設備應用程序還比較單一,主要以通信功能的應用居多。根據數據顯示,15 ~19 歲網民人均手機App 人均數量為59 個,而50 ~59 歲網民人均31 個,60 歲以上則更少。這說明中老年網民獲取信息的應用不夠多元,網絡空間利用率不夠充分。從外部環境來看,媒介融合效果初顯,堅守在傳統媒體陣營的中老年受眾面對新媒體的“撩撥”之后自然有接近新媒體的心理欲望。但與此同時,新媒介并不及傳統媒介簡單、易操作,無人教授與信息不對稱等擺在中老年面前的鴻溝,反而造成了與新媒體的疏離。而對于信息的篩選、判斷能力的不足以及從眾心理是影響中老年正確媒介向度的禍因。許多UGC 生產的內容價值導向錯誤會影響中老年人的價值判斷,掌握新媒介手段之后的技術濫用還會助長不良信息的流通態勢。
2.3 身份轉向困難,觀念亟待升級
中老年智能媒介應用中社交通訊與影音直播等App 的安裝數量要遠大于閱讀學習或者應用程序。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在人口紅利下瓜分市場的規模已逐漸穩定,那么稀缺性內容就會成為接下來互聯網空間發展的迫切需要。從這一點來看,中老年新媒介使用現存兩個矛盾,第一個是信息升級與中老年認知僵化的矛盾;第二個是受眾向內容生產者身份的轉變與中老年群體生產力與認知能力不足的矛盾。較之于傳統媒體,新媒體對用戶參與程度提出更高要求,技術賦能給傳受雙方的雙向互動提供了更多可能。在轉型升級中,中老年用戶群需要被給予更多的關注與幫助,而對于其自身而言,掙脫傳統消費觀念與媒介意識的束縛才有可能完成從“受眾”向“用戶”的身份轉變。
3 順應媒介環境發展,提升中老年媒介素養
3.1 發揮主持人話語權力優勢,因勢利導推進媒介融合進程
當前,傳統媒體依然是中老年依賴的信息載體。傳統媒體所樹立起的權威性無疑是“圈粉”的重要利器。傳統媒體節目多年樹立起的品牌優勢也是持續吸引中老年追隨的軟實力。主持人是傳播活動中的重要一環,對受眾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會有深刻的影響,“主持人話語的黏合功能讓受眾在了解他人的同時感覺到自己與社會和世界的相聯。”節目主持人作為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的聯結點自然是絕佳的引領受眾的角色,要因勢利導、循序漸進地引領中老年從“受眾”向“用戶”的跨場域交流。
3.2 降低準入門檻,構建積極媒介觀念
對于中老年而言,思維與行動都不及青年一代敏捷,微信、QQ 之所以成為中老年新媒介社交的主要應用,就是因其門檻低、操作簡單。根據對城市中老年使用互聯網困難原因的調查數據顯示,認為操作難度大的中老年比例占據被調查人數的41.3%,可見操作難度大直接影響到了中老年互聯網的使用。技術賦能在改變傳播生態的同時還應注意程序開發的公平性、適用性、易操作性,要充分考慮中老年用戶的現實困難,降低入門的門檻,才能釋放中老年使用新媒介的活力。
其次,由于中老年文化層次的不同也需要來自家庭的援助,作為子女應該適當予以幫助,更要積極引導父母樹立正確的媒介觀。缺少批判意識,對媒介信息全盤接受,看待問題片面化、極端化,這也是甄別能力缺失的重要表現。,從社會幫助角度,社區可以發揮積極的宣傳作用,普及新媒體基本常識;老年大學可以開設新媒體課堂等,為中老年樹立正確的媒介素養觀助力。
3.3 完善立法制度,構建綠色媒體環境
在互聯網思維逐步形成的時代,用戶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使信息的傳播效率與利用率都獲得最大化,在體量與效率同步提升的同時,也為不良信息提供了滋長的空間,根據調查發現,中老年更愿意在自媒體平臺閱讀、轉發公眾號文章。而自媒體初始生產者由于目的、見識、文化程度的參差不齊,推送的內容難免會出現錯漏,往往呈現出一家之言、一己之見。而由于中老年正處在從傳統媒體向新媒體轉型的過渡時期,往往會將對傳統媒體的依賴、信任“移植”到新媒體中,這就為不良信息的傳播在中老年受眾群中開辟了渠道。要重視信息源頭,實行更為嚴謹的新媒體行業規制,技術賦能為大眾帶來更多的話語空間,而話語權力的濫用會打破媒介生態環境的平衡,當前完善規制要從兩個維度著手,一是劃分邊界,對網絡空間的言論和行為進行界定;二是確立規范,明確政府、服務商、網民等互聯網主體的義務與權力。信息源頭的純潔性以及傳播過程中的合理性都將是立法對重構用戶媒介素養的重要保證。
4 結語
媒介是聯系國家與人民的紐帶、是文明延續的載體。而媒介素養是衡量人民幸福感的隱性指數,中老年的媒介素養也關系到晚年生活質量的高低。身處媒介融合時代的中老年群體需要重新審視自身掌握與運用媒介的能力,重新勾勒媒介素養的框架,營造積極健康的媒介環境,拓展新媒體職能、釋放新媒體活力,使中老年更好的融入智能媒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