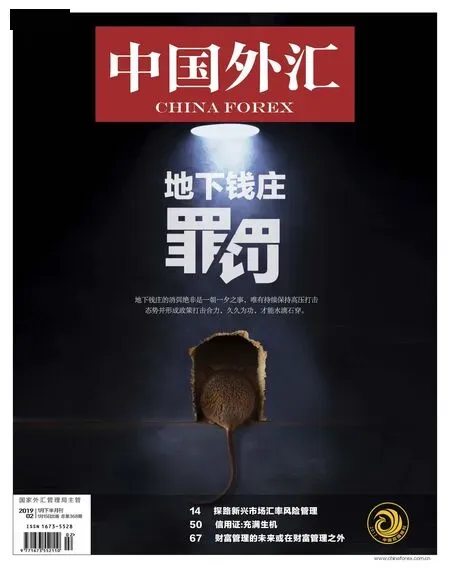資產價格與貨幣的“便宜與昂貴”
2018年資產價格為何全面下跌?這一難題的答案很可能隱藏在貨幣中。廣譜資金價格下降的背面是貨幣貴了、貨幣少了。
根據德意志銀行的統計,2018年以美元計價的全球資產累計負回報的占比高達93%,是1901年有統計以來的第一次,甚至比1929年大蕭條時期還要差。資產負回報簡單地說,就是資產價格出現下降,分析者往往稱之為下跌甚至是暴跌。不過,換個角度,也可以說這些資產的價格較當初更加便宜了。
比如,2017年12月16日購得一枚比特幣需要支付19497美元,而1年后只需要3200美元,便宜了84%。再如,如果不是在IPO的時候購買香港上市的10只“科技獨角獸”股票,而是在2018年年末購買,則平均可以少支付46%的金額。同樣,2018年年末購買一桶布倫特原油比10月高點的時候購買要便宜42%,購買一籃子深圳成分股比1月底高點的時候購買要便宜38%。如果是考慮在北、上、深購買二手房,壞消息是北京和上海的房價還在上升,但深圳年底購入二手房的價格已較4月份便宜8000元,或13%。在2018年8月的數據表明,香港寫字樓租金出現強勁增長;但半年后的數據顯示,全年香港中環的高端寫字樓成交196宗,同比下降45%,特別是12月,僅成交3宗,是2008年以來單月最低成交記錄。
對于資產價格下降這樣一個客觀事實,在資產持有人眼里是價格下跌,暴跌和財富損失;而在貨幣持有人看來是便宜,是投資機會和潛在的盈利。資產價格和貨幣價格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正如我們可以用貨幣多、貨幣便宜來解釋商品價格的全面持續上升(通貨膨脹)一樣,2018年資產價格為何全面下跌這一難題的答案,很可能也隱藏在貨幣中。廣譜資金價格下降的背面是貨幣貴了、貨幣少了。
從全球中心貨幣——美元的角度看,貨幣的確是變昂貴了。2018年美國10年國債收益率平均水平為2.91%,較2017年上升58個BP,較2016年上升108個BP。美國充分就業的經濟基本面和走高的通貨膨脹率,使得市場擔心美聯儲可能較預期的更為“鷹派”。進入2019年,歐洲央行也將開啟貨幣政策正常化的進程。美國和歐元區兩大發達國家央行一起收縮資產負債表,引發市場對“錢緊”和“錢貴”的擔憂。
此外,較為重要的是,2018年中國在雙支柱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下,有效控制了整個社會債務擴張的增長速度,這對全球資產所產生的外溢效應還沒有得到市場分析人士的充分重視。盡管代表資金價格水平的存款類機構質押式7天回購利率從2018年年初2.87%的水平下降到年末2.65%,表明資金面寬松,但信用利差明顯走闊,信用資質不佳的借款人融資難上加難。資金價格之外,收縮顯著的是資金的數量。以最常用的M2增速為例,2011年至2016年的平均增速為13.4%,2017年下降到9.3%,2018年前11個月進一步下降到8.3%。以181萬億元的M2存量計算,少增1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少擴張1.8萬億元的債務。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各個部門不斷加杠桿,抬升宏觀杠桿率對于全球經濟走出金融海嘯的“泥沼”貢獻顯著,同時也與包括比特幣、大宗商品價格、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房價、香港中環的寫字樓租金等廣譜資產價格的上升不無關系。鑒此,中國通過加強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加入到收縮全社會債務增速的行列,對于理解全球領域廣譜資產價格的同時下降至關重要。
展望2019年,來自美國的好消息是,美聯儲在最新的一次議息會后將2019年加息的次數從3次調低到2次;但壞消息是,根據美國利率期貨交易的信息預測,2020年美聯儲可能要降息一次。金融市場認為,美聯儲不可能“走在曲線之前”,即先于經濟基本面的惡化而調整貨幣政策。這也就意味著,美元“貴”和美元“少”的局面還不能迅速緩解。
來自中國的好消息是,從2018年7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后,央行、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等各方積極落實,發揮“幾家抬”合力疏通信用傳導渠道。但考慮到信用擴張與收縮的內生性,在全球金融市場不確定性上升、主要發達國家央行仍然在收縮資產負債表、國內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繼續“去杠桿”、家庭資產負債表面臨修復等諸多約束條件的制約下,國內私人部門的信用擴張能夠如期出現嗎?未來的實踐將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