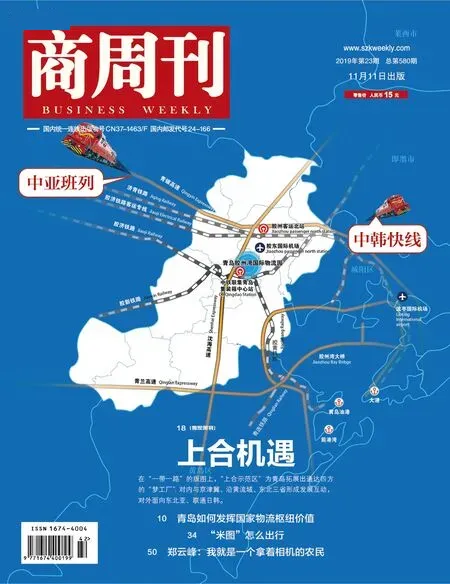騎行虹口
文 / 圖 特邀撰稿 大方無隅
一座城市的底蘊,往往就包含在這些寵辱不驚的細節里。
上海的秋天很通透,早上的陽光也很溫暖,我騎在單車上,清晨的陽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長,和這座城市融為了一體。
上海是我年輕的時候生活過的城市,所以便會有一種自然的喜歡。這座城市的變化快得讓人應接不暇,雖然這里有那么多的高樓大廈,但我還是喜歡能見證時光流轉的深巷弄堂,就像我在尋常的街頭遇到的這家小面館。上海這個城市裝得下大大小小的夢想,而令我難以忘懷的上海老味道就藏在這樣的弄堂里。
我們能夠記得住城市的繁華,常常會因為一些街市。有街就會有市,街道像是城市的血脈,上海更不例外,一條條縱橫交錯的路結成網,把一座城市的細節和記憶織得細細密密的。有些路很張揚,另一些路,則嫻靜安逸,內斂得秀外慧中,這也是低調的奢華。
高大濃密的夾竹桃和暗紅色的清水磚墻,簇擁著街道,人們不緊不慢地從這些尋常的街頭走過,演繹著城市從容不迫的節奏。
我從四川北路拐進寶安路的時候,還在一個尋常的弄堂門口,見到了上海魯迅初級中學的名牌,一座城市的底蘊,往往就包含在這些寵辱不驚的細節里。
沿街的這些里弄才是心目中老上海的感覺,經過山陰路的恒豐里是比較大的里弄,里面是石庫門式的樓房,這處里弄的歷史接近百年了。1927年,羅亦農與周恩來、趙世炎等共同領導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指揮部聯絡點就曾設在此處。歷史風起云涌,故事就發生在這樣的地方,貌似平淡無奇卻又如此與眾不同。
這個早晨給自己選擇的目的地是多倫路,這里曾經留下過許多人文歷史的印痕。
多倫路是上海的文化之路。眾多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化名人,像魯迅、郭沫若、丁玲、茅盾等都曾在此居住,除了文化名人,白崇禧、孔祥熙、湯恩伯這些當年的歷史人物的公館也在這條多倫路上,我們可以從這些有故事的洋房中感受這些名人的氣息,上海的多倫路是獨一無二的。
多倫路原名竇樂安路(Darroch Road),以曾受到清朝光緒皇帝接見的英國傳教士竇樂安命名。街口的牌坊邊上樹起了老路標,還有長衫的先生和小報童的塑雕,讓人回想起那并不久遠的往昔。
即便是一些其貌不揚的房子也是歷史的容器。比如眼前的燕山別墅依然是一處普通的民宅,而這里邊也曾經住過許多有名的人物,除了一些文學名流,張國燾在解放之前也曾經住在這條尋常的弄堂里。

這里的許多建筑,充滿了歷史感,也洋溢著文藝范兒
有些老房子也被改成了海派的私家菜館,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海明威寫巴黎的那本《流動的盛宴》,我騎著單車從這樣的老街上悠然而過,也仿佛是在享受一頓流動的盛宴!
這里的許多建筑,除了充滿歷史感,也洋溢著文藝范兒。
許多曾經在這條街上生活過的名人,如今被做成了雕像,永久地定格在時光里,他們日復一日的在這里凝視著偶然路過的人們,那些平靜的眼神,仿佛可以洞穿時空,鮮活了那些久遠的歲月。
我遇見了瞿秋白,也遇見了柔石。
柔石曾任《語絲》編輯,并與魯迅先生共同創辦“朝花社”,他就義的時候還不滿30歲。和他一起的,還有另外幾張年輕的面孔,只要活著就有意義,就不在乎歲月的老去,即便生命都不復存在,而他們的故事還在曾經生活的城市流傳著。
白崇禧曾經的寓所為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所建,外觀典雅端莊,四根白色的柱子大致是科林斯式的柱頭,總體保護的不錯。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是我國臺灣著名的作家,他曾經在這里度過了一段童年時光,還專門寫過回憶這些舊居的文字,如今這里已經用作了醫院的醫療用房。
街邊的每一棟房子都承載著一些過往,只要你愿意探尋,它便有講也講不完的故事。
多倫路上到處散發著文藝的氣息,我一路下車推行,讀讀墻上或地上那些關于該片區域的事例以及人物介紹,這樣的感覺很愜意。
這里有各種各樣的小博物館和藝術空間,我路過了一棟毛澤東像章館,據說這里邊的像章收藏有幾萬枚呢。
葉圣陶身穿長衫的立像就在路邊,他手中握著書卷,仿佛正要走上講臺。我們的山東老鄉臧克家曾經說過:“溫、良、恭、儉、讓這五個大字是做人的一種美德,我覺得葉老先生身上兼而有之。”
同樣在街邊用平靜的眼神注視著我的,還有郭沫若、茅盾、沈尹默這樣的文人。我忽然間想起了當年去佛羅倫薩的時候了解到的“司湯達綜合征”。當年法國大作家司湯達來到意大利,在佛羅倫薩終日沉醉于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杰作。當他在圣十字教堂見到了米開朗基羅、伽利略和馬基雅維利的陵墓,突然感到心臟劇烈顫動,甚至有些頭暈目眩。醫生診斷這是由于頻繁欣賞藝術珍品使心理過于激動所致,這種因強烈的美感而引發的罕見病癥從此被稱為“司湯達綜合征”。我不知道走在多倫路上的人們會不會因為在這條街上如此密集的名人效應和文化氛圍而有類似的反應?起碼我的內心是有一些激動的。
我在街道轉彎的地方也見到了丁玲的雕像,這是一個少女的形象,我想大致反映的是從湖南老家到上海來的時候的狀態吧,那眼神當中有一些憧憬,也有一些拘謹,分明流露出每個人都有過曾經青澀的青春。
雕像后面應該是一家餐吧,幾個老伯正坐在那邊閑聊,抑揚頓挫的上海話聽上去有幾分親切,這才是生活原本的樣子。
“老電影”咖啡館,是一家以舊電影為特色的主題咖啡吧。卓別林的立像儼然成了這里的門童。門口的招牌上用粉筆寫著一些電影的名字,都是一些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老片子,傳達給我們這個城市許許多多的老故事。
這邊還有一座好看的鐘樓,夕拾鐘樓的名稱取自魯迅先生著名文集《朝花夕拾》。而我在聽到這座鐘樓的名字的時候,腦子里邊反應出的兩個字是“惜時”,漢語就是如此的美妙,同樣的發音居然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這座白色洋樓很搶眼,小樓當中,曾經住過著名的民主人士王造時,“一條多倫路,半座上海城”,這里真是一個臥虎藏龍的地方。
在鴻德書房的門口,我見到了內山完造的塑像,這里并不是內山書店的原址,卻是一段佳話的紀念。內山完造與魯迅先生是摯交,曾數次幫助魯迅先生避難。魯迅那首有名的七律《慣于長夜過春時》就是寫在避難期間。
一個人推著自行走在這街道上,走在一塊塊小石頭鋪砌成的路面上,色彩斑斕的小花點綴著街道,透著一種洋氣,更洋溢著人文的氣息。
永安里通著四川北路,也是有情調的老房子,周恩來和鄧穎超曾在這里居住過。三層的房子掩映在林蔭中,也掩映在時光的深處。與四川路交界的地方也有一處街門,也是西式的,海派的模樣。
四川北路曾經充斥的煙火氣息似乎淡了些,我至今記得在還有饑餓感的大學時代,這條路上的皇上皇西點房飄出來的誘人香味,這是我關于這座城市的青春記憶的一道印痕。
山陰路口的新華書店很懷舊,其實它隔壁的工商銀行更有故事,這才是內山書店的舊址,我遠遠的看見魯迅先生和內山完造先生的浮雕塑像,把那段情誼定格在時光里。
大陸新村是魯迅在上海最后的寓所。這是一片紅磚紅瓦磚木結構的三層里弄房屋,如今已經是住滿了尋常人家。有人騎著電動車拐入弄堂,有人和我一樣騎著單車悠然而過,這里就是一處平平常常的院落,只是門口多掛了一塊魯迅故居的牌子。
門口的山陰路必定是魯迅當年常走的,人們如今稱它為魯迅小道。看到山陰路名,自然聯想到蘭亭和紹興,那里是魯迅的家鄉,那里有茴香豆和烏篷船,那里有社戲也有三味書屋。
弄堂的墻上有魯迅語錄,落款是山二居委,其中一幅上寫的是這樣的話:“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品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這樣的語句現在讀來依然充滿了正能量。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房子是茅盾住過的地方。茅盾三十年曾與魯迅相鄰,關系很密切,經常來往。茅盾在這里住了兩年,寫下了《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
1946年,茅盾夫婦從香港再次來滬,住進和魯迅曾徑的住處相隔的門里,只可惜,魯迅已仙逝十年,兩位老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里,也是里弄住宅。如今弄口墻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瞿秋白也是避難于此,只住了三個月,這短短的三個月里,他竟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的編選并對魯迅作了精辟論述,第一次給予了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戰士”的高度評價。
大陸新村門口的地面上鋪著一塊鑄鐵的銘牌,上面用中英文標注了虹口這個地名,還有一句英文是“The Garden District”,的確,用花園形容這里很貼切,這里彌漫著花園的芬芳和人世間的煙火,更有濃濃的文化氣息在晨光中飄蕩。
街上仍舊是瑣碎的日常,我與人們一起穿城而過,沒人會留意我這樣的過客。就是這樣平平淡淡、從從容容的日子,行跡匆匆而過,耳畔的吳儂軟語充盈飄灑,我騎著單車重逢了老上海,這座歷久彌新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