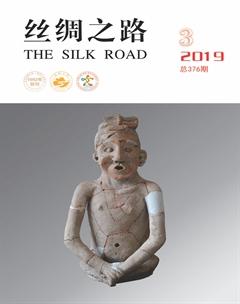讀《禹王書》三嘆
胡瀟 胡秉俊
[摘要] 該文首次發表于2019年第3期《大家》。文章從《禹王書》的宏大敘事、獨具特色的寫作手法及作者銖積寸累、困知勉行的執著三方面入手,探析馮玉雷在長篇小說《禹王書》“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藝術魅力。
[關鍵詞] 《禹王書》;宏大敘事;文化氣場;藝術魅力
[中圖分類號] I04?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1005-3115(2019)03-0118-04
發表在云南出版集團《大家》文學期刊上的《禹王書》是馮玉雷第5部長篇小說。刊發的縮略版8萬多字,只是全書的1/3篇幅。
展開《禹王書》,一種強烈的古老文化氣場撲面而來,似有綿綿不絕的洪荒之力奔涌著。如此,已不能用平時閱讀小說的方式去瀏覽。我們采取讀史書的方法,一邊閱讀一邊做筆記,在沉浸感動之間,穿插著查閱資料印證、辨析一些問題。掩卷回味,感慨萬分,余音繞梁,一詠三嘆。
一、《禹王書》的宏大敘事令人嘆為觀止
《禹王書》是“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大手筆之力作。時間跨度之大,從盤古開天辟地,三皇五帝神話傳說,到禹繼舜位建立夏朝;地域范圍之廣,西至昆侖,東達海濱,北望燕山,南抵南海,居九州環顧四方,乃至輻射西亞、東南亞;人物形象之眾,涉及近百個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所描寫刻畫的人物形象就有倉頡、脩己、夸父、嫘祖、羲和、常羲、黃帝、蚩尤、鯀、山羌(牧羊女)、重華(舜)、華胥、施黯、盤古、姜嫄、后稷、女嬌(女媧)、共工、伯益、皋陶、精衛、樂師夔、啟、義鈞、娥皇、女英、防風、后羿、姮娥(嫦娥)等40多個;故事情節之多,幾乎涵蓋盤古開天辟地、女媧補天、摶土造人、精衛填海、黃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共工怒觸不周山等全部神話傳說;涉及史料之豐富,可以看出《山海經》《尚書》《楚辭》《莊子》《列子》《淮南子》《史記》《左傳》《國語》《禮記》《漢書》等等。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禹王書》的宏大氣象,如劉熙載所論“敘事之學,須貫六經九流之旨;敘事之筆,須備五行四時之氣”。作者心中的小目標應該如《周易》所言“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當我們以現代人的視角審視歷史和傳說時,解讀、結構、重構,批判性思考等諸多方式,究竟該如何把握,這對于作者無疑是一種挑戰和考驗。《禹王書》洋洋大觀,百科全書式的圖景,卻并非簡單排列組合。作者把散見于龐雜圖書資料中的故事和人物,圍繞著大禹和女媧(女嬌)的形象塑造,打通時空精心編織在一起。從材料的選取,到故事情節的展開和銜接,再到人物形象的刻畫和成長,所謂選擇性敘事和想象性敘事在小說中有機統一,充分展示了作者馮玉雷深厚的文化積淀、精心的構思和豐富的想象力。對于這種重構歷史和傳說的文學化敘事,評判標準不能簡單化強調“客觀”“真實”,應該是建立在當代人類認識水平之上的充滿理性光芒的哲學思考。對讀者來說,每個人的領悟建構在其自身的價值取向和已有的知識體系之上,正如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好的音樂要有音樂的耳朵,見山見水,見佛見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都是同理。文學鑒賞的過程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再創造的過程,作者與讀者共同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
正因《禹王書》氣勢宏大,以我們的文科功底、文化傳播研究方向,且在歷史文化方面下過一些粗淺功夫,讀起來猶有一種厚重的壓力。可以想見,沒有一定專業背景的人讀《禹王書》難免會有艱澀之感。因此說,作品是屬于小眾的陽春白雪。好在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大家都耳熟能詳,這又有利于作品接地氣面向大眾。有人建議馮玉雷出個注解本,看似玩笑,卻不無道理。我們的建議是可以作一個簡要的人物圖譜作為附錄,以便大家閱讀。至于是否再作一個故事梗概或主要故事情節及引文出處,可再斟酌。當然,也可遵循另一個準則,“一旦作品開口說話,作者就應該閉口緘默”。
對此,本身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所謂“國手置棋,觀者迷離,置者明白。《離騷》之文似之。不善讀者,疑為于此于彼,恍惚天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讀者或許擔心別人說自己“眼低”,敢于公開說讀不懂或沒有完全讀懂作品,確需要一定的勇氣。我們的體會,讀《禹王書》的過程中查了一些資料,對豐富和重構自己的知識體系是大有裨益的。作者著力刻畫的兩個人物形象,大禹和女媧的傳說,有很多史料支撐。《史記·六國年表》:“禹興于西羌。”西羌地域,古今學者都認為在今甘肅地區,當代一些學者甚至主張馬家窯文化即西羌部族遺存。《淮南子·修務訓》云:“禹生于石。”高誘注:“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應劭曰:“啟生而母化為石。”《左傳》有“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還有“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等等。《太平御覽》引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俗說,天地初開辟,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絙泥中,舉以為人。”《淮南子·覽冥訓》記載:“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于是女禍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小說中的一些情節由上述史料而生發。
二、《禹王書》獨具特色的寫作手法令人贊嘆
《禹王書》的書寫,是頗有馮玉雷個性特點的“這一個”。作品塑造出諸多英雄形象,通篇貫穿的大禹形象和女媧(女嬌)形象暫且不說。當黃帝鄭重宣布“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天地成形,萬物著落,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余成歲,神呂調陽”;以及“天干地支搭配的《黃帝歷》在眾人歡呼中誕生”之時,一個高大的英雄形象誕生了。
舜(重華)“的智慧絕非平常人所能看到”,他“告訴別人的道理正好把握在大家都能夠理解的程度,不多不少,不遲不早,恰到好處。這是多數人都無法做到的”。他將堯禪讓時告誡他的“十六字心法”鄭重地傳給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禪讓之后,仍“流盡汗水,淌干心血,鞠躬盡瘁”,直到病死在九嶷山,一個高大的英雄形象躍然紙上。
當開篇的第一個人物倉頡在閬風苑公布造字方案,造字,丟失,倉頡和山羌外出尋找“啃噬文字”的山羊,重新“打撈”文字,直到“禹代表倉頡交付新文字”時,一個智慧堅毅的英雄形象呼之欲出。脩己、山羌、皋陶、夸父、后羿,一個一個人物形象漸次躍出。
時代呼喚英雄,每一個時代都有屬于這個時代的英雄,每一個人心中都有屬于他自己的英雄。對《禹王書》而言,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是歷時13年治水的大禹和煉石補天、摶土造人的創世女神女媧。女媧的傳說早于大禹治水時代,作者將大禹的妻子涂山氏之女嬌與補天造人的女媧合體,雖難免“穿越”之嫌,但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無疑增添了更大的空間。何況《世本》之《三皇世系》《帝系》中有“禹娶涂山氏女,名女媧,生啟”的記載,也算有出處。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形象,其精神也是民族精神的源頭。
《禹王書》雖然在宏大的背景下敘事,但不影響其細膩的語言描寫、行動描寫、心理描寫、細節描寫,以及具有沖擊力的場面描寫和畫面感,還有其詩意語言的音樂性。第一章中有一段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描寫:“脩己步履蹣跚,跌跌撞撞,艱難邁出破碎步伐。坎坷阻擋,她重重摔倒。喘息片刻,向前爬幾步,歪歪斜斜站起來。站而未穩,趔趔趄趄,向后倒去。她慌亂揮舞雙手,試圖抓住云朵或鳥翼,都滑脫了。她仰天摔在地上,磕碰,磕碰,碰出金星無數。短暫頭疼夾雜著短暫眩暈。她爬起來,晃晃悠悠站穩,踉踉蹌蹌向前。邁出幾步,被裸露樹根絆倒,磕、磕、磕、碰、碰、碰,向前栽倒,臉觸碰地,鮮血直流。她氣息奄奄,昏厥過去……”
小說中又以這段完全相同的文字描寫了禹、倉頡、夸父,第八章中對“很多人”遭受洪災后的群像描寫也用了這段話。
對禹(文命)這個集神話和史話于一體的英雄人物,其形象塑造從還在孕育之時起貫穿全篇,既有語言、心理、動作、神態等正面描寫,也有通過其他人的訴說、想象、分析、贊譽進行的間接描寫。女媧(女嬌)的形象,“隨著太陽冉冉升起,隨著‘候人兮猗的吟唱,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從萬道霞光中飄然而至”。從女媧補天開始,作者不惜筆墨,勾、皴、點、染、擦,白描、潑彩,加上雕塑、雕刻種種技法,一個生動感人的女神向我們走來。九個“九天之夜”的鋪陳,36500塊彩石將天補好;七個“七天后”女媧整理出300多個文字;大量的動作、心理描寫,展示出一個既感天動地又有血有肉的英雄母親(妻子)形象。“女媧低下頭,泣不成聲:‘河水本清,是什么讓它變得如此渾濁呢?”讀到此處,不由人沉浸其中,陷入深深的思考。
從第二章中山羌輕聲哼唱“候人兮猗”,這句中國最早的情詩就開始在空中飄蕩、回響。脩己、禹、女嬌反復吟唱“候人兮猗”,女媧激情長嘯“候人兮猗”,大禹和女媧輕聲合唱“候人兮猗”,女媧化為三生石,金童玉女如泣如訴:“候人兮猗”“候人兮猗”……
還有一些閃光耀著思想光芒的文字,例如:
嫘祖說:“每個人的腳步都是自由的。無論走到哪里,都要帶上自己的陽光。”
大禹說:“天地萬物,人倫規章,道成之,德蓄之,律約之。”
重華說:“用對人就是做對事。”
大禹說:“人的強大不是征服了什么,而是承受了什么。”
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充滿張力的第一人稱代詞“卬”。凡此種種,使得人物形象立體、豐滿、生動。
歷史和神話傳說題材,與現實題材作品相比,更強調走進去和跳出來的有機統一。作者既要置身其中,與人物同呼吸共命運,又要能以局外之身站在一個高度,觀察關照以及引領帶動讀者咀嚼反思。這既要求高超的匠心手藝,也要有理性思辯的高度和境界。讀《禹王書》,我們想到了古人說古詩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我們想到了《莊子》“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并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我們還想到了斯賓諾莎的箴言:“心靈理解到萬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圍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范圍內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為它們受苦。”
三、作者銖積寸累、困知勉行的執著令人感嘆不已
梁啟超先生在《治學雜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讀一部名著,看見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細密……你所看見的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不知他這成果原是以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以我們對馮玉雷的了解,他在治學上是下過大功夫和“笨功夫”的,“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可以作為他的精神寫照,“胼手胝足”的是大禹,也是玉雷。
近20年來,我們見證了馮玉雷創作《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遺書》《野馬,塵埃》等作品。我們在出版《甘肅文化傳承與發展述論》時多次向他請教和探討。馮玉雷的文化功底,當然主要來自他的勤勉和孜孜以求,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因素,就是甘肅深厚的文化底蘊。
甘肅是華夏民族和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季羨林先生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甘肅以其文化上的多元性、包容性、滲透性、融合性,承載著華夏文明數千年的深厚積淀,融匯著古今中外多種文化因素的豐富內涵。
黃帝是由神話人物脫胎而成的歷史人物的典型。《史記》將黃帝列為五帝之首,黃帝所屬部族很可能起源于甘肅東境。我國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主流文化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以渭河流域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而甘肅境內大地灣一期文化,是渭水流域時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它是目前所能追溯到的仰韶文化的源頭之一。我們今天見到的史前陶質樂器,就包括甘肅史前文化遺存出土的陶質鼓、鈴、哨、塤等。
伏羲之后黃、炎二帝,所代表的的部族是走下黃土高原向東發展的并與新地域土著部族融合而成的新群體。華夏民族就是在各個部族之間交往、滲透,沖突、戰爭中融合形成的。反映夏代地理認知水平的《尚書·禹貢》,其“九州”中的雍州包含了今甘肅的東部和中部,隴南的部分地區則歸于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