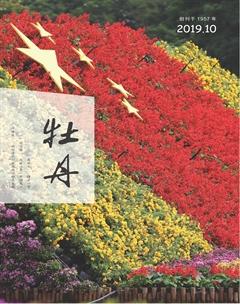淺談文房四寶融合當代生活的美育意蘊


筆、墨、紙、硯并稱“文房四寶”,但此名并不是同筆、墨、紙、硯的出現而并行的。文房四寶的發展與我國歷史上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系,作為物質藝術,包含著豐富的美學意蘊。本文意在探討筆、墨、紙、硯并稱“文房四寶”的淵源和美學意蘊,探究其背后的匠心之美,并結合當代生活的現狀,探索兩者交融的現實意義。筆者旨在從美學美育的角度出發,淺析文房四寶融入當代生活的美學價值及美育意蘊。
一、“文房四寶”名稱淵源及美學意蘊
從秦漢時期到魏晉南北朝,筆、墨、紙、硯的制作愈來愈成熟,因其實用性和精神美而被文人合稱“筆墨紙硯”;到宋代,“文房四寶”之名成為了筆墨紙硯的專指;元代以后,“文房四寶”則特指為“湖筆、徽墨、宣紙、端硯”;隨著時代的推進,明清時期“文房四寶”之名盛行。
當代,“文房四寶”有時為泛指,包括了筆架、水滴等文房用具。筆、墨、紙、硯的制作除技術工序外,還囊括了書畫、雕刻等各種藝術手段,其自身便是藝術品。從精神方面看,其內含文人氣節,工藝匠人的匠心也為之賦予了另一種精神美。從側重文房四寶的實用性到因與文人密切關聯而被賦予的精神性、藝術性,文房四寶詮釋了其豐富的美學價值,符合中國傳統美學的意象美。
二、“文房四寶”與當代傳承創新
筆墨紙硯留下了燦爛的遺產,直到今日也令人贊嘆不已。一直以來,傳統與現代碰撞的聲音從未平息。筆者認為,筆、墨、紙、硯中透出的人文與美學精神對當代生活有著非凡的意義,傳統的傳承與創新可以在時代的變遷中不斷發展。
唐代女詩人薛濤曾設計詩箋,相傳由“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成,詩人李商隱曾吟:“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信紙的“紅”到了現在成為春聯的“紅”,貼紅聯也成為春節代表喜慶的習俗,紅色象征著中國式傳統精神,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當下,科技急速發展,傳統工藝展現出新的生命力。如墨水的制作逐漸標準化,現代墨塊比起傳統的固體墨和墨汁更容易攜帶和使用。同時,人造毛的出現降低了制筆的成本,也刺激了行業的發展,使大批高性價比的毛筆得以進入尋常人家。不僅如此,傳統工藝也在當代被激活和賦能,如毛筆的制作原理應用于現代化妝刷的制作,樂活了市場。筆、墨、紙、硯在形態上的變遷,也體現了當今時代的另一番情趣。
三、“文房四寶”在當代生活的精神啟迪
筆者曾參觀徽墨之都——歙縣老胡開文墨廠,發現僅在刻硯這一道工序上,也有很大的學問。工人們講究手腕間的力度、眼和手的配合度、心腦拿捏的細膩度。小小幾寸的刻硯也需耗上一周以上時間,可謂“一刀一刻皆匠心”。還有安徽涇縣崇星宣紙廠制作的手撈宣紙——由四十四名工人合力制作的三丈三“超級宣紙”,一次次對發號、力度、角度的磨合,造就了世界紀錄,顯示了堅毅獨特的匠心。紙簾的編織,也需心、手、眼的有效合一。在快節奏的當代,這些手工藝為時代真誠地保留了幾分細膩和平靜。
北京大學教授葉朗曾解說席勒游戲說的內涵:“審美對于人的精神自由來說,審美對于人的人性的完滿來說,都是絕對必需的。沒有審美活動,人就不能實現精神的自由,人也不能獲得人性的完滿,人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他認為,美育的根本目的是發展完滿的人性,學會體驗人生,使自己感受到一個有意味、有情趣的人生,從而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華,以成就人的全面發展。而文房四寶的匠心不僅體現在制作的匠人身上,還展現在使用它們的文人墨客身上。王羲之的《蘭亭序》真跡早已不知所蹤,其書法意蘊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臨摹下展示出不同的風采,筆、墨、紙、硯隨著時代的演變,在文人的手中,不斷傳承、改進,為我們展開一番獨特的美的意象世界。
美育可以激發和強化人的創造活動,培養和發展人的審美直覺和想象力。文房四寶投射出的光輝符合了美學觀,其高價值的藝術性有利于培養當代人的審美能力,其蘊含的匠心精神也正契合了美育的核心。文房四寶所代表的傳統文化精髓,對當代人們的的審美心胸、審美趣味的培養具有不容小覷的能量。
四、結語
文房四寶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當代生活美學教育不可缺少的參與者。人的一生,從胎兒一直到老年都應伴隨著美育。文房四寶融入當代生活,不僅是文化傳承的必經之路,更是追求人性完滿、人生境界的美育核心。從傳統精神的角度來看,文房四寶自身所帶來的藝術價值承載著智慧,其上銘文刻畫更具美學意味,貼合美的意象;從融合當代生活的角度來看,傳統美學意象使得當代教育受益,培育人們的審美心胸和審美趣味。
試想,如若人們沒有被賦予文人氣息的“文房四寶”,人們或許仍將擁有筆、墨、紙、硯,卻會少了筆之心、墨之魂、紙之氣、硯之節。在浮躁的當代,這等傳統氣節時刻提醒人們:人的一生不僅只有物質的追求,還有健全人格、完滿人性的追求。“文房四寶”并不僅僅代表“筆、墨、紙、硯”,更是代表了文人氣節、傳統精神,應將之結合現代生活,以美育人,成為當代人的精神追求。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
作者簡介:陳洪(1997-),女,浙江溫州人,本科,研究方向:藝術設計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