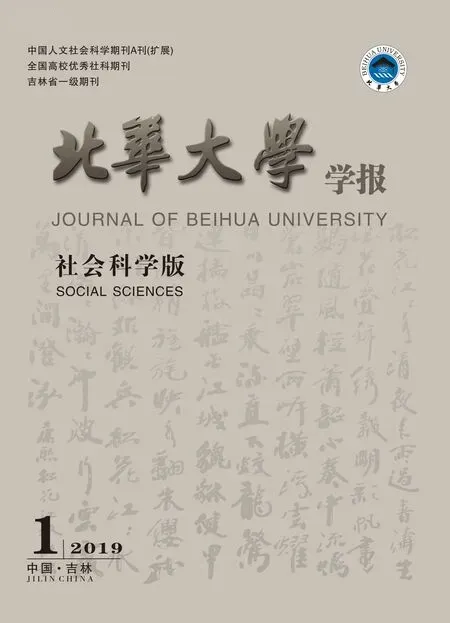區域、區位與區別:哈爾濱百年發展史中的三次轉型與三次高峰
高龍彬
哈爾濱是一座年輕而獨特的城市。隨著中東鐵路的修筑和開通,現代意義上的哈爾濱僅有百余年的發展歷程。在百年發展中,哈爾濱出現了三次轉型,并伴隨著三次高峰。最初,哈爾濱從一個松花江邊松散的聚落形成為一個“洋華雜處、中西交融”的近代化國際性大都市,作為鐵路附屬地的哈爾濱逐漸成長為一個連接東西方的“路徑”和“窗口”,成為當時中國、東北亞乃至世界的一個樞紐。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哈爾濱實現了由鐵路附屬地到獨立自主的歷史性跨越,并日益成為了一個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城市。特別是蘇聯援華項目的建設和展開,哈爾濱出現了第二次的發展高峰。但哈爾濱作為中國東北的核心地位被沈陽所替代,尤其表現在最初的政治方面。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特別是目前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哈爾濱突破原有較為單一的以工業為中心的經濟模式,形成了區域化多元性成長型的發展愿景。哈爾濱正在努力爭取再次成為東北亞的中心和樞紐。哈爾濱的三次轉型都與俄國(蘇聯、俄羅斯)密不可分。在戰爭與和平的語境下,哈爾濱這座城市總也抹不掉俄國的影子。
一
自1896年至1945年間,中東鐵路的修建促進了哈爾濱城市的形成,哈爾濱實現了從傳統農業聚落到近代新興城市的第一次轉型。同時,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了哈爾濱的第一次發展高峰,成為胡適所稱的“東西方文明的交界點”。作為“T”字形中東鐵路節點的區位優勢體現在,哈爾濱確立了中國東北、東北亞以及歐亞交流中心的地位。這一時期,哈爾濱城市的發展變化更多是一種外力作用的結果,內力的表現相對薄弱。
哈爾濱城市的近代化是“被迫的”、“后發的”或者是“殖民化”的結果。哈爾濱這座城市“同俄國動蕩的現代政治史(包括帝制末年的革命活動)有關聯。它是中東鐵路的樞紐——這條鐵路是沙皇建造的,通過中國的東北(當時稱‘滿洲’),使聯結俄國東西兩部分的西伯利亞鐵路大動脈有了一條捷徑。在鐵路沿線兩側,是一個特殊的地區,由俄國管理和警衛。”[1]33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講到,“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使命;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2-3]作為鐵路附屬地的哈爾濱,俄國、日本等國建設性的結果不僅僅表現在物質方面,也表現在精神文化方面,從而形成了一個“多元、交互與共生”的城市。但是,需要強調的是首先是破壞性。“快速的鐵路建設使一座新興城市在這里誕生。這條鐵路是為了沙俄——當時侵略中國的殖民主義強國之一——的需要而興建的。”[1]3120世紀20年代初,瞿秋白在哈爾濱的感觸:“俄國的哈爾濱,俄國的殖民地”。“俄國人住在這里,像在家里一樣。”哈爾濱被稱為“東方小巴黎”、“東方莫斯科”和“東方芝加哥”等,就是在這時形成的。在某種意義上,這些稱謂是殖民主義的后果,帶有殖民主義色彩。
這一階段需要厘清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是鐵路附屬地、行政區劃與市政管理問題。
《華俄道勝銀行章程》(1895年11月)、《中俄御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1896年6月)與《關于東清鐵路建設及經營合同》(即《中國政府與華俄道勝銀行入股合同》,1896年9月)等條約是中俄兩國關于修筑中東鐵路的一些具體條款,并沒有對鐵路附屬地做出明確的界定和劃定。從實際情況來看,現在的哈爾濱道里、南崗和香坊區的部分區域和道外區的八區等地屬于鐵路附屬地,而道外區絕大部分并不歸屬鐵路附屬地,屬于中國政府管轄(這也要看不同的歷史時期)。鐵路附屬地最初是由中東鐵路管理局管理。在一定時期,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亦是鐵路附屬地的最高行政長官。從理論上,相關解釋首先需要對鐵路附屬地、租界、租借地等概念進行闡釋。此外,目前有的學者對中俄之間這些條約的性質提出新的觀點,既然中東鐵路是中俄兩國簽訂條約建立華俄道勝銀行共同建設,那就不存在侵略或殖民問題。但是,筆者認為,這要看兩國簽訂條約的歷史背景,不能孤立地看問題。
租界、租借地和鐵路附屬地等存在差異。上海、天津的各國租界與整個上海市、天津市的關系,和中東鐵路管理局與哈爾濱的關系不同。上海沒有“淪陷”前,中國人對上海是擁有主權的,而作為鐵路附屬地的哈爾濱基本上是由俄國人來管理。租界是隔離的,而鐵路附屬地是開放的。上海、天津是先有城市后設租界,上海是在原松江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且后來還設有松江道。而哈爾濱是隨著中東鐵路的建設而逐漸形成的,直接就是鐵路附屬地,所以有的研究哈爾濱的俄文書籍直接命名為“哈爾濱,俄國的遠東分支”。盡管在哈爾濱形成之前也存在一些聚落,但是不穩定的,季節性和流動性較強。
哈爾濱不同歷史時期的各種行政區劃及其市政管理是一個亟待厘清的問題。段光達在《哈爾濱早期城市特點芻議》一文中指出,1926年,哈爾濱的市政管理權依舊沒有統一,整個城市一分為四,仍處于多重行政管轄的特殊格局之中。其各自管轄范圍如下:“傅家店屬于吉林省濱江縣;道里區、南崗區屬于哈爾濱特別市;馬家溝、顧鄉、香坊、偏臉子、正陽河等其余江南各區,統歸東省特別市政管理局屬哈爾濱市;松花江哈爾濱段北岸的松浦區,則由黑龍江省長官公署下屬的松北市政局管轄(1920年初該局設立時稱馬家船口市政局)。”[4]這一論述說明了哈爾濱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也反映了哈爾濱城市歷史的獨特性和多元性。
筆者在《關于“猶太人在哈爾濱”的歷史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1945年以前特別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道外是形成了以八區為核心的哈爾濱的生產加工中心,道里是形成了中央大街為核心的哈爾濱的金融商業中心,南崗則是形成了以東西大直街為核心的哈爾濱的行政管理中心。歷史地形成了三個區在哈爾濱的不同職能,并且是形成了一個有序運轉的體系或系統。[5]此外,道外以正陽大街(今靖宇大街)為中心形成了中國人的商業貿易中心;還有在香坊形成了哈爾濱較早的工業特別是輕工業的中心。1917—1920年在哈爾濱生活過的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指出,“在沙俄勢力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哈爾濱發展成了三個不同的區域:一個是在松花江畔的‘碼頭’商業區(現為‘道里區’);另一個是稱為‘新城’的行政區(現為‘南崗區’),這里有寬闊的馬路和軍政機關的高樓大廈,中東鐵路局也在這里;最后一個就是前文所述的‘傅家甸’(現為‘道外區’),是本地居民區。”[1]37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盡管道里、南崗、道外、香坊在行政管理上還屬于不同的國家或政府,呈現“兩國、三省、四方”的市政管理格局,但是在經濟上是互通的。現在需要相關專家和學者對哈爾濱的早期行政沿革進行微觀研究,把不同時期的行政區劃和市政管理厘清。
第二是開埠、設治與城史紀元問題。
濱江道奏準于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即公元1905年10月31日;設立于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即公元1906年5月11日。哈爾濱在“光緒三十一年中日‘滿洲’善后條約開為商埠,又開對外貿易之嚆矢。”[6]1905年12月22日,中日雙方締結了《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又稱《‘滿洲’善后協約》)三款,附約12款。在附約第一款中就提到,“中國政府應允,俟日俄兩國軍隊撤退后,從速將下列地方中國自行開埠通商”,其中就有,“吉林省內之長春(即寬城子)、吉林省城、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姓”。可見,從時間上來看,哈爾濱是奏準設治在前,而開埠在后,并且哈爾濱是“被”日本開埠的,不是俄國,只不過是日俄戰爭的結果。但是,開埠加速了哈爾濱關道的設立。“添設哈爾濱關道折”中指出,“目下兩鄰和議已成,聞有長春以南鐵路歸日,以北鐵路歸俄之約,是三省鐵路已分界限,吉(林)(疑為江)兩省盡在俄之勢力圈中,彼所失利于南,將必取償于北。近日所索之事,非占我土地,即奪我利權,并我之內政,亦思干預。”[7]由于哈爾濱區位的特殊性,松花江北岸的馬家船口及后來的松浦鎮本來屬于黑龍江將軍管轄,但是實際上由吉林將軍管理。這從哈爾濱關道是由吉林和黑龍江將軍共同奏請中亦有所反映。
關于哈爾濱關道設治有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是,哈爾濱設治與城史紀元問題的關系。哈爾濱城史紀元的代表性陳述目前有中東鐵路說、設治說、開埠說甚至金源說,其中中東鐵路說還分為開工和竣工兩種討論。關于設治說,柳成棟強調“奏準設立哈爾濱關道即哈爾濱設治,是哈爾濱近代城市建設的最權威的紀念日”。同時,他指出“中東鐵路的修建,絕非只形成一個哈爾濱,導致城市(鎮)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在于其本身的內在因素即內因起作用”。“中東鐵路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產物,哈爾濱近代城市紀念日絕不能定在與帝國主義侵略相關的恥辱之日。”[8-9]筆者認為,我們應該承認歷史事實和相關條約的客觀結果,不能進行情緒化論述。關于哈爾濱的城市特質,米大偉總結,“作為現代城市功能和定位的哈爾濱,主體內容自然是哈爾濱作為城市的歷史,它的發生、發展是中東鐵路建設帶來的,是一座借中東鐵路的修筑和經營的機緣,由村鎮聚落點迅速轉化的現代城市。”[10]這些村鎮聚落點主要是隨著鐵路建設形成的鐵路村。
隨著現代行政區劃的變動,一些原來不屬于哈爾濱的地域進入哈爾濱行政區劃,如阿城。從而哈爾濱有了“千年文脈、百年設治”的界定。但是,筆者認為,不能因為行政區劃的變動,把不屬于哈爾濱原有區劃的歷史看作哈爾濱城市的歷史組成。
二
從1945年至1978年,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哈爾濱實現了從鐵路附屬地到獨立自主的第二次轉型。伴隨著蘇聯援華項目的實施與傳統工業型城市的形成,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哈爾濱出現了第二次發展高峰。由于受蘇聯營造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影響,建國初期我國實施“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這個時期哈爾濱受外力作用仍然顯而易見,同時內在的張力亦逐漸彰顯。但是,哈爾濱作為東北核心的區位優勢逐漸弱化,特別是在政治方面,是突變;在經濟方面是漸變的。
根據《雅爾塔協定》等相關條約,蘇軍進軍我國東北,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滅亡。1946年4月28日哈爾濱光復,并成為我國最早解放的大城市。隨后,中國共產黨最高指揮進入哈爾濱,哈爾濱一度成為了解放戰爭的指揮中心。遼沈戰役勝利后,東北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后方。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亦來哈籌備新政協的召開。在建國定都北京前,哈爾濱亦被選為首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哈爾濱曾被稱為“共和國的長子”。1950年毛澤東訪蘇歸來,途徑哈爾濱時,視察了哈爾濱車輛廠和參觀哈爾濱市貌。在156個蘇聯援華項目中,有13個項目落戶哈爾濱,哈爾濱日益成為一個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城市。
這一時期需要弄清的問題如下:
首先,國際上中國與蘇聯的“博弈”。
在這個方面,問題突出表現在:蘇軍解放東北時的所作所為、哈爾濱解放時蘇軍與國民黨的交接、蘇聯單方面撕毀援華項目合同等。
1946年4月28日,哈爾濱光復。光復前,蘇軍是與國民黨進行的交接。而那時共產黨的軍隊就在哈爾濱周圍待命,迎接哈爾濱的解放。蘇軍把哈爾濱交給國民黨政府應該是另有所圖,不僅僅因為國民黨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中國共產黨東北局是從中蘇關系的高度和國家整體利益去處理此問題的,欲擒故縱,盡管喪失了一部分利益,這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默認狀態。最終是以楊綽庵為代表的國民黨接收人員兩進兩出哈爾濱,沒能在哈爾濱站住腳。雖然在哈爾濱建立相關機構,但是接收人員沒有在哈爾濱取得實質性成果。哈爾濱光復前后,蘇聯、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抗聯等各種力量在哈爾濱的較量有待深入的微觀研究。
1960年,蘇聯單方面撕毀援華項目合同并召回在華專家,實質上是美蘇冷戰格局下社會主義陣營中蘇之間“斗爭”的一種結果。我國著名俄國史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聞一指出,“冷戰”表面上是不打仗,而實際上在準備有朝一日以戰爭手段來結束“冷戰”,這是形式上講。而在實質上,“冷戰”是兩種制度的較量、兩個主義的拼搏、兩種意識形態對壘的旗號下進行的爭奪世界霸權和宇宙空間的戰爭,最終所導致的是世界的一分為二。中國是以蘇聯為主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地緣和歷史等因素,哈爾濱是蘇聯實施在華政策的重要區域。
“一五”時期,哈爾濱是國家重點建設城市之一,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建設工程,有13項設在哈爾濱(哈爾濱電機廠、哈爾濱汽輪機廠、哈爾濱鍋爐廠、哈爾濱軸承廠、哈爾濱偉建機器廠(原哈飛)、哈爾濱東安機械廠、哈爾濱東北輕合金廠(原哈爾濱101廠)、哈爾濱量具刃具廠、電碳廠、電表儀器廠等),成為國家重要工業基地,并迅速由一個消費城市轉變為新興工業城市。蘇聯援華項目規劃了中國的工業布局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國的工業基礎,項目的積極意義是值得肯定的。不可否認的是蘇聯援華項目也有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目的。1960年,蘇聯撕毀合同和撤回專家,在某種意義上是雙方特別是蘇聯方面誤讀的結果。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社會主義陣營仍由蘇聯主導是毫無疑義的。但在誰領導社會主義陣營方面,蘇聯領導人出現誤讀。1960年,蘇聯撤回專家時,在哈援華項目早已建成并投入生產。雖然沒有造成致命性的打擊,但是相對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損失。總體而言,蘇聯在哈援華項目是利遠遠大于弊。蘇聯在哈援華項目與哈爾濱城市工業布局及城市發展等方面的關系,也是一個有待梳理的課題。
其次,國家內中央與地方的“平衡”。
在這個時期,在中央與地方的“平衡”中,哈爾濱的地位和作用隨之變動。陳毅元帥曾經講過,“淮海戰役是人民用小推車推出來的”。以此類推,遼沈戰役是用中東鐵路拉出來的。作為中東鐵路樞紐的哈爾濱的作用那時并沒有改變。作為解放戰爭的大后方,包括哈爾濱在內的東北為整個中國的解放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哈爾濱歷史地位的變化始于解放戰爭后期,隨著部隊的推進以及整個東北和全國的解放,哈爾濱逐漸退出在我國東北的核心位置,由沈陽取而代之,包括政治和經濟方面特別是政治方面。這是全國重新布局的需要。應該說明的是自1904年日俄戰爭和1905年《樸茨茅斯和約》后,我國東北以長春為分界線劃為‘南滿’和‘北滿’,哈爾濱是‘北滿’的中心,沈陽是‘南滿’的中心。但是整個東北的經濟中心在哈爾濱。這種局面最遲也要持續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甚至延續到1946年。東北海關的各種數據就是一個堅實的佐證。從政治方面,創立于沈陽后到過安東、哈爾濱和佳木斯等地并最終回到沈陽的《東北日報》,以及從延安到哈爾濱和佳木斯等地后到沈陽的魯迅藝術學院,突顯了沈陽在東北的區位優勢。這一方面的研究也是一個有待深化的命題。
三
自1978年至現在,哈爾濱實現和正在實現從現代工業主導到區域多元成長的第三次轉型。同時,21世紀初期哈爾濱也完成與正在完成從東北老工業基地到消費服務型城市轉化的第三次發展高峰。這個高峰將會持續性延展。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和幾十年的建設,哈爾濱正在由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城市向綜合性多功能的現代化城市轉變。在這個時期中,哈爾濱的自身發展內力是城市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外部力量特別是蘇聯(俄羅斯)的推動力作用不大,效果不明顯。這表現在我們對蘇聯(俄羅斯)的過分熱情,甚至是過分依賴和蘇聯(俄羅斯)對我們的過分冷淡的強烈反差。實際上,近40年來哈爾濱沒有成為中俄關系中的一個中介、砝碼和通道。但是,目前哈爾濱正在逐漸改變這種現狀,恢復哈爾濱第一個發展高峰時期的歷史地位。
建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哈爾濱不像濟南和青島是山東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屬雙核驅動,亦不像沈陽和大連是遼寧的政治和經濟中心,也是雙核驅動,而哈爾濱既是黑龍江省的政治中心,又是經濟中心,是一種單核驅動。這是一種優勢與劣勢并存的狀態,然而目前哈爾濱在優勢方面發揮充分,削減劣勢。“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經濟自信和偉大復興的充分體現,亦是我國在新形勢下實施新的獨立自主外交戰略的整體部署。哈爾濱需要充分發揮在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優勢。
這個時期需要梳理的問題有:
首先,國家關于東北全面振興戰略中的哈爾濱與蘇聯(俄羅斯)因素。
2014年8月,國家制定并實施《國務院關于近期支持東北振興重大政策舉措的意見》,“支持東北地區全面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機制、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這是針對“目前也面臨新的挑戰,去年以來經濟增速持續回落,部分行業生產經營困難,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和結構性矛盾凸顯。”而提出的目的是“為鞏固擴大東北地區振興發展成果、努力破解發展難題、依靠內生發展推動東北經濟提質增效升級。”2015年1月11日,中國共產黨哈爾濱市第十三屆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擴大)會議上指出,《關于近期支持東北振興若干重大政策舉措的意見》是“國務院專門為推動東北地區振興而量身打造的,也為東北地區全面振興提供了又一個難得發展機遇”。哈爾濱要“在新一輪東北地區全面振興中贏得主動”。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蘇聯先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1991年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葉利欽實施“西化”的改革,以及后來的普京與梅德韋杰夫的“普梅”或“梅普”組合“新政”,蘇聯(俄羅斯)一直在忙于自身的轉型。當然,哈爾濱這個與俄國(蘇聯、俄羅斯)有著密切關系的城市也在進行這方面的改造或改革。中國·哈爾濱國際經濟貿易洽談會(哈洽會)及中國—俄羅斯博覽會所體現的中俄關系特別是經濟關系下的政治關系有待深化研究。
其次,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俄羅斯與哈爾濱因素。
國家“一帶一路”構想提出后,各省各地都在尋找與此構想有所“交叉”的方面,其實背后的目的就是爭取構想帶來的各種優惠政策。黑龍江包括哈爾濱處在新的“歷史機遇期”。在“東部絲綢之路”上的黑龍江與俄羅斯遠東地區有幾千公里的邊境線,哈爾濱曾經是世界上俄僑的最重要聚居地之一。黑龍江對俄各口岸的實際效能有待進一步提升。哈爾濱“音樂之城”的美譽,源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俄僑藝術家的貢獻。雖然現在俄國人不再對蘇聯歌曲、油畫等文化感興趣,但是我國人民對此還是有著根深蒂固的熱戀,哈爾濱就是連接俄羅斯和中國的最好紐帶,緣于哈爾濱既有歷史淵源又有資源優勢。世界各地的原駐哈爾濱的僑民“哈爾濱人”及他們的后代,對哈爾濱有著無盡的眷戀。澳大利亞的哈爾濱人協會、波蘭的哈爾濱人協會以及以色列的原居中國猶太人協會等等,都是哈爾濱的寶貴資源。但是,哈爾濱要有過硬的條件,讓他們能來哈爾濱,留在哈爾濱。“冰城夏都”也是哈爾濱的一塊招牌。如何做大做強哈爾濱和黑龍江的旅游文化更是一個巨大的命題。哈爾濱和黑龍江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有生命力的、有生產力的相關政策,關鍵是實施,需要持之以恒、循序漸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壯大是一個城市成熟的標志,但這是一個艱難的轉型。
總之,在百年發展中,哈爾濱經歷了三次不同意義的轉型,并且帶來了三次非同尋常的發展。緣于區位的變化,哈爾濱的地位和作用也隨之變化。但是,這是一個歷史的進程,不是人為因素能夠改變的。哈爾濱城史研究需要國際視野和微觀研究,需要客觀總結哈爾濱城市發展的歷史規律。“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哈爾濱站在新的“歷史機遇期”上,廣闊天地,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