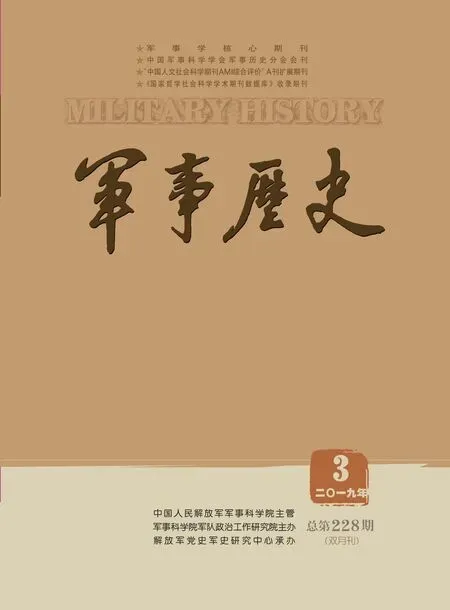日本陸軍“中堅層”的總體戰理論及其對侵華戰爭之影響
研究日本陸軍,德國因素不可忽略。1920—1930年間崛起的日本陸軍“中堅層”軍人①本文所定義的日本陸軍“中堅層”指成長于日俄戰爭之后,活躍于侵華戰爭時期,或參與陸軍侵華政策的制定,或在中國戰場實地制定作戰計劃、參與指揮作戰的日本陸軍中高級軍官、參謀。具體來說,這一群體中的大部分人生于19世紀末,在日俄戰爭后開始接受近代化軍事教育,系統接受過陸軍幼年學校、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教育。20世紀30年代前后在陸軍中央或關東軍擔任參謀或者基層指揮官,此后或在陸軍中央擔任課長以上重要職務,或在中國戰場擔任指揮官、參謀長,在侵華戰爭中逐漸成長為高級將領,參與制定、實施侵華政策,最終軍銜基本都是將軍。,大都有赴德國留學考察的經歷,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形成的總體戰理論影響。考察他們的思想,必須將其置于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組織環境之中。對于他們而言,總體戰無疑是未來戰爭的發展方向,日本軍事必須跟上時代步伐,徹底改革,與整個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軍人需要在政府中掌握更大的權力。而這與當時陸軍高層的觀念不無捍格,于是中下級軍官與高級軍官間的分野逐漸顯明。這些中下級軍官由于教育背景和經歷相似,內部凝聚力強,有一定的群體界限和明確的立場觀念。隨著其群體的不斷壯大,實力不斷增強,日本陸軍省的重要職位,逐漸由他們所掌握。于是,可以看到,昭和時代日本陸軍的發展走向,受到歐洲陸軍,特別是德國陸軍發展的強烈影響,軍部勢力日漸膨脹,侵蝕政治權力,頗有與政府相抗衡之勢。
與此同時,在國內動員一切力量、在國外掠奪殖民地資源以支持國防和戰爭經費的總體戰理論已經成為日本陸軍“中堅層”軍人的集體認識。其中代表性人物永田鐵山、石原莞爾鼓吹的日蘇、日美決戰論,則為動員總體戰提供了理論依據。關于日本的總體戰,既往研究多從體制的角度進行探討。②代表性研究可參見[日]纐纈厚:《総力戦體制研究:日本陸軍の國家総動員構想》,東京:三一書房,1981年;郭鑫:《日本對華侵略與國家總動員體制的建立》,《軍事歷史研究》2015年第1期。本文更多關注日本陸軍“中堅層”軍人對歐洲總體戰理論的接受、發展及實踐過程,并嘗試探討總體戰理論與侵華戰爭、日本陸軍戰略布局的關系。
一、日本陸軍總體戰理論的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戰略戰術的不斷發展,呼喚新的軍事理論對之加以總結和概括。戰爭中機槍、坦克和飛機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當時的戰局。而大量高新技術裝備、武器彈藥的補給,則有賴于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軍隊不再是軍人之爭,而且是武器之爭、經濟之爭。拿破侖時代一次決戰決定戰爭勝負的場景已不復存在。世界大戰成為長期的、持久的戰爭。國家的經濟潛力成為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①參見陳雷:《經濟與戰爭:抗日戰爭時期的統制經濟》,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4、25頁。一戰后,德國著名將領魯登道夫等人提出的總體戰理論在當時的歐洲流行起來。魯登道夫認為,國家和政府“要把全民族的政治、精神、經濟和軍事聯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為戰爭服務”。國家的任何事業,如盡可能擴大軍事工業,控制中央銀行對貨幣的發行,頒布戰爭經濟動員令,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和普遍義務勞動制,實施戰時食品、服裝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給制等,均須在政府的控制下施行。②參見[德]埃里希·魯登道夫:《總體戰》,戴耀先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125頁。這種策略實質上也是德國應對20世紀20年代末經濟危機給出的藥方。
德國的總體戰理論對當時同樣深陷經濟危機,且與德國有諸多相似之處的日本頗具誘惑。特別是日本陸軍在軍事近代化過程中師從德國,進行了軍事制度和軍事教育的改革。一戰前后,不少接受了近代化軍事教育的青年軍人被派赴德國留學、考察。這些后來成為日本陸軍中堅的軍人不僅深受德國總體戰理論的影響,也是日本總體戰理論的倡議者、研究者和實踐者,其中永田鐵山和石原莞爾尤具代表性。
二、永田鐵山的國家總動員理論及施政主張
日本陸軍中較早提出總體戰理論的是永田鐵山。永田在日本陸軍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但中國學界至今對其研究尚不充分。永田1884年生于長野縣,1898年進入陸軍幼年學校,1904年和1911年分別自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畢業,1913年被派往德國留學,研習軍事,是典型的接受了“精英”教育的陸軍“中堅層”軍人。1923年,永田進入陸軍參謀本部,任教育總監部課員,次年任陸軍大學教官。1930年,永田升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其間,提出整體戰戰略思想,并著手整合軍制及軍備,成為日本陸軍統制派的精神領袖。1935年8月,永田被皇道派陸軍中佐相澤三郎刺殺。
雖然早逝,但永田鐵山對于20世紀30年代前后日本陸軍的人事與政策,均可謂一開山人物。他所建立的人事建構,對日本陸軍的走向有著重要影響,而其軍事戰略思想,為后來者學習借鑒,成為日本陸軍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重要參考。
永田鐵山的軍事戰略思想與他的歐洲經歷有很大關系。1911年陸大畢業后,永田被派往德國進行軍事調查。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永田親眼目睹了這場大規模的現代戰爭,意識到未來戰爭是國家總體性的戰爭,必須動員一切人力、物力,集全國之力,方能在戰爭中獲勝。1920年,永田任臨時軍事調查委員時提交了一篇名為《關于國家總動員的意見》的報告書,指出,“所謂國家總動員,即將國家掌握的一切資源、機能,暫時或永久地用于戰爭,為實現最有效地利用,進行統制和分配”,“以全部國民之權力,傾注于實行戰爭之大目的”。③[日]臨時軍事調査委員:《國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陸軍省,1920年5月,第2、3頁,東京:國立國會図書館,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81168,2017年10月6日。
永田認為,以往日本的常備軍制度,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時代的發展要求。戰爭已經不單純是軍人之事,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事;不是單純武力對抗之事,而是經濟競爭之事,因此必須將“人力、武力、有形、無形的一切要素”轉化為戰斗力。如欲在戰時與群雄逐鹿,必須在平時做好準備計劃。這種計劃包括國家總動員的具體內容,由國民動員、產業動員、財政動員、精神動員等組成。①參見[日]臨時軍事調査委員:《國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陸軍省,1920年5月,第3、4頁,東京:國立國會図書館,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81168,2017年10月6日。國民動員,是指為了適應軍隊和戰時國民生活的需要,而統一控制、調整和有效地配置人員。永田指出,必要時應采用“強制勞役制度”,通過“國家強制權”強制從事勞務。永田還主張學習英法等國設置“國防院”,統一管理國家總動員的相關事務。②參見[日]川田稔:《昭和陸軍の軌跡 永田鉄山の構想とその分岐》,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第68~69頁。
現代戰爭打的是經濟戰。現代武器裝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戰爭的走向。永田高度關注飛機、坦克等最新精銳武器的保有量,指出一戰結束時,飛機方面,日本擁有大約100架,而英、法、德等國家的飛機數量是日本的幾十倍。坦克方面,即使在1932年初,美國也有1000輛,法國有1500輛,蘇聯有500輛,而日本僅有40輛,相差明顯。因此,永田提出產業動員即是按計劃生產設備和產品,應該大力推行生產的統一標準,以便民用產品軍用化。同時,統一生產標準還可以增加生產效率,增加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③參見[日]川田稔:《昭和陸軍の軌跡 永田鉄山の構想とその分岐》,第72~73頁。
以往,日本多以俄國為假想敵,但永田認為,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動,日本的敵人可能不僅是俄國,甚至有可能是英美等世界強國。日本要想與強國對抗,憑借本土的資源肯定遠遠不能滿足要求,因此不僅要動員本國的資源,還要侵占其他國家的資源。永田的德國經驗,也堅定了他的信念。在他看來,德國之所以可以堅持四年半,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占領了油田、煤礦等重要資源。鑒于此,與日本臨近的“滿蒙”地區,自然成為永田腦中理想的資源供應地。
總而言之,永田認為現代戰爭是國家總體實力的戰爭,而不單單是軍隊的戰斗,建設精銳軍隊是國防的基礎,但憑國家軍隊的整備還不足以取得勝利,必須對國家總動員做好準備,“為了增加國家的國防資源,要采取一切手段方法,要提前設定計劃,以備一旦事情緊急,能采取合適的統制辦法,從而最為迅速、最為高效地發揮國家的戰爭能力,此為目前最重要的事宜,一日亦不可遲延”④[日]臨時軍事調査委員:《國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陸軍省,1920年5月,第2、3頁,東京:國立國會図書館,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881168,2017年10月6日。。也就是說,國家的一切資源、制度,都應圍繞著戰爭需求加以利用、改造。
1926年永田進入陸軍省后,開始嘗試將其理論轉化為日本陸軍的政策。1933年10月,《國防本義及其強化之提倡》正式出版發行。這本小冊子集中體現了陸軍省的政策導向。陸軍省圍繞這本小冊子,在內閣會議上作出說明:“就像這本冊子所詳述的那樣,現在的國防非常廣泛,僅靠最小限度地保有軍備,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同時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思想等各個方面加以強化和整理,才能真正充實國防力量來進行戰爭”,“本次發表的冊子,著眼于陸軍大臣圍繞著國防上的要求和希望,就國家內外國策的確定,對首相提出的要求,其目的在于向國民展示軍部對完善國防的希望,并普及國防思想”。⑤陸軍省:《〈國防の本義と其の強化の提唱〉に関する閣議説明案》,1935年6月2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40200214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可以看到,這個小冊子的立場,得到了陸軍大臣的肯定,并且作為軍部立場,向全體日本國民進行宣傳。
對照內容也可發現,小冊子的精神與永田所倡導的國家總動員體制相符合。小冊子將戰爭推到一個神圣的地位,認為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⑥《2、國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陸軍省新聞班パンフレット(13冊)昭和9年—昭和13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51205072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在小冊子中,國防成為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環節,具有崇高的地位,國防是一個國家生存的最必要條件。⑦參見《國防的真實意義和加強國防的主張》,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譯:《1931—1945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3頁。國防是目的,統制則是手段。
永田和其他統制派的理論經驗,來自于一戰。因此小冊子中,一戰成為最為顯著的國際背景和理論來源。小冊子指出,一戰以后國際秩序陷于混亂,呈現出分崩離析的狀態。由于國家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傳統的單純憑借武力進行作戰,已經不合時宜。國家間的戰爭形式由純粹武力戰而轉向整體戰。同時,小冊子中提到,一戰使戰前與戰時的區分更為模糊,戰前如無準備,戰時便不可能取得勝利。①參見《國防的真實意義和加強國防的主張》,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譯:《1931—1945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125、128頁。因此,戰前準備須以戰時需要為標準。針對日本資源不足的情況,小冊子指出,必須獲得海外資源,以充實國防產業。而且,國內的經濟、社會政策,也必須圍繞作戰的大方略展開。總之,戰前的一切準備,都是為了順利過渡到戰時的統制經濟。②參見《國防的真實意義和加強國防的主張》,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譯:《1931—1945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128、129頁。
從這個意義而言,國防具有無所不包的統攝性和覆蓋性,具有四個層面的統制:政治統制、經濟統制、社會統制、文化統制。基于此,“必須重新檢討國家全部結構,必須對財政、經濟、外交、政略以及國民教化堅決實行根本改組。為了國防的目的,努力對皇國偉大的精神、物質潛力進行組織統制,加以一元化的運用,使之成為最大限度的實力”③《2、國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陸軍省新聞班パンフレット(13冊)昭和9年—昭和13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51205072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具體而言,可從五個方面推進:第一,實行積極軍備,反對只有遭遇入侵才動用武力,而是要借助武力支持國家發展,這就為實施侵略提供了足夠的借口。第二,總體戰與統制經濟必須相互結合,造成軍備常態化、經濟軍事化的態勢。第三,后方必須服務前方,創造穩定的環境,“使士兵無后顧之憂”。第四,統制政策與日本皇道文化相結合,樹立牢固的國家本位主義,強調要“堅信建國理想和皇國使命”。第五,統制政策要有機構依托,必須建立“以國防為本位的各種新機構”,系統地施行各項統制政策。
小冊子指出,能否克服列強的壓迫關乎日本未來能否成為真正的強國。為此,日本國民必須深刻理解國防的含義,將其作為戰勝列強的重要武器。小冊子分析當時已處于國際秩序崩潰的時代,國際競爭必將日趨激烈。國防權的自主獨立,是不可動搖的天下公理,④參見《2、國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1)》,《陸軍省新聞班パンフレット(13冊)昭和9年—昭和13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51205072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不容任何國際組織限制或干預,任何旨在壓制日本國防能力的措施,都將被視為對日本的威脅。換言之,國防政策針對的是當時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日本對于國際條約限制本國軍備這一情況十分不滿,已有意嘗試沖破這種秩序。
1935年9月,統制派池田純久撰寫了《當前陸軍的非常時期政策》。該文件集中體現了永田時代統制派對外擴張的理解認識,⑤參見《當前陸軍的非常時期政策》,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譯:《1931—1945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129、130頁。池田將日本的改革與“滿洲事變”相關聯,提出“應該以滿洲事變的爆發為契機,進行日本的改革”。改革成功之前,由于“日本的經濟處于窒息的狀態,在這樣混沌的國內形勢下,進行的大陸政策只能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⑥出自池田純久在日本投降后的回憶。池田純久:《支那事変勃発前後に於ける諸動向に就て》,1945年12月26日,《雑綴 昭和20年12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111116997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
三、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及總體戰構想
永田鐵山的后輩、統制派另一代表人物石原莞爾也有在德國學習的經歷。受一戰影響,石原非常關心一戰后國際政治經濟大勢,并從歐洲國防經濟學、總體戰理論中獲得靈感,用“皇道”思想加以包裝,形成他頗具個人特色、頗為系統的“最終戰爭論”和總體戰構想。
所謂“最終戰爭論”,是石原在對世界戰史作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結論,也是其軍事理論的核心。①最終戰爭論萌芽于石原莞爾所受的完整的軍事教育及多年對戰爭歷史的研究。在德國留學期間,石原基于對歐洲戰史的深入研究,初步形成最終戰爭論的想法。1925年,石原從德國回國途中,途經哈爾濱,在國柱會為其舉行的歡迎會上,首次發表了關于最終戰爭論的論述。1926年,石原擔任陸軍大學教官,開設歐洲戰史講座,為此他用一年時間整理了詳細的講義,介紹歐洲中古世紀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歷史。這份講義的內容是最終戰爭論的基本雛形。1927年,石原發表《現在及將來的日本國防》,1928年任關東軍參謀后,相繼發表《戰爭史大觀》《扭轉國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關東軍滿蒙領有計劃》《滿蒙問題之我見》等文章和建議,提出了系統的戰爭理論。1940年5月29日,石原在京都以“人類前史終將結束”為題發表演講,內容由立命館大學整理,并以《最終戰爭論》定名出版,這是對石原莞爾戰爭觀和戰爭理論的一個完整總結,也是現在廣為流傳的最終戰爭論文本。參見張芝瑾:《石原莞爾的中國認識與亞洲觀》,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系教學與研究中心,2010年,第44~46頁。石原主張世界和平無法通過宗教、教育、政治改革等手段來實現,人類自身制造了發動戰爭的武器,因而只能通過一場世界大戰才能最終實現世界和平。而這場最終戰爭將在世界兩大對立陣營即東方與西方之間進行。東方與西方的對立不僅源于對領土與市場的爭奪,而且由于歷史原因,兩個集團的價值觀是根本對立的,因而必然要發生沖突。西方的代表是美國,而日本則必須代表東方與美國進行最后一戰。這場大戰將以世界最終戰爭的形式出現,然后進入由天皇統治的和平時代。這場大戰即將爆發,日本國民應具有時刻為此做準備的覺悟。同時,為“幫助”中國對抗西方入侵者,日本應出兵維持“滿蒙”地區的治安和經濟。為了持久戰作部署,日本應考慮在中國占領地的兵力,威脅到“滿蒙”的俄國軍隊的兵力,一旦失去制海權后如何對抗登陸中國的外國軍隊,保證日本本土的守備,奪取菲律賓、香港等地所需的兵力等問題。②參見[日]石原莞爾:《現在及將來ニ於ケル日本の國防》,[日]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 國防論策》,東京:原書房,1975年,第58~68頁。
石原認為日本進行最終戰爭的形式就是總體戰。首先就士兵數量而言,目前是所有適齡男性參加戰爭,到了決戰戰爭,男女老少將全部參戰。③參見[日]石原莞爾:《世界最終戦論》,大阪:立命館出版部,1940年,第34、35頁。因而他鼓吹“以戰養戰主義”,戰爭一旦不能迅速取勝,必然會被拖入“持久戰爭”。那么,就必須在對方國家收集戰爭資源,達到以戰養戰。以戰養戰的核心,旨在占領對方國家的領土,控制主要的戰略資源,并有計劃地從事資源采集工作,支持軍事工業。④參見[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周啟乾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261頁。因此,日美之戰的前提是把“滿洲”作為日本的“生命線”“補給線”,先打敗蘇聯,并使中國成為日本作戰的“盟友”。
石原的戰爭觀極為殘酷。他認為,總體戰所要攻擊的目標,并非只是精銳的部隊,而是那些“最虛弱的人和最重要的國家設施”,“工業城市和政治中心才是應該徹底摧毀的。所以男女老少、山川草木、雞鴨鵝狗都應該一樣對待”。全體國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石原認為日本為應對總體戰,必須早作準備,肅整官員,完全廢棄城市中中等以上學校、分散部署工廠,并以此為基礎整合城市人口,必要時強行征改建筑。⑤參見[日]石原莞爾:《最終戰爭論·戰爭史大觀》,郭介懿譯,臺北:遠足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第24頁。
在石原的最終戰爭論和總體戰設想中,中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石原認為,中國不僅是日本戰時經濟的資源供給地,還應成為日本對美作戰的“盟友”。這也是他的另一重要理論——東亞同盟論的中心內容。1936年6月,石原在《從軍事看皇國的國策國防計劃要綱》中提到“東亞聯盟”一詞,“為做好戰爭的準備,目前的國策就是要先達成東亞聯盟,并希望能將中國大陸、滿洲作為世界戰爭到來時日本的基地,短期則可以防備蘇聯南下之用”⑥參見[日]石原莞爾:《軍事上ヨリ見タル皇國ノ國策竝國防計畫要綱》(昭和八年六月),[日]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 國防論策》,第113~114頁。。石原認為東方世界自古奉行“王道”,東亞國家應在“王道”之下結成聯盟,與西方抗衡。具體來說就是日本、中國和所謂“滿洲國”在“國防共同、經濟一體化、政治獨立、文化溝通”的原則下互相合作,以期在最終戰爭中取勝。但在這一聯盟中,日本須處于領導地位。石原認為中國無法依靠自身力量抵抗西方入侵者,必須由日本整合東亞各民族,與西方爭雄。石原將中日戰爭形容為“為了中日兩國相互提攜而有的煩惱”①[日]石原莞爾:《最終戰爭論·戰爭史大觀》,第26、27頁。。
石原絲毫不掩飾其對希特勒的崇拜,稱之為“英雄”。他認為德國雖在一戰中失敗,但已經重新崛起。希特勒上臺后,施行舉國一致的策略,全力擴充軍備。德國的機械化兵團裝備精良,素質占優,而且一般師團與英法聯軍相比,在人數上也占有優勢。因此,德國在整體軍事力量上占據相當大的優勢。借鑒德國總體戰設立“統帥”的想法,石原很自然地將天皇推上了這樣的位置。天皇既是萬世一系的宗教領袖,也是代表日本的最高權力中樞,同時還是戰時的最高司令長官,可以順理成章地擔負起政治、經濟、軍事三位一體的統帥職責。②參見[日]石原莞爾:《最終戰爭論·戰爭史大觀》,第32頁。
石原提出的兩個理論以及總體戰思想,分別從世界秩序和東亞秩序兩方面入手,表面看起來是站在東方文明的立場上與西方文明相抗衡,有一定的迷惑性,也深得當時日本朝野的共鳴。尤其他主張完全占領“滿蒙”為最終戰爭做準備的構想,對當時正苦惱于“滿洲問題”的日本軍人和一部分日本國民而言,具有特別的吸引力。但其實質卻并非弘揚所謂“東方王道”,而是為日本的侵略擴張提供合法性依據。他所設計的世界秩序和東亞秩序,都賦予日本“理所當然”的領導地位,迎合了日本國內日益高漲的自大情緒,為日本發動戰爭、侵略亞洲提供了理論支持。日本學者加藤陽子評價說:“中日開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沒有人可以講清楚,而石原莞爾的東亞聯盟論恰恰在意識形態層面對此給出了明確闡釋,因而獲得了特別是地方青年的廣泛支持。”③[日]加藤陽子:《総力戦下の政—軍関係》,[日]倉沢愛子など編:《戦爭と占領の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巖波書店,2005年,第23頁。
四、日本陸軍對總體戰理論的實踐
近代以來,日本一步步蠶食周邊鄰邦,不斷試圖拓展勢力范圍,其眼界也從東亞走向世界。在日俄戰爭中,日本戰勝俄國,取得中國東北部分“勢力范圍”。此后日本把中國東北當作其“特殊利益”地區。1908年9月25日,內閣會議宣稱日本有在“滿洲的特殊地位”。日本不但與俄國劃分各自“勢力范圍”,還規定在南北“滿洲”各自有設施鐵道、電線的權利。并且提出在該地區擁有防衛的必要,為后來所謂“維持治安”駐兵預做準備。其后,日本不滿足于鐵道、礦山權益的要求,進一步提出所謂東北“特殊地域”論。1912年,日本在對俄談判中擅自將“特殊利益”的分界線擴大至內蒙古,為“滿蒙分離”埋下伏筆,企圖把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為日本所有。
從“滿洲”到“滿蒙”,從“滿蒙”到東亞,日本對外擴張的要求日甚一日。為此,理論家想盡方法,為侵略制造合理性。永田鐵山主張的圍繞戰爭進行國家總動員、軍部政黨化,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東亞聯盟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借鑒了德國的總體戰理論而出爐的。
永田對于陸軍統制派有著開創性的意義,一方面他為統制派的軍事戰略思想奠定了基調,另一方面他憑借自身在陸軍省的影響力,延攬意見相近的青年“精英”,進入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使他們在陸軍省的勢力日漸壯大,成長為陸軍“中堅層”。石原莞爾、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田中新一、武藤章、松井石根等皆受惠于此,并在侵華戰爭中擔任重要職務。同時,作為永田的擁躉和繼承者,他們延續了籌備總體戰的路線,占領“滿蒙”、進而侵占華北、攫取中國資源作為國防和戰爭的經濟基礎,將對蘇、對美戰爭的理論設想付諸實踐。
1928年,石原莞爾被派往中國東北擔任關東軍參謀。通過對中國東北的實地考察,石原分別提出了《扭轉國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關東軍滿蒙領有計劃》《滿蒙問題之我見》等一系列企圖占領中國東北的計劃。1931年5月,他在《滿蒙問題之我見》中明確提出,通過“謀略”制造機會,不待統帥命令,以軍事政變方式進行武力占領的設想。①參見許育銘:《石原莞爾與九一八事變》,《中華軍史學會會刊》(臺北)2003年第8期,第147頁。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石原等陸軍“中堅層”軍官協助指揮關東軍占領了“南滿洲”的主要城市。他們的計劃是占領整個東北,建立偽滿洲國。1931年10月,石原被任命為關東軍作戰課課長。1932年,在石原等人的推動下,偽滿洲國成立。石原的東亞聯盟論,與他對“滿洲國”的構想緊密相關。1932年7月25日,在石原等人的鼓動下,“滿洲帝國協和會”成立。協和會的宗旨頗具迷惑性,聲稱要使“滿洲國”擺脫日本的政治支配,成為民族協和的獨立國家。②參見《日本東聯運動的演進》,申報出版社編:《申報年鑒》(民國卅三年度),上海:申報出版社,1944年,第1116頁。這一想法能否實現姑且不論,倒是暴露了成立協和會的真實目的,即樹立一個東亞諸民族親善的“樣本”,使其他東亞國家仿效“滿洲國”,臣服于日本的領導。1933年夏,石原意識到,要設計一個有效的政治架構,以完成“世界最終戰爭”的挑戰。因此,他要將“滿洲國”納入到制度設計之中。東亞聯盟正是以“滿洲國”為最初雛形設計的,包含東亞各國的政治體系,實質是將日本對東亞各國的侵略行徑合理化。
石原莞爾的戰略思想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決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以石原為首的戰爭指導課制定的《國防國策大綱》,將石原的構想上升到國策的高度。《大綱》旨在解決蘇聯對“滿洲國”戰略,提出一方面要加強“滿洲國”的建設,另一方面要補充海空軍的力量,保持戰略威懾。1936年8月,廣田弘毅內閣的五相會議根據《大綱》的精神,決定了《國策基準》,肯定了石原等人加強“滿洲國”軍事力量的提議,要求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于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對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③參見《國策基準》,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譯:《1931—1945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136、137頁。其次,石原提出按國防要求,統籌國家的工業生產和產業結構,并且仿照蘇聯,制訂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石原等人的《日滿產業五年計劃》于1937年5月作為《重要產業五年計劃》移交給陸軍省實施。計劃旨在提高工礦業生產能力,使主要產品出現跨越式增長。這項計劃最終被近衛文麿內閣認可,成為國策。
1936年,石原提出將日本勢力限定在華北兩省之中。1937年,石原提出暫緩武力控制華北的政策。陸軍戰爭指導課在其授意和指揮下,于1937年1月制定《帝國外交方針改正意見》,大方向是驅逐英國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勢力,在東亞和東南亞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聯盟,確保資源,最終與美國決戰。④參見[日]石原莞爾:《帝國外交方針改正意見》(昭和十二年一月六日),[日]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 國防論策》,第194頁。從長期戰略看,石原基本上是主張南進。但強調在此之前應先擴充對蘇戰備,讓蘇聯放棄在遠東的攻勢,確保后方安全。石原認為,以日本當下的軍備情況,同時準備對華、對蘇作戰是不可能的,⑤參見[日]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東京:芙蓉書房,1978年,第88頁。因此,更希望通過政治方略,使中國服從于日本的控制。東亞聯盟這一形式就顯得格外重要。⑥參見參見史桂芳:《“東西文明對立”下的東亞聯盟論》,《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在華北問題上,石原與永田鐵山的考慮有相似之處,都是以確保資源、備戰世界大戰為中心。石原認為應該從中國確保獲得國家總體戰所需的短缺資源,早在發動九一八事變之時,石原就曾考慮依靠“滿蒙”的資源,不足以進行長期持久的國家總體戰,應該立足“滿蒙”,奪取河北、山西等華北地區,進而視情況占領“中國本部的要都”,從而確立“東亞自給自足的道路”⑦[日]島田俊彥:《日本關東軍覆滅記》,李汝松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6頁。。他還曾說,“統治滿洲”的目的是為了做好開發中國本土資源的準備,以備未來的“世界爭霸戰爭”。同時,他在《帝國外交方針改正意見》中又提出不進行“華北分治活動”,強調“不能因為華北的資源而失去理智”,并稱,現在談論華北的資源“有害”無益。①參見[日]石原莞爾:《帝國外交方針改正意見》(昭和十二年一月六日),[日]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 國防論策》,第194頁。石原之所以主張暫緩武力控制華北,旨在以經濟侵入代替政治控制,避免短時期內因華北問題與美英等國發生軍事沖突,而絕非意味著放棄日本在華的勢力擴張。
由此,石原莞爾所在的戰爭指導課主張應開展“日中經濟合作”,這與永田鐵山的主張出現較大分歧。永田曾提出要在南進中獨占中國的市場和資源,為北抗蘇聯提供足夠的戰略儲備。但石原反對這種一戰時的思路,他認為通過與英美合作,同樣能夠達到經濟擴張的效果,而獨占中國資源則易引發美國的軍事干預,日本暫無勝算。在石原主政時期的參謀本部,“以日滿為范圍的自給自足經濟”成為主導,主張日本暫時放棄從獨占事業中獲取資源的努力。而放棄獨占中國資源所造成的虧空,則可通過與英美合作,從兩國手中獲取必要的對蘇軍事物資來彌補。
盧溝橋事變后,統制派內部出現分化。如上文所述,石原從其對世界和東亞局勢的長期規劃出發,認為此時日本不宜擴大中日間的戰爭,以日本當時的經濟形勢而言,一旦陷入與中國的持久戰將不利于對蘇、對美戰爭,且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業已崛起,中國人不可能如日本所預期的那樣輕易屈服。因此,他主張以“滿洲”為據點,逐步蠶食中國,“希望盡可能避免戰爭”。如果日本從國內增派3個師團的兵力,將會引發全面對華戰爭,并有發展為持久戰的危險,日本自身的國防戰略將會因此走向崩潰。“如果日中兩國發展成長期戰爭,蘇聯一旦打過來,目前的日本毫無把握”。這就是石原的“不擴大”政策。據時任參謀本部作戰參謀的井本熊男回憶,石原曾在參謀本部內多次發表反對增兵的言論,并預測海軍一定也會在上海制造事端,并以此為借口出兵上海,因此參謀本部不可出兵。②參見[日]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第88頁。
然而,石原的這一主張與以武藤章為代表的統制派成員的意見大相徑庭。武藤等人主張軍事冒險,加緊侵略中國,以完成對美蘇的軍事、經濟準備。武藤等人堅持認為,中國尚處于不可能實現國家統一的分裂狀態,如果日方態度強硬,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就會屈服;現在,應堅持軍事上的強硬姿態,予其一擊,使其屈服,把華北五省納入日本的勢力之下;而且,現在需要華北與滿洲相輔相成,以增強對蘇戰備,眼下的事態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絕好機會。應該說,武藤的認識已經為蔣介石所預料。蔣認為,“盧案已經發動十日,而彼徘徊威脅,未取正式開戰,是其無意激戰,志在不戰而屈之一點,此其外強中干之暴露也”③《考慮日本政府態度》(1937年7月16日),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第343頁。。
一言以蔽之,武藤主張通過軍事打擊,使國民政府屈服,實現一直以來的分裂華北政策,通過日本實質控制華北五省獲得壟斷性的統治權,從而確保華北的資源和市場。當時,武藤曾宣稱,如果從國內向華北派遣3個師團,“那里的一堆廢物將會舉起雙手投降”,所以駐華日軍并不打算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決定擴大戰局。然而,出乎其意料的是,中方予以強硬反擊,戰事驟然擴大。
值得注意的是,武藤等人的軍事打擊論主要根據還不在于其對華認知,而在于他們對國際局勢的判斷,尤其是對歐洲戰局的關注。當時,德國宣布重整軍備后進駐萊茵蘭非武裝區,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并受到國際聯盟的制裁,歐洲局勢日趨緊張。在這樣的形勢下,武藤等人從防備下一次世界大戰的觀點出發,對石原的政策抱有強烈的危機感,企圖完全確保華北的軍需資源和經濟權益。武藤認為:國民黨的外交政策是旨在恢復國家主權、恢復領土的“革命外交”,“絕無將來放棄滿洲”的意思,而是“想要(把滿洲)收回自己的國家”,并借助美英和國際聯盟的力量“對抗日本”,今后,它也肯定會“對日本拔刀相向”。對此,日本必須謀求“日滿合作”,進而“影響到中國本土”。武藤未把中國視為“盟友”,而是企圖逐漸把中國并為日本的勢力范圍。其背景則是要求確保日本的軍需資源和獲得市場,以備未來的國家總體戰。武藤一派得到了當時內閣和陸軍領導層的支持,石原莞爾的政治主張則一再被否定,人事方面也再難立足,最終黯然退出陸軍的決策核心。
五、結語
日本自1874年出兵臺灣以來,經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一步一步發展到七七事變——全面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有其內在的對外擴張邏輯。日本侵略擴張的首要目標就是中國大陸,而其“滿蒙”政策就是大陸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近代以來,日本從地理位置、經濟價值、國防意義等方面反復論證“滿蒙”地區之于日本的戰略重要性,主張歷史上較之中國,“滿蒙”與日本更為接近,為日本出兵占領“滿蒙”制造理論依據。20世紀20年代,永田鐵山、石原莞爾等接受過新式教育的日本陸軍“中堅層”憑借歐洲總體戰理論進一步為武力出兵“滿蒙”制造借口,并提出第一步占領“滿蒙”,繼而迅速以武力使中國屈服,然后進軍東南亞,最終和美國對決的戰略設想。隨后他們在中國東北進行參謀旅行,考察風土人情、軍政關系、守備情況、地理地形,據此提出必要時可以通過制造“謀略”(即發動事變)來促成侵略計劃的實施,發動九一八事變。
在發動九一八事變之時,石原莞爾曾提出為支持國家總體戰,僅憑“滿蒙”的資源遠遠不夠,還需河北省的鐵礦、山西省的煤炭等資源,必要時應占領“中國本部的要都”。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駐華日軍頻頻對華北地區進行武力侵犯,蠶食中國領土。到1937年,這一趨勢已形成了巨大的慣性和推動力。即使石原本人出于對國際局勢的考慮,轉而主張日本應暫緩武力控制華北,且他出于務實的考慮,認為日本國力尚不足以支持中日戰爭,應以“滿洲國”為據點,獲取戰爭資源,同時調整對華策略,先從政治和經濟上控制中國,但他的想法卻已很難獲得同僚的認可。當時蘇聯內部發生清洗,軍隊力量減弱,歐洲則為德國所牽制,武藤章等人認為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美英等列強不會介入東亞問題,日本發動對華戰爭“事不宜遲”,這一加劇對華侵略力度的政策已經成為主流。于是,石原在對華策略上與陸軍省、駐華日軍出現了較大分歧,并迅速被排擠出日本陸軍的核心。自此,日軍逐步陷入對華持久戰爭的泥潭,最終發動太平洋戰爭,走向毀滅,可以說是對總體戰理論進行了一場失敗的戰爭實踐。
永田鐵山主張的統制軍備進行國家總動員的理論、石原莞爾宣揚的最終戰爭論,為日本動員總體戰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也滿足了日本國家和軍人對外擴張、攫取資源、實踐戰爭的野心。然而,這種德式戰爭理論因不顧人民生存需要,煽動舉國體制,把中、美、蘇乃至整個東亞都卷入戰爭框架中,最終使日德兩國都遭受到了戰爭的反噬。
受歐洲軍事思想理論和戰爭實踐的深刻影響,日本陸軍中堅們預期一個崛起的日本將成為美國在亞太利益的威脅,因此急于為他們認為終將到來的日美戰爭做準備。可見,日本的侵華戰爭,是其全球稱霸戰略的一部分。其進一步襲擊珍珠港,對美國宣戰,固然有軸心國同盟配合德國歐洲戰場的考慮,也是日本一貫以來亞太戰略的體現。在這個意義上,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的侵華戰爭就已在世界戰爭體系之內,并發展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東亞也是二戰策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