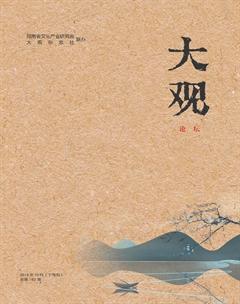浮沉之路
何青


摘 要:張洹出現在中國當代藝術拍賣市場上至今已有16個年頭,橫跨油畫、裝置、行為藝術與攝影的勤勞創作使他成為當代目前攝影中拍賣成交總額最高的藝術家。其攝影作品拍賣價格在2004年至2015年間步步高升,但從2016到2017年則略有降低,2018年稍有回暖,但仍和盛時差距甚遠。
關鍵詞:張洹;當代攝影;攝影拍賣
2018年11月25日下午,香港佳士得亞洲當代藝術專場第0257號拍品《泡沫系列》以28.8275萬元人民幣落槌。這是張洹2018年在藝術市場上的最后一件攝影拍品,也是2018年總共成交的兩件作品之一。相比慘淡的2016年和2017年,2018年的成交金額大于這兩年的總數之和。但如果查閱2005年至
2015年間的拍賣總額,張洹的攝影作品只有2009年度成交額略低,其他年份都遠高于2016年—2018年。那么可以提出問題:應該如何對張洹的攝影藝術品進行投資?
一、東村與紐約的遷徙
張洹的藝術是從北京東村開啟的。在此之前張洹以美術生考學,后成為美術教師,又移居北京進入中央美術學院研究院研修。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的前一年,張洹搬入北京藝術家聚居區——東村。東村里的藝術家成日無所事事,混跡在一起創作生活,張洹也因此認識了榮榮、馬六明、左小祖咒等游民藝術家。無所顧忌的、離經叛道的即興創作得到了他們的寵愛,于是張洹也開始學會將內心騷動的情緒經由行為藝術來表達,并用攝影的方式記錄下來。《12平方米》、《65公斤》以及里程碑式的作品《為無名山增高一米》等行為作品均創作于東村。東村塑造了張洹,但東村也容納不下張洹,1998年張洹帶著自己的藝術理想前往美國紐約。
在紐約的張洹繼續著不出名不罷休的行為表演,并多次參加國際重要當代藝術展,如1998年于舊金山現代美術館及紐約亞洲社會藝廊所舉辦的“內與外:新中國藝術展”,同年在紐約PS1當代藝術中心舉行的“朝圣—風與水展”等等。1998年9月,在由高名潞策劃下的“蛻變與突破:華人新藝術”展中,張洹以他的創作作品“為魚塘增高水位”被選為展覽目錄及媒體宣傳封面,也開始在國際藝術圈受到矚目。
二、拍場上刮起的“中國風”
2002年4月28日,張洹的作品首次登上拍賣的舞臺,20世紀90年代在北京東村創作的《12平方米》在香港佳士得20世紀中國藝術專場中以3.8萬人民幣成交,從此便開啟了張洹的拍賣時代。據雅昌藝術網所示,張洹目前個人最高價攝影作品為2014年11月22日香港佳士得秋季拍賣會成交的《家譜》(2000年作),成交價位496萬港元(391.34萬元人民幣)。這件作品在筆者統計的中國當代攝影作品拍賣排行榜中位于第三,僅次于王慶松的《跟我學》(2003年作)和艾未未的《摔破漢甕》(1995—2004年作)。截至2018年12月28日,張洹的攝影作品在中國(含港澳臺)共上拍126件,成交件數99件,成交率78%,總成交額為3998.162萬元,是目前中國當代攝影藝術品拍賣成交總額最高的藝術家。在所有成交的作品中,累計拍賣金額最高的三件作品分別為《家譜》(2000年作于紐約),成交12次,1718.23萬元;《泡沫》(1998年作于北京),成交14次,440.58萬元;《我的紐約》(2002年作于紐約),成交8次,338.9萬元。
《家譜》是目前最受市場青睞的作品,創作于紐約的艾姆赫斯特。張洹邀請了三位書法家在他臉上書寫“天、人、福、祿”等帶有中國傳統意味的字符和一個家庭的故事,并將 “愚公移山”四個字寫在腦門上。從早寫到晚,書法勞作和中國傳統文化吞沒了張洹的臉。他的解釋是“天黑的時候,我的臉已經成一片黑了,我的特征也隨之消失了,沒有人知道我是什么膚色,就好像我的身份沒有了,這個人消失了。”“其他的文字還有對一個人未來命運的預測,比如說顴骨的形狀代表什么,痣長在不同的位置意味著什么。人的命運難以琢磨,有一種神秘的東西在控制我們的命運。”書法和氏族這些令西方人倍感新奇的中國文化符號被張洹粗暴地運用在人的面孔上,生成了一種諱莫如深的視覺形象。但是在身體上進行書寫的張洹并不是第一人,早在1964年日本電影《怪談》里就出現了在臉部書寫的鏡頭。1997年彼得·格林納威的枕邊書也多次出現在身體上書寫的畫面。雖然張洹的表達內容有所不同,但其創作手法的創新性仍有待考量。因此,《家譜》這件作品的拍賣高價主要與西方語境下對中國文化的好奇和追逐有關,從純粹藝術價值和創造力的體現來說,并不是張洹所有作品中最高的一件。
《泡沫》與《我的紐約》在張洹的攝影作品拍賣紀錄中分別位于二三名,與《家譜》不同,這兩件作品中更強調個人情緒的表達,中國符號相對弱化一些。《泡沫》中張洹完成了十五次口含家庭不同老照片并在全臉涂滿肥皂泡的行為表現,人生如夢似泡影,一切都是短暫的也是被決定好的。但用這種兩者直接的混合來表達“吃掉自己、吃掉家庭、人生如泡沫”的觀點有一些牽強,而且選擇了15個同樣的泡沫除了數量上可以形成陳列以外,沒有感覺到其他的必要性,數量的含義在此失效了,并顯得有些莫名。相比之下,《我的紐約》直白很多,但這種全身貼滿生肉片在紐約街頭行走的行為藝術更像是一種滑稽的噱頭表演,方式同樣簡單粗暴,缺少了藝術的深思和創意的趣味。張洹的創作時間是2002年,當時也許較少有中國人會在西方公共空間做出這樣大膽的行為表演,所以從這個的角度來講張洹是成功的。但如果作為藝術品來評價,《泡沫》和《我的紐約》仍顯得粗糙,缺乏經過深思的表現方式與內涵。
三、早期作品更具升值潛力
佳士得官網曾有這樣一段話:“市場價值未必反映藝術品的歷史價值,中國藝術家的攝影作品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市場價值卻被低估。舉例而言,榮榮的攝影作品記錄了20世紀90年代初北京東村一些前衛藝術家的著名行為藝術表演。這些表演瞬間消逝,探索人體與自然及都市環境之間的關系,對現今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非常重要。”1994年,張洹與榮榮合作創作了《12平方米》,他渾身涂滿蜂蜜在逼仄骯臟的廁所里待了整整一小時,任由蒼蠅和飛蟲爬滿他的全身。對于藝術家來說這只是一場行為藝術,但對于生活在城市底層縫隙的人們來說這就是他們日常生活的寫照,也是一種心理狀態。1995年,張洹、馬六明、左小祖咒等11人策劃了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的經典之作《為無名山增高一米》,一米多高堆疊的層層人體給了觀眾對于性、自然以及人類生存的一切的豐富的解讀空間。1997年,張洹以《為魚塘增高水位》重現了《為無名山增高一米》的概念,對生命的局限、徒勞和無效再次進行表達。這些作品的拍賣巔峰均在2006年,之后便逐年下跌,除了《無名山》之外,《12平方米》和《為魚塘增高水位》從2010年以后甚少出現在拍賣場。這些早期作品生猛、自然且具有較高的社會意義,是有可能記入中國當代藝術史和攝影史的經典之作,因此有著更好的市場前景。與前文所述已在市場上拍出高價的作品相比,張洹早期的攝影作品更具升值潛力。
觀察圖2、圖3張洹攝影作品的成交金額圖表我們可以看到,張洹的攝影作品拍賣出現過三個小高潮,分別是2006年、2008年和2014年。2003—2006年是金額增長最快的幾年,在經歷了2008年奧運的中國熱后,2009年出現了第一次大幅下跌,成交量最低至38%。2009年到2014年進行了小幅回暖,而2014—2016年又跌了一段。在市場的浮浮沉沉中,雖然張洹的交易數據并不平穩,時而波動,但仍穩坐中國當代攝影藝術市場交易排行榜的首位。然而張洹去紐約后的作品與早期作品相比缺少藝術性,觀點也不夠明確,表達方式簡單粗暴,說的內容含糊其辭。20世紀90年代在東村的作品生猛有力,不需要太多語言闡釋也能感受到其藝術激情與思想,因此這些早期北京東村的作品更具有投資價值。張洹是藝術家工廠化創作的先鋒軍,開啟了中國藝術家工作室的新方式,他的整體上升空間取決于是否能在未來拿出更有力的作品,并在藝術史和攝影史上留名。
參考文獻:
[1]李欣.影像藝術品收藏與投資[M].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7.
[2]顧錚.世界攝影史[M].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2.
[3]馬健.收藏品拍賣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作者單位:
武漢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