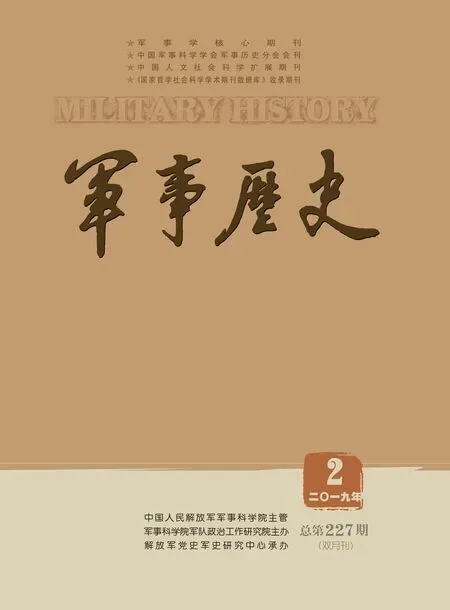從《尚書》“三誓”看三代早期國家的正統性觀念構建*
一個政權的存在不僅要有武裝力量作為支撐,而且需要國家正統性,亦或稱為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予以維系。①政治合法性,也稱政治正當性或正統性,自人類有政治生活開始,政治合法性即已成為一種必須的政治訴求,但作為一種現代政治學概念,最先由馬克斯·韋伯在其著作《經濟與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提出。馬克斯·韋伯認為被統治者對統治者命令的服從并非僅僅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還有對統治合法性的信仰和信任。依據信仰的內容不同,韋伯將人類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類型分為三種:法制型統治(正當性建立在平等公正的法律之上)、傳統型統治(正當性建立在“一直存在著的權威”之上)、卡里斯馬型統治(也稱魅力型統治,正當性建立在統治者個人的非凡品質和魅力之上),這三種純粹類型的統治在人類史上,總是以混合狀態出現。古代社會基本上以后兩種統治類型的混合為常態,即魅力型統治一般出現在非常狀態下,而傳統型統治則出現在常規時期。合法性理論在韋伯之后又經過了李普塞特和亨廷頓的改造,但此二人的著眼點在于以選舉和民主為基石的現代社會,其理論并不適用于分析古代社會。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主義者羅爾斯在20世紀70年代新的合法性理論思潮中提出以政治正義和良序社會為基準來構建政治合法性,盡管分析對象仍是現代民族國家,但其明顯的非西方化特征對我們有很大啟示意義。在中華文明早期,三代國家的建立均通過軍事手段完成,此在今文《尚書》之《甘誓》《湯誓》《牧誓》有所載。從“三誓”內容看,三代開國之君極為重視戰爭的理據,由于是奠定政權的王朝戰爭,這些理據亦彰顯著新政權的正統性觀念。通過對以“三誓”文本為代表的上古軍事誓詞進行剖析,不惟可以管窺早期國家正統性觀念之構建,亦對相關經史疑難的解決有所助益。
一
欲以“三誓”探析三代王朝正統性觀念,宜先說明何以聚焦《尚書》之《甘誓》《湯誓》《牧誓》三篇文獻,這便涉及“三誓”的性質問題。《湯誓》為商湯伐桀、《牧誓》為武王伐紂的戰前誓詞,此無疑義,惟《甘誓》所載何事,學界有所分歧。為方便敘述,茲列其文: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①《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7《夏書·甘誓》,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5頁。
除了上引傳世《尚書·甘誓》之外,《墨子·明鬼下》引載了幾乎一樣的文字,只是其題名為《禹誓》。《莊子·人間世》《呂氏春秋·召類》均認為禹伐有扈氏,而《呂氏春秋·先己》以及西漢的《書序》《史記》都力主夏啟伐有扈氏。由此,關于作誓的夏王就有了啟和禹的爭議。學者或有調和,主張禹、啟都討伐了有扈氏;或認為《甘誓》本是“無主的古文”,儒墨之說均為平添。②參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865頁。面對如此經史疑難,從早期國家政權正統性構建的視角,或有新意。
大禹依靠治水的功績,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其政權的建立具有充足的正統性,因此對諸侯以及外族的征伐也無須更多的借口。大禹在涂山會盟天下諸侯,防風氏族長來遲一步,竟被禹公開處決,而無須過多的理由;而對待三苗等外族,禹的戰前誓詞也較為簡略,《墨子·兼愛下》中還引用了一個《禹誓》,其文載大禹言:“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封諸君,以征有苗。”③《新編諸子集成·墨子校注》卷4《墨子·兼愛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78頁。于此,禹在討伐有苗的理由就是,有苗興起了,以天命來討伐。與此不同,《甘誓》中的夏王討伐有扈氏時,不僅有普通戰前部署,恩威并施,在宣揚“天用剿絕其命”“天之罰”之前還著重強調了“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這與大禹誅殺防風氏、討伐有苗時的態度有很大不同。從政權正統性的角度看,《甘誓》的夏王更可能是夏啟。
啟伐有扈氏不是單純的王朝最高權力對諸侯叛亂的平定,其中觸及了更為深刻的政治背景。文獻記載,大禹死前欲效仿堯舜,將共主之位讓與伯益,然他的臣僚都擁護夏啟,于是啟繼承了共主之位,以父死子繼的形式開創了世襲的夏王朝。益或稱伯益,《漢書》稱其為“少昊之后”,又《史記·秦本紀》載“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秦之先伯翳,嘗有勛于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學界公認,少昊族與秦之先民均為東方部落,傳說益在堯舜時代便嶄露頭角,最大的功績是助禹治水,據禹亦試圖將天下禪讓之。《夏本紀》記載:“十年,帝禹東巡守,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④《史記》卷2《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3頁。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此說基本承襲于《孟子·萬章》,其主張益讓天下于啟。與之不同,古本《竹書紀年》則提出了“益干啟位,啟殺之”的說辭⑤參見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頁。,類似的尚有文獻提出禹名義禪讓于益,實際讓啟自取之的觀點。對此爭議,美國學者艾蘭用結構主義的視角予以考察,頗具啟發意義。艾蘭認為,啟在與益的權力爭奪中取得了勝利作為基本史料,儒家與法家以不同的政治哲學觀點予以利用,造成了截然相反的歷史敘述,但不能以此抹殺啟與益奪權斗爭的真實性。⑥參見艾蘭:《世襲與禪讓——古代中國的王朝更替傳說》,孫心扉、周言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而益的奪權失敗則直接導致了有扈氏的叛亂。
有扈氏,學界有同姓諸侯說和東夷說兩種不同的觀點。同姓諸侯說主要依據的先秦文獻是《世本》,其文曰:“有扈,姒姓”,又說:“姒姓,夏禹之后。”⑦[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陳其榮增訂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第11頁。后人多襲承此說,或以發揮。劉起釪據《左傳·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認為將觀、扈與各代異姓諸侯叛亂并提,說明觀與扈都是異姓諸侯。又據《昭公十七年》提及東夷的少昊部落有“九扈”一支,認為有扈氏為東夷,此說可從。①參見《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卷48《昭公十七年》,第2084頁。而伯益正是東夷部落的族長,因此啟殺伯益后引起了有扈氏的激烈反抗。《史記·夏本紀》記載:“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②《史記》卷2《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84頁。道明了兩個問題:其一,啟伐有扈氏的原因是后者不服,不服的原因正是其政治領袖伯益在權力爭奪中失敗;其二,從“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可反觀,有扈氏作亂得到了其他諸侯的響應,其他諸侯不服的原因則可能與夏啟開創的家天下統治模式有關。
由此,《甘誓》所記載的“甘之戰”與《湯誓》所載“商湯伐桀”、《牧誓》所載的“武王伐紂”有共同的性質,即奠定新政權統治的王朝戰爭。也正因此,夏啟面對有扈氏的叛亂,一方面要整備軍隊,加以動員,積極備戰;另一方面,他必須加緊政權正統性建設。在討伐有扈氏時,夏啟祭出了“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的口實,這既是對有扈氏的聲討,也是夏王朝正統性構建的基石。
值得說明的是,自古史辨運動風起以來,古籍、古史遭到了普遍質疑,但是不同于今文《尚書》中《堯典》《皋陶謨》《禹貢》等文獻那般爭議之劇烈,專家普遍認為《甘誓》《湯誓》《牧誓》文本雖經后儒整理,卻基本保留了各自時代的歷史面貌,是了解三代政權初始的難得史料。由此,以《尚書》“三誓”為依據,探究早期國家正統性觀念的構建是切實可行的研究途徑。
二
記錄三代王朝戰爭戰前誓詞的“三誓”均提出了戰爭理據,這些理據正是新政權對其正統性觀念的構建。前文已引《甘誓》全文,其戰爭理據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現分列《湯誓》《牧誓》所載的戰爭理據: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臺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臺?’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③《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8《商書·湯誓》,第160頁。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④《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11《周書·牧誓》,第182頁。
引文內容主要包括天帝信仰、官人之法、安民之政以及祭祀傳統四個方面,下文以此為切入,探究早期國家政權正統性觀念的構建。
(一)天帝信仰與早期國家政權。早期國家的先民往往存有原始思維,宗教是其信仰的基礎,三代時期的最高信仰便是“天”與“上帝”,《甘誓》《牧誓》提出的“天之罰”,《湯誓》中成湯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均是這種信仰的體現。而早期國家正統性觀念的構建,往往以天帝信仰為最主要的依據。
學界通常認為,商人信奉上帝神,周人信仰天神。卜辭中,上帝神不僅可以呼風喚雨,還有決定戰爭勝負、農產豐欠、商邦禍福等神權,而“帝臣”“帝工”“帝史”等帝之屬官的存在更體現上帝神的至上性。①參見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68頁。商人以上帝信仰為基礎,又將上帝與商族構建起“擬血緣”關系。一方面,以“大邑商”為核心的邦國聯盟成員均是上帝的子嗣,所謂“王司敬民,罔非天胤”②《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10《商書·高宗肜日》,第176頁。;另一方面,從周人宣揚的“改厥元子”(《尚書·洛誥》)可反觀,只有商王族才是上帝的“元子”,即長子。由此,“大邑商”就是眾邦之長,這也正是商代復合式國家結構在正統性觀念上的體現。殷周鼎革之際,周人將上帝和天神合一,形成了“皇天上帝”(《尚書·召誥》)的信仰。周統治者通過“改厥元子”代替了商人的共主地位,繼承了商代“帝·元子·子”的倫理政治結構。隨著新生政權的日漸穩固,作為天下共主的周人儼然成為了諸侯之君,于是又構建出“天·天子(王)·臣”的新政治倫理關系。可見,《湯誓》“畏上帝”,《牧誓》宣揚的“天之罰”都有著鮮明的時代性,其不僅是王朝戰爭的理據,更為新生政權的正統性奠定了基礎。
由于周人接受了商人的上帝信仰,經過周人整理的《詩》《書》等早期文典習有以“天”代“帝”的現象,這就會造成觀念的混淆,那么,《甘誓》所載“天之罰”是夏人的思想還是周人的思想的竄入呢?由“威侮五行”的含義看,前者更為可從。關于“五行”,學界有“水、火、金、木、土”五種物質說、五星的運行說、“仁、義、禮、智、信”五種品質說、五段時節說以及五官說等多種觀點。③五種物質說,主要依據《尚書·洪范》提出的“五行”,即水、火、金、木、土,五種物質。后儒在此基礎上,肆意發揮,認為“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由此提出了五種品質說。民國來,隨著學者對《洪范》成書年代的重新審視,五物質說、五品質說也隨之受到了質疑,在此基礎上,以劉起釪為代表的“五星運行說”得以提出。與之相對,以金景芳為代表的學者依舊堅持“五種物質說”。其中,五星運行說的觀點正與“天之罰”相吻合。世界歷史表明,早期農業文明國家的天文學都十分發達,古代埃及、蘇美爾文明如是,華夏文明亦如是。新石器晚期的陶寺遺址便發現有觀測天文的石柱,不惟如此,《禮記·禮運》載孔子“欲觀夏道”而“得夏時”、成書于戰國的天文物候典籍名為《夏小正》恐非古人無故附會,夏王朝應該是十分重視天文歷法的。如此,夏啟在王朝戰爭的“甘之戰”,祭出有扈氏“違背天道流行”“將受天的懲罰”這類的戰爭理據是令人信服的,而對“天時”的重視也成為了夏王朝立國的正統性觀念之一,雖歷經久遠,文獻不足,但至東周賢達仍識記之。
“三誓”所及天、帝作為早期國家的主要信仰,既是王朝鼎革的戰爭理據,又是三代新政權爭相構建正統性觀念的主要對象。
(二)官人之法與早期國家政權。《禮運》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④《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卷21《禮記·禮運》,第1414頁。在古代的政治觀念中,選賢任能、為官允公是政權穩定的基本前提。《堯典》載帝堯之賢在其用人,如咨事于四岳、“乃命羲、和”之官,平秩四方四時,綱紀天下;⑤參見《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2《虞書·堯典》,第119頁。帝舜所以能威服四方也在于其“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⑥《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3《虞書·舜典》,第128頁。《左傳·文公十八年》也載,舜能任用“八愷”“八元”,“流四兇族”,有大功二十是他為天子的主要原因。⑦《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卷20《文公十六年至十八年》,第1862頁。夏商以降雖然家天下,統治階層仍深諳人是治亂之源的道理,《殷本紀》言成湯能任用伊尹、女鳩、女房等賢臣⑧參見《史記》卷3《殷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4頁。,《詩經·棫樸》序言“文王能官人”。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卷16-3《大雅·棫樸》,第514頁。在早期國家政權構建過程中,官人之法不僅昭示著統治者的德行、亦能折射出王朝的治亂之象。
“三誓”對用人失政的討伐,即體現了選官制度在政權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甘誓》聲討有虞氏“怠棄三正”,①怠棄三正,大傳言“正色三而復者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鄭康成解釋為“天地人之正道”,馬融以為“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經師聚訟紛紜。劉起釪結合出土金文與傳世文獻,指出“三正”“多正”等皆指諸大臣官長。參見劉起釪:《釋〈尚書·甘誓〉的五行與三正》,載《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192頁。正,長也,《詩經·節南山》“覆怨其正”,毛傳如是。②參見《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卷12-1《小雅·節南山》,第440頁。《爾雅·釋詁》也言“正,長也”③《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卷2《釋詁下第二》,第2576頁。。《周禮·太宰》“而建其正”,鄭玄云“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④《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卷2《天官冢宰第一·大宰》,第649頁。。大盂鼎言“二三正”等(《集成》02837),張亞初、劉雨總結為“正是長帥的統稱”⑤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58頁。。《甘誓》指出有扈氏的主要罪愆就包括廢置辱慢其大臣官長,一方面暗示了有扈氏德行的敗壞,另一方面官長被怠棄意味著管理秩序的混亂。《牧誓》稱罪商王時言其“惟婦言是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商王紂非但不任用賢能,反倒嬖于婦人,妲己之言是從,⑥參見《史記》卷3《殷本紀》,第105頁。又大肆招攬四方邦國的有罪逃亡之徒,任使為大夫卿士。紂王此行不僅敗亂了商王朝的統治綱紀,還致怨于四方諸侯,直接導致了外服統治秩序的瓦解。《湯誓》雖未討伐有夏末王用人政策的弊亂,夏桀的相關失政卻在后世流傳。《立政》記載周公回溯夏商之際的歷史,稱夏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⑦《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17《周書·立政》,第230頁。夏桀的罪行還包括他棄置先代舊官,失去了畿內大族的支持。可見,三代的用人之法除了選賢任能外,仍需滿足世家大族世官的政治需求,《禮運》稱之為“大人世及以為禮”⑧《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卷21《禮記·禮運》,第1414頁。。
世族世官是先秦時期主要的選官之法,《堯典》稱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逸周書·度邑》言商湯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⑨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卷5《度邑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70頁。即殷有三百六十族共同構成了商王朝的統治基礎,怠棄各血緣家族族長而不任,無異于自毀政權。《甘誓》言“怠棄三正”,夏桀則“弗作往任”,商紂不僅以罪人為卿大夫,甚至“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連親族兄弟都不能任官為政。“三誓”以此稱罪于敵國,一則在輿論上進一步瓦解對方政權的支撐力量,再則亦是為本國舊族“封官許愿”的政治愿景,表明了新政權構建過程中,己方世族和對方來歸之族皆有一席之地。要之,“世族及官”不僅是“三誓”歷史背景下的政治策略,亦是早期國家政權構建的制度支柱。
綜而言之,“選賢去惡”和“選任親族”是三代理想政治與現實政權需要的官人之法。早期國家在政權正統性的構建過程中,既要宣稱對理想政治模式中明君賢臣的渴望,又要滿足血緣家族的政治訴求。而在其政治實踐中,以世族世官為基礎、輔以賢臣為政,這樣的用人之法能在較大程度上穩固統治基礎、厘定政治秩序。“三誓”從不同層面昭示敵國用人之弊,既是討惡行善的政治宣稱,也是對歷史經驗的認知與總結。
(三)安民之政與早期國家政權。盡管文獻所見有關早期國家階級分化的表述不甚明顯,但從其中“民”“庶”“眾”“國人”等詞的用例可見先秦時期至少已有平民階層的出現。作為早期國家主要的勞動生產者與政權支持者,令平民安居樂業是維護政權穩定的必要條件,因此《尚書》中記載了很多執政者有關“安民”的論述。《皋陶謨》載大禹與皋陶討論為政之道,“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知人與安民同列為治國的基本。⑩參見《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4《虞書·皋陶謨》,第138頁。周公告誡康叔管理東土時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釋詁》云:“保,康安也”,“乂,治也。”也將安撫民眾作為施政中的重要一環。①《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14《周書·康誥》,第203頁。當執政者作出重大決策時,也必須參考民眾的意見。如盤庚遷殷時曾遇“民不適有居”,反對遷都,盤庚不得不于王庭召集“眾”進行訓誡以便政令順利施行。②《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9《商書·盤庚上》,第168頁。《梓材》說:“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洪范》也說:“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可見平民的意見在決定王朝大事時具有相當的作用。③參見《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12《周書·洪范》,第191頁。三代的統治者雖然掌握了國家權力,仍知百姓安定才能維護其統治的穩定性,因此在早期國家政權的構建中安民作為施政的一環,其結果直接影響到王朝的興衰。
《湯誓》和《牧誓》中對于時王暴虐百姓的聲討集中體現了安民之政的實施與政權穩固的關系。《湯誓》言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遏,止也”,“割,奪也”,夏邑,“《白虎通·京師篇》云:‘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④《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8《商書·湯誓》,第168頁。孔穎達傳:“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⑤《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8《商書·湯誓》,第168頁。《湯誓》指出夏桀不能愛惜民力,使民安居,反而奪其收斂,因此失去了民眾的支持。有眾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一方面指責夏桀德行敗壞,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喪失內部支持加速早期王朝的崩潰。《牧誓》載武王討伐商紂云:“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孔穎達疏:“奸宄,謂劫奪。”⑥《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卷11《周書·牧誓》,第183頁。商王不僅任用奸佞,侵奪民眾,還通過嚴刑峻法壓制反對聲音,“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⑦《史記》卷3《殷本紀》,第106頁。由是內外離心,殷人弗親,諸侯益疏,直接導致內外服制的衰落與商王朝統治秩序的瓦解。
安民是先秦時期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政策。為實現這一目標,統治者要做到愛惜民力、聽取眾意。在早期國家構建政權正統性時,不僅需要取得“天”的認同,也需要獲得庶人的支持。為維護國內社會秩序,就要求執政者在政治實踐中合理征用民力,確保民眾能夠安心從事生產,并時常征詢其意見。安民之政是鞏固統治的基礎,“三誓”對敵方暴虐百姓的討伐,反映了三代政權構建中民意的重要性。
(四)祭祀傳統與早期國家政權。不僅天帝信仰、官人之法、安民之政,在上引《牧誓》所舉戰爭理據中,“昏棄厥肆祀弗答”也是武王伐紂的口實之一,即從宗教祭祀之角度構建周代統治的正統性。正如《左傳·成公十三年》所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早期國家政權的統治基礎依賴于軍事力量的威懾與祭祀傳統對不同階層的維系,足見祭祀傳統也是早期國家政權正統性構建的重要方面。
《禮記·表記》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⑧《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卷54《表記第三十二》,第1642頁。從卜辭看,商代社會也確實籠罩在宗教的氣氛之下。除前文所及上帝神,商人還信仰祖先神和自然神,其中尤對祖先神的祭祀最為重視,卜辭常有“百羌百牢”(合集300)、“羌三百”(合集297)等對祖先神貢獻大量犧牲的記載,誠如專家所總結:“就祭品情況看,殷人祭祖的犧牲、人牲常以數十、數百為限。”⑨晁福林:《論殷代神權》,《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而在商人的觀念中,祖先神又可以大致分為“與商王有血緣關系,但年代久遠、世系不可考祖先神”“與時王有明確世系關系的祖先神”以及“部分對商王朝發展有功績的舊臣”。⑩朱鳳瀚:《商周時期的天神崇拜》,《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可見,商人通過祭祀祖先的宗教形式維護著王族與異族統治階層的特殊地位,此為商代“神權”社會下國家政權正統性構建的基柱。
商代晚期,因于王權的逐步強化及帝辛獨斷的個性,卜辭及殷彝中鮮有祭祀祖先的記載了,可見商紂晚期確實放棄了對祖先神祭祀的傳統。①參見王暉:《周原甲骨屬性與商周祭禮的變化》,《歷史研究》1998年第3期。周武王由此指責其“昏棄厥肆祀弗答”。克商以后,周代統治者在宗法分封制度框架內逐步建立起系統性的廟制、喪服制度,使得各階層貴族依據血緣疏近進行不同的祭祀儀程,在制度方面確保了祭祀傳統服務于周家天下的穩固。
三
如上所述,從“三誓”體現的早期國家正統性觀念主要包括天帝信仰、官人之法、安民之政與祭祀傳統等方面,不惟如此,“三誓”還包含了關于戰爭與早期國家問題的諸多內容。如,三代政權政治理性的漸進覺醒和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中“義戰”理論的產生。
從《甘誓》中夏啟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側重的是天道與用人,到《湯誓》中商湯批判夏桀“遏眾力”所體現的愛惜民力、順應民心,再到《牧誓》中周武王所列紂王“婦言是用”、怠棄親族、不敬先祖、任用佞臣、殘害“百姓”,并說其將受“天之罰”,周初的正統性觀念已然多元且完備。由此,“三誓”所載戰爭理據的差異確實體現了三代王朝政治理性的逐步覺醒。值得玩味的是,《湯誓》中,有眾問“我們的王不體恤我們,為何舍棄我們的農事不做而去討伐夏氏?”商湯給出的原因是夏王“遏眾力”,這固然體現了商湯順應民意,愛惜民力,可是這里商湯以“遏眾力”的方式,去討伐夏桀“遏眾力”,存在著明顯的邏輯矛盾。面對商“眾”的如此質疑,以“遏眾力”為理由去討伐夏桀顯然是商人統治集團的失策,這既反映出了商代對民力的愛惜,對民意的重視(優于《甘誓》),也暴露了其政治理性的欠缺(不及《牧誓》)。
戰爭是國家發展進程中暴力沖突的最極致體現,但以三誓為代表的中國早期國家戰爭誓詞卻以順天、應民、討罪為號召,一方面成為早期國家正當性構建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也為戰爭本身增添了政治倫理化的道德審判色彩。早期國家鼎革之際的三場重要戰爭,經過這一正統性號召,也成為先民記憶中順天應人、吊民伐罪的“義戰”楷模。與此相應,“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②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69頁。“興滅國,繼絕世”③《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卷20《堯曰第二十》,第2535頁。等也成為“義戰”所必須遵守的原則。而儒者所謂“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等說,④參見《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卷14(上)《盡心章句下》,第2773頁。更是對此“義戰”的極端宣揚。若溯源探流,可以發現“義戰”是三代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也是推進早期國家向秦漢一元化成熟帝制國家演進的重要力量。“義戰”在中國早期國家誕生之初即相伴而生,又存續于三代多邦林立的獨特社會政治生活之中。這種戰爭模式即是對征服者的一種道德約束,要求師出有名,必須順天應人;又是眾多小邦弱族對于新領導者的政治期許。在此意義上,“義戰”也成為中國早期倫理政治的重要表征。
綜上,《甘誓》記載的是夏啟于甘地伐東夷有扈氏的戰爭誓詞,與《湯誓》《牧誓》一樣都是反映三代政治正統性構建的重要史料。具體而言,《尚書》“三誓”不僅反映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正統性構建包括天帝信仰、官人之法、安民之政與祭祀傳統等諸多方面的內容,獨具早期國家特色。而且通過“三誓”,也可以了解三代早期國家政治理性有著漸進覺醒之過程。不惟如此,以“三誓”為代表的戰爭思想也是中國古代軍事“義戰”理論的重要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