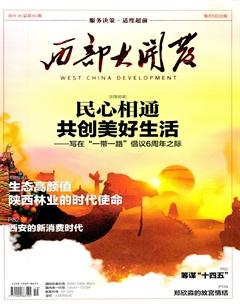鄭欣淼的故宮情結
王遂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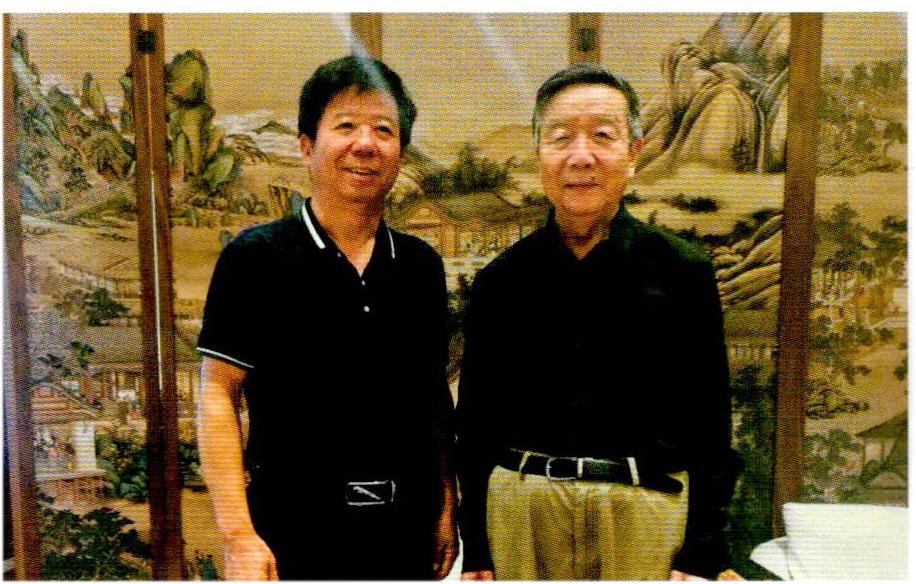


談石鼓再話文物風雨南遷
年逾七旬的鄭欣淼儒雅和善。風神健朗。談起文化,字字珠璣,嚴謹暢達:“文化既是一個民族內在的精神基因和外在的精神標識,也是一個民族根本的價值依托和力量源泉。”
如果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無疑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中華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源于黃河流域的中華文明已開始形成;公元前2000年左右,第一個世襲制的統一政權夏朝建立;公元前17世紀,甲骨文出現。文字系統的成熟和廣泛使用,使得中華文明的歷史譜系得以追溯。中華民族從文明源頭處逐漸積淀形成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得以代代相傳。
竇德盛先生對大篆書體情有獨鐘,經過60多年的研習與領悟,逐漸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被譽為“中國大篆走向世界第一人”。出于對老部長創建故宮學、重視石鼓研究的敬意,竇德盛恭敬地贈送了篆書作品“石鼓重器國之文脈”,話題自然就談到了石鼓文。
作為故宮曾經的掌門人,鄭欣淼對石鼓文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他說:石鼓在唐初發現于咱們陜西陳倉北坂,也就是今天的寶雞石鼓山,+面石鼓分別刻有大篆四言詩一首,共計718字。秦始皇當年統一文字就是以它為母體,康有為稱其為“中華第一古物”。2013年1月1日,《國家人文歷史》雜志將“秦石鼓文”列入全國九大鎮國之寶。
越是稀罕的東西命運就越離奇,背后的故事就越精彩。鄭欣淼的語速不快,每個字似乎都沾了些故宮的古意,深沉而雋永。
他說,當年由于發現石鼓的鄉民大多都不識字,鼓上文字的年代又特別久遠,鄉民們就把石鼓當作天賜神物供奉起來。這件事雖然當時轟動朝野,但并沒有得到統治者的足夠重視。后來,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看到石鼓之后非常震驚,上書朝廷,建議將這些石鼓運置太學院妥善保管。出于事與愿違的激憤,韓愈懷著悲憤的心情,寫下了傳誦一時的《石鼓歌》。
是的,研習傳統文化,這是必須背誦的經典作品。今日提及,似乎又增添了些許厚重,些許滄桑,些許觸及靈魂的感慨、責任與擔當。至今依稀記得歌論及發現的過程:“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做鼓的過程:“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石鼓文的特點:
“辭嚴意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保存的價值:“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
唐元和八年,時任鳳翔府尹兼國子祭酒的鄭余慶看到了韓愈當年的奏章后再次上書,石鼓由石鼓山遷移到雍州(今鳳翔縣)孔廟之中。不幸的是,其中的一面鼓(作原鼓)在途中丟失了。唐末,戰亂起,余下的石鼓再次散落民間。
清風徐來,茶香裊裊。古意盎然的氛圍中彌漫著時光深處的情緒和節律,在場的歷史繼續演繹偶然與必然的因果。
轉眼就到了宋朝。宋仁宗也對石鼓傾情至深,就讓在鳳翔主政的司馬池(司馬光的父親)將石鼓進獻入宮。因為當時只找到了九面鼓,司馬池就命人私下做了一個贗品,不然,如何復命?直到北宋皇佑四年,失傳238年的作原鼓,終于被民間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向傳師在訪遍關中之后,在一個屠戶的家中找到了。遺憾的是,這戶人家將作原鼓的上半部分鑿去,中間挖空,做成了一個舂米的石臼,并把邊緣部分當成了磨刀石。因此,鼓上的七行字也磨損的只剩下了四行。
至此。十面石鼓終于團圓了。
接下來,竇德盛講述了幾個細節:宋大觀二年,酷愛金石書畫的宋徽宗在讀了有關石鼓的文獻之后。下令將石鼓運到汴京(今河南開封)。為了彰顯石鼓的珍貴,保護上面的文字,他下令將黃金磨成粉調成糊糊,全部填涂了鼓上的文字。后來,又將這些石鼓運到皇宮深處,只供他一個人觀賞。歷經滄桑的石鼓,上面的文字已由最初發現的718字,磨損的只剩下432字。公元1125年,靖康之變爆發,金人南下侵入汴京,將石鼓等大批文物運至燕京。由于石鼓重量大,運輸困難,加之當時的金人并不怎么了解中原文化,誤認為石鼓最珍貴的地方就是文字所注的泥金。于是金兵把金子全部摳掉后,將石鼓丟棄在了荒郊野外。
值得慶幸的是,到了元朝初年。大學者虞集無意間在荒草叢中發現了這些珍貴的石鼓,洗刷干凈移至國子監存放。從此。石鼓在北京度過了元明清三個朝代。
談到石鼓后來的命運,鄭欣淼接著說,1931年事變爆發。北京很快進入了動蕩時期。安然度過了700多年的石鼓,再次遭逢命途多舛的厄運……
這段歷史,江蘇省文聯主席章劍華歷時15年創作了長篇紀實文學“故宮三部曲”——《變局》《承載》《守望》,以《承載》改編的電視劇《國寶奇旅》藝術地再現了當時的情景。
1933年1月,日軍進入山海關,華北屏障失守,局勢險惡,故宮作為重要的文化寶庫,此刻全然暴露,危如累卵。面對北平隨時可能失守的危險,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自1月31日起將故宮所藏文物分批裝箱運往上海,并由國民政府指令北平市政府及交通部門全力協助,以求完成故宮文物南遷計劃。如此危局長途運輸,險境重重,極有可能導致大量文物失散。因此,計劃既出。輿論嘩然。魯迅就曾以反對故宮文物南遷專門賦詩:“闊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針對洶涌而至的輿情。南京《救國日報》發表重磅文章《為遷移故宮古物告政府》,敦促國民政府速做決策:“故宮古物,若不遷移,設不幸北平被敵人占領,將古物劫奪而去,試問中國將何法以恢復之?行見中國文明結晶,供敵人戰利品,可恥孰甚!”文物不能再生。數千年的文化精華萬不能毀于日寇,南遷已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談及文物南遷,鄭欣淼對這段歷史了如指掌,猶如歷歷在目:1933年2月5日晚,故宮博物院第一批文物自太和門搬出,至5月15日運走文物5批。共13427箱又64包精品文物在上海暫存之后,于1936年開始分5批遷入了專門新建的南京朝天宮庫房。1937年8月13日,日軍轟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根據戰時文物宜散不宜聚的原則。南遷文物分“南線”“北線”“中線”共3批向西遷移:80箱文物走“南線”,經長沙、貴陽。1938年抵安順,1944年12月接運到四川巴縣;7286箱文物走“北線”,經寶雞、漢中、成都,1939年7月抵峨眉;9369箱文物走“中線”,經漢口、宜昌、重慶、宜賓,1939年7月抵樂山。
2003年1月1日中午,臺北故宮博物院前院長秦孝儀先生在臺北凱麗飯店設宴招待鄭欣淼一行。
“我與秦院長的交往與感情,主要是心靈上的相通,趣味上的相投。第一次見面,我送先生兩冊北京故宮的文物圖錄,他則送我一套《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以他書法作品制作的2003年掛歷、還有他書寫的六體‘千字文,又帶來訪問大陸期間所寫詩歌讓我欣賞。”秦孝儀院長雅好收藏,尤用心于文房清玩,諸如牙、骨、竹、木雕等各類文房用具,頗多精品,馳譽臺灣收藏界。2000年,他在卸任故宮院長之際,將這些畢生的收藏以及明清善本舊籍等,悉數捐獻給臺北故宮博物院。
文人交往,自然以作品為媒。看到毛公鼎,鄭欣淼即席填詞,《百字令·參觀臺北故宮博物院》:“翡翠雕工,毛公鼎古,償愿看瓊久……風云變色,國寶暌離久。但有故宮名兩岸,一脈相傳深厚。”秦孝儀現場奉和《鵲橋仙》:“故都如夢,流光似水,張緒當年風柳。……結繩中絕,余燔漸熄,誰是補天高手?幾時日月復光華。須先是河山重繡。”2004年,秦孝儀在臺北舉辦了個人詩文書法文房展覽。爾后,又在自己家鄉——湖南省博物館舉辦了“筆力詩心——秦孝儀詩文書法文房展”。鄭欣淼應邀出席并寫詩相贈:“游子忽焉老,故園秋亦深。湘兮岳麓氣,楚些汩羅魂。文筆驚殊域。收藏富寶珍。忘年情誼重,相見語諄諄。”
200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這一年北京故宮的大事、喜事特別多,其中就有與兩岸故宮交流有關的事。
2005年4月28日,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邀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攜夫人一行來故宮參觀。這是60年來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正式對話。因為具有載入史冊的歷史意義,鄭欣淼至今記憶猶新:連戰一行于28日上午到達北京,下午即來故宮博物院參觀,由我親自陪同講解。走過午門,首先來到太和殿前的廣場,并在這些宏偉的古建筑前合影留念。在參觀了中軸線的保和殿、乾清宮、坤寧宮、御花園后,連戰在乾清宮前題寫了一幅對聯:“昔日禁城百年滄桑難回首,今日故宮幾番風華齊向前”,橫批為“繼往開來”。我代表故宮向連戰贈送了仿制的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和《故宮珍寶》《故宮鐘表》兩本書籍。在故宮漱芳齋小憩之時,連戰突然問我:“您說話好像有陜西口音?”我說自己就是陜西人,我問他,您在臺灣可以吃到陜西的小吃嗎?他說,羊肉泡饃、涼皮都能吃到,但是厚厚的鍋盔吃不到,他一邊說著一邊伸出右手,把拇指和食指張開到五六厘米的樣子比劃著。我從中感受到了濃濃的鄉情。
另外一段趣聞是:這一年9月25日,臺灣著名學者、作家李敖在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陪同下,參觀了故宮武英殿的《盛世文治——清宮典籍文化展》以及太和殿、景仁宮和鐘表館,在漱芳齋看了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我向李敖先生介紹了故宮大修、文物清理和學術研究等工作。我曾在鳳凰衛視上看到他講過,北京故宮有“宮”無“寶”,臺北故宮有“寶”無“宮”,我便介紹了北京故宮的藏品狀況,他聽后才知北京故宮收藏的豐富與珍貴,對自己所說連聲表示“懺悔”,并說要把他收藏的一幅字捐獻給故宮。2006年3月,劉長樂先生轉送來李敖先生給故宮的捐獻,并有他的錄像錄音,他說了如下的話:我請鳳凰衛視劉長樂先生、王紀言先生到故宮博物院去見我所佩服的鄭欣淼院長,履行我去北京時的一個宿諾。我在故宮博物院當場答應,將我收藏的“孤魂野鬼”——乾隆皇帝的書法捐出來。這是一件國寶,是乾隆皇帝在我國五代時期書法家王著的《千字文》后邊寫的跋語。它與原件早已分家,流落到臺灣,陰差陽錯到了我的手里。這個字本來就是在故宮寫的,今天我把它捐出來,使它回到故宮,成就了一段佳話。所以不但我回來了。我還把“孤魂野鬼”帶回來了。最后,李敖深有感慨地說:再也不要去逛故宮博物院了。因為看了以后你會“天良發現”,把你手里所有的“贓物”捐出來。我回到臺灣拖了五個月,最后才履行這個諾言,又不甘心,又很高興。2009年10月,鄭欣淼赴臺灣出席雍正展開幕式,專門看望了李敖先生,感謝他的捐贈,代表北京故宮贈他《韓熙載夜宴圖》的復制品,他則回贈臺灣20世紀70年代影印的《山谷老人書贈其甥雅州張大同卷》(為張大千藏品)一函二冊。
雖然久居京城,鄭欣淼依然說著一口地道的陜西話。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談及家鄉,烙印般的記憶里涌現的還是舊時情景:“沉沉小院向南開,覆地繁陰有老槐。耕讀相傳差亦足,溫飽自奉實堪哀。三秋稼穡人勞頓,四處求知我去來。聞道故園貌非舊,此心憶往尚如孩。”(《雜感》十首之一)情系桑梓的赤子情懷,溢于言表。
咳珠唾玉幸承教,又看題詩八斗才!
此刻,窗外的古槐正悄悄地幻化為故鄉的“老槐”,在游子心中站立成精神的圖騰,溫暖靈魂,撫慰鄉思。
鄭欣森簡介
鄭欣淼,1947年1 0月生,陜西省澄城縣人。1970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0年7月參加工作。先后在中共澄城縣委、渭南市委及陜西省委工作,曾任陜西省委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和陜西省委副秘書長。1992年1 1月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組組長。1995年9月任青海省副省長。1998年12月任國家文物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2002年9月至2008年11月,任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黨組成員。2002年9月至2012年1月,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為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9月故宮博物院成立故宮研究院,受聘為院長。
鄭欣淼還曾擔任一些重要學術和社會兼職:中國魯迅研究學會會長、中國紫禁城學會會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博物館》雜志(全球中文版)學術顧問、中華詩詞學會會長、中國博物館協會名譽理事長。同時,還受聘為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兼職指導教師、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導師、浙江大學故宮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特聘教授,以及南開大學兼職教授、南開大學故宮學與明清宮廷研究中心名譽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