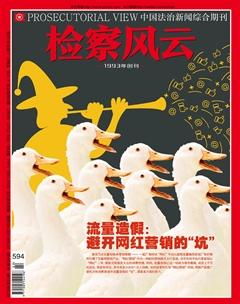無私無我 何有“三難”
王文昌

張岱《夜航船》載有“為三難”,原文如下:“鮮于侁,字子駿。方新法行,諸路騷動。侁奉使九載,獨公心處之。蘇軾稱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為‘三難。司馬光當國,除京東轉運,曰:‘子駿,福星也。”
鮮于侁,宋朝頗負盛名的一代賢吏,歷任京東路轉運使、集賢殿編修,在陳州知府任上去逝。揆諸歷史,蘇軾對于同朝為官的鮮于侁評價可謂恰如其分。鮮于侁在任上不避豪強,勇于任事,許多貪官污吏應聲落馬,受到嚴懲,可謂“上不害法”;當時王安石在全國范圍強力推行新法,深得皇帝信任,炙手可熱,鮮于侁為了百姓的利益,為百姓仗義執(zhí)言,把官司一直打到神宗皇帝那里,可謂“中不傷民”;蘇軾被貶,眾叛親離,鮮于侁卻說:“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愿也。” 蘇軾路過揚州,鮮于侁不避嫌疑,親自為蘇軾設宴洗塵,寫下“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的動人詩句,可謂“下不廢親”。
蘇軾的“為三難”值得我們認真玩味并努力實踐。為官“三難”,何以難?不易做到,所以難。何以不易做到?“私”字存內,“我”字當前!心中總是橫著一個“我”,眼前總是一個“私”,何以放開手腳?何以坦坦蕩蕩?何以義薄云天?
為此,還想起了清代的鄭板橋。鄭板橋不僅字好,畫好,詩好,其實為官也是敢作敢為,有聲有色。在濰縣任知縣時,山東發(fā)生水患 ,百年一遇,濰縣更烈,幾乎餓殍遍野。鄭板橋下令“大興修筑,抬遠近饑民赴工就食”。有人提出應當先層層上報朝廷,他斷然拒絕:“此何時,俟輾轉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自任之。” 一句“有譴,我自任之”斬釘截鐵,擲地在聲,今天讀來仍然讓人熱血沸騰。鄭板橋這種不避公罪、敢作敢為的背后,是“衙齋臥聽瀟瀟雨,疑是民間疾苦聲”的深厚為民情懷。
《禮記·孔子閑居》中記載了孔子與子夏的一段對話。子夏問孔子如何為政?孔子答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并解釋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像天地日月一樣無私,自然無畏,無畏才會直道而行,以法為大,以民為大,以公為大。凡事“義之于比”,這里的“義”便是國家利益、人民冷暖,便是法比天大,說到底,就是“我自無我”,不計利害。任何一個官員,如果能夠做到這“三難”,就一定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利于人民的人”。
“三難”并不難,只在去一個“私”字,只在去一個“我”字。倘如此,看似波詭云翳,立定高處之時,自然煙消云散,雨霽風清,一片光明。
為政“三難”,一千多年前的鮮于侁做到了,今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共產黨人更應當做到,也完全有理由、有能力做到!
圖:王儉? 編輯:夏春暉? 38675320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