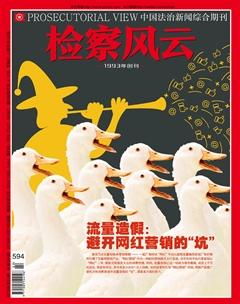舊王孫
劉強
中國近代繪畫史上的“南張北溥”歷來為世人所重,南張即張大千,北溥即溥心畬。從畫名上講,溥心畬較之張大千遜色不少,但從藝術成就上看,兩人難分軒輊。畫家于非闇曾說:“張八爺(張大千行八)是寫狀野逸的,溥二爺是圖繪華貴的。論入手,二爺高于八爺;論風流,八爺未必不如二爺。南張北溥,在晚近的畫壇上,似乎被南陳(陳洪綬)北崔(崔子忠)、南湯(湯貽芬)北戴(戴熙)還要高一點。”
近日,上海龍美術館舉辦了“舊王孫”館藏溥儒書畫展,精選館藏的近60套作品,借溥儒書畫用印“江山為助筆縱橫”“心畬翰墨”“飛鴻”區(qū)分為三大板塊,分別呈現(xiàn)溥儒的山水(由宋、明名家入手,師法古人、師法造化,清貴超凡、意境悠遠);道釋、花鳥(靜逸脫俗、深具個性);人物、動物、書法(別開生面、意趣橫生)的面貌。這是龍美術館繼2013年館藏溥儒書畫展之后,時隔六年,再次舉辦特展,以追慕大師藝術風采。

層臺臨水(設色絹本)
舊時王孫
溥儒(1896—1963),原名愛新覺羅·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自號羲皇上人、西山逸士、舊王孫、松巢、釣鯨魚父等。清道光帝曾孫,恭親王奕?之嫡孫,末代皇帝溥儀之兄長,詩文、書畫皆頗有成就。

鐘馗套鬼(設色絹本)
溥心畬少時天賦異稟,5歲時拜見慈禧太后,慈禧夸獎其曰:“本朝靈氣都鐘于此童”。6歲啟蒙,拜京師耆宿為師。10歲時習滿文和英文。15歲時入貴胄法政學堂讀書(后并入清河大學,18歲時畢業(yè)于清河大學)。1917年,奉母命同清末陜甘總督多羅特之女羅清媛結理,羅亦好丹青,兩人感情篤深,可謂琴瑟和鳴,頗有趙管之風。1947年農(nóng)歷七月初八,羅清媛卒于西山,這使得溥心畬悲痛難抑,后每逢七夕,常觸景生情,時有悼念忘妻之作。
辛亥革命后,溥心畬在母親的督促下,在西山戒臺寺隱居讀書習字,故有號“西山逸士”。喜作駢儷之文,因駢儷近畫,故而習之,并漸漸走上繪畫道路。溥心畬學畫沒有老師傳授,全仰賴自己的揣摩體悟,誠如此次畫展的介紹,所謂“師法古人、師法造化”。溥心畬曾自述:“我是沒有師承的。從前我家里藏的古人名跡很多,舉凡晉唐宋元各朝代都有。我把這些真跡取來臨摹,再讀書,再觀察真山水真事物。”1937年,母親過世,溥心畬傷心欲絕,為置辦喪事,不惜將家中所藏陸機的《平復帖》以四萬元賣給了張伯駒。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溥儀成為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溥心畬極為抵制,寫下了《臣篇》以明其志,指責溥儀“九廟不立,宗社不續(xù),祭非其朔”。他自己也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多次拒絕日本人的求畫和高官厚祿的誘惑,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但對于清朝皇室成員和遺老遺少則又飽含了復雜的個人情感。時人贈以“舊王孫”的雅號,溥心畬欣然接受,并請王福庵為其刻印“舊王孫”一方,常現(xiàn)其書畫作品。溥心畬作為中國人對于日本侵略是深惡痛絕的,但作為皇室后裔,他對于滅寂的清王朝也充滿著依戀和懷舊之情。
北宗為體
溥心畬初學繪畫由“南宗”入手,他在談到自身繪畫經(jīng)歷時提到,“初學四王,后知四王少含蓄,筆多偏鋒,遂學董、巨、劉松年、馬、夏,用篆籀之筆。始習南宗,后習北宗,然后始畫人物、鞍馬、翎毛、花竹”。
繪畫上的“南北宗”最先是由明代董其昌提出來,董其昌所倡導的“南宗”直接影響了清初“四王”,并成為明末清初最正統(tǒng)的流派。在技法上,“南宗”注重用筆平淡樸實,用墨秀潤蘊藉,而氣勢外露的風格則被認為是用筆的大忌。他們一般先由淡墨起稿,反復皴擦,漸施濃墨,畫面虛實交替,層次厚重。“四王”中的王原祁在談到用墨時也強調“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

山水畫(設色紙本,局部)
董其昌及王原祁的用墨和格局直接影響了初學繪畫的溥心畬。雖然溥心畬初學時并無師承,以自學自悟的方式臨摹了大量清宮內(nèi)府所藏的宋元明清古書畫,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影響有清一代的統(tǒng)治畫壇的“四王”畫風。但逐漸深入研究和體會“四王”之風后,他感覺到了這種風格中的流俗呆板之弊端,溥心畬在其《寒玉堂書畫論》一書中提到,“董文敏畫山,起于淡墨,以深墨破之,秀潤之色,溢乎筆端,然非古也”。

高士圖(設色絹本)
溥心畬轉而投向“北宗”,作畫直接用濃墨起稿,先定輪廓,略帶皴擦,格局形成后,再賦色,最后在不足之處稍作彌補。“北宗”的山水畫注重勾斫,山石輪廓明晰,多用斧劈皴,氣勢恢宏,而“四王”用筆綿軟,忌棱角分明,秀潤有余而氣勢不足。溥心畬的書法雖然力追二王,有瀟逸的帖學之美,但在繪畫方面,他卻提倡以篆隸之筆入畫,強調線條的金石之力,這就與“北宗”的線條要求不謀而合。
藝精多面?
當溥心畬的山水畫風格逐漸打開局面之后,其繪畫題材也日益廣泛,此次畫展中展出的道釋、花鳥、人物、動物等畫作,皆展現(xiàn)了其作為大師級藝術家藝精多面的才華。
他的花鳥、鞍馬作品繼承了宋人的筆法和氣韻,其論及花鳥畫家時,所舉大多也為宋人,“宋文與可竹,揚補之梅,溫日觀葡萄,鄭所南蘭,趙子固水仙:皆習之積年,專乎一物,精氣形骸,與之俱化。故其神理超然,獨擅千古。”但他對宋人花鳥畫法的繼承又不拘一格,沒骨、雙勾、淺絳、重彩,無一不融會貫通。
溥心畬家藏一幅宋人易元吉的《聚猿圖》,他時常臨摹補習,故亦有多幅猿畫行世。在《寒玉堂書畫論》一書中,溥心畬還專章“論猿”,“古人畫猿有嘉善之意。畫猿,只以墨筆點成。白猿惟用墨漬,工筆次之。易元吉入山結廬,窺獐猿出沒,畫極動靜之妙。牧溪、梁楷皆喜畫猿,世有傳本。兩宋畫院多善畫猿,不獨此三子也”。
“舊王孫”溥心畬,以其豐厚精深的文化底蘊,融詩、書、畫、印為一體,瀟灑明麗地寫就了文人畫的最后一筆。1949年,溥心畬浮海去臺,先后任教于臺灣師范大學和香港新亞學院,與張大千、黃君璧并稱“渡海三杰”。雖身在孤島,但其對故鄉(xiāng)的思念卻終身未減,“已近清秋節(jié),兵煙處處同。山河千里月,天地一悲風。兄弟干戈里,邊關涕淚中。京華不可見,北望意無窮”。
編輯: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