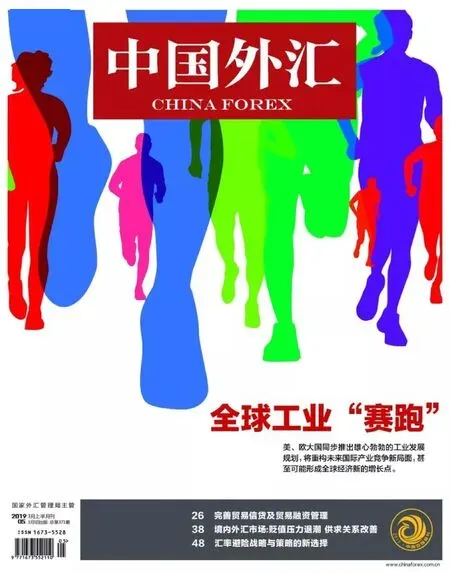原則監管國際應用的啟示
文/孫永泰 編輯/閆靜
作者單位:外匯局吉林省分局
2008年的金融危機,引起了各國對金融監管理念和監管方式的反思。各國普遍意識到過度強調規則的明晰化、體系化、制度化,既無法滿足當前金融混業經營、跨界發展、創新驅動、權益保護的時代訴求,也不符合及時識別系統風險、阻斷并防范風險蔓延、保護金融市場安全穩定的根本要求。主要國家實行的分業監管、行為監管、過程監管的微觀規則監管,在遏制金融風險跨行業、跨地區、順周期、多渠道快速蔓延方面明顯力不從心。而加拿大“混合監管”、澳大利亞和荷蘭“雙峰監管”強調的宏觀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的原則監管模式,則有效抵御了金融危機的沖擊。這引起了各國的廣泛關注。
各國監管模式的選擇
原則監管模式的優勢在于能夠從整體上把握監管目標、監管方向和監管策略,厘清監管問題所在,調整監管重點的靈活性較大,有利于金融創新和發展。同時在該模式下,監管者與金融機構的密切關系也能促使監管政策的執行過程更加精準順暢,及時解決問題。規則監管模式則著眼于規則的具體性、行為的統一性、條件的一致性、事實的既定性、過程的規范性和激勵的明確性。兩者不是相互對立的關系,而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即規則監管需要原則監管的宏觀把控,原則監管需要規則監管予以落實和支撐。
在各國金融監管實踐中,監管模式的選擇受國家文化、管理體制、金融市場發展情況、內外部經濟金融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監管方式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單純采用規則監管或原則監管的情況。
英國在審慎監管不足的情況下提出“更多的原則性監管”,將三元雙峰監管整合為二元雙峰監管,進一步明確了審慎監管與市場行為監管的關系和邊界,強化金融機構高管責任,并在金融科技創新領域大力倡導基于原則與協調的“監管沙盒”實驗。
美國提出風險性和原則性監管是金融監管的長期目標,對其《多德-弗蘭克法案》進行調整,精簡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涵蓋范圍,并在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強化了市場行為監管的作用。
日本也在積極探索規則監管和原則監管的最優結合,南非則是在市場行為監管能力嚴重缺失的背景下進行“雙峰監管”模式改革。
不難發現,各國金融監管改革都是強化監管短板,而不是用原則監管取代或剔除規則監管。現行的監管模式已形成強調防范系統風險、維護市場秩序、倡導金融發展的監管原則與聚焦行為合規性管理、業務溝通協調的監管規則的統一體。
協調原則監管與規則監管
為了更好地滿足總體金融風險防范的要求,實現原則監管與規則監管的優化組合,筆者對我國現行的外匯管理模式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要強調外匯業務監管的系統性,注重目標結果和風險導向。隨著業務類型和業務渠道的不斷創新,外匯業務規模急劇膨脹,且越來越呈現出關聯性、復雜性、綜合性、隱蔽性,僅就單筆業務越來越難以判斷交易的真實性合規性。因此,外匯監管應從對單筆業務的關注轉向對業務的整體態勢、系統走勢、類型特征、渠道模式的關注,從系統管理的高度綜合看待具體的外匯業務,形成業務操作的規則體系和業務監管的邏輯框架。外匯管理不應僅從規則監管出發,還應適時逐步引入原則監管理念,全面把握市場主體的行為特征,提煉行為風險點,從外匯管理的重點和難點出發,確立外匯業務監管在宏觀與微觀風險防范、穩定市場秩序、創新業務發展等方面的并舉目標。以業務效果和監管效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明確目標實現方式,有效防范跨境資金異常流動風險。
二是要嚴守保障真實合法用匯需求的底線,明確責任邊界與要求。第一,外匯業務是平衡國際收支、保障涉外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環節,外匯監管應確保機構和個人合理合法用匯需求的正常辦理,滿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合理訴求。第二,厘清監管部門、銀行和用匯主體在外匯業務中的權責邊界。銀行應從業務受理入手,強化對事前和事中業務規則的把握,承擔審核交易真實性合規性的職責,把好外匯業務監管的第一道關口。
總之,應進一步協調原則監管與規則監管,形成規范的外匯業務監管框架,充分發揮原則監管的統領性和規則監管的針對性,實現原則監管與規則監管的優化組合,以形成監管的最佳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