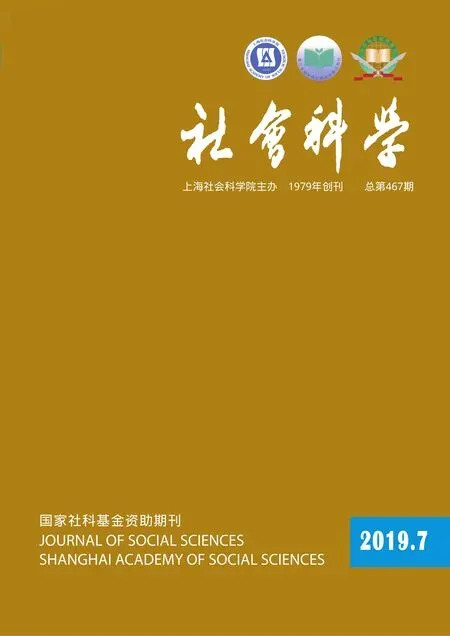從載體更新到議程再造:網絡民主與“大數據民主”的比較研究*
徐圣龍
引 言
早在2011年,麥肯錫公司在《大數據:下一個創新、競爭與生產力的前沿》報告中就指出,“數據已經無所不在,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每一個經濟體、每一個組織以及每一個數字技術的使用者之中”,并且,“對于世界經濟而言,數據可以創造非常重要的價值,包括提高企業和公有部門的生產力和競爭力,為消費者創造大量的經濟價值”[注]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June,2011,pp.1-2.。到2016年,麥肯錫公司再次重申并強調了這一觀點,即大數據對于社會生活,特別是經濟生活將帶來革命性的轉變,其指出,“五年后,我們仍然堅信這一觀點,即大數據的潛力遠沒有‘夸大其詞’。事實上,我們認為,2011年有關大數據的報告只是揭示了冰山一角。今天,伴隨著數據及其分析手段的巨大增長,有關數據的應用和機會發生著相應的改變”,“改變的步伐正在加速”,“這一系列變革的趨勢正在開啟‘工業解體’,并提出全新的組織挑戰”[注]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The Age of Analytics:Competing in a Data-driven World”,December 2016,p.21.。
在市場領域,大數據的應用已經較為普遍,從最初的“炒作周期”(Hype Cycle)開始進入“部署階段”(Deployment Phase)。Matt Turck認為,“經過數年時間的發展,大數據開始從炫酷的新技術,發展到部署在生產中的核心企業系統”[注]Matt Turck,“Firing on All Cylinders:The 2017 Big Data Landscape”,April 5,2017,http://mattturck.com/bigdata2017/.,這意味著大數據實質上擁有了改變生產交往的能力,它正在按照自身的屬性和特點重塑既有的生產流程和商業形式。在此基礎上,麥肯錫公司斷言,“引領趨勢的前沿公司,正在利用其能力,以全新的思維方式解決業務問題。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引入了數據驅動(Data-Driven)的商業模式,這令整個行業感到意外”[注]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The Age of Analytics:Competing in a Data-driven World”,December 2016,p.1.。在大數據深刻改變著生產交往和商業形式的同時,這種“數據驅動”的模式也必然會波及整個社會,它預示著一種潛在的、革命性的變化正在發生,即“數據驅動世界”(Data-Driven World)的到來。
作為政治領域主要構成的民主治理,無疑會受到大數據帶來的“數據驅動世界”的沖擊。這一沖擊將在何種層面、以何種方式展開,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一般而言,政治領域的應用要落后于市場實踐,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大數據對于政治領域的革命性影響,可能會“遲到”,但不會“缺席”。基于此,研究大數據對于民主交往潛在的、革命性變革,具有重要價值。因此,筆者將以政治領域的民主交往為對象,基于網絡時代與大數據時代的區分,闡釋大數據對于民主治理的革命性影響。
一、“大數據民主”的內涵與研究路徑
如何界定大數據對于民主交往的影響,需要明確兩個前提:第一,大數據的本質屬性是什么,這決定了在何種框架內探討大數據與民主的關系問題。雖然這一問題并不直接指向“大數據民主”,但是,具有方法論的意義。第二,大數據區別于工業社會以及互聯網的最大特點是什么,這決定了如何具體展開“大數據民主”的特殊性。這一問題直指“大數據民主”如何區別于既有的民主范式,打破有關民主實踐的常規性認知,特別是工業社會民主交往及其補充形式——網絡民主的局限。
其實,這涉及到區分網絡時代與大數據時代的必要性。固然,理解大數據對于社會變遷的影響,從大數據的屬性和特點出發即可,但是,因為在非生產領域,對于大數據革命性變革的認識還存在模糊地帶,尤其是不少對于大數據條件下民主治理的研究,仍然延續了網絡民主的范式,所以,既要從大數據的屬性和特點出發,闡釋大數據對于民主治理的改變,更要從大數據時代與網絡時代的區分出發,說明大數據的不同之處以及它對民主治理的革命性影響。
(一)基于物質能力的民主交往變遷
如何理解大數據對于政治交往的影響,特別是對于民主治理的改變,目前還沒有較為共識性的看法。在商業領域,對于大數據的革命性認知已經較為普遍,比如“工業解體”、“組織再造”、“數據驅動”、“智慧社會”、“信息社會”等概念,都承認大數據將帶來不同于工業時代的社會變遷,它不是簡單地將工業社會的“產品”通過互聯網加以擴散和傳播,它是要再造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態。在這一新的社會形態中,大數據具備自身的物質基礎(即生產力),重塑原有的生產流程和商業形式(即競爭力),并波及社會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這是理解大數據時代的一個前提性認知。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可以將大數據界定為一種物質能力。作為物質能力的大數據,它的革命性影響將在兩個層面展開:第一,生產層面,大數據會“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通過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獲得有巨大價值的產品和服務,或深刻的洞見”,即大數據可以創造價值;第二,交往層面,“大數據是人們獲得新的認知、創造新的價值的源泉;大數據還是改變市場、組織機構,以及政府與公民關系的方法”,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會因為大數據而發生改變[注][英] 維克多·邁爾-舍恩伯格等:《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盛楊燕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頁。。
大數據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改變,本質上預示著一場有關生產及交往方式的革命性變遷。正如戴維·博利爾(David Bollier)指出的,“社會的各個系統緊密相連,隨著全新的軟件工具和技術被發明出來,并用于數據分析,以獲得有價值的預測和判斷,一種全新的‘知識的基礎設施’正在成為現實”[注]David Bollier,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Big Data,Washington,DC:The Aspen Institute,2010,p.1.。這里,“知識的基礎設施”(Knowledge Infrastructure)正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物質生產能力。馬克思曾明確指出,“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形式、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頁。,因此,大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能力,它的出現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交換和消費形式”。換言之,在既有的生產和交往形式下,新出現的大數據,必然會改變原來的“生產、交往和消費”等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內容。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4頁。,大數據正是這一帶來社會交往變遷的物質生產能力。
將大數據定義為一種“知識的基礎設施”,作為一種物質的生產能力,構成了研究大數據及社會交往變遷的邏輯起點。固然,這個論斷可能還存在一定的爭論,但是,又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大數據正在帶來人類社會的整體性變遷。既然作為一種物質的生產能力,大數據也會要求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交往形式,其中,包含政治的交往方式,特別是民主治理的內容。可是,在現有有關大數據條件下民主治理的研究中,多是從網絡民主的視角出發,忽略大數據的物質生產屬性,這很容易造成停留在網絡民主的范式之中思考大數據對于民主治理的影響。事實上,大數據帶來的政治交往變遷潛力,已經遠遠超出了網絡民主的范疇,這一切的起點正是在于大數據作為“知識的基礎設施”,將改變整個人類的社會生活。
筆者將大數據時代的民主交往定義為“大數據民主”。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生產改變交往,交往包括形式和內容。大數據對于民主交往的改變,涵蓋民主形式和民主內容兩方面,形式方面受大數據的技術特性影響,內容方面受大數據的物質屬性影響,這直接帶來民主內涵和外延的變遷,預示著全新民主實踐范式(包括民主概念、民主構成要素、民主結構、民主功能等)的生長[注]筆者認為,大數據提供了全新的民主實踐范式,它在民主參與、民主結果等方面,解決了前大數據時代在民主實踐上的諸多困境,提供了全新的民主實踐可能。參見徐圣龍《大數據與民主實踐的新范式》,《探索》2018年第1期。。目前,“大數據民主”這一概念并不是約定成俗的用法,還存在諸多爭議和模糊之處,因此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規定:第一,“大數據民主”用于指稱政治生活中大數據的應用所帶來的民主實踐變遷,并不是指大數據自身發展是否需要民主化的問題;第二,“大數據民主”特指大數據作為一種物質生產能力,其對于政治領域民主交往的影響所產生的全新民主實踐范式;第三,“大數據民主”并不是類似于既有的網絡民主、電子民主等民主形式,它需要置于生產與交往的邏輯關系中加以考察;第四,“大數據民主”只是描述大數據時代民主實踐變遷的初步概念,并不是絕對準確或不容置疑的概念界定,不過,大數據要求既有民主實踐的適應性轉變卻是發展趨勢,并將在未來成為客觀事實。
(二)“大數據民主”研究路徑的確證
一般而言,民主的研究路徑可以區分為定性和定量兩大類。定性的民主方法主要是將民主的理想范式加以規定,并將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實踐通過理想范式加以評價,以提出民主改進的方法。后來,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的興起,民主的規范研究方法開始“退潮”,民主的量化研究開始流行開來,即民主科學,特別是圍繞民主選舉的測量研究。但是,在前大數據時代,民主科學的研究方法并不屬于自然科學的范疇,相反,其只能納入社會科學領域,而社會科學領域又被稱之為“準科學”。其中原因有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有關民主交往過程的全部數據,無法有效收集、存儲;第二,即使存在民主交往實踐的相關數據,也缺乏挖掘民主海量數據的能力,以實現民主交往的“科學化”。正因為如此,工業社會民主實踐的科學多數時候都是“樣本科學”,即通過樣本研究,“映射”整體情況,從而描述民主實踐活動。
“大數據民主”的研究路徑主要建立在大數據的技術特性基礎之上,它將徹底扭轉現有民主科學方法的局限性,同時也會影響到民主的規范研究方法。正如鄧肯·沃茨(Duncan J.Watts)所指出的,之前,“有關社會網絡的數據只是圍繞一些小群體的一次性的粗略數據”,“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參與者的自我描述,這其中有著大量的主觀偏見、觀點錯誤和模糊論述”,相反,基于互聯網的溝通和交互的社會網絡研究改變了這一局限,“一方面,我們可以實時觀察數以百萬計的個體基于真實影響的行為選擇,另一方面,計算機技術也可以使我們模仿和處理海量的社會網絡中的個體行為”,因此,“社會網絡科學”出現了[注]Duncan J.Watts,“A Twenty-first Century Science”,Nature,Vol.445,February 1,2007,p.489.。作為其中的民主網絡,它同樣因為海量數據的收集、存儲、管理和分析的應用,實現了民主的科學研究方法。在大數據的背景下,民主的科學研究將不再依賴于“民主樣本”,因為,“樣本即總體”,大數據對于民主科學方法的改變正是在于“不用隨機分析法這樣的捷徑,而采用所有數據的方法”[注][美] 維克多·邁爾-舍恩伯格等:《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盛楊燕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頁。,前提也在于民主交往相關數據的收集和挖掘正成為可能。
另外,“大數據民主”也會影響傳統的規范研究方法。在規范研究方法中,通過“理想類型”的標準衡量民主交往實踐,其中,因果關系的探究是主要方面。但是,大數據將會改變民主方法中的因果邏輯。基于民主交往的全數據和數據挖掘,可以充分釋放民主事實,即相關關系,而不是基于民主概念的邏輯演繹過程。因為,基于假設的因果邏輯,一方面,其被證實的難度和成本都非常大,很難獲得確證性結論;另一方面,即使是“緩慢的、有條不紊的因果關系”[注][美] 維克多·邁爾-舍恩伯格等:《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盛楊燕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頁。,也存在僵化和教條的可能,這反而會阻礙民主實踐的發展。與之相對,“相關關系分析法更準確、更快,而且不易受偏見的影響”,并且,“通過去探求‘是什么’,而不是‘為什么’,相關關系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了這個世界”[注][美] 維克多·邁爾-舍恩伯格等:《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盛楊燕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5、83頁。。“大數據民主”對于民主方法的改變是全面的、徹底的,不管是民主科學研究方法還是民主規范研究方法,都會受到大數據技術的影響,發生實質性轉換,提供全新的民主內容,這又構成民主議程得以再造的方法論基礎。
但是,在現有有關“大數據民主”的研究中,多是沿用了網絡民主的范式,沒有從大數據的生產屬性、特別是它的技術特性出發,展開民主治理的相關研究。這里存在兩類研究誤區:第一,將“大數據民主”等同于網絡民主或電子民主。比如,在《“互聯網+”政治:大數據時代的國家治理》一書中,作者認為,“電子民主是新技術平臺下民主發展的一種新載體。它實質上就是公民切實、全面參與民主運作程序的一種民主形式。故公民的切實和全面的參與是電子民主區別于以往其他民主形式的最典型的特征”[注]高奇琦等:《“互聯網+”政治:大數據時代的國家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頁。。這里,作者將大數據時代的民主治理等同于“電子民主”。第二,將“大數據民主”認定為豐富和拓展了現有的網絡民主和電子民主,比如,有學者認為,“互聯網的勃興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使得人人擁有麥克風,人人都可以通過網絡終端查閱、轉發、評論公共事件和公眾人物。公眾的生活在賽博空間(Cyberspace)和現實時空中穿梭,關注政治和政治參與的熱情日趨高漲,自然而然地也就推進了民主政治”,并且,“大數據時代的網絡‘大民主’依托網絡平臺天生具有開放性、平等性、互動性”,其表現形式“與‘文化大革命’時期‘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式的‘大民主’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只不過政治營銷的媒體從紙媒體變成了富媒體”[注]陳潭等:《大數據時代的國家治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251頁。。這里,作者雖然將大數據時代背景下的民主實踐界定為“大民主”,不過,“大民主”與之前的網絡民主、電子民主并無實質性差異,只是在開放性、平等性、互動性等方面獲得了進一步的擴大和增強。
筆者認為,理解“大數據民主”,首要在于明確大數據的根本屬性,即物質生產能力。在此基礎上,基于生產與交往的關系,從大數據的技術特性出發,包括對于海量參與的吸納、對于非結構化參與的有效處理、對于相關關系即事實性關系的發掘等,才能充分理解大數據對于民主治理的革命性影響。否則,又會落入網絡民主的研究范式,只是將“大數據民主”理解為豐富和拓展了工業社會民主交往的形式,忽略大數據在生產領域已經產生的具有革命性和顛覆性的物質能力。
二、網絡民主對民主載體的更新
網絡的出現無疑沖擊著原有的工業社會,正如阿爾文·托夫勒所描述的,“一個新的文明正在我們生活中出現”,“它的深刻意義,就像一萬年前發明農業的第一次浪潮對人類解放的變革,或者如同工業革命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所帶來的震撼世界翻天覆地的變化”[注][美] 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譯,新華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確實,網絡的出現影響了工業社會的生產及交往方式,怎么夸大其革命性意義都不為過。只是,這種改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以最樂觀的估計,也要幾十年才能完成。正因為如此,一方面,網絡的出現正在以“點滴式”改變著社會交往,包括政治交往;另一方面,在真正完成這一革命性轉換之前,它仍然需要依附于既有工業社會的生產和交往形式。托夫勒將這一轉型中的歷史階段界定為“革命性的前提”,筆者認為,這是對過渡時期的最好注腳,在這一階段,“我們是舊工業文明的最后一代,又是未來新文明中的一員”,“我們許多個人的煩惱,痛苦和轉向,都能從第二次浪潮與第三次浪潮之間的巨大沖突,在我們個人和政治制度中所引起的矛盾里找到根源”[注][美] 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譯,新華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頁。。網絡對于民主交往的影響,也正是建立在這一邏輯前提之上。
網絡催生民主交往的改變,但是,這一改變是以既有的民主交往為依據的。換言之,網絡所帶來的民主新內容、新形式,是運轉于工業社會民主實踐之中的,而不是脫離現實語境,演繹出全新的民主實踐形態。這是理解網絡與民主關系的基本出發點。在此之外,網絡民主的發展也在推動著全新民主實踐形態的形成,這一生長過程伴隨著物質生產能力的革新以及經濟政治結構的迭代。這時,全新的民主交往將因為生產交往的改變而成為事實,網絡民主正是構成其前期準備和孕育過程。
(一)網絡豐富和拓展民主實踐的形式
網絡對于民主交往的改變,比較早的論述如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認為,“如果民主意味著個體權利的具體表達和對公職人員的決定權利,那么,在網絡空間和數字身份的影響下,現在就需要一個全新的概念來描述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關系”,其中,政治過程受到電子網絡的影響,“產生了全新的去中心化的對話方式,創造了人機結合的全新形式,全新的個體和集體的‘聲音’、‘身影’、‘交互’,已經成為政治組成和政治集團的全新構成”[注]Mark Poster,“Cyber Democracy:The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Sphere”,1995,http://se.unisa.edu.au/vc~essays.html.。政治過程中的民主交往因為網絡的介入,正在變得和之前大不相同,甚至需要被重新定義。不過,新出現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內容和形式,還遠不足以改變現實政治中的民主實踐過程,換言之,網絡的出現只是豐富和拓展了既有民主實踐的載體和形式,工業結構下的民主生活也僅僅是迎來了存量調整和增量改變。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網絡民主不是獨立的民主形態,而是媒介與民主新的結合形態,它的突出特性就是為參與者提供了一個‘對話的廣場’和‘互動空間’,重現了‘廣場政治’的某些要素,豐富和拓展了民主的內涵”[注]郭小安:《網絡民主的概念界定及辨析》,《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
正因為如此,不少學者提出了對網絡民主的警惕和防范,主要原因也在于:作為過渡形態的民主交往,網絡民主并不能獨立為一種完整的民主實踐范式,相反,它需要依附于工業結構下的民主實踐,這在帶來一系列全新要素的同時,也有可能打破工業社會民主交往的“脆弱”平衡,即網絡民主宣稱的價值目標、程序規則、善意結果并不一定能夠實現,甚至可能造成完全相反的結果。比如,有學者明確指出,“網絡技術政治功能的另一個方面,即它的專制主義特性”,與之對應,即會產生依托網絡技術的帝國主義,“網絡技術帝國主義可以表述為:掌握網絡核心技術和強大網絡資源的國家,通過網絡技術傳播其政治文化,影響甚至左右若干國家的政治文化,進而實現特定政治目的的網絡技術政治壟斷”[注]婁成武、張雷:《質疑網絡民主的現實性》,《政治學研究》2003年第3期。。確實,這種擔心是合理的,一方面,網絡民主在民主實踐特別是民主載體方面,創新較多,這無疑宣示工業社會民主交往更新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網絡民主依附于既有民主實踐,更不能取代工業社會的民主交往,那么,過分夸大網絡民主的實效,甚至用網絡民主取代既有民主實踐,這都可能帶來相反的結果,即“‘網絡民主’的發展很可能超出了現實社會所具有的監控能力,導致政治秩序的紊亂,使民主走向反面”[注]曹泳鑫、曹峰旗:《西方網絡民主思潮:產生動因及其現實性質疑》,《政治學研究》2008年第2期。。
其實,對網絡民主的批評和質疑,根本還是在于網絡民主并不能獨立為一種民主實踐范式,是屬于新興民主實踐興起過程中的過渡形態,是依附于工業社會民主交往的重要補充和創新形式。明確了這一點,則可以較為客觀地評價網絡與民主實踐的關系。事實是,網絡的出現催生了既有民主實踐的改變,特別是在民主形式和民主載體方面,很多原有的民主實踐方式都實現了互聯網化,而一些新興的互聯網民主形式也方興未艾,這無疑是網絡改變民主實踐的重要表現。網絡對于民主實踐的改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現有民主的信息化,即利用網絡信息技術鞏固和加強民主,如電子選舉、電子投票等;二是對現有民主的重塑和拓展,如網絡加強了直接民主的成分,重塑傳統的代議民主形式;三是網絡引發的新的民主形式,如網絡公共空間的協商對話、電子議政廳、電子廣場、在線民主等”[注]郭小安:《網絡民主的概念界定及辨析》,《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這三個方面的改變大大拓展了民主實踐的載體。
總體而言,“網絡作為一種技術媒介,它可以改變民主的作用形式”,并且,“技術對于民主的影響往往局限于治理方式的更新和改變”,“網絡技術可以從治理方式上改變民主的面貌,但不可能從國家形式上顛覆代議民主制度,網絡民主與代議民主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可以相互作用,共同補充”[注]郭小安:《網絡民主——媒介與民主關系的新形式》,《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這一有關網絡民主的共識性認知,至少可以得出兩方面的結論:第一,網絡的產生并沒有顛覆工業社會的民主交往實踐,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網絡仍然依附于工業社會的生產關系和交往形式,這一點上,它與大數據的生產屬性存在本質差別,網絡民主包含于工業社會的生產與交往關系之中。第二,網絡確實帶來了某些新的要素,這些要素影響到工業社會的民主交往,特別是在形式和載體多樣化方面。但是,既有民主實踐仍然支配著網絡民主的運轉過程,網絡所具備的技術特性還不足以重塑工業社會的民主交往,這一點與大數據的技術特性存在根本差異,特別是在海量參與和非結構化參與方面。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作為拓展和豐富工業社會民主交往形式和載體的網絡民主,仍然包含于工業社會民主實踐過程之中。
(二)網絡民主為“大數據民主”準備的條件
網絡對于民主交往的影響,雖然附著于工業社會的民主實踐過程,但是,改變也是真實發生的,并且,這種改變預示著全新民主實踐范式的孕育。筆者認為,一方面,需要承認網絡民主所存在的不足,即網絡民主不足以取代現實政治中的民主機制;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即網絡確實更新和拓展了民主實踐的載體、形式、方式等,這種改變正在重塑現實民主交往過程。網絡對于民主交往革命性轉變的未來意義,主要有兩個層面的內容:
第一,網絡不斷實現民主觀念表達、民主選擇偏好、民主政治行為等民主交往的各個組成要素的電子化、數字化,這為大數據改變民主交往提供了不竭的“原料”。根據麥肯錫公司的最初定義,大數據就是指“數據規模超出了典型意義上數據庫軟件工具所能捕捉、存儲、管理和分析的范圍”[注]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June 2011,p.1.。這一海量數據不僅存在于商業領域,在政治領域同樣如此。那么,作為一種物質生產能力的大數據,其并不局限于保有海量數據,這還只是第一步。“畢竟容量只是表象,價值才是本質”,“大數據的真正意義還在于大價值”,即“大數據是指人類有前所未有的能力來使用海量的數據,在其中發現新知識、創造新價值,從而為社會帶來‘大知識’、‘大科技’、‘大利潤’和‘大智能’等發展機遇”[注]涂子沛:《數據之巔:大數據革命,歷史、現實與未來》,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259頁。,這才是大數據生產能力的存在依據。大數據對于政治交往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在海量數據的支撐下,必然要求相應的“數據治國”,即“要憑借對數據的有效收集、處理和分析來治理國家,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具體政策”[注]涂子沛:《大數據》,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新版自序,第Ⅶ頁。。作為國家治理重要組成的民主交往,也需要建立在對數據的“整合、分析和開放”基礎之上,這一系列的工作在網絡條件下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網絡為“大數據民主”發展提供了充分而必要的民主交往的數據準備。
第二,網絡民主為“大數據民主”的數據“整合、分析和開放”提供了前期訓練,它嘗試實現不同于工業社會民主交往的全新內容,特別是在普遍參與和非結構化參與兩個方面。因此,多數學者認為,隨著網絡的出現,它可以更加充分和有效地實現民主內涵,“真正的政治參與要求公民們致力于和其他公民的直接討論。因特網的政治影響,于是經常借助協商民主人士所提供的透鏡而被觀察。人們希望因特網將會擴展公共空間,既擴大所討論的意見范圍,也擴大能參與討論的公民人數”,最后,“聚焦于政治平等——且特別聚焦于使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在實踐中變得有意義”[注][美] 馬修·辛德曼:《數字民主的迷思》,唐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頁。。不過,這種形式上的政治平等及其實踐意義,在網絡條件下很難充分實現。換言之,離開了大數據的生產屬性和技術支持,政治交往領域的民主實踐還很難脫離工業社會民主交往的范疇。比如,民主參與的充分性如何有效保證,即使擁有了互聯網的支持,普遍的、海量的政治參與也是不可想象的,多數學者也表達了相應的擔心;民主公意的有效性如何實現,特別是民主內涵的充分釋放,以及非結構化參與達至公共意志的過程,單純的網絡民主并不能解決這一系列的問題,不管是在生產與交往的關系之中,還是單純地從技術特性出發。當然,網絡民主提出的這些有益嘗試是值得肯定的,因為很快在“大數據民主”條件下,參與的廣泛性和公意的有效性將因為大數據的生產屬性和技術支持而獲得實質性的進步。網絡民主無論是從民主交往的數據準備,還是從民主實踐的全新內容,都為“大數據民主”的生長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在這一點上,需要對網絡民主持有更為開放的態度,肯定其積極、建設性意義,正視互聯網、特別是緊隨其后的大數據對于民主交往可能帶來的革命性轉變。
三、“大數據民主”對民主議程的再造
“大數據民主”區別于網絡民主的根本之處在于,其來源于大數據這一物質生產能力的轉換,是建立在全新的生產與交往基礎之上,故而,其提供的也是全新的民主實踐范式,圍繞民主實踐過程,需要重新進行定義。筆者認為,“大數據民主”作為全新的民主實踐范式,區別于工業社會的民主實踐,也超越了網絡民主對于民主形式和載體的更新。換言之,“大數據民主”解決了工業社會民主實踐的諸多問題和不足,使得民主參與的普遍性和民主公意的有效性發生實質性改變。基于此,民主實踐的議程將發生適應性轉變。這里,民主議程包括民主的發起,即民主參與階段;民主參與數據的處理,即結構化、半結構化、非結構化參與階段;民主決策結果和民主執行,即民主實質的實現階段等三個方面的內容。與大數據的生產屬性和技術特性相適應的民主議程再造,正是托夫勒所描述的“第三次浪潮”在民主交往領域將會發生的事情。這一民主過程會打破對于工業社會民主交往的常規性認知,顯得“不可想象”,但是,卻又是現實可能的。
(一)民主發起階段:大數據對海量參與的支持
在前大數據時代,民主交往的形式主要通過代議、代表的機制來完成。在經常反對民主的聲音中,普遍的參與爆炸構成否定直接民主的一個重要理由。并且,因為技術條件的限制,即使允許普遍的直接參與民主,也無法有效處理普遍參與所帶來的海量民主數據,這反而會造成民主運轉的失效,帶來不可避免的政治不穩定因素。因此,在世界范圍內,工業社會的民主形式主要以代議制的方式來實踐。甚至如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在區分民主內容與民主形式的基礎上,圍繞民主形式,也并不一味強調普遍的、直接的參與民主。這是基于工業社會生產能力和交往關系的必然結果。但是,代議制民主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使是在西方,對它的批評也沒有間斷過,認為它不能也不可能體現人民主權的實質,是一種初級的民主,是一種因直接民主一時不具備實現條件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湊合的權宜之計”[注]唐麗萍:《從代議制民主到參與式民主——網絡民主能否重塑民主治理》,《蘭州學刊》2007年第3期。。由此可見,代議制民主在民主的本質內涵上與民主的原初涵義存在落差,只是,在物質條件不具備和技術手段不充分的背景下,這種落差被默認為民主實踐的現實。
互聯網興起之后,對于民主本質內涵(即人民主權)的呼聲開始出現,并且認為,互聯網將為人民的普遍參與提供關鍵的物質支撐和技術支持。這在網絡民主的研究中已經成為一個常識性的觀點,即“與代議民主制的間接、有限、精英的特性相比,以網絡政治信息傳播手段為其技術基礎的網絡民主制具有直接性、平等性、便捷性等特點”[注]唐麗萍:《網絡民主能重塑民主治理嗎?——對現代民主制三種形式的解讀》,《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3期。,這在很大程度上更為符合民主的原初內涵和人民主權的本質特征。但是,擔心與憂慮也隨影而行,特別是對于互聯網中民主操控與民粹主義的擔心,因此,各種有關“烏托邦”、“網絡暴政”、“多數暴政”、“非理性”等批判聲音開始出現。這一現象其實很好理解,即使是在現實的民主交往中,也很難避免這類問題,關鍵在于,網絡民主參與是不平衡的、也是非常容易失控的。對于不平衡,它主要表現在多數沉默;對于失控,它主要表現在人為操控因素的存在。特別是民主參與的充分性方面,如何保證各種聲音同時存在,互聯網并不能很好地做到這一點。換言之,互聯網之中的民主參與,結果都容易偏向“聲響最大”的參與主體,它無法有效應對海量參與帶來的不同聲音的有效處理。
大數據不同于網絡民主的地方,根本原因在于其來源于生產與交往的關系,直接原因則在于其提供了不同于互聯網的技術手段,即對于海量參與的支持。在全新的民主交往活動中,公民的價值觀念、選擇偏好以及行為方式都將通過數字或符號的形式加以收集、存儲、管理和分析,這時,民主議程將不再是簡單的比例代表制、意見征集、樣本映射、個別訪談等方式,也不再是片面地倒向“聲響最大”的參與主體,而是通過對參與者民主交往全數據的處理,以完成普遍的、直接的民主參與過程。大數據條件下的海量參與將經歷三個環節:第一,民主交往數據的范圍界定。在這一環節,需要確認哪些數據屬于“大數據民主”的范疇,特別是那些在工業社會民主交往中不被納入民主議程的海量參與數據。因此,可以將大數據背景下民主交往數據從兩個方面進行類型區分:一方面,分為結構化數據與半結構化、非結構化數據;另一方面,分為離線數據與實時數據流。第二,民主交往數據的收集和傳輸環節。這一環節主要通過大數據公共平臺和各種大數據技術,收集和傳輸民主交往所產生的系列數據。比如,對于結構化、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民主交往數據,可以通過Sqoop、Flume等方式進行收集傳輸;對于民主交往的數據流,可以使用Kafka方式進行收集傳輸。第三,民主交往數據的存儲環節。“大數據民主”首先允許海量參與,這意味著覆蓋全體參與者的全部參與行為,乃至價值觀念和選擇偏好。并且,它并不會如網絡民主那樣,只是直觀地展現“聲響最大”的參與主體,而是對全部參與主體的民主數據進行存儲。海量參與數據使得“大數據民主”根本區別于之前的民主議程,它是“大數據民主”得以可能的“原料”。海量參與數據,包括不同類型的海量數據,可以通過分布式文件系統進行存儲、管理,比如HDFS和Tachyon,它們可以高效、廉價、可擴展地實現民主交往海量數據存儲、管理。
(二)民主數據處理階段:大數據對非結構化參與的涵括
在前大數據時代,民主數據的處理能力是非常貧乏的。這種民主數據處理能力的匱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民主海量參與數據處理能力的匱乏。工業社會民主交往主要通過代議制和代表制來完成,直接原因正是在于既有民主制度無法容納海量民主參與。這不管是對于發達國家還是轉型國家來說,都是同樣適用的。這在亨廷頓研究后發國家的民主轉型中,有過較為充分的論述。因此,流行的代議民主機制成為唯一可能的選擇。互聯網的興起是民主數據處理能力改善的一個福音,但是,這種改善仍然是有限的。一直到谷歌“三大論文”[注]Sanjay Ghemawat,Howard Gobioff and Shun-Tak Leung,“The Google File System”;Jeffrey Dean and Sanjay Ghemawat,“MapReduce:Simplified Data Processing on Large Clusters”;Fay Chang,Jeffrey Dean,Sanjay Ghemawat,Wilson C.Hsieh,Deborah A.Wallach,Mike Burrows,Tushar Chandra,Andrew Fikes,Robert E.Gruber,“Bigtable:A Distributed Storage System for Structured Data”,Google,Inc..的出現,才在技術上有效解決了這一難題。谷歌“三大”論文提出的GFS、MapReduce、BigTable等概念,正是構成后續大數據分布式存儲和處理系統的奠基石。第二,民主海量參與非結構化數據處理能力的匱乏。不管是在工業時代還是在互聯網興起之后,民主參與的代議制形式多數通過選舉民主的方式來完成,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前大數據時代不具備充分的處理非結構化數據的能力。選舉民主主要產生結構化的數據,它通過簡單的“是/否”或者“A/B/C...”等完成民主選擇,并將民主結果建立在這一簡單的二元選擇(非此即彼)之上,忽略了民主選擇的充分內涵,特別是民主參與主體的意見表達和非二元選擇訴求。網絡民主在反映“聲響最大”的參與主體方面,不過以另外一種形式重復了這種二元選擇。大數據的技術優勢在于,它不僅可以容納海量的結構化數據的處理過程,同時也能有效應對海量的非結構化數據的處理,包括文字、圖片、視頻、動畫等。這與民主參與主體充分的民主表達是聯系在一起的,避免了民主內涵的化約傾向。
民主數據處理能力的強弱決定了民主實踐新范式是否可以成立。工業時代民主交往的代議制形式保證了當時條件下民主數據的有效處理,互聯網時代民主形式的多樣化、特別是直接參與化傾向,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民主數據處理能力還較為有限。大數據的興起,不管是在民主數據量的層面還是質的層面,都提供了不同于前大數據時代的民主數據處理能力。筆者認為,相對于海量民主參與數據的處理,非結構化海量數據的處理能力真正實現了大數據條件下民主范式的轉換,并充分實現民主的“人民主權”本質。因為,只有充分的民主表達,才能實現充分的民主內涵;而充分的民主表達,必然會產生簡單數字之外的多樣數據類型,即文本、圖片、視頻等。在民主數據處理階段,它主要經歷兩個環節:第一,民主交往數據的處理環節。“大數據民主”所產生的海量數據,需要通過分布式文件處理系統進行快速、高效的分析,它是與海量數據存儲相對應的環節。對于離線數據,包括結構化、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可以通過MapReduce、Spark進行處理;對于民主交往的實時數據流,可以通過Storm進行處理。第二,民主交往數據的挖掘環節。數據挖掘環節主要針對相關關系展示民主事實,它與數據處理環節相聯系。在數據處理環節,可以通過算法模型獲得有關民主實踐的一般性知識,但是,通過數據挖掘,可以更好地實現民主交往的公意內涵。現在,一般常用的數據挖掘語言如R、Python等都可以用于民主交往數據的挖掘過程,特別是對于非結構化民主交往數據的挖掘。
這里,筆者嘗試以協商民主為例,較為直觀地展示民主數據處理中非結構化數據的挖掘對于民主內涵充分實現的重要意義,它也構成民主新范式得以成立的重要依據,因為,它確實不同于常識中的民主實踐過程。協商民主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治理形式,其中,平等、自由的公民在公共協商過程中,提出各種相關理由,說服他人,或者轉換自身的偏好,在廣泛考慮公共利益的基礎上利用公開審議過程的理性指導協商,從而賦予立法和決策以政治合法性”[注]陳家剛:《協商民主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年第3期。。這里的關鍵在于,每個參與協商民主的主體,他們所提供的意見、看法、觀點,如何在多主體、特別是海量主體的參與中,最后實現民主決策。如果只是簡單的商談和討論,最后進行票決,那么,它與選舉民主并無實質性區別;如果它依賴某個個體最終作出決策,還是無法充分吸納多主體的各類意見。當然,協商民主更加趨于民主的本質內涵,但是,民主本質內涵的實現過程卻并不能自動實現。大數據所具有的非結構化民主數據的處理能力,提供了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比如,以“A”主題的商談為例,基于Python語言,大數據首先可以將全部參與主體的意見表達納入數據處理過程(數據準備);其次,針對協商的主要表達形式——文本,大數據具備一系列的文本挖掘技術,可以從全部民主數據(文本)中提取有價值信息,比如,通過TF-IDF實現關鍵詞的發掘、通過LDA模型實現文本主題提煉、通過情緒分析實現文本歸類、通過詞向量分析實現主題詞之間的語義分析,等等。這一系列的文本挖掘,可以全面、客觀地展現協商過程所有參與主體在“A”主題下的觀點提煉、觀點聚類、不同觀點相關關系等,這對于充分商談基礎上的民主決策無疑是非常關鍵的。
(三)民主結果與執行階段:算法優化與趨向民主實質
前大數據時代的民主結果輸出,主要由集中方式或多數表決的方式來完成。一般而言,民主結果的執行階段,還包含反饋環節。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前大數據時代,任何意義上的民主決策并不能真正、充分地實現全員參與,所以,其不可避免地存在集中和精英傾向,這要求不斷修正民主決策,以更好地符合公共意志;第二,即使充分地實現精英決策與大眾參與的有效結合,并不能保證民主決策結果的理性與正確,因此,需要通過反饋環節來實現民主結果的合理化。戴維·伊斯頓就指出,反饋環的意義在于,“當局生產輸出,社會成員對于輸出作出反應,這種反應的信息獲得與當局的溝通,最后,當局作出下一步的可能行為”[注][美] 戴維·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王浦劬譯,華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頁。。可見,前大數據時代的民主反饋,既可以彌合精英決策與大眾參與之間的落差,也可以限制民主結果的不合理因素。
在“大數據民主”的決策與執行階段,它不存在第一方面的問題,即不充分參與導致的民主落差。不管是海量參與還是非結構化參與,“大數據民主”提供了充分參與,并將充分參與的民主交往數據納入處理過程,最后輸出民主結果。問題的關鍵在于第二方面,即大數據條件下的民主交往是否會產生不合理的結果?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這不能簡單等同于前大數據時代民主結果的非理性。因為,“大數據民主”提供了公共意志的凝練過程,但作為民主結果的公共意志是否合理,則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至少在盧梭意義上的公意與眾意(或馬克思意義上民主內容與民主形式)的統一過程,在大數據條件下仍然存在漫長的探索過程。這里涉及到的就是大數據條件下民主交往的反饋環節,它主要指向民主數據處理的算法優化過程。
在民主結果輸出與執行階段,“大數據民主”包含兩個環節的內容:第一,民主結果輸出環節。在這一環節,通過民主參與海量數據的處理與挖掘,可以實現民主參與的充分性與民主公意的有效性相結合,輸出民主結果或公共意志。民主結果的輸出可以通過可視化的方式,直觀展示出來,從而完成大數據條件下民主交往的一次過程。第二,經歷過大數據支撐的民主參與、民主數據處理和民主結果輸出,需要進入到具體的民主執行階段。這是大數據條件下民主交往的二次過程。在民主執行環節,通過大數據對于民主實踐相關數據的收集、存儲、管理和分析,辨識民主決策與公共利益的吻合度。如果民主決策符合公眾利益,那么,民主交往數據處理階段的算法模型就是合理的,如果二者相悖,則有必要根據民主實踐情況來優化算法模型。算法其實就是“任何良定義的計算過程,該過程取某個值或值的集合作為輸入并產生某個值或值的集合作為輸出”[注][美] Thomas H.Cormen,Charles E.Leiserson,Ronald L.Rivest and Clifford Stein:《算法導論》,殷建平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在大數據時代,“計算型社會”的興起成為必然,“關于人和社會本身的數據現在已經極為豐富,而且這類數據還在快速增長,未來一切的社會現象、社會過程和社會問題,都可以而且應該通過以計算為特點的定量方法分析解決,這樣更加精確、更加科學”[注]涂子沛:《數據之巔:大數據革命,歷史、現實與未來》,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275頁。。這說明,根源于生產與交往關系的大數據,將不可避免地產生社會計算。這種社會計算應用于民主交往領域,就要求盡可能地實現民主結果與公共意志的一致性,一致性的完成有賴于民主交往數據處理階段的算法模型根據民主實踐數據的反饋作出優化。在優化民主算法模型的過程中,“大數據民主”不斷趨于民主本質,即建立在充分參與基礎上的公共意志的實現。
結 語
通過比較網絡民主與“大數據民主”,可以更好地發掘大數據對于工業社會民主交往的革命性意義。這種意義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大數據的物質能力。從生產與交往的關系中理解大數據,更為符合大數據的根本特質。它不僅表現在生產領域的巨大價值創造,也表現在對交往形式的革命性再造,比如“工業解體”、“組織再造”、“智慧社會”等。在國外,有學者將其定義為“知識的基礎設施”,這同馬克思所描述的物質能力是一致的。因此,理解大數據的生產屬性,是理解大數據影響人類社會生活包括民主生活的邏輯起點。比如,維克多·邁爾-舍恩伯格就指出,“現在大多數人都認為大數據是一個技術問題,應側重于硬件或軟件,而我們認為應當更多地考慮當大數據說話時會發生什么”[注][美] 維克多·邁爾-舍恩伯格等:《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盛楊燕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頁。,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大數據的顛覆性意義。第二,大數據的技術特性。大數據首先是一種物質能力,其次是一種技術手段。這種技術手段區別于工業時代及緊隨其后的互聯網,它聚焦于海量數據,特別是擅長于非結構化數據的處理,這對于民主交往的普遍參與是非常重要的。大數據可以有效實現從大眾參與到公共意志的民主過程,在民主的不同環節區別于工業社會的代議制民主以及網絡民主。這種區分是顛覆性的,它會打破人們有關民主議程的常規認識,轉而從大數據的技術特性出發,再造全新的民主流程。
從區別于工業時代的代議民主及其補充形式網絡民主,到大數據帶來民主治理范式的轉換,再到大數據民主實踐范式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得到支持,還有很長的一段發展過程。目前,在大數據如何影響民主治理問題上,已經取得了一些共識,比如,大數據技術應用于民主實踐可能會帶來改變、大數據與國家治理的結合等。但是,這明顯是不夠的。“大數據民主”會在何種意義上“顛覆”工業社會的民主交往(包括區別),其生成的民主治理新范式是什么?這都需要以大數據的雙重屬性(即物質屬性與技術特性)為邏輯起點,全面、系統展開“大數據民主”的構成要素。
當然,在肯定“大數據民主”積極、正向意義的同時,還需要認識到目前條件下“大數據民主”發展所存在的諸多障礙。這類限制性條件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工業與信息社會交匯期,大數據發展還不充分,比如有關民主治理的觀念、偏好、行為還不能以數字或符號的形式加以收集、存儲、管理、分析和應用,這無疑會影響“大數據民主”對于民主治理的積極作用;第二類是“大數據民主”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種負面效應,比如數據公共性、數據公益性、數據權、數據隱私等方面的問題,這無疑會影響到“大數據民主”對于民主治理的建設性作用。因此,以積極、建設性的態度對待大數據對于民主交往的影響,將“大數據民主”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之中,這是必要的;同時,處理好既有民主交往與大數據條件下民主交往之間的關系,承認既有民主范式與“大數據民主”范式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發揮合力,這無疑是推動民主治理實踐的關鍵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