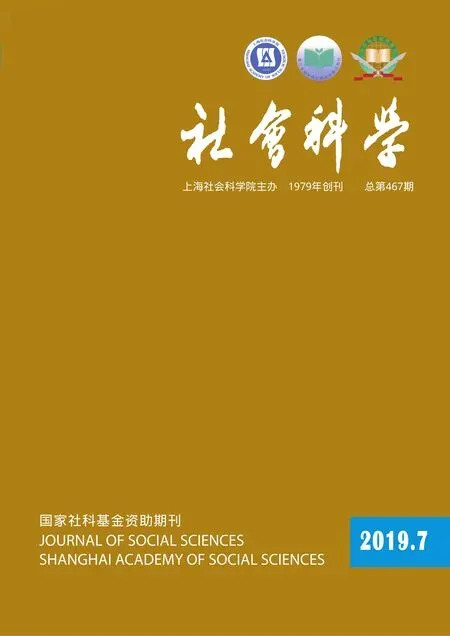“五四”文學研究的三個緯度*
——從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 (1917-1927)》部分導言說開去
王光東
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1917-1927)的文學理論和作品選集,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全書共分十卷,由蔡元培作總序,編選人作每一卷的導言,胡適編《建設理論集》、鄭振鐸編《文學論爭集》、茅盾編《小說一集》、魯迅編《小說二集》、鄭伯奇編《小說三集》、周作人編《散文一集》、郁達夫編《散文二集》、朱自清編《詩集》、洪深編《戲劇集》、阿英編《史料.索引》,這十位編選者都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和推動者。本文重點分析的是胡適、周作人、茅盾、鄭伯奇所寫的導言,重讀這些導言,對于我們進一步理解“五四”與“西方”、“五四”與“傳統”的關系以及“五四”文學的一些理論、觀念對后來文學的影響等都是有意義的,特別是導言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觀點對今天文學研究的啟示性價值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一 “文化傳統”之于 “五四文學”
中國文化傳統之于“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關系是復雜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反叛封建傳統的過程中,對于傳統文化又表現出熱烈的肯定和創造性的轉化,他們的這種雙重態度,源于在傳統文化的漫漫歷史中,發現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性力量。民族文化的發展一定是傳承中的創造。中國的文化傳統是豐富的,先秦諸子、唐宋詩文、儒學經典、道家典籍……,豐富的文化傳統在歷史的進程中,沉淀為我們民族的精神和個性。“五四”作家在反對封建禮教法則對人性的壓抑時,同時又在文化傳統中尋找建構現代文化的資源,郭沫若對先秦文化中的孔子、老子給以熱烈的贊美,周作人、胡適在新文學大系導言中,分別從傳統文人創作和民間文學兩個方面說明了新文化、新文學與傳統的關系,為我們如何理解“傳統”、發展傳統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周作人在他撰寫的“散文一集”導言中說:“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的,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雖然在文學發達的程途上復興與革命是同一樣的進展。在理學與古文沒有全盛的時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當的長發,不過在學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們讀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趣幾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難免有若干距離,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于禮法的反動則又很有現代的氣息了。”[注]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7頁。顯然周作人是把“五四”時期的現代散文看作是明清散文的一種復興和轉化,“現在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又因時代的關系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注]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8頁。這種由古代轉化而來的“新的傳統”,同時又是傳統的一部分,那么,是什么力量賦予傳統新的因素呢?在周作人看來“即是西洋科學哲學與文學上的新思想之影響”[注]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10頁。。由此看來,“五四”時期的新文學作家在接受外來影響時,并不是否定傳統,而是謀求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郭沫若在他的《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論中德文化書》《偉大的精神生活者王明陽》等文章中,也同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新文化建構的資源和力量。他認為不論是老子和孔子或他們之前的原始思想中,卻能聽到兩種心音:“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動的實在之表現!——把一切的事業由自我的完成出發!我們的這種傳統精神——在萬有皆神的想念之下,完成自己之凈化與自己之充實以至于無限,偉大而慈愛如神,努力四海同胞與世界國家之實現的我們這種二而一的中國固有的傳統精神,是要為我們將來的第二的時代之兩片子葉的嫩苗而伸長起來的。”[注]郭沫若:《<文藝論集>匯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頁。郭沫若在傳統中發現了自我實現和承擔世界國家責任的現代精神,他對于傳統文化的這種態度和周作人在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語中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們都是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中賦予傳統文化新的意義,以謀求新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那么,又該怎樣理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既肯定傳統又反叛傳統的雙重態度呢?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社會歷史發生轉型和變化時,我們所面對“傳統”往往呈現出它的“兩面性”特征:一方面是不適應歷史發展的滯后性;一方面是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內容與歷史發展有意義的相關性。只有反叛這種“滯后性”,同時賦予相關性歷史文化有意義的創造性力量,才能推動傳統文化的更新,以適應新的社會歷史發展的需要,創造出新的文化形態。周作人等現代知識分子對傳統文人思想的發現,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具有了巨大的現代性價值。
胡適與此有所不同,它是在傳統文化中“民間文化”這一緯度上尋找新文化、新文學的建設資源。“民間文化”與“文人文化”既相聯系又有所區別,胡適在他的白話文學史中,曾把“文人的民間化”和“民間的文人化”看作是中國文學不斷發展的兩條路徑,這兩者有一個共同的指向——“民間”是文人創作的資源并賦予文學生命的力量。在他看來,文學變革的動力是與民間聯系在一起的,依據這樣的思路,新文學的產生也必然不能脫離與民間文化的聯系,所以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認為:“中國白話文學的運動當然不完全是我們幾個人鬧出來的,……我們至少可以指出這些最重要的因子:第一是我們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作品,……第二是我們的老祖宗在兩千年之中,漸漸的把一種大同小異的‘官話’推行到了全國的絕大部分……,第三是我們的海禁開了,和世界文化接觸了,……使我們明了我們自己的國語文學的歷史,使我們放膽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的文學革命。”[注]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15-16頁。這個文學革命所延續的就是一千多年來白話文學,也就是民間的俗文學,胡適在“民間俗文學”的傳統中找到了新文學發展的道路。劉半農與胡適持有相同的文學觀念,劉半農認為:“中國內地的歌謠中,美的分子,在情意方面或在詞句方面都還很豐富。”[注]劉半農:《劉半農書話》,陳子善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頁。他不僅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把自己的詩學主張與民間文學相關聯,而且還依賴江陰民歌創作了新詩《瓦釜集》。周作人在《歌謠》周刊發刊詞中說得更為明確:“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有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曾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當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注]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頁。由上論述可以看到,中國現代早期的知識分子對于傳統的民間文化寄予了高度的熱情。任何時代的文化都存在著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區別,與下層民眾密切關聯并與他們的生活方式融為一起的民間文化,雖然浸透著主流文化的影響、體現著某個時代的價值觀,但是這一民間文化傳統由于與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血肉相連,往往具有鮮活、生動、率真的生命活力,譬如民歌、民謠都是來自于下層民眾真實的聲音,它的藝術內容及其表達形式與已成規范的文人詩詞相比較,具有更為強烈的創造性,這也正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創造新文學的過程中,極力張揚民間文學的重要原因。由此反思一下當下的文學創作,當代許多作家所缺少的正是向民間尋找資源的自覺意識。
我們面對的傳統是復雜而又豐富的,傳統文學的存在形態也是多元和多層次的,怎樣發現“傳統”并激活它使之成為新的文化形態的組成部分,是從“五四”直至今天都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二 “混合性”與異域文學的接受
“五四”文學與西方文學的關系,是“五四”文學研究中的又一個重要問題。一個民族和國家對異域文化的接受往往是與自身的民族文化傳統相關的,自身的文化傳統往往制約著接受外來文化的路徑和內容。鄭伯奇在《小說三集》導言中,用美國的心理學家史丹萊·霍爾的發生心理學理論,來解釋中國“五四”新文學的發生,認為“五四”文學在接受西方文學影響時具有“混合性”的特點,一個作家的創作可能同時受到多種西方文學思潮因素的影響,這一特點導致了“五四”文學構成內容和表現形式的復雜性(這種“混合性”在“五四”文學乃至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不同階段都有所表現),這一特點也說明了中國文化傳統具有包容性的胸懷和氣魄以及吸納外來文化的能力。重視這一特點,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在發展過程中,一直與外國文學有著緊密的關聯,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重視中國作家創作區別于其他國別作家的獨特性;而且要充分的意識到“本土”文化傳統如何制約異域文化的接受等問題。
霍爾認為:人類的進化是將以前已經通過了的進化過程反復一遍而后前進的,鄭伯奇說:“若把這個臆說大膽的應用在文化史上面,我們也可以說,人類文化的進步,是將以前已經通過了的進化過程反復一番而后前進的,在文化落后的國家或民族,這種現象更為顯著。”[注]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1頁。由此鄭伯奇在回顧“五四”新文學第一個十年時認為:“中國文學的進展,我們可以看出西歐二百年中的歷史在這里很快地反復了一番。這不是說中國的新文學已經成長到和西歐各國同一的水準,落后的國家雖然急起直追也斷不能一躍而躋于先進之列。尤其是文學藝術方面,精神遺產的微薄常常使后進國暴露出它的弱點。我們只想指出這短短十年中間,西歐兩世紀所經過了的文學上的種種動向,都在中國很匆促地而又很雜亂地出現過來。”[注]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2頁。這一論述說明了西方文化、文學對于“五四”文學的影響不是單一的,而是混雜的,西方意義上的文學思潮和作品在中國并沒有出現,正如茅盾在《小說一集》導言中說:“我們回顧第一個‘十年’的成果,也許會有一個疑問:為什么我們的‘新文學運動’的初期跟外國的有點不同?在我們這里,好像沒有開過浪漫主義的花,也沒有結寫實主義的實。”[注]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12頁。這種現象的產生,當然與我們的文學傳統、“五四”時期的歷史現實、作家的審美理想等等問題有關,但與這種“混雜的影響”也是有關系的,鄭伯奇在《小說三集》導言中認為:“所謂‘人生派’實接近帝俄時代的寫實派,而所謂‘藝術派’實則包含著浪漫主義以至表現派未來派的各種傾向。這種傾向的混合并不是同時湊成的,這里自然有個先來后到,但這些傾向有個共同的地方所以能夠雜居,確是不容否認的事。但這些傾向中比較長遠,而最有勢力的當然是浪漫主義了。”[注]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3頁。鄭伯奇雖然指出了“人生派”與“藝術派”主要特征,但也看到了作家作品中所具有的“混合性”的特點,在創作社的這批作家中,特別是郁達夫和郭沫若的小說創作中,日本“私小說”的因素也是比較明顯的。“五四”新文學創作所呈現出的這種“混合性”特點,啟示我們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過程中,要重視如下幾個問題:1.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中國文學面對著與西方文學不同的文化傳統、社會現實,也就不可能沿襲著西方文學的發展軌跡向前發展,這也就要求我們研究中國“五四”文學時,要重視中西文學不同的發展路徑,這雖然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但我們仍舊對于這種“差異性”重視不夠,直接把一些“西方理論”照搬挪用,這種現象在新時期以來表現得更為突出。新時期以來的文學與“五四”文學的“異域文學接受”有著很大的相似性,“混合性”也是其明顯特征,西方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化、文學因素,同時雜糅在中國作家的創作中,因此簡單地套用某種文化理論來分析中國文學,就會帶來作品分析的隔膜感。從這樣的意義上說,“新文學大系”的導言,從文學現實出發,在具體作家作品的分析過程中,說明作家寫作意義的研究方法仍舊是我們應該重視的一種研究方法,這也就帶來了我們需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中國新文學研究的“本土化”問題。2.所謂“本土化”不是簡單的拒絕外來理論,而是一種思維方法的轉變,也就是從“中國問題”出發去展開研究。曹錦清在《如何研究中國》中認為:“西方的理論和概念必須按照中國的語境加以語義學上的改造,通俗來講就是中國化。如果這個過程不完成,用輸入的西方理論直接套裁中國是要誤讀中國的。另外,把西方理論掩藏著的價值觀念作為一個普世的價值觀念我們也會犯錯誤,價值觀念從來不是普世的。價值觀念的來源只能是本民族內在的需求和當下實踐的需求。”[注]曹錦清:《如何研究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頁。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中,我們可以看到導言作者大多都是以“中國”為中心來研究中國問題,對西方理論的理解是融入中國問題的分析中的,因此魯迅在充分肯定西方文學對“五四”作家的影響時,又深刻的提出了中國作家在“中國語境”中的獨特性;胡適在“進化論”影響下形成了“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其目的是為了推倒舊文學,建立白話為一切文學工具的新文學觀念;鄭伯奇則從中國作家的歷史境遇出發,分析他們接受外來影響的必要性及其差異。這種從本土出發分析問題的思維方法,是“五四”一代作家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資源,只有在這里我們才能找到真實的自己和藝術的力量。
三 “社會性”作為文學的批評原則
新文學大系導言不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重要文獻,而且是文學批評的經典性文本。導言作者評價文學作品的原則不盡一致,具有濃重的個性化色彩,但對后來的文學研究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魯迅那種戰斗的現實主義精神及其文藝思想,不僅影響著文學史的發展,而且影響著知識分子的精神和靈魂。茅盾在小說一集的導言中,以表現“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作為評價作品的基本原則,對于今天的文學批評而言仍舊是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
茅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的導言中,對于“五四”文學前半期創作提出了批評,認為有兩個重大缺點,“這兩個缺點,第一是幾乎看不到全般的社會現象而只有個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觀念化。”[注]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10頁。“大多數創作家對農村和城市勞動者的生活很疏遠,對于全般的社會現象不注意,他們最感興味的還是戀愛,而且個人主義的享樂的傾向也很顯然。”[注]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9頁。“‘人物都是一個面目的,那些人物的思想是一個樣的,舉動是一個樣的,到何種地步說何等話,也是一個樣的’。這些戀愛小說內的主角大抵不是作家自己就是他的最熟悉的伴侶,可是一搬上紙面尚不免觀念化,無怪那極少數的描寫農村生活和城市勞動者生活的作品更其觀念化得厲害!”[注]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10頁。文學創作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茅盾認為是“生活的偏枯”造成的,顯然茅盾是從“文學表現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的角度來分析和評價“五四”前期的小說創作的。批評家對小說作品的評價可以有多樣化的角度,這一時期的戀愛小說雖然有觀念化的傾向,但從人的個性發展,反抗封建倫理法則的角度分析也有其時代價值,但是茅盾要求文學反映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人的豐富性與復雜性,也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文學意義的。茅盾秉持的是現實主義的文學批評原則,重視文學的“真實性和豐富性”,這一現實主義的文學批評理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是深遠的。事物總是有其兩面性,當我們把“真實”作為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并且“絕對化”,就會帶來對文學形式、技巧以及人與生活之間多樣化審美關系的忽視,新時期個人化的“先鋒主義”寫作,在回歸“文學本體”的過程中,某種意義上也是對這一文學寫作原則的反撥,但是當文學的個人化寫作發展到一個階段,呈現出疏離廣闊的社會生活,成為個人的“小世界”的表達,生活以及由生活產生的意識日益狹窄時,文學與人,文學與生活之間的多樣化、豐富性的審美關系就會再一次變得簡單化、觀念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特別重視茅盾在導言中提出的,“生活的偏枯”會帶來“文學的偏枯”的觀點,由此對今天的文學創作有所思考。
新世紀以來,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中國當代城鄉關系的巨大變化所帶來的社會現實的變化,已經深刻的影響并改變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觀念。伴隨著這種變化,出現的一些優秀文學作品也以“史詩”性的品格與這個時代建立了深厚的審美關系,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當下小說創作中存在的“生活偏枯”的問題,這一問題主要呈現在如下兩類小說的創作中:一是網絡小說寫作,一是部分青年小說家的“純文學”寫作。網絡小說與紙媒小說相比較而言,它有著不同于紙媒小說的生產方式,在文化資本的操縱下,市場化的影響以及對讀者閱讀消費的期待,使網絡小說更關心閱讀者的趣味和閱讀量,因此可讀性、通俗性成為其主要的特點,而支持這種可讀性的是男歡女愛、類似于武俠小說的人的超能力的夸張敘述、或者是黑幕、獵奇的感官刺激……如此以來,我們很難在網絡小說中看到對現實生活的嚴肅思考,社會關系中“人的情感與生活”的豐富性被所謂的虛擬想象簡單化,生活或者說人們普遍“感知的社會生活”在網絡小說中的呈現是不夠的。這類文學作品作為一種消遣,只要無害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從文學理應承擔社會責任的角度來要求這些作品,這些缺乏鮮活、生動生活經驗和社會深度的作品是難以有真正的藝術價值的。對于部分青年作家而言,“生活偏枯”也是當下值得重視的問題,特別是那些正在學校讀書或者剛剛走出校門的青年作家,其作品題材的狹窄和處理題材的能力的貧弱,和茅盾批評“五四”前半期創作時提出的問題是一樣的:“第一是幾乎是看不到全般的社會現象而只有個人生活的小小的一角,第二是觀念化。”[注]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10頁。“五四”前半期的小說創作存在的問題與當下部分青年作家存在的問題是如此的相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茅盾在導言中的一段話,對于今天的作家而言仍然是有意義的,茅盾說:“怎樣克服這些缺點呢?許多人的見解并不一樣。從當時的青年群內(包括了青年的作者和讀者)發出來的最普遍的呼聲只是很干脆的一句話:讓他自由發展就好了!(《小說月報》十三卷各期的通訊欄內就記錄著一部分這樣的現象)。但是,空空洞洞的一句‘讓他自由發展’顯然不是當時實際所需要。十二卷七號的《小說月報》有特別的一欄——‘創作討論’,企圖把這問題更具體的研究一下。參加討論的,共有九位,在現今看來,其中有一位署名說難的《我對于創作家的希望》最為切實了。(這位說難,記起來好像就是胡愈之)。他這篇文章指出了作家們除‘感情的鍛煉修正和藝術力的涵養以外,實際社會是不能不投身觀察的。文學(廣義)中之文法語法方面,是不能不分心研究的。舊來之語體小說,是不能不參考的。新聞紙第三面的紀事,是不能不多看的。而且街談巷議和許多外行人的議論,也是不能不虛心聽受的’。可是當時青年的創作家或有志于創作的青年卻不耐煩下那樣的水磨功夫。”[注]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10-11頁。茅盾這段對“五四”前半期青年創作家的評價和分析,同樣應該引起今天的青年作家的深思。
四 結 語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十個導言所包含的理論思想、研究方法以及理解文學史的觀念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影響是深遠的,大部分導言體現出的文學史觀是“進化的歷史文學觀”,他們對于新文學的理解和認識都與這一文學史觀有著密切的關系,那么這一文學史觀在今天應該怎樣理解呢? 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中,蔡元培寫的總序,鄭伯奇胡適等人寫的序導言中,都談到了文學的進化問題,胡適在《建設理論集》導言中對“歷史進化的文學觀”表述的尤為清楚 :“文學革命的作戰方略,簡單說來,只有‘用白話作文作詩’一條是最基本的。這一條中心理論,有兩個方面:一面要推倒舊文學,一面要建立白話為一切文學的工具。在那破壞的方面,我們當時采用的作戰方法是‘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就是說:‘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云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故不能工也。……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注]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版,第19頁。胡適等人所持有的這一“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揭示了不同時代的文學之間的差異性以及時代精神對文學發展的重要影響,是“五四”新文學建立過程中的重要理論與思想,這一理論使現代知識分子找到了反抗舊文學的必要性和建立新文學的合理性,在實踐層面上以無畏的勇氣構建新的文學世界,創造出了具有鮮明時代特點的“五四”文學,豐富了中國文學的內容以及藝術表達形式。這種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確認了文學與時代同步發展的內在聯系,推動了中國文學的轉變和發展,其歷史意義和文學意義都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文學創作與文學史研究不同,文學史研究應重視文學史發展過程中,文學存在形態的多樣性,不然就會忽略審美習慣、趣味的繼承性和文學發展的聯系性,對文學存在形態的豐富性進行“簡化”處理。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作為“五四”時期的“作戰方法”其歷史意義是巨大的,但是作為今天我們研究文學史的原則是需要反思的,在強調文學的進化、發展時,不要忽略文學的繼承性以及與文化傳統的關聯性,并由此為基礎開拓文學史的研究視野和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