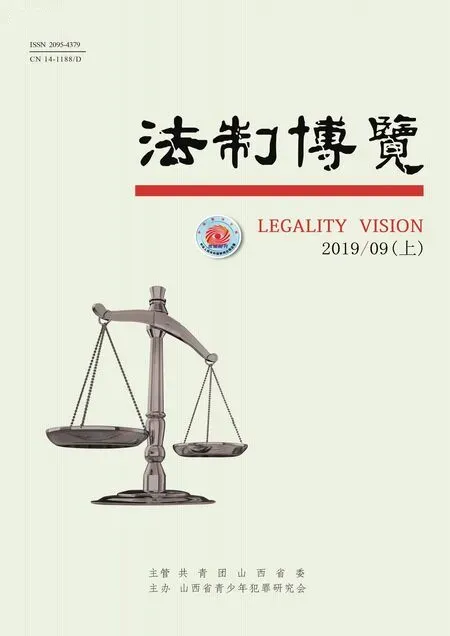憲政編查館與修訂法律館關系考
戴馥鴻 楊 波
成都大學法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6
在清末的法制改革中,最為人所知的機構即為修訂法律館了。修訂法律館的存在時間從光緒三十年直至宣統三年清廷覆亡。在這一段時間里,修訂法律館在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的率領下,邀請日本法律學者岡田朝太郎、志田甲太郎、松岡正義等參與清末法典的修改和起草。后來,清末修律的主要成果《大清現行刑律》、《民事刑事訴訟律草案》、《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編》、《刑事訴訟律草案》、《民事訴訟律草案》、《法院編制法》等都是由修訂法律館主要負責完成的,這些法典至今在我國部分地區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修訂法律館展開修律工作的第三年,清廷發布上諭仿行立憲籌備憲政,接著即設立憲政編查館統籌一切與憲政有關的編制法規、統計政要諸事宜。從此,憲政編查館成為清朝末年一切政治法律活動的管理機構,修訂法律館也開始在憲政編查館的統率下開展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修訂法律館和憲政編查館必然會發生很多職能和工作中的聯系。這里,筆者不會太過注意修訂法律館和憲政編查館在人員和機構的交叉,而主要是著眼于在清末法制改革中,憲政編查館設立以后修訂法律館地位發生的變化。
一、修訂法律館的開設
根據陳煜博士的考證,修訂法律館源于刑部下設的律例館。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清廷發布上諭:“現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這一上諭宣布了清末修律的開始。當時“沈家本為刑部左侍郎,伍廷芳也剛剛從出使美國任上召回,以四品卿銜道員賞四品京堂候補”,“尚無具體官名”。此時的修律,根據前文的研究,是以劉坤一和張之洞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為基礎的。從這個時候開始,至修訂法律館正式開設,沈家本和伍廷芳由于教育背景和人生經歷的不同,在修律方案上自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沈家本意在改造舊律,伍廷芳想要創造新律”。于是,沈家本著手開始將大清律例內“全部條例反復講求,復查歷屆修例章程應分別刪除、修改、修并、移改、續纂”等,一俟編訂。而由于清廷急需發展工商,設立商部,“茲派載振、袁世凱、伍廷芳,先定商律,作為則例。”伍廷芳作為諳習東西洋各國通商狀況的新式人才,于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被派去修訂商律,同年,則起草并頒布《商人通則》和《公司律》,并以《欽定大清商律》頒行。而伍廷芳也于該年七月十六日被任命為清廷新設商部左侍郎,籌辦一切通商事宜。可見,修律伊始,兩位修律大臣都是根據清廷“采西法以補中法之不足”的變法原則分別工作,并沒有設立獨立的修律機構,也沒有制定系統的修律計劃。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在于此時修訂法律事宜沒有專門負責的機構或獨立的身份與名義,僅僅是由兩名分屬不同機構的大臣負責其事。
這一狀況在光緒三十年發生了初步的變化。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一日,沈家本、伍廷芳“酌擬大概辦法,遴選諳習中西律例司員分任纂輯,延聘東西各國精通法律之博士、律師以備顧問,復調取留學外國卒業生從事翻譯,請撥專款以資辦公,刊刻關防以昭信守”,并以修訂法律館的名義開始辦事。根據沈家本、伍廷芳奏設修訂法律館的意圖,修訂法律館的職責一為修訂律例,一為翻譯東西洋各國法律書籍。
然而,這一階段的修訂法律事宜在人事和職權上仍然存在三個大的問題。第一,修訂法律雖然正式以修訂法律館的名義辦事,但是卻依然是在刑部之下,主要以原屬刑部律例館的人員具體辦事,修訂法律館并沒有自己專門的辦事章程、辦事人員和機構設置。第二,修律大臣沈家本為刑部侍郎,伍廷芳為外務部侍郎,而且伍廷芳光緒三十二年又被派駐美墨秘大使,兩位修律大臣分屬不同機構,難以統一辦事。第三,光緒三十二年清廷發布仿行立憲上諭,著改定官制,改革官制之后,刑部改為法部責任司法,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以使司法和審判大權分立,取司法獨立之效。原修律大臣、刑部侍郎沈家本則遷任新設大理寺正卿,這使得修訂法律的人事關系更為復雜和混亂。這三個問題導致修訂法律館的修律工作難以統一行使,再加上官制改革以后,中央部院的調整導致修訂法律館的身份和權屬更加受到爭議,使該館無法獨立完整地展開修律工作。
二、憲政編查館與修訂法律館的獨立
如前所述,修訂法律館源于早年設于刑部之下的律例館,至修訂法律觀開館修律以后,由于修律大臣沈家本仍然為刑部侍郎,所以,該館依然為刑部附屬機構,缺乏獨立性。至官制改革以后,沈家本授任新設大理院正卿,大理院掌管審判事宜,刑部掌管司法事宜,取權力分立之效。然而在整個中央官制的改定過程中,修訂法律館的地位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尤其是在法部與大理院就司法權限的劃分引發部院之爭之后,雖然爭論并非因修訂法律的權限引起,但是隨著部院之爭擴大,再加上人事歸屬不清,修訂法律館的地位以及修律權的歸屬也受到了法部和大理院之間爭論的影響。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改任大理院正卿張仁黼就修訂法律的組織機關、修律宗旨等問題首先發難,同一日兩次上奏,指出:“臣愚以為修訂法律,以之頒布中外,垂則萬世,若僅委諸一二人之手,天下臣民,或謂朝廷有輕視法律之意。甚且謂某某氏之法律,非出自朝廷之制作,殊非所以鄭重立法之道也。”將矛頭直指修律大臣、刑部侍郎沈家本,認為沈家本有借修律侵奪皇權之嫌疑。張仁黼認為:“請欽派各部院堂官,一律參與修訂法律事務,而以法部大理院專司其事”。其意圖很明顯,即要共同執掌修律權。對此,法部侍郎、修律大臣沈家本答復到:“原奏所成修訂法律事體重大,擬請欽派部院大臣會訂,而以法部、大理院專司其事”等,“均屬切要之言”。后來,法部尚書戴鴻慈針對此事也上折指出:“若夫編纂之事,委諸一二人之手,固覺精神不能專著。”戴鴻慈贊同張仁黼由法部和大理院專司修律事宜的意見,并對該意見做了補充,認為應該“欽派王大臣為總裁”,管領修律事宜。針對張仁黼批評的“某某氏之法律”,沈家本深感惶恐,在歷數修訂法律館近幾年來在翻譯各國法律,編訂古律,改定舊律方面的實績之后,提出:“臣學士淺薄,本未能勝此重任,加以進來精力日遜,每與官員討論過久,及削稿稍多,即覺心思渙散,不能凝聚,深懼審定未當,貽誤非輕。再四籌思,惟有仰懇天恩,開去臣修訂法律差使,歸并法部、大理院會同辦理,廣集眾思,較有把握”。沈家本的奏折既有辯解的意思,又有宣戰的意圖。如此,關于修訂法律館的歸屬以及修律權的歸屬,瞬時成為清末法制改革過程中急需明確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在中央官制改革剛剛完成不久,各部院權限尚在厘定階段,而清末立憲又面臨一個權力分立的問題,修律權的歸屬即為立法權的歸屬。如此,對修律權的歸屬和修訂法律館地位的明確界定就非常的必要。而這個結果最終由憲政編查館做出。
關于修訂法律館的地位及修律權的爭論發生在光緒三十三年五月至六月。而該問題的解決直至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五日憲政編查館成立以后才由憲政編查館做出最后定論并得以解決。前面我們數次提到,憲政編查館負責籌備立憲期間一切編制法規、統計政要諸事宜,而且在《憲政編查館辦事章程》第二條第三款明確指出:該館“負責考核修訂法律館所定法典草案,各部院、各省所訂各項單行法及行政法規。”其中法典草案就是指“由修訂法律館所編訂的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諸法而言”。修訂法律館應該以獨立于法部和大理院的身份負責修律事宜,并直接向憲政編查館負責。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五日,草擬修訂法律辦法,就之前法部和大理院關于修律權及修訂法律館的地位問題給出最終的結論:
各國編纂法典,大都設立專所,不與行政官署相混,遴選國中法律專家,相與討論,研究其范圍,率以法典為限,而不及各種單行法。誠以編纂法典,事務浩繁,故不能不專一辦理。原奏所謂特開修訂法律館,無論何種法律,均歸編纂一節,范圍太廣,擬請飭照各國辦法,除刑法一門,業由現在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奏明草案不日告成外,應以編纂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諸法典及附屬法為主,以三年為限,所有上列各項草案,一律告成。其所請欽派王大臣為總裁一節,查修訂法律館之設,專為編纂法典草案起見,將來尚須由臣館核定,該館似無庸再由王大臣管理,免致重復。又所請以法部、大理院專司其事一節,查立憲各國,以立法、行政、司法三項分立為第一要義。今若以修訂法律館歸該部院管理,是以立法機關混入行政及司法機關之內,殊背三權分立之義。
根據此修律辦法,各部院及修訂法律館所編訂的法律法規盡歸憲政編查館核議,修訂法律館得以在身份上與各部院平行,脫離了刑部和大理院的束縛,得以獨立負責修律事宜。基于對之前身份和地位不明確而得到的教訓,根據憲政編查館制定的修律辦法,修訂法律館于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即奏請正式開館辦事,制定《修訂法律館辦事章程》十三條,館內設“提調、纂修等員及延聘東西法律名家”,由提調“奏調任用各員陸續到館”辦事,館內“設二科,分任民律、商律、刑事訴訟律、民事訴訟律之調查起草,設譯書處,任編譯各國法律書籍,設編案處,任刪定舊有律例及編纂各項章程,設庶務處,任文牘、會計及一切雜物。”
至此,修訂法律館真正獲得了獨立的地位,根據《修訂法律館辦事章程》該館負責“擬定奉旨交議各項法律;擬定民商訴訟各項法典草案及其附屬法,并奏定刑律草案之附屬法;刪定舊有律例及編纂各項章程。”并根據《憲政編查館辦事章程》,將所編訂律例法典及各項章程交付憲政編查館核議。至光緒三十四年,憲政編查館制定九年籌備立憲事宜清單,并命中央各部院將該機構根據籌備清單所應負責事宜開單臚列報憲政編查館負責,修訂法律館遂于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將該館所應負責事宜奏報憲政編查館審議,開始在憲政編查館的統率下負責修律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