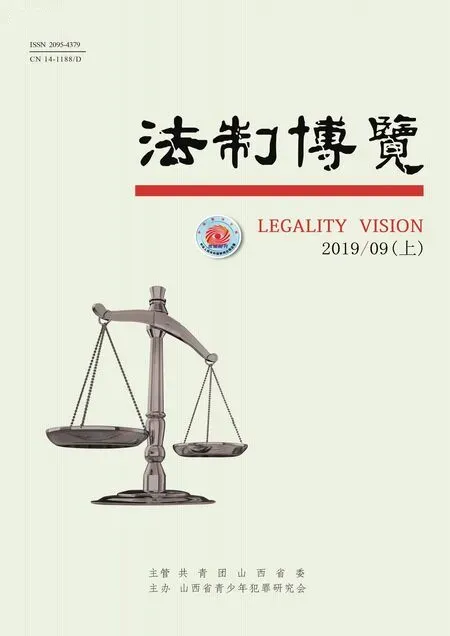論公證遺囑的優先效力
姚 遙
江蘇省南京市南京公證處,江蘇 南京 210000
我國法律意義上的遺囑,是指立遺囑人生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對其遺產或其他事務所作的個人處分,并于立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的法律行為。我國的《繼承法》一共規定了五種遺囑形式,即口頭遺囑、自書遺囑、代書遺囑、錄音遺囑和公證遺囑,其中公證遺囑是方式最為嚴格的遺囑,較之其他的遺囑方式更能保障立遺囑人意思表示的真實性。《繼承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不得撤銷、變更公證遺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四十二條規定:“立遺囑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數份內容相抵觸的遺囑,其中有公證遺囑的,以最后所立公證遺囑為準;沒有公證遺囑的,以最后所立的遺囑為準。”《遺囑公證細則》第二十二條規定:“公證遺囑生效前,非經立遺囑人申請并履行公證程序,不得撤銷或者變更公證遺囑。”根據上述規定,在我國,公證遺囑的效力高于其余四種遺囑的效力,具體包括:一、公證遺囑必須經過公證程序方可撤銷或者變更;二、立遺囑人死亡時留有多份遺囑的,最后所立公證遺囑生效。然而,現今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公證遺囑的優先效力表示反對,繼而引發了學界對于公證遺囑的大討論。
一、反對者們對公證遺囑效力優先的質疑
目前而言,反對者們對于公證遺囑效力優先的質疑主要有三點:一、認為公證遺囑效力優先違背了遺囑的立法目的;二、認為公證遺囑效力優先違背了遺囑自由原則;三、認為公證遺囑效力優先限制了立遺囑人的遺囑撤銷權。
首先,反對者們認為公證遺囑效力優先違背了遺囑的立法目的。遺囑繼承和法定繼承,其根本區別就在于確定繼承人范圍以及被繼承人遺產的種類、數量、份額時是否體現了被繼承人的意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法律制定遺囑制度,就是為了充分尊重被繼承人的意思自治,使得被繼承人的遺產能夠按照其意愿流轉,是法律保護公民個人財產權利的一種體現。這就要求最終生效的遺囑必須是立遺囑人生前真實自愿的并且是最終的意思表示。反對者們認為法定繼承的優先效力使得上述立法目的在部分情況下無法得到實現,公證遺囑絕大多數都可以被確定為立遺囑人真實自愿的意思表示,至于是否是最終的意思表示,則未可知。尤其是在立遺囑人立下公證遺囑后如遇突發情況,其想變更或撤銷公證遺囑時往往不具備再次履行公證程序的能力,這將導致公證遺囑所體現的并不是立遺囑人的最終意思表示,盡管在辦理遺囑公證時立遺囑人的意思表示是真實的。
其次,反對者們認為遺囑效力優先違背了遺囑自由原則。基于近代民事法律制度的一項重要原則即私法自治原則再結合我國《繼承法》第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并可以指定遺囑執行人”、《繼承法》第二十條第一款的規定“立遺囑人可以撤銷、變更自己所立的遺囑”,反對者們認為我國是采納了遺囑自由的原則,即立遺囑人享有訂立遺囑的自由、選擇遺囑形式的自由以及撤銷、變更遺囑的自由。而公證遺囑效力優先則在立遺囑人訂立公證遺囑后剝奪了其選擇遺囑形式的自由和撤銷、變更遺囑的自由,因為公證遺囑一旦成立,日后立遺囑人想要變更、撤銷遺囑必須再次履行公證程序,而無法通過其他的遺囑形式自由變更、撤銷。反對者們認為這是對遺囑自由原則的侵犯。
最后,反對者們認為公證遺囑效力優先限制了立遺囑人的遺囑撤銷權。基于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則以及遺囑本身的性質,立遺囑人在遺囑成立但尚未生效之前可以任意撤銷遺囑顯然是天經地義。反對者們認為這就包含了立遺囑人可以在任何時間及使用任何方式撤銷曾經所立的遺囑。然而公證遺囑的優先效力使得立遺囑人在訂立公證遺囑后必須再經過公證程序才能撤銷遺囑,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立遺囑人撤銷遺囑的權利。
總而言之,反對者對于公證遺囑效力優先的質疑,主要集中在最后一份公證遺囑未必代表立遺囑人的最終意思表示,同時公證遺囑限制了立遺囑人選擇遺囑形式和撤銷、變更遺囑的自由。
二、筆者對公證遺囑效力優先的肯定
筆者認為,反對者們對公證遺囑效力優先的質疑,看似其道理:公證遺囑程序復雜、繁瑣,耗時較長,不似其他遺囑形式隨時隨地就可以訂立,也不能保證立遺囑人在訂立最后一份公證遺囑后不會改變意愿。然而,反對者們所堅持的“自由”,有時也會成為保障立遺囑人“最終”意思表示的障礙。反對者們之所以堅持保護立遺囑人訂立遺囑的各種自由,均是相信立遺囑人能夠理性地訂立遺囑,處理好身后的事務。然而,現實生活并非總是如我們設想的一般美好。就目前看來,在我國,立遺囑人絕大多數是老年人,一旦受到家庭情況變化、自身健康狀況變化、生活時局變化的影響,立遺囑人極易陷入非理性的狀態下。立遺囑人在非理性狀態下所立的遺囑未必就能帶代表其最真實的意思表示,甚至可能與其在理性狀態下的真實意思表示相悖。另一方面由于除公證遺囑以外的其余遺囑在形式內容和保管上均具有極大的隨意性,立遺囑人去世后繼承人對于其所有遺囑很難收集完全,在有多份遺囑的情況下有時也很難判斷何為立遺囑人最終的意思表示,這對于還原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都是極大的障礙,由此造成司法資源浪費的情況亦不罕見。例如沒有簽署日期的自書遺囑,僅憑文字很難判斷立遺囑人是在何種情緒、身體狀態下立下遺囑,甚至無法確定訂立遺囑的時間,更加無法確認其是否為立遺囑人“最終”的意思表示。這些公證遺囑就完全可以避免。由于《繼承法》《公證法》《遺囑公證細則》等法律法規的存在,公證遺囑自當嚴格遵照公證程序辦理,其間公證員將反復與立遺囑人溝通,了解其身體情況、家庭情況以及立遺囑人內心的真實想法,對于年老體弱、危重傷病等特殊人員還要錄音或錄像。經過如此嚴格的程序,公證遺囑基本可以保證是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經過公證員的審查也能夠保證遺囑內容的合法性,實踐中公證遺囑極少被推翻或不采納也充分證實了公證遺囑的高質量。加之現在各地公證處都有上門服務,真正因突發情況來不及到公證處撤銷、變更遺囑的畢竟是極個別的情況,筆者認為并不能因此而徹底否定公證遺囑的優勢。
另一方面,依筆者的從業經驗而言,普通百姓認為公證遺囑的效力較其它形式遺囑為高并非完全基于法律上的優勢規定,更多是基于對公證機構公信力的認可,很多立遺囑人在并不知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也知道公證遺囑不能隨便更改,公證遺囑的公信力之深入人心可見一斑。有學者說得好:公證在某種意義上,是將當事人的法律行為或有法律意義的事實、文書植入社會公共信用體系的過程,使當事人可以通過相對便捷的程序和較小的代價獲得法律意義上的證明。公證遺囑因其較高的社會公信力,而要求立遺囑人在行使撤銷權、變更權時采用相同的程序以獲取相對等的公信力,在筆者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同時,公證遺囑并非過度限制立遺囑人的自由,事實上在立公證遺囑之前立遺囑人完全有選擇其他遺囑形式的自由,在辦理公證遺囑的過程中公證人員也會反復提示立遺囑人。而一旦立遺囑人選擇公證遺囑的形式,勢必會因公證遺囑的高公信力而受到相應的限制。其實我國的法律對于遺囑的形式并非如反對者們所言完全沒有限制,例如遺囑的形式法律只規定了五種,對于其他諸如打印遺囑、錄音遺囑等均未做規定,由此可見我國法律對于遺囑并非采取完全放任自流的態度,還是有所限制的。
因此,筆者認為現行的公證遺囑效力優先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利大于弊,簡單地取消公證遺囑的效力優先性實不可取。
三、筆者對完善公證遺囑的一點建議
然而如前所述,反對者們對于公證遺囑效力優先的質疑也不無道理,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公證遺囑事后的撤銷、變更無法從權、從簡,特殊情況下使得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無法得到法律的支持,從而違背了遺囑立法的本意。筆者認為,我國的遺囑立法可以設立緊急情況下的特殊遺囑制度,參照設立口頭遺囑的情形,在發生嚴重疾病、交通障礙、自然災害等臨危急情況下,如立遺囑人無法親自到公證機構變更或撤銷遺囑,可在兩名以上的見證人的面前,設立見證遺囑或口頭遺囑等特殊遺囑。在危急情況解除后的一定合理期限內,立遺囑人應當及時到公證機構變更或撤銷公證遺囑,否則特殊遺囑即告無效。如此一來,既可以揚公證遺囑之長,又可以避免公證遺囑之短,解決公民的意思表示和公證遺囑權威性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公證機構也應當各自完善運行制度,合理簡化遺囑公證的辦證流程,并對有實際需要的上門遺囑優先辦理,真正做到未老百姓著想,將公證服務于民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公證遺囑效力優先性自一九八五年《繼承法》實施一來就一直存在,幾十年來運行良好。如今雖然出現了一些質疑,但實踐證明公證遺囑的效力優先性依舊利大于弊,簡單地將其取消并不可取。公證行業應當進一步完善公證遺囑立法并彌補實踐中的缺陷,使得公證遺囑業務運行更加良好,那么質疑的聲音必將在不遠的將來隨風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