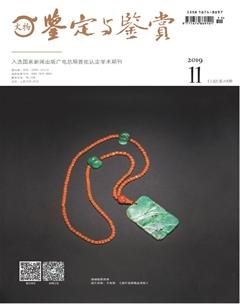遵循與悖離
李康
摘 要:“淵明情懷”是晉宋以后文人一直書寫的重要主題,并且形成了較為固定的書寫范式。南宋遺民詞人筆下的“淵明情懷”在遵循傳統的同時,又在書寫方式上有所悖離,呈現出單一性傾向和挽逆性傾向。這種悖離是南宋遺民詞人特殊的文化心理造成的,“淵明情懷”的書寫也因此增加了帶有時代和群體烙印的新質素。
關鍵詞:南宋遺民詞;“淵明情懷”;書寫方式;遵循;悖離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以其詩文為核心建構起來的“淵明情懷”包含:“任真自得”①的人生追求、“安道苦節”②的品格操守、恬淡曠遠的胸襟懷抱、返璞歸真的美學境界,對后世文人的精神世界有著極為深刻且深遠的影響,成為他們在作品中反復觀照吟詠、思慕追和的書寫主題。在“淵明情懷”漫長的書寫史中,南宋遺民詞人對“淵明情懷”的書寫頗具新意,他們超越了傳統書寫范式的拘囿,以破為立,書寫出了“漢民族亡天下”的深哀巨痛,為“淵明情懷”增加了異態文人群體的獨特印記。
相比前人,南宋遺民詞的“淵明情懷”書寫方式呈現出單一性傾向,核心意象高頻率復現是其采用的主要方式。“淵明情懷”是以陶淵明詩文為載體呈現出來的,其中的意象、語句、意境等則是各個時期士人書寫“淵明情懷”時所共同選用的對象。“和陶”“擬陶”“詠陶”和對詩文意義的檃括、意境的化用、意象的借用、詩句的引用等,是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淵明情懷”的主要途徑。在多種書寫方式中,南宋遺民詞人很少采取“和陶”等整體性沿用陶淵明詩文意義、意境的方式,而多是借用其核心意象來構建書寫體系。因而,“淵明”“五柳”“桃源”“南山”“晉菊”等核心意象高頻率的復現成為其書寫的重要特點。這種高頻率復現在作品中以三種形式呈現出來:一是各核心意象在遺民詞中整體性的集中出現,比如“淵明”意象出現22次,“南山”意象出現20詞,“晉人”“晉夢”等出現33次。二是個體詞人對某一意象的反復使用。比如“桃源”意象在張炎的詞中出現了7次。這種現象并不唯一,在其他遺民詞人身上也多有體現。三是多個核心意象在一首作品中疊加出現。比如趙玉淵的《念奴嬌》(中年怕別)中將“菊宋”“折腰”“淵明”三個核心意象集中到一句詞中。
意象的運用講求陌生化,但如果某些意象受到同時代某一作家群體的特別關注,并且突破個體風格的局限在他們的作品中進行反復的強調和表現,我們就不能把這種現象看成是偶然的藝術巧合。這無疑反映出詩人們更深層次的心理積淀。同為書寫隱逸之趣,蘇軾和辛棄疾詞都曾在完美檃括陶詩原作的基礎上彰顯出明確的“我”之形象和自我情懷,但選擇檃括的書寫方式卻決定了詞中自我形象與情懷和原作具有一致性走向,屬于改其詞而不改其意。作者選擇檃括這一方式的目的就是要表達和陶淵明一致的心志情懷。“和陶”等其他整體性沿用的書寫方式也都具備這一特點。而南宋遺民與慣常采用的核心意象高頻率復現于作品的書寫方式則完全不同。盡管這類核心意象本身都被陶淵明詩文附加了特殊的意蘊,并且在士大夫話語系統中約定俗成,但是它們進入作品時呈現的是碎片化的狀態,表現的是“淵明情懷”的某一側面或某一質素。所以,使用這一書寫方式往往表現的是“淵明情懷”的局部而非整體,與其他意象組合后,作品最終生成的意蘊可能就會與“淵明情懷”既有交纏,又有所不同。如仇遠的《秋蕊香》:“三徑歸來秋早。門外金鋪誰掃。東籬不種閑花草。惱亂西風未了。霜華侵鬢淵明老。南山曉。啼紅怨綠駸駸少。自采落葉英黃小。”詞中包含了“東籬”“淵明”和“南山”三個核心意象。“東籬”“南山”在“淵明情懷”的話語系統中表達的是靜穆淡遠、閑適出塵的意蘊。而在這首詞中,詞人在這三個意象外還選用了“西風”,寫“西風未了”帶來的無奈;選用“霜華”寫“霜華侵鬢”的悲涼;選用紅花、綠草寫“啼紅怨綠”的哀傷。這些含蘊明顯與“東籬”和“南山”所表達的靜穆出塵的意蘊不屬于同一指向。因而,這首作品雖然復現多個“淵明情懷”的核心意象,但其表達訴求卻遠比核心意象的內涵更為豐富復雜。
南宋遺民詞“淵明情懷”書寫方式還呈現出挽逆性傾向,多數“淵明情懷”意象的語境含義是與原始意義相悖的。張炎詞多數“淵明情懷”的書寫多有這一特征,如“那又知、五柳門荒,曾聽得、鵑啼了”(《水龍吟·春晚留別故人》),“桃花遠迷洞口,想如今、方信無秦”(《聲聲慢·賦漁隱》),“待去隱,怕如今、不似晉時”(《聲聲慢·為高菊墅賦》),“休去、休去,見說桃源無路”(《如夢令·題漁樂圖》),“東晉圖書,南山杞菊,誰識幽居懷抱”(《臺城路·章靜山別業會飲》)等。毫無例外,在這些詞句中“淵明情懷”核心意象的原初意義都是被質疑或否定的。通過這種方式詞人暗示出當今“人間無處可避秦”的社會現狀。“五柳門荒”“不似晉時”“桃源無路”等皆是在言說現實社會中“隱”而不得,“隱”而不能。“淵明情懷”的“隱”是身心真正地忘懷世事,超越煩愁。但刻骨銘心的國仇家恨、異族政權的強迫征召、個人生計的窘迫無著,使詞人不可能尋找到精神上安寧平和的太平樂土。所以詞人身隱而心難隱,“誰識幽居懷抱”,他們利用對傳統意蘊挽逆傳達出內心的哀怨與迷茫無著之感。
挽逆方式的運用在南宋遺民詞的書寫中較為普遍。劉辰翁詞風豪放沉郁,獨立于南宋遺民詞掩抑低回、婉轉凄切的主體風格之外,顯得特立獨行。但在他的作品中我們仍然看到了挽逆式書寫,比如這首《水調歌頭》:“不飲強須飲,今日是重陽。向來健者安在,世事兩茫茫。叔子去人遠矣,正復何關人事,墮淚忽成行。叔子淚自墮,煙沒使人傷。燕何歸,鴻欲斷,蝶休忙。淵明自無可奈,冷眼菊花黃。看取龍山落日,又見騎臺荒草,誰弱復誰強。酒亦何有好,暫醉得相忘。”這是一首重陽詞,但整首詞并沒有重陽節應有的歡愉之情和祝福之意,而是充滿了世事滄桑、年華老去的無奈和傷感。下闋觸筆書寫“淵明情懷”,詩句“淵明自無可奈,冷眼菊花黃”中用“自無可奈”寫即使陶淵明面對此番情景也會無可奈何,沒有辦法超脫出去,用“冷眼”顛覆傳統“淵明情懷”中陶淵明與菊花的關聯,由原來的青睞轉變為漠然。這里的書寫方式明顯是運用了挽逆的手法,通過否定原有意蘊來表達現實性的感受。
南宋遺民詞在“淵明情懷”書寫方式上對傳統的悖離是由其特殊的文化心態決定的。就心理狀態而言,絕大多數南宋遺民的隱逸是被動的,是在國破家亡的社會背景下為堅守自己的志節而不得已的選擇。他們的隱逸與以“淵明情懷”生發主體陶淵明為代表的常態社會下的士人之隱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心態。常態社會下士人的隱逸多數還是主動認同和追求一種自然醇真、高蹈出塵的人生境界,他們文化心態里并未涉及改變自我文化身份和被動的自我放逐。南宋遺民詞人文化心理的糾葛是極其復雜深刻的。歸隱山林并沒有使遺民們輕松而坦然地投入世外林泉,相反給士人帶來的是身心俱疲的折磨。在儒家思想的潛移默化下,經世致用的用世思想、治國平天下的使命意識、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責任感構成了中國士人精神世界的主體,南宋遺民詞人當然也不例外。但在特殊的歷史氛圍中,他們所做出的疏離主流社會歸隱山林,以失語狀態對抗元蒙政權,其人生唯一選擇弘揚了士人忠孝節義的道德力量,同時卻消解了積極入世精神外化的可能。這意味著中國士人傳統的人生價值在南宋遺民詞人身上嚴重失落。此時走上“獨善”之途,其實就是徹底扼殺了世代士人孜孜以求的建功于世的人生理想。在這種文化心理下,他們在書寫反映隱逸心態的“淵明情懷”時與傳統大有不同。傳統的書寫是要表現與陶淵明一致的由隱居山林帶來的淡然與平和。而遺民詞人們的書寫則是表達因亡國而被迫隱逸的失落不甘和悲慨怨懣。因而,其采用的書寫方式也必然要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悖離。悖離不但沒有使這些反復使用的意象和意境在他們的詞中失去新鮮感,反而增強了新的表現力,成為表現遺民悲怨凄婉、無處依托、心靈痛苦的強有力手段。同時也為“淵明情懷”增加了帶有時代和群體烙印的新質素。
參考文獻
[1]龔斌.陶淵明集校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唐圭璋.全宋詞[M].北京:中華書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