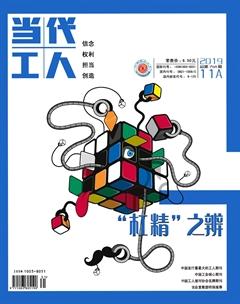劃清義務邊界比判決對錯更重要
劉興偉
明斷是非,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難的事情之一,因為真實的生活、具體的場景總是千差萬別,而這恰恰又是司法審判最常遇到的情況,更是當下對司法審判所賦予的時代使命。
在法制史上,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春秋決獄”,而在當下我們面臨的是快速的城鎮化進程,及城鎮化給社會帶來的最直接影響——人與人之間從“熟人社會”快速進入到“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的維系主要靠道德和社會關系,“陌生人社會”更多的是講規則。“陌生人社會”的規則并不容易建立,明晰的規則是類似于統一市場、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這種規則不是大而化之的原則,而是具體到摔一個跟頭究竟是誰的責任這種具體而鮮活的權利義務邊界。
小琳與公交公司、住建局之間的糾紛,本質上不是一起簡單的侵權或合同糾紛,而是對現代生活中陌生人之間義務邊界的界定。小琳下車有一定注意義務,司機開車有一定服務義務,市政有一定維護保養義務,如何平衡這三者的關系,一審和二審針對舉證情況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中肯地講,作為公共服務提供者,市政的義務最為明顯,即便不能及時維護保養,作出適當的警示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避免糾紛的發生。小琳和司機義務的平衡有一定難度,加上公交公司受運輸服務合同調整,且公交公司和市政存在共同侵權的情節,最后呈現出這樣的裁判結果。
判決答案是否正確不能簡單論斷,從法律思維出發最重要的也不是對錯,而是這一答案能夠保持統一性和終局性,即能否經受住更多個案和時間的考量。由此形成的具有統一性和終局性的邊界劃分,對陌生人社會而言將是寶貴的財富。
除了以上標準,對這種義務邊界的劃分還有一個有趣的判斷尺度,那就是換位思考。政治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了著名的“無知之幕”理論,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會在一個規則中扮演什么角色時,他所認同的規則很可能就是公正的規則。比如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不從小琳的角度出發,也不從公交公司和住建局的角度出發,而是先落下一塊“無知之幕”,假設自己可能會成為這三個義務人中的任何一個,這時的我們會認同怎樣的義務界定?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裁判者的答案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所以,羅爾斯在“無知之幕”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概念“重疊共識”,就是那個大多數人認同的答案。這個共同認同的部分將是一個社會得以良性運轉的重要基石。
從某種程度上說,裁判者無法憑空建構“重疊共識”,裁判行為更多是對“重疊共識”的一種外在表現和反饋,當這種反饋達到一定程度,社會便會擁有一份寶貴的社會公共財富。在社會形態快速變化的今天,司法審判的終局性常常會受到時代變化的影響,也正因如此,在每一個個案中努力劃清權利義務邊界的裁判者尤為值得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