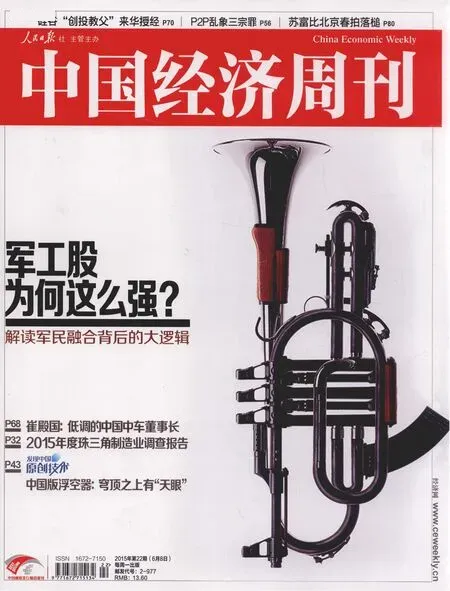實施競爭政策,應對復雜經濟形勢
王山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風險挑戰,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今年三季度,我國GDP初步核算的同比增長率為6.0%,比上年同期回落0.5個百分點。在復雜經濟形勢下,更需要將 “競爭中性原則”、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落到實處,對此,需要研究好競爭政策內涵和外延、競爭政策工具選擇、競爭政策實施路徑等問題。
如何認識競爭政策?
競爭政策是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的根本保障,也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一項基本政策。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提出要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同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要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足見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對當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從世界各國和經濟體的競爭政策實踐來看,競爭政策一般包括競爭法律制度以及與之有關促進競爭的公共政策,競爭法律制度是其主體,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美國、歐盟的競爭政策實踐主要采取了狹義的方式,其競爭政策被稱為競爭法,以反壟斷法為核心內容。如歐盟競爭政策的主體內容主要包括禁止限制性商業行為、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合并審查、國家援助審查、競爭宣傳、國際交流與合作等。而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則從廣義角度界定競爭政策。前者將競爭政策界定為包括競爭法和其他旨在促進經濟發展的競爭相關措施, 如部門管制和私有化政策;后者將競爭政策界定為市場競爭相關的所有政策,包括貿易政策、調控政策和政府為處理私營或公共企業的反競爭政策所采取的各種政策。
競爭政策概念移植于國外,受此影響,我國學者對競爭政策的理解,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競爭政策是指以促進和鼓勵公平競爭為核心的競爭法律制度。廣義的競爭政策是指一整套旨在確保市場競爭免受不當限制的政策和法律。
對競爭政策的界定存在著不一致的看法,給競爭政策的頂層設計和具體實施帶來困擾,需要對競爭政策有個一致性的界定。實際上,從我國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政策主張和具體實踐可以得出,對中國特色的競爭政策內涵的界定,既要考慮借鑒世界各國和經濟體對競爭政策內涵界定的普遍做法,也需要在移植世界各國和經濟體有關競爭政策內涵的同時,考慮我國特有的政治環境、社會基礎、經濟發展狀況、價值取向、法治背景對維護公平競爭的兼容程度,立足現階段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的現實需求,堅持問題導向,體現競爭政策界定的“中國化”。
在分析世界各國和經濟體競爭政策實踐基礎上,立足我國國情和對競爭政策實施現狀判斷,可考慮將我國競爭政策內涵分為理念上的內涵和實踐上的內涵。理念上的內涵界定采用廣義的方式,可將競爭政策理念上的內涵界定為:黨和國家為了維護公平市場競爭而制定的解決競爭問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理念上的內涵闡明了對維護公平競爭的立場,但在實踐過程中需要抓住重點,不能面面俱到,而要考慮競爭政策可操作性,將競爭政策范圍限制在規制市場壟斷、行政壟斷范圍內。可將競爭政策實踐上的內涵界定為:反映黨和國家反壟斷意圖的指導原則和措施,既包括反壟斷法、體現反壟斷法條款的相關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也包括體現在黨中央文件中各種反壟斷主張。
如何看待競爭政策工具?
競爭政策工具既可以界定為 “客體”,也可以界定為“活動”。如果將競爭政策工具界定為“客體”,有關維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可以看作是競爭政策工具;如果將競爭政策工具界定為“活動”,有關維護公平競爭的治理活動可以看作是競爭政策工具。若將競爭政策限定在反壟斷領域,《反壟斷法》是“客體”范疇的競爭政策工具,而公平競爭審查、競爭倡導則是“活動”范疇的競爭政策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反壟斷法》與公平競爭審查、競爭倡導不是同一語境下的競爭政策工具,故此,在制定和實施競爭政策過程中,不宜將“客體”范疇競爭政策工具即《反壟斷法》和“活動”范疇競爭政策工具即公平競爭審查、競爭倡導放在同一層面。
實際上,對經濟政策工具內涵一般是從“活動”范疇來界定的,例如將公開市場操作、調節存款準備金和再貼現等作為貨幣政策工具,將財政收入、財政支出、政府投資等作為財政政策工具,而鮮有將貨幣領域和財政領域的法律作為政策工具。因此,對于競爭政策工具界定宜從“活動”范疇界定,根據我國《反壟斷法》目標,可以將競爭政策工具看作:為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以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而采取的各種手段和方式。
根據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的實現競爭公平有序、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等要求,結合《反壟斷法》等要求,我國競爭政策工具包括7個政策工具(“4+1+2”),分別為:禁止壟斷協議、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經營者集中審查、禁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爭,公平競爭審查,競爭指導、競爭倡導。
如何實施好競爭政策?
在實施競爭政策時,可考慮聚焦黨中央和國務院有關實施競爭政策新要求和反壟斷相關法律規范,呼應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實施競爭政策的新期待。
在競爭政策界定方面,區分理念上的內涵和實踐上的內涵,將“反映黨和國家反壟斷意圖的指導原則和措施,既包括反壟斷法、體現反壟斷法條款的相關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也包括體現在黨內文件中的各種反壟斷主張”作為實施競爭政策的內涵和外延。在競爭政策目標方面,將競爭政策目標限定在反壟斷領域,以避免制定和實施競爭政策中混亂和不確定性。將“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作為競爭政策目標。在競爭政策工具方面,從“活動”角度而不從“客體”角度界定競爭政策工具,將“禁止壟斷協議、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經營者集中審查、禁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和限制競爭,公平競爭審查,競爭指導、競爭倡導”作為現階段競爭政策主要選擇的工具,綜合運用。
在競爭政策范圍方面。統籌考慮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有關實施競爭政策的部署安排、反壟斷法以及有反壟斷條款的其他法律。聚焦反《壟斷法》所規制的范圍,同時兼顧其他法律中反壟斷條款,如《專利法》《價格法》《合同法》《對外貿易法》《旅游法》《中小企業促進法》《港口法》《標準化法》《電子商務法》等涉及的反壟斷條款。
在競爭政策措施方面。考慮從優化競爭立法、強化競爭執法、加強競爭指導、創新競爭倡導、重點領域競爭政策落實、強化競爭司法協作等角度,堅持問題導向,兼顧一般和重點,研究制定全方位的競爭政策實施措施。在競爭政策保障方面,考慮從競爭政策實施規劃、競爭政策實施人才和資金保障、競爭政策實施評估和考核、競爭文化培育等方面,為競爭政策實施提供綜合保障體系。
責編:陳棟棟 chendongdong@ceweekly.cn 編審:張偉美編:孫珍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