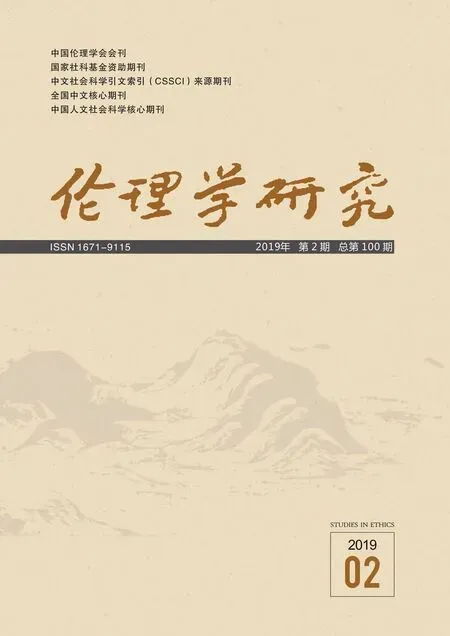論《顏氏家訓》中的政治道德教育思想
洪衛中
《顏氏家訓》是北齊文人顏之推所寫的一部教訓子孫的著作,也是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從修身、齊家兩方面來論說讀書人如何立身處世、傳業揚名、振興家族的著作,故后人譽之為“古今家訓以此為祖”[1](P205),《顏氏家訓》因此不斷被后人研究。不過,到目前為止,人們研究最多的還是《顏氏家訓》中有關子女的成長教育、立身處世教育內容和思想,對其中寓含的政治道德教育思想則缺乏必要的研究。筆者不敏,下文試對此作探討,不妥之處,敬請指教。
一、政治道德教育思想為《顏氏家訓》一顯著特色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戰爭不斷、政權頻繁更迭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士族享有特權并極重視家族發展的時代。無論出世還是入世,是佐命帝王建立功業還是幫助權臣篡權發動政變,士族文人的最終目的不外是發展家族、振興家族,因而門戶之興或保持門戶也就成為六朝士族不懈的追求。譬如西晉末年八王之亂時大族紛紛避禍南下,時衛玠也“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啟諭深至,為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2](P1067)。再如齊“建武中,(王思遠)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欲并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后名’”[3](P660)。這種以門戶為重的現象不僅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漢人士族中普遍存在,即使在北魏朝廷下的漢化鮮卑貴族中也不乏見之。如北魏高宗拓跋濬乳母常氏對高宗保護有功,故而高宗即位后,常氏被尊為皇太后,其兄常英、弟常喜等也因此被封官加爵。不過常英當初侍奉母親宋氏不如妹夫王睹恭謹,故而有人對常太后說:“何不王睹而黜英?”常太后卻說:“英為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4](P1817)又如陸凱也曾置酒對諸親說:“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耳。”[4](P906)可見重視門戶發展乃魏晉南北朝士族階層生活中之最大要事。
然而另一方面自夏王朝開啟家天下政治模式后,中國人心里從此又有了家與國為不可分割之整體思想,甚至認為家與國就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家是國最小的社會單位,是國的縮小,而國則是家的擴大和延伸。這種家國同構理念對中國古人思想影響深遠,使他們將家的治理和國家的治理幾乎看作是同一回事。如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5](P46)《詩·大雅·思齊》也說:“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6](P410)《大學》也說:“家齊而后國治”[7](P4),又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7](P9))《孟子》更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7](P278)不難看出,先秦以來的理論思想無不將家和國的關系緊密維系在一起,甚至很大程度上認為沒有家庭的很好治理也就沒有國家的很好治理,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7](P9)。同樣,沒有國家的強盛繁榮穩定也就沒有家的和平與安寧。如春秋戰國之際,“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8](P3101)。西晉末年,“政亂朝昏,禍難薦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兇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涂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2](P2297)。故而在戰國末出現的《呂氏春秋》就指出:“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9](P376)。因此我們也就看到先秦以來無論貴族還是一般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多在這種家國同構思想的深刻影響和作用下為國家的安穩和興盛不斷去奮斗,為保衛國家義不容辭走上戰場。
魏晉南北朝時期盡管政權更迭頻繁、戰爭和天災不斷迫使人們更多地珍重生命和注重家族利益,但家國同構理念在質的權重上并沒有多少減少,只不過因政治環境、生存環境的改變不少士人對家國同構理念的理解換了一種方式而已,至于一定時候某種程度上他們對家族利益的重視超過了對政權統治的重視,在效力于國的同時更致力于對家族的經營,這也就使得注重家族發展并對子孫作家訓成了這時期士族乃至一般庶族在政治上的一個顯著特點。
顏氏家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不是顯赫的甲族膏粱,卻也是文化盛門,它以儒學立家并秉持儒家精神立身處世。盡管到南北朝后期在仕宦上它已漸趨一般,但在文化上仍然占有不可忽視地位。如蕭繹為湘東王出鎮荊州時,顏之推父親顏協即為湘東王國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10](P727)。因梁江陵政權滅亡而被迫北遷的顏之推歷經南北,在感受魏晉以來社會上特有重視家族利益氛圍和不同政權對文化世家大族重視的同時,也愈加認識到了家國同構理念的不可分割,從而把發展家族利益和處理與政權之間關系緊密結合在一起,故而人生后期他在撰家訓教導后人如何興立門戶、揚名家族的同時,也特別注入較多的政治思想教育,從而使得本是如何教子、齊家的家庭教育很大程度上也滲透了與國家層面相關的政治道德教育思想。錢穆所謂魏晉南北朝“當時門第傳統的共同理想,所期望于門第中人,上自賢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兩大要目:一則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內行,一則希望其能有經籍文史學業之修養”[11](P171)雖點出了當時大部分士族傳承過程中的一大特點,但并不全面。考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家族門第傳統可發現,這時期士族門第在傳承中的一個較為顯著現象就是,除了特別原因外,家族每代成員都會盡可能與統治政權發生關系,參與政權之中。只不過,這點較少被記載和論說而已。
也因此,相比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作家訓者不少,如諸葛亮作有《誡子書》、王修撰有《誡子書》、王祥作有《訓子孫遺令》、嵇康撰有《家誡》、羊祜也撰有《誡子書》、王昶撰有《家誡》、顏延之作有《庭誥》、王褒撰有《幼訓》等,然考察這些家訓內容,它們絕大多數都只是停留在對子孫立身、處世、為人、治學、避禍等方面不同程度的說教上,于齊家論之都不是很多,遑論具體的政治道德教育思想了,因為在他們看來士人的發展就應遵行《大學》中所說,身修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7](P4)。因而只需論立身、處世等就足矣,其他則無需再論。盡管徐勉《為書誡子菘》中涉及到一點政治思想教育,但也僅表達為:“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12](P3238-3239),而北魏的楊椿在《誡子孫》中總結居官經驗時對子孫雖也作出一定的做官方面教育,但內容也不過是告誡諸子孫要“宜深慎言”[12](P3720)而已,至于如何對待政事、如何對待君主、如何為官等皆諱莫如深,不作絲毫涉及,不像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于政治道德思想方面對諸子教育不僅內容多,且涉及面也不少,所以這也就使得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眾多家訓中政治倫理道德思想教育成為《顏氏家訓》一顯著特色,甚至如后來司馬光的《家范》和《居家雜儀》、袁采的《袁氏世范》等著名家訓也少有《顏氏家訓》中這樣多的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唯有曾國藩的家書中稍有涉及。
二、《顏氏家訓》中政治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顏氏家訓》中政治道德教育思想雖沒有被顏之推以專門篇章形式作單獨論說,但梳理綜合之后可發現,它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內容。
1.對忠君政治道德思想的論說
在《顏氏家訓》中顏之推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來教導諸子立身、處世、為人以及傳業揚名的,因此在家訓中他不僅強調家庭內部的孝悌,而且談到了忠君。不過,顏之推身仕梁、西魏、北齊、北周、隋等南北五個政權,按照先秦以來崇奉的政治道德思想“事君不貳是謂臣”[13](P347),“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14](P73)和兩漢以來“忠臣死君命”[15](P2414),“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15](P1874)“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2](P1399)的思想意識來看,顏之推算不上一個忠臣[16]。對此顏之推自己也承認,在江陵政權被滅后,他就曾說:“小臣恥其獨死,實有愧于胡顏”[17](P623)。不過由此反觀顏之推,可知其心中并沒有泯滅忠君思想意識,也因此面對“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18](P389)這樣一個政治現實狀態時,顏之推也就不能完全超脫但重利益而不顧節操倫理,其祖父顏見遠不臣二主的行為和顏氏固有家風使他在罔顧是非的朝代更迭中最終還是毅然決然地選擇了追求“王道郁以求申”[17](P625)這樣的艱難人生之路。也就是說在骨子里顏之推實質上仍深懷忠君思想意識,只不過現實中他事多個政權的行為和事實讓他自覺與自幼就接受和形成的倫理節操意識相違背,他也就難以底氣十足地向世人鮮明宣揚和論說兩漢以來的忠君思想。然而忠君不但一直是顏氏家族秉承的倫理道德,事實上于顏之推而言,除了身事多個政權之外,他的言行無一不顯示他具有較為濃厚的忠君意識,而且身事多個政權并非他主動選擇,而是被迫為之,且這種行為又幾乎是魏晉南北朝士人階層中一種普遍現象,因此對顏之推來說,作為顏氏家族成員他必須傳承忠君思想,而作為“王道郁以求申”的儒教振興者他也必須擔當這種責任。
只不過因時代的變化顏之推的忠君思想已并非如其祖父那樣僅表現為單一的忠一家一姓君王之節,而是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個為原初層面上的忠,即先秦以來“事君不貳”的忠臣思想。在這個層面他的思想贊同為君盡節者,對違背儒家忠君思想者予以嚴厲譴責。譬如對北齊宦者田鵬鸞“斷四體而卒”依然不吐露半點后主下落,他就極為贊嘆:“蠻夷童卯,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18](P202)又說:“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18](P166)。另一個方面則是他因時因世發展的新的忠君理念。在這方面他認為“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18](P166),又說:“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18](P391)。在這里顏之推宣揚的是一種新的忠君理論,即作為士人,不論臣仕哪個政權,只要忠于職守,對政權作出有益于其發展的建議和貢獻,在危難之際能見危授命,就是忠君,換句話說也就是平時在崗位上盡忠職守,不瀆職不侵權,為國家的發展提出必要的建議和謀略,在危難時刻為國家分擔憂愁,承擔保衛國家的使命,以國家社稷為重,就是忠君。而且他還認為,在非常之際,忠君既可以選擇舍棄雙親為主死節,也可以選擇盡孝保家而不以身徇主,二者不管作何選擇都是正確的。不難看出,顏之推這種新的忠君理論因時代的變化更多也更主要的表現在了對工作和職責的恪守、對使命的完成、對雙親的孝敬和對家族的發展,卻淡化甚至不論政治道德。應該說顏之推的這種新的忠君思想既不同于先秦至兩漢以來統治者所倡導和追求的守一家一姓王朝而為之殉節的“不屈二姓”的“夷、齊之節”[18](P258),也異乎于先秦儒家的那種官吏盡忠于民和事上忠誠、不貳其心的忠的思想[19](P381-387),是亂世之下顏之推因時總結形成的一種新的忠君政治道德思想,“是將儒家忠君思想作了現實化的時俗新解”[20],很大程度上也是這個時代士人忠君思想的反映。而顏之推在《家訓》中也就是將這樣的忠君思想傳遞給后人的。
2.為舊君避諱的政治道德意識
自先秦以來到兩漢,人們對君臣關系的意識雖然幾經變化①,但總體上還是以周禮中尊君尊王思想為圭臬,因此《春秋》中不但顯明尊王思想,還積極倡導“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21](P192),而且這種避諱并非單單只是對尊、賢、親者的名、字避諱,還包括對他們尤其是君王所做的某些非道德行為的隱諱不書;不僅對健在者避諱,也對逝去者避諱。而且“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22](P196),一如張舜徽先生所論:“古者事涉君親,必多隱諱,此歷朝所以無信史也……茍事涉君主,必為隱諱。則君主之祖先、子嗣、戚姻,以及權柄之貴臣,皆在所必諱。”[23](P79-80)而就避君諱而言,其實質就是要體現和表明對君主政治道德上的思想敬重。
東漢末軍閥割據稱雄以及魏晉南北朝政權頻繁更迭帶來了不少士人至少臣仕兩家不同姓氏君主的事實,這在儒家和先秦以來的社會政治道德角度來說,無疑是一個不爭的不體面之事,因此,大多數士人對自身或他人臣仕二姓君主或王朝皆緘默其口,不論是非;在現實生活中也都在言行上表現為臣仕新朝新君后也不毀辱舊君舊主,這不僅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內在要求,也是士君子立身處世的內在品質素養表現。亂世之下的顏之推秉承了這樣的政治道德理念,為此在教育后人對待臣仕過的舊君時,不但對那些非毀舊主舊君者不以為然,還十分反感,甚至給予批評。他說:“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制檄,則目紹為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18](P258),又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18](P237)。可見在顏之推的眼里彰顯舊君之過是很不道德的行為,是士人為人立身處世的大忌,由此他教育后人即使不免出仕新朝,對舊君舊主也要敬重,少言甚至不言其過錯,事涉舊君舊主要多為隱諱。相比較而言,庾信在《哀江南賦》中詆毀、侮辱舊君梁元帝為“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于己”“既言多于忌刻,實志勇于刑殘。但坐觀于時變,本無情于急難”[24](P740)不免顯得在政治道德方面要遜顏之推一籌。
3.從政為官方面的政治道德思想
中國古代政權結構和治理模式決定了士人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參與到政權之中,這就決定了士人必須遵行儒家“學而優則仕”思想之路去走,這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及其后代而言也不例外,因此仕宦之途也就成為絕大多數士族文人為保持門戶、發展家族不得不走之道路。深受魏晉南北朝社會重家族思想影響、念念不忘“傳業揚名”[18](P608)發展家族的顏之推對入仕為官尤為重視,因此在家訓中對這方面也作出了較多論說。
首先在入仕思想上他認為要保持正確的態度,即“守道崇德,蓄價待時”。顏之推說:“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18](P334)在他看來,士人入仕的前提條件首先就是要堅守“道”、崇尚“德”,然后在此基礎上不斷增強自身才干,等待時機而出仕。很明顯,作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并要繼續發展儒家思想的顏之推在這里所說的“道”無疑是指儒家思想,而其所謂的“德”也無疑是指儒家思想準則下的倫理道德,顏之推所表達的入仕思想實質就是要求后人按照儒家思想修身立世、遵循儒家道德做人處事,等待時機。他認為如果這樣還是官爵不登、俸祿不入,那也只能說是天命如此,萬不可去強求。顏之推的這種思想和孔子所謂“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25](P1068)思想很大程度上有著相同之處,甚至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孔子這一思想的另一種表達。因此,顏之推也就頗為反對以違背儒家道德思想的行為方式去入仕參政。他說:“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非士君子守法度所為也。”[18](P330)對這類取官行徑顏之推極為反對。同樣,對“須求趨競,不顧羞慚,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喧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這種不顧羞恥巴結權貴、混淆視聽、揚人之過、夸己之功來跑官要官行為他也是強烈反對和不齒的,所謂:“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18](P334)在他看來,這些入仕為官途徑都是非“守道崇德”行為,都不可踐行之,從而教育后人入仕為官必須走正道,注重守道修德,在條件成熟或時機允合時再憑德才入仕。
其次在為官宗旨和目的上忌貪利躁進,主張“濟世益物”和不“費人君祿位”。歷經南北的顏之推盡管仕宦不墜,卻也坎坷兇險,特別是耳聞目睹“自喪亂已來,見因托風云,僥幸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五人也”[18](P347)這樣血淋淋的官場現實時,他愈加深感其九世祖顏含所立家規的正確性,那就是:“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12](P2225)。盡管此家規咋一看似乎限制了顏氏后人在政治上的發展,不利于顏氏家族的發展,但實質上卻是避免顏氏后人在官場上犯下不務實而貪功躁進的良苦用心。因此,顏之推寶持崇重之,并諄諄告誡后人做官不可僅圖升遷、貪位趨競,更不可逐勢躁競。由此他要求后人為官必須遵行先祖所定家規,“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18](P347)。并要求“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18](P347)。可以說顏之推的這種為官思想不僅承繼了其九世祖顏含為官理念,也吸取了當代為官者貪位逐利不為實務的教訓,所以在仕宦上他要求后人秉持一個正確的態度和思想。他認為做官就應該“濟世益物”和不“費人君祿位”。
不過魏晉南朝是士族在政治上占據優勢強權的時代,士族不但享有為官特權,“平流進取,坐至公卿”[26](P438),在職守上也多表現出“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2](P1992),“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2](P136)這樣一種從政狀態,至于梁世時這種士族官風發展到了極為腐朽地步,不但許多當官者“難可以應世經務”[18](P317),還出現了諸多“士大夫恥涉農商,差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才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18](P143)這樣一種現象,也就是說,士族為官者多呈現出為官而官、混事為官,不作為、不擔當,盡圖奢侈享受、保官位長久之現象。
對這種官場腐朽之風帶來的墮政和無所事事混世的為官態度,顏之推持堅決反對態度。他教育后人說:“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18](P315)“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世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18](P395),又說:“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盡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18](P354)在他看來,士人無論是否為官都應該多做有益于社會、有益于國家發展的事,不能整天高談闊論、吃喝玩樂、附庸風雅而無所事事,從而浪費國家給予的俸祿;君子處世為人應該抑制私欲,正己率人,秉持慎獨精神,為社會、為百姓、為國家多作貢獻,并惠及自然萬物,從而為官一方即能治理一方、造福一方,讓百姓生活幸福,讓國家發展良好。他認為君子為官不能為國家發展出謀劃策做貢獻、不能為百姓想盡辦法謀福利,這是極為可恥的。所以他教育后人說,作為朝廷大臣就應該具備“鑒達治體,經綸博雅”的能力,作為文史大臣就應該發揮“著述憲章,不忘前古”的作用,作為軍中大將就應該具備“斷決有謀,強干習事”的謀略,作為地方治理大臣就應該具有“明練風俗,清白愛民”的才干和節操,作為外交大臣就應該具有“識變從宜,不辱君命”的聰慧,作為興造大臣就應該能發揮“程功節費,開略有術”[18](P315)的長處,只有這樣,才能算是忠君盡職,不費君王所給予的官位和俸祿。不難看出,“崇道守德”“濟世益物”和不“費人君祿位”正是顏之推教育后人如何為官做事的主要內涵。
最后在對待公權和私利上主張“守法度”[18](P330)。東晉南朝時期不僅是士族門閥在政治上得意時期,也是強權豪門橫行時期。北朝盡管沒有經歷門閥控政,也不存在士族在政治上始終霸占權位時期,但社會上也普遍存在著權貴恣肆、貪污暴虐現象,可以說不論是東晉南朝還是北朝都存在著大量權貴高官不遵法度這一事實。這種高官權貴不遵法度不僅主要表現在上論為官者不作為、墮政怠政和貪功冒進方面,還表現在為官者大肆貪污受賄和搶奪、霸占他人財物上。不過如此為官者大多也都難有善終,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身死家破,故而在總結南北仕宦教訓中,顏之推在為官對待公權和私利上教育后人要嚴“守法度”。盡管“守法度”是顏之推就士人取官方式而言,但事實上“守法度”思想貫穿于顏之推為官政治思想的各個方面。
其一,他認為做官就要安分做事,規矩做人。不無事生非,不妄論國事,不亂議是非,更不空言取利。否則,像那種“攻人主之長短”“訐群臣之得失”“陳國家之利害”“帶私情之與奪”行為,即使最初可能因巧言利舌而獲一時升遷和賞賜,但最終必會陷入“不測之誅”[18](P330)。
其二,他認為做官就應該廉潔自守,不貪污受賄,不買官賣官,也不趨炎附勢。他說:“齊之季世,多以財貨托付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臍,亦復何及。”[18](P335)在顏之推看來,依靠違法亂紀、貪污腐敗和買官賣官得到的一切利益雖然暫時僥幸能讓個人和家庭榮耀一時,讓親戚朋友沾權獲利,但終究都會因違法而自食苦果,縱然免去一死,最后也莫不破家失財,悔恨終生。可見,在顏之推的政治道德思想里,不論為官朝廷還是為官一方他都主張清廉自守、清白做人。
其三,他認為做官不可僭越法律。漢晉南北朝時期權貴、游俠僭越法律、踐踏法紀而謀私利、遂私欲的現象頻頻發生,顏之推對這些現象和行為持強烈反對態度。他說:“至如郭解之代人報仇,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于君親者,又不足恤焉。”[18](P338)在他看來,踐踏法律、擅自侵害他人性命者不是君子所為,因而那些無視法律、欺壓良善、侵暴百姓者遭致法律嚴懲也就不值得絲毫同情。
“家世歸心”的顏之推重佛家因果,也重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甚至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和佛家的“五禁”教義相比類,認為“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18](P368)。可以說,顏之推的“守法度”,不僅反對任何違法行為,也反對任何違背倫理道德行為,這可以說是顏之推不同于同時期其他士族的突出的政治道德思想。
三、《顏氏家訓》政治道德思想對顏氏后人的影響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教育子孫修身立世、傳業揚名的同時,于其中煞費苦心地注入了諸多政治道德教育思想,以確保顏氏后人在學而優則仕之后為官過程中能順利發展,而他的這種良苦用心也確實起到了應有之作用。
在《顏氏家訓》的引導之下,顏氏后人此后世代為官朝廷時,既不貪高官厚祿,也很少附勢逐利,卻多能清廉忠君,濟世益物,積極作為。不僅做到了為官都能兢兢業業,不“費人君祿位”,還做到了“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世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如顏之推兒子顏游秦入唐做廉州刺史時,即勵精圖治,使百姓和樂,百姓為之作歌謠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27](P2596)再如顏之推孫子顏師古雖然因為性格耿直在仕途上跌宕起伏,但他只要為官就能兢兢業業。史載:“太宗以經籍去圣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于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于天下,令學者習焉。”[27](P2594)而師古弟顏相時“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為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27](P2596)。顏之推四世孫顏惟貞為官更是為時人所稱,其“選授洛州溫縣、永昌二尉,每選皆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介眾曰:‘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后又“以清白五為察訪使魏奉古等所薦”,至于唐肅宗贊其曰:“頻擢甲科,屢升循政”[28](P3450)。到后來顏真卿、顏杲卿等為官更是沒有絲毫偏離顏之推的為官思想。顏真卿、顏杲卿不但一生為官正直、不巴結權貴,最后還在安祿山叛亂唐朝時都以忠節殞身。特別是顏真卿,“凡五為侍郎右丞,三為尚書,四為御史大夫,七為刺史,二為節度采訪觀察使”[27](P3442),為官皆忠于職守,堪稱為官者典范,一如其自己所說:“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徇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緒汝等當須會吾之志,不可不守也。”[27](P3414)顏真卿這種“政可守不可不守”的為官思想可以說正是對顏之推為官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可以說,《顏氏家訓》中的政治道德教育思想在確保顏氏家族此后于政治仕途上平穩發展的同時,也確保了顏氏家族此后成員能嚴格約束和規范自身的政治行為和思想,不會走向皇權政治的對立面,從而使顏氏家族能始終保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并能始終與皇權相維系。
[注 釋]
①如王國良認為,在西周初、中期到春秋初期,君臣關系表現為三個特點:“臣子對君主只能從一而終,不能叛離或另事新主”,“君辱臣死”,“君主被殺,大臣須討伐逆賊,否則便是與弒君者同謀”。但到春秋時孔子則提出“以道事君”的思想;戰國時孟子在繼承了孔子思想基礎上“對君主權力的合法性進行了探討”,而荀子則認為“天下為公”。參見王國良《從忠君到天下為公——儒家君臣關系的演變》,《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第58-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