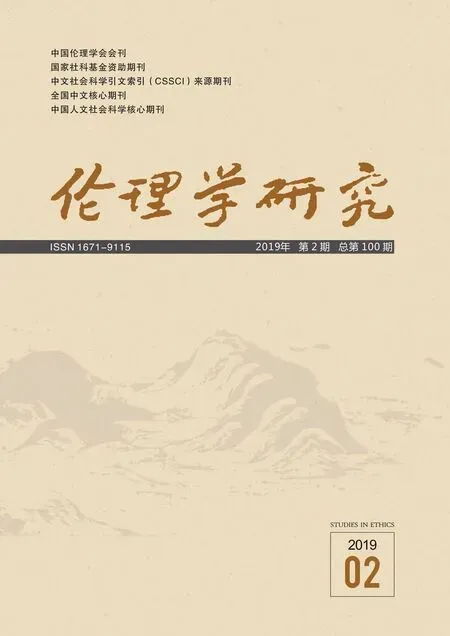論“基因編輯”技術的倫理界限
李 石
據2018年11月26日人民網消息,一對“基因編輯雙胞胎”在中國誕生,這是全世界首例基因定制人類的誕生。這對雙胞胎的基因被一個名叫賀建奎的科學家及其研究團隊人為修改,天生具有對艾滋病的免疫功能。這一事件標志著人類正式進入了“人造人”的時代。賀建奎稱,這一科學實驗事先通過了倫理審查。然而,“基因編輯嬰兒”有可能引發的倫理和政治危機還遠遠未可知。人類偷嘗禁果會引發如何的天崩地裂,或許才剛剛露出冰山一角。本文將以“基因編輯嬰兒”案例為出發點,從科學研究的目的、科學研究的過程和科研成果的應用三方面討論科學研究的倫理界限。
一、科學研究與價值中性(value neutrality)
所謂科學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指的是:為了認識客觀事物的內在本質和運動規律而進行的觀察、實驗、試制、推理等一系列的活動。科學研究與人類其他學術活動的根本區別在于科學研究的方法。科學方法是一種知識獲取的經驗方法,這在17世紀以來一直是科學發展的特征。科學研究通常包括下述步驟:首先,研究者通過觀察和歸納提出假設;第二,研究者設計實驗驗證自己的假設,并得出結論;第三,研究者以更廣泛的人類經驗驗證自己的科研結論并形成普遍化的知識。第四,以新技術、新發明等形式對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進行實際的應用[1]。
科學研究的概念告訴我們,科學研究的目的是尋求關于客觀世界的確定無疑的知識。換句話說,在“真”“善”“美”的價值區分中,科學研究的目的是求“真”。科學研究的目的是通過觀察、假設、實驗、推理等科學方法,尋求關于客觀世界的普遍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學研究的目的是“價值中性的”。另一方面,科學研究的“價值中性”還體現在對科研成果的評價上。通過科研活動所獲得的知識,只有“真”“假”之分,而沒有“善”“惡”之分。世界上不存在本身就是“善”的知識,也不存在其本身就是“惡”的知識;所謂“善”“惡”僅僅是對科研成果之應用的評價,而不是對知識本身的評價。如果一項科研成果是經得起實驗驗證并且符合廣泛的人類經驗的,那么這一科研成果就是“真”的;反之,科研成果則為“假”的。
上述關于科學研究的“價值中性論”在近幾十年中受到國內外許多學者的批評。批評者們提出了與之相對的另一種觀點:科學研究的“價值關聯論”,他們認為科學研究與人類社會的價值判斷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下面我將從科學知識、科研工作者以及科學陳述幾個方面來討論“價值中性論”與“價值關聯論”之間的爭論。
第一,一些學者認為有些科學知識本身就是邪惡的。例如,宋啟林引證了英國《觀察家報》的報道:“阿斯利康公司(全球領先生物技術公司)參與秘密開發的一項叫做‘終止子’的技術已獲得專利。該技術使農作物產生不育種子,使農民無法從收成中自由地采種,因此不得不每年向生物技術公司購買新的種子。”[2]這一例子讓我們看到,阿斯利康公司對“終止子”技術的應用是“邪惡的”,侵害了普通農民的利益。然而,這并不能推出“有些科學知識本身就是惡的”這一結論。顯然,“終止子”這一技術如果用在一些有害植物上就可能增進人類社會的福利。與其他科研成果一樣,“終止子”這一技術本身并沒有“善”“惡”之分,只有人類對它的應用才涉及到“善”與“惡”的判斷。認為某些科學知識本身就可能是邪惡的,并且以此為理由而中斷某一領域的科學研究,這無異于“掩耳盜鈴”。科學研究并不是打開“潘多拉盒子”的那只手。因為,“潘多拉盒子”遲早要被自然之手打開。面對未知世界,人類不可能像鴕鳥那樣,將頭埋進沙子里躲避風暴,只有積極主動地探明世界的普遍規律,大膽地應用自己的智慧,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災難,造福人類。
第二,一些學者認為,科研工作者是生活在特定文化傳統和權力關系中的人;所以,科學家在設定研究目標、設計實驗過程以及對新知識進行應用時,都不可能不受到各種價值判斷的影響[3]。確實,科學家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們必然受到生活于其中的人類社會的各種價值因素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下述三個例子來審視這種影響。首先,科學家及其發明的產品可能會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價值取向的影響。前不久從谷歌人工智能離職的李飛飛在一次題為“人工智能——力量與責任并存”的演講中提到,由于開發人工智能的大多數研究者為男性,這使得人工智能也帶有了性別偏見。亞馬遜的人工智能招聘軟件學會了剔除那些含有“女性”字眼的簡歷。還有,科學家可能受到政治和軍事勢力的左右。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原子彈”的研發和使用。二戰期間,美國集中了西歐和本國的大批精英科學家,經過兩年的秘密研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緊接著,政治家們和軍事家們并沒有聽從科學家們的勸阻,執意將原子彈投向了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最終造成約20萬日本居民死亡。再有,在經濟活動主導的現代社會中,資本對科研活動的深刻介入,使得許多科學家不得不站在“資本”的立場上做研究。這方面最富爭議的例子就是“轉基因農作物”的研發和應用。在1996年以來的20年間,美國孟山都公司開發并壟斷了轉基因農作物的相關技術,尤其是壟斷了轉基因農作物的種子,并以此牟取巨大利潤。可以說,孟山都科研團隊的所有研發和應用都是在資本逐利的邏輯下進行的。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科學家與科學研究的“價值中性”之間的關系:雖然科學家有可能受到各種價值因素的影響,但是,科學研究本身卻是“價值中性的”。這一判斷基于兩個理由:第一,不論科學家站在什么立場上做研究,他們的研究成果都只有“真”“假”之分,而沒有“善”“惡”之分。如果是“真”的研究結論,那就是對人類知識的增進,如果是“假”的研究結論,那么,對于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就毫無意義。第二,雖然具體的科研活動可能是出于邪惡的動機,其后果也可能是災難性的。但是,作為抽象的人類科研活動來說,其本身的目的卻只能是“求真”,而這一目的是無所謂善惡的。科學活動預先假定,真理本身就是目的。追求真理既是科學的最終目標,也是科學的持續動力[4]。
第三,一些學者認為,科學陳述本身就蘊含著價值判斷[5]。例如:“吸煙有害健康”,基于人們對“健康”的態度和理解,這一陳述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對“吸煙”的價值判斷;并非是完全不包含價值因素的事實判斷。科學陳述包含價值判斷,這種觀點根源于對“事實與價值二分”的質疑:如果“事實”與“價值”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如果“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可以相互推導;那么,將科學研究當作僅僅是對于客觀事實的陳述和探究,就是站不住腳的。科學研究的“價值中立論”就是錯誤的。
18世紀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從認識論角度明確地提出了“事實”與“價值”二分的思想。休謨認為,在他以前的道德哲學家都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不加說明地從事實判斷推導出價值判斷,也就是從以“是”為聯結詞的命題推出以“應當”為聯結詞的命題[6](P509-510)。這被休謨稱為是“自然主義謬誤”。在休謨看來,關于“事實”的命題與關于“價值”的命題是截然二分的。換句話說,關于客觀世界的知識和主觀價值判斷是截然二分的。科學研究的“價值中立論”正是植根于“事實”與“價值”的二分:科學研究是對客觀世界的探索,其目的是發現客觀世界普遍存在的因果聯系。科學研究的成果是對世界的“客觀描述”而非“主觀價值判斷”,這一點不論是對于自然科學還是對于社會科學來說都是適用的。自然科學是對于物理世界的因果性的探索,而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等)則是對人類自身以及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的探索。否定科學研究的“價值中性”會從根本上動搖“事實”與“價值”,“客觀”與“主觀”之間的界分。當然,在當代哲學研究中“客觀”與“主觀”,以及“事實”與“價值”之間的界分,并非毫無爭議。但是,目前這種二元界分仍然是人們分析問題和認識世界通常的出發點。而且,對這一基本界分的懷疑將動搖整個人類話語體系。因此,本文將在這一界分的基礎上展開討論,并在這一界分的基礎上支持科學研究的“價值中立論”。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科學研究的“價值中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判斷。并非科研活動的所有方面都是“價值中性的”,也并非所有方面都是“價值關聯的”。“價值中性論”與“價值關聯論”之間糾結不清的爭論,常常根源于人們所討論的是科學研究的不同方面。因此,下述澄清是必要的:第一,作為人類以經驗方法探索客觀世界的抽象的科學研究,其目的是求“真”,這一目的是價值中性的。第二,人類社會中不同科學家進行的各種具體的科學研究,其動機有可能受到政治、文化、宗教、商業利益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并非是“價值中性的”。第三,進行科學研究的主體——科學家,可能受到其身處的環境中各種因素的影響,并非時刻站在“價值中性”的立場上進行科研活動。第四,科學研究的成果是新知識和新技術,只有“真”“假”之分,是“價值中性的”。第五,科學研究的具體過程有可能侵犯人們的權利、損害人們的利益,不是“價值中性的”。第六,對科研成果的應用有可能增進人們的福利,也有可能傷害人們的利益,不是“價值中性的”。
在厘清了科學研究的不同方面與價值判斷之間的關系后,我們可以得出下述結論:第一,在“價值中性”的方面,科學研究不應該受到倫理的限制。正所謂“科學無禁區”,人類不應該武斷地禁止任何領域的科學探索。盡可能多地探明客觀世界的真相,這是科學研究的終極目的。第二,在科學研究與價值判斷相關聯的方面,科學研究必須受到倫理的限制和規范。將科學研究的過程、科研成果的應用限制在正當的范圍之內,這是倫理學家應該關注的問題,也是倫理學家的責任所在。
基于上述理論推導,我們來審視“基因編輯嬰兒”這一案例。首先,“基因編輯”的相關研究其目的是“求真”,與其他科學研究一樣,也是增進人類知識的科研活動。因此,人們不應該完全禁止“基因編輯”的相關研究。但是,在具體的實驗過程、“基因編輯”的實驗對象以及對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等諸多方面,科研活動都應該受到嚴格的倫理限制。下面,我將分別從“基因編輯嬰兒”實驗的過程以及“基因編輯嬰兒”技術的應用兩個方面,討論科學研究應該受到哪些倫理限制。
二、科學研究的過程應以“權利”為限
目的的正當性無法替代過程和手段的正當性,“善”與“應當”是兩個獨立的價值標準,這是道義論倫理學的一條基本準則。基于這一準則,科學研究“求真”的正當目的,并不能成為其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和方法的正當理由。為了達到一個正當的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這是不符合倫理規范的。這一道德原則約束著所有人類活動,當然也包括科研活動。科學研究的具體過程和手段必須符合特定社會、特定文化的規范體系。從根本上說,科學研究的過程應該以“不侵犯權利”為界限,在科研過程中不能損害任何人(包括科學家和被實驗對象)的生命、健康和自由。
在科學發展的歷史上,科學家為科學實驗付出健康甚至是生命代價的例子并不少見。尤其是在化學、生物以及核物理方面的科學實驗中,許多參與實驗的科研人員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對于化學實驗來說,一些實驗藥品本身具有毒性或者易燃、易爆,極有可能侵害實驗參與人員的健康和生命。創立諾貝爾獎的瑞典化學家諾貝爾就曾在研制炸藥的過程中,炸死了與其一同進行科學實驗的親弟弟。生物實驗也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一些病毒和細菌一旦感染上,就會讓實驗者付出生命的代價。對于核物理實驗來說,實驗藥品具有放射性,對試驗人員具有巨大的健康隱患。兩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居里夫人就因長期接觸放射性物質而患上白血病,早早離開人世。
上述例子反映的是科學研究的過程可能對科學家造成的各種傷害。然而,有一類特殊的實驗,將人體作為實驗的對象,極易對受試者造成傷害,侵犯他們的各種“權利”,這就是“人體實驗”。20世紀發生的一些慘絕人寰的“人體實驗”讓人們清醒地認識到“權利”的重要性。二戰期間,德國醫學家們以猶太人、吉普賽人、波蘭人以及各國戰俘為對象而進行的各種人體實驗:雙胞胎實驗,骨骼、肌肉和神經移植實驗,顱腦損傷實驗,低溫試驗,芥子氣實驗,海水實驗,毒藥實驗……都嚴重侵犯了受試者的各種權利,被用于實驗的人們常常經受百般痛苦,掙扎著死去。當然,還有日本法西斯在二戰期間以中國人為對象進行的各種人體實驗,都是嚴重違背人類道德、十惡不赦的科學活動。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各國開始重視對于科學研究的監管。最開始是在美國,當時,一些醫學研究的丑聞被揭露出來,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項長達40年的梅毒研究。在公共資金支持下,在對近400個黑人梅毒患者進行的醫學實驗中,科研人員不給患者任何藥物,觀察他們身體的變化,每天抽血檢查。受試者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參與了這項實驗,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在社會輿論的推動下,美國“國家生物醫學和行為研究受試者保護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于 1974 年成立,并發表了《貝爾蒙報告:保護研究中人體對象的倫理原則和指導方針》[7],闡述了在科學實驗中對受試者權利進行保護的基本原則:第一,尊重個人。《貝爾蒙報告》指出,科學研究者必須將受試者當成具有自主性的個體來看待,這要求科學實驗必須在受試者充分了解以及自愿同意的條件下才能進行。任何科學實驗都不能侵犯受試者的自由權、知情同意權、隱私權,等等諸種權利。第二,善行。科研人員應該在功利主義的立場上考察科學研究是否能給人類帶來好處。科學研究應致力于使最大多數人從中獲益。因此,那些極有可能給人類帶來災禍的技術應用是應該受到限制的。第三,正義。《貝爾蒙報告》主張,那些能夠推進人們福祉的科研成果應該被人們平等地分享。因此,科學家在選擇實驗參與者時,必須平等地對待不同社會背景的受試者。不應只選擇自己喜好的人參與有潛在益處的研究,或者相反,選擇社會底層的成員參與有潛在害處的研究。基于這三條基本原則,《貝爾蒙報告》規定了對科學實驗進行倫理審查的三個主要方面:第一,考察科學研究是否侵犯了受試者的相關權利,這其中包括:生命權、健康權、知情同意權、隱私權、等等;第二,考察科學研究的風險和收益之間的對比關系,判斷科學實驗是否為了較小的利益而讓受試者冒太大的危險;第三,考察科學研究是否公平地選擇了參與對象,是否平等地對待了不同社會背景和親疏關系的受試者。
《貝爾蒙報告》的起草和出版還推動了相關的立法進程。1974年,美國聯邦教育與福利部通過了《保護受試者法規》,并授權“倫理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對醫學實驗中受試者的權益進行考察和保護。2005年,美國聯邦衛生與福利部修訂了《保護醫學研究受試者聯邦法規》(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與此同時,除了“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具體監督,美國的行政機構也參與到對與人體相關的科學研究的監督當中。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和美國衛生部保護人類研究辦公室負責監管各地的倫理審查委員會,并且制定了“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具體工作標準。
美國與科學實驗的倫理審查相關的各項立法和制度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對象。英國、瑞典、日本等國也逐漸完善了科學實驗的倫理審查制度。與此同時,在國際層面,世界衛生組織還制定了生物醫學倫理審查的相關指南。這些規定成為此后人們進行與人體相關的科學實驗的基本倫理準則。
在明確了科學研究過程的倫理限制——受試者的權利——之后,我們來考察“基因編輯嬰兒”這一科學研究的過程是否有侵犯權利的事情發生。首先,這一科研活動涉及三個方面的人員:科學家、“基因編輯嬰兒”以及“基因編輯嬰兒”的家屬。第二,“基因編輯嬰兒”實驗不會對科研人員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任何威脅,因此,不會侵犯科學家的權利。第三,據報道,主導實驗的科研團隊事先向“基因編輯嬰兒”家屬闡明了這一科學實驗及其相關后果,并征得了家屬的同意。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基因編輯嬰兒”家屬的知情權沒有被侵犯,而且,他們是在完全“自愿”的情況下參與實驗的,他們的自主權也沒有被侵犯。另外,“基因編輯嬰兒”實驗不會對“基因編輯嬰兒”家屬的健康造成任何威脅,因此,該實驗也沒有侵犯“基因編輯嬰兒”家屬的健康權。
關鍵的是第四點:“基因編輯嬰兒”實驗是否會侵犯“基因編輯嬰兒”的權利?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實驗是對“胚胎”進行的,而在法律上,“胚胎”并不能被當作行為主體。也就是說,“胚胎”還不是人,因此也就談不上人所擁有的“權利”。如此看來,“基因編輯嬰兒”實驗也沒有侵犯“嬰兒”的權利。因為,在做實驗的時候,“嬰兒”還是“胚胎”,而“胚胎”并沒有權利。但是,這一推論卻是有問題的。正如生命倫理學家邱仁宗在回應賀建奎事件時強調的:“衛生部門早有‘對于轉基因胚胎禁止移植進入人體生殖器內’的規定。”①②也就是說,在現行相關法規的規范下,通常基因被修改過的“胚胎”并不會發育成“嬰兒”。而賀建奎所主導的科學研究,則打破了這一規則,讓基因修改過的“胚胎”發育成了“嬰兒”。從這一違規操作來看,“基因編輯嬰兒”實驗很有可能侵犯了“嬰兒”的權利,包括“嬰兒”的生命權、健康權、自由權,等等。
“基因編輯嬰兒”的生命部分地由科學實驗所決定,這一事實極大地損害了“基因編輯嬰兒”的自由。自由意志與自然規律之間的矛盾關系曾一度困擾著人類:如果世間萬物都是被因果規律所決定的,那么,人的生命、人的思想、人的行動還有什么自由可言?德國哲學家康德的道德哲學曾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種合理的回答。康德認為,“在自然界中每一物件都是按照規律起作用。唯獨有理性的東西有能力按照對規律的觀念,也就是按照原則而行動,或者說,具有意志”[8](P23)。也就是說,人因為具有“意志”,能夠根據自然界的因果關系為自身的行為制定法則而擁有自由。意志為自身立法,所以人擁有自由。然而,這種自由對于“基因編輯嬰兒”來說卻并不存在。因為,“基因編輯嬰兒”還來不及為自身立法,就已經被科學家們決定了。對于自然出生的人來說,自然之手賦予了人們生命,而人自身的意志為自己設定行動的準則,人依照自己的行動準則而行動,所以人是自由的。但是,對于“基因編輯嬰兒”來說,科學家之手修改了其生命。所以,在誕生之后,“基因編輯嬰兒”的自由就懸而不決。“基因編輯”技術使得“基因編輯嬰兒”的自由受到了極大的損害,即使沒有完全喪失自由,他(她)的生命也是部分地被科學家們所決定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基因編輯嬰兒”的生命部分地被決定,自由受到極大損害,健康也因基因編輯技術的不成熟存在巨大隱患,“知情權”和“自愿參與”這些對于人體實驗的基本要求,更是無法兌現。所以,“基因編輯嬰兒”實驗的過程有侵犯實驗對象之權利的嫌疑,超出了科學研究應有的倫理限制。
三、科研成果的應用以“公共利益”為限
科學研究不僅在科研活動的具體過程中應受到倫理限制,科研成果的應用也應受到嚴格的倫理限制。科學研究所發現的新知識以及發明的新技術有可能增進人類的福利,也有可能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對于科研成果的應用,應以其可能產生的后果作為倫理考量的依據:那些能增進人們利益的應用就是應該鼓勵的,而會給人們帶來災難的應用則應該禁止。在應用某項科研成果會給人類帶來什么樣的后果還不甚明了的情況下,新技術、新知識的應用則必須慎之又慎。
“基因編輯嬰兒”這一新技術的應用會給人類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是造福人類還是禍患無窮?目前,這一問題的答案還不甚明了。一方面,人類可能通過“基因編輯”從根本上攻克一些給人類帶來巨大痛苦的疾病。例如此次“基因編輯嬰兒”想要攻克的“艾滋病”。某些種類的癌癥也被證明與基因有著緊密的聯系,所以也可能通過“基因編輯”而被攻克。另一方面,“基因編輯”技術也可能帶來許多負面效應。首先,因為基因技術還不夠成熟,科學家們對于基因的許多秘密還不完全清楚,對于修改基因后會發生的各種情況還不能準確而全面地預測到;而且實驗過程也沒法保證“百發百中”。這些懸而未決的技術問題給“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帶來許多不確定因素,稍一出錯就可能對當事人及其家屬造成極大的傷害。其次,如果基因編輯技術被大范圍地應用,將有可能從根本上顛覆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甚至影響人類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相對平衡,而這將可能引起人倫關系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下面我將站在倫理學者的角度,在假定“基因編輯嬰兒”技術已經發展成熟并得到廣泛應用的前提下,對“基因編輯人類”的后果進行設想。
第一,人類之所以有道德、做了不道德的事會受到懲罰,這是因為人類有自由。如上節所述,“基因編輯嬰兒”實驗極大地損傷了“基因編輯嬰兒”的自由。這就為孩子出生后是否應逐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形成獨立的道德人格罩上了陰影。打個比方,如果一個人的基因在出生之前被編輯過,而這個人生下來之后酗酒;那么,他可能會說:“科學家怎么沒有給我去除酗酒的基因呢?酗酒不是我的錯啊,因為酗酒而傷害別人甚至犯罪,這些都不是我的錯啊!因為,我是被決定的,我只是編輯我基因的科學家們的作品,是編輯我基因的人沒有做好。”而這樣的質疑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人類自由的消解將最終導致人們“自我”的消解;而沒有了“自我”,人也就無所謂道德,無所謂責任可言。
第二,“自我”的消解必然會帶來倫理關系的混亂。親子關系是最基本的人倫關系,也是其他人倫關系的基礎。當嬰兒成為了科學家和父母合作的作品,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就會陷入危機。就像基因被編輯的人會將自己的不良行為歸結為科學家的失誤一樣,孩子也會將自己的種種不如意和過錯完全歸結于父母的失誤。孩子可能會怪父母為什么沒有給自己編輯高智商、高情商、健壯體能的基因,而這樣的歸因思維必然會打亂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正常關系,擾亂孩子正常地、負責任地去發展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既然父母可以參與編輯孩子的基因,那么父母就有可能為了一己私利而對孩子的基因進行修改。例如,將“孝順基因”“聽話基因”編輯到孩子的基因當中,使孩子生下來后能夠被自己更好地控制,成為自己人生的延伸。人類科技能力的增長有可能將人倫關系中的“權力”和“控制”進一步強化,那些在人倫關系中處于強勢地位的人將應用新技術加強對弱勢方的控制。還有,“基因編輯嬰兒”技術,修改了孩子的基因,這使得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傳承”關系也變得非常模糊。目前,如果父母不能確定孩子是否親生,可以通過基因檢測而得到確證。然而,如果“基因編輯嬰兒”技術被廣泛使用,那么,父母就無法通過“基因檢測”而確認哪個是自己的孩子,這將給人類社會最基本的人倫關系蒙上一層陰影。
第三,人倫關系的顛覆還有可能改變整個社會的結構,“基因編輯嬰兒”的出現有可能危及到社會中不同階層人們之間的平等關系。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任何新技術都將首先被社會中的優勢階層享用。“基因編輯嬰兒”這種新技術也不會例外。“基因編輯嬰兒”技術一旦市場化,社會中掌握更多資源的人們會首先享受這種服務。這些人為了讓自己的后代繼續處于社會中的優勢地位,會千方百計地在自己的后代中編入優秀的基因,讓自己的后代更健康、更聰明、更優秀、更有權勢,而這勢必會加劇社會中的各種不平等。因此,“基因編輯嬰兒”的出現以及大范圍的推廣,不但不會推動社會朝著公平正義的方向發展,反而會加劇社會的不平等甚至激化不同階層人們之間的矛盾。最可怕的是,也許最終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為了緩解社會矛盾,優勢階層會在弱勢階層的后代中混入“奴性基因”,讓他們的后代乖乖地安于自己被欺壓的社會地位,而人類社會則將朝著奴隸社會的方向發展。
上述三方面的預測,不禁讓人想起愛因斯坦的預言:有人問愛因斯坦,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用什么武器,愛因斯坦回答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戰人們肯定會用石頭。”在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之前,愛因斯坦預見到原子彈爆炸后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性后果,曾極力阻止卻沒能成功。以史為鑒,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不禁要問:不受限制的科學研究,福兮?禍兮?
任何新知識、新技術的應用都必須以是否造福人類為限,這是所有科研活動的倫理界限。不論是科學家,還是推動新知識、新技術之應用的其他角色,包括政治家、軍事家、企業家,都應該嚴格遵守這樣的倫理限制。與此同時,倫理學家的責任在于,從人倫和政治角度預測新知識、新技術的應用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并進一步明確科學研究的倫理界限。更重要的是,在理論探討的基礎上,建構相應的法規和倫理審查機構,切實地將科研活動以及科研成果的應用限制在不侵犯任何人的權利,以及增進人類福利的范圍之內。
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針對人體實驗中受試者權利保護的法律,僅在相關部門的規章中有一些保護受試者權利的內容。例如,2010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所發布的《中醫藥臨床研究倫理審查管理規范》、2010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所發布的《藥物臨床試驗倫理審查工作指導原則》、2016年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發布并于同年6月1日施行的《醫療器械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2016年由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布并于同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等等[9]。這些法規雖然在原則上對人體實驗進行了倫理規范,但是卻沒有詳細列出相應的懲戒措施。也就是說,如果在相關試驗中,受試者的權利受到侵犯,那么,受試者很難依據相關的法規得到補償、討回公道。同時,實驗的組織者、實施者也可能輕易地逃脫懲處。實際上,這種尷尬的情況正發生在“基因編輯嬰兒”實驗這一案例中。目前,組織這一實驗的科學家賀建奎,雖然受到世界各地科學家、倫理學家的口誅筆伐,但卻似乎逍遙法外。因為,根據中國目前的法律法規,很難對其行為進行實質性的處罰。還有,除了相關立法的缺失之外,目前我國對具體的科學實驗進行倫理審查的“倫理審查委員會”也常常形同虛設。在通常情況下,這一委員會的成員大多由進行實驗的內部人員組成。正所謂“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如此這般的“倫理審查”絕不可能真正發揮對科學實驗進行倫理限制的作用。
基于上述情況,我國亟需在下述三方面建構對科學實驗進行倫理限制的相關制度:第一,盡快起草和完善保護各類與人體相關的科學實驗中受試者各項權益的法律,包括生命權、健康權、知情同意權、賠償權,等等。尤其要對相關實驗人員在違反這些規定時應受到什么樣的處罰,以及由哪些部門來執行相應的處罰,做出詳細的規定。第二,對于醫學領域的臨床實驗更應加強監督管理。推行強制性的臨床試驗注冊制度,以行政權力對所有臨床實驗進行倫理監督。第三,盡快建立獨立于各實驗機構的“倫理監督委員會”。委員會成員應由倫理學家以及獨立于相關科學實驗但具有相關學科知識的科學家共同組成。這些學者應在充分商討的前提下對具體的科學實驗的風險、可能給人類帶來的利益、對受試者的影響、是否侵犯受試者權益等相關因素做出獨立而專業的評估。同時,“倫理監督委員會”的相關意見應該成為科學實驗是否可以進行的決定因素。那些沒有通過倫理審查的科學實驗,絕對不能擅自進行,否則實驗相關人員將接受相應的處罰。而且,處罰條款也應具體列出。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對科學實驗進行嚴格的倫理限制勢在必行,而在這方面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注 釋]
①關于“轉基因胚胎禁止移植進入人體生殖器內”的規定,可參見下述規定:科技部和原衛生部2003年聯合下發的《人胚干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2003年原衛生部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和人類精子庫倫理原則》、2016年原國家衛生計生委頒布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和2017年科技部頒布的《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安全管理辦法》。
②《中國日報》對邱仁宗的采訪: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8-11/27/content_37322763.htm.[參考文獻]
[1]“scientific method”,Oxford Dictio naries:British and World English,2016,retrieved 28 May 2016.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scientific_method.
[2]宋啟林.關于科技倫理若干問題的探討[J].文化與教育,2003(4).
[3]李醒民.科學價值中性的神話[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1).
[4]J.Bronowaski,“The Value of Science”,A sense of the Future,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1977.
[5]Patrick Grim:Meaning,Morality,and the Moral Sciences.Philosophical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1983(3).
[6]休謨.人性論(下冊)[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7]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DHEW)(30 September 1978).The Belmont Report.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8]伊曼努爾·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9]曾予,趙敏.美國臨床試驗中受試者權利保護制度的節儉意義[J].醫學與法學,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