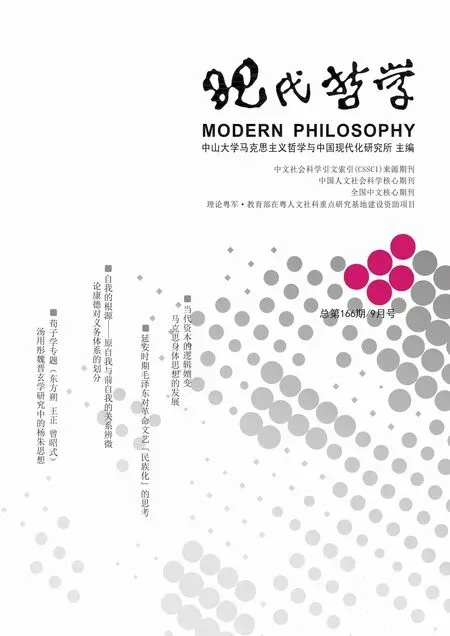論荀子的心學論證
——以《正名》為例
曾昭式
劉師培評儒家邏輯:“吾中國之儒,但有興論理學之思想,未有用論理學之實際。觀孔子言‘必也正名’,又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蓋知論理學之益矣。而董仲舒亦曰:‘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則亦知正名為要務矣。而《荀子·正名篇》,則又能解明論理學之用,及用論理學之規則。然中國上古之著,其能用論理學之規則者,有幾人哉?”(1)劉師培:《國文雜記》,《左盦外集》卷十三,萬仕國點校:《儀徵劉申叔遺書》第11冊,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第4959頁。他把《荀子·正名》視為中國古代思想中少數能夠用邏輯學規則論證思想的經典,認為中國有自己的邏輯,研究中國邏輯宜“循名責實”(“今欲正中國國文,宜先修中國固有之論理學,而以西國之論理學參益之,亦循名責實之一道也。”(2)同上。)和“解字析詞”(“今欲詮明論理,其惟研覃小學,解字析詞,以求古圣正名之旨,庶名理精誼,賴以維持。”(3)劉師培著、勞舒編、雪克校點:《劉師培學術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頁。)。但劉師培沒有具體的中國邏輯研究,也沒有指出“中國固有之論理學”是什么、“古圣正名之旨”為何。本文以《荀子·正名》為例,在總結百年中國古代邏輯研究的基礎上,欲回答中國邏輯之類型和特征。
一、中國古代邏輯的稱謂與“正名-用名”論證類型
劉師培稱中國古代邏輯為“論理學”,也有學者稱之為中國“名家”“名學”“辯學”“名辯學”“邏輯(學)”“符號學”“名學與辯學”“理則學”等。暫且不論這些稱謂的成因,今舉幾例,目的是基于這些稱謂而考察其內容所指。
1.“名家”為章太炎所提出。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講學記錄的《國學概論》涉及中國古代邏輯部分,他稱之為“名家”。此“名家”指“名家是治‘正名定分之學’,就是現代的‘論理學’,可算是哲學的一部分。尹文子、公孫龍子和莊子所稱述的惠子,都是治這種學問的。惠子和公孫龍子主用奇怪的論調,務使人為我所駁倒,就是希臘所謂‘詭辨學派’。《荀子·正名篇》研究‘名學’也很精當。墨子本為宗教家,但《經上》、《經下》二篇,是極好的名學。”(4)章太炎:《國學講義》,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第28頁。此“名家”與“名學”義同,與“邏輯”義同。“正名定分之學”等同于“論理學”(即邏輯學)。
2.“名學”稱謂的所指也沒有離開演繹和歸納邏輯思想,如嚴復于1903年翻譯的《穆勒名學》、楊蔭杭1903年著的《名學教科書》、胡適1922年著的《先秦名學史》。雖然虞愚將中國名學分為“無名”“正名”“立名”“形名”四個學派,但其分類標準仍然是以西方邏輯為根本來確立中國古代邏輯的類型,如其言“而名學乃吾國先哲正名實之術”(5)虞愚著、劉培育主編:《虞愚文集》第1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5頁。,“而《墨辯》對于推理、論證、判斷、概念,均有詳細之討論”(6)同上,第447頁。,中國名學“除討論推論是非外,又注重實際人事……然其側重倫常之道,謀人類切身之幸福,固為希印二土所不及”(7)同上,第541頁。。此“吾國先哲正名實之術”既有推論的討論,也“注重實際人事”。
3.“辯學”,如郭湛波在其著作《先秦辯學史》里說:“中國論理學有名學、形名學、辯學,等名詞,我以為‘名學’二字太寬泛,‘形名學’太生澀,所以就用‘辯學’二字。”(8)郭湛波:《先秦辯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自序”第5頁。“形名學是講思想的(Logic),正名學是講倫理的(Ethic)。”(9)同上,第3頁。
4.“名辯學”,如周云之言:“‘名辯學’的體系特點,一是正名學(概念論)和論辯學(推理論)的相對獨立和有機結合,二是正名學和論辯學的體系應當是各以《正名》篇和《小取》篇的理論體系為基本依據。而如果僅僅是作為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概括與總結,那就只需要按照名(概念)、辭(命題)、說(推理)、辯(論證)的理論體系加以表述就完全可以了。”(10)周云之:《名辯學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143頁。劉培育認為,“‘名辯學’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建構的一門學問,主要研究正名、立辭、明說、辯當的方法、原則和規則。這門學問的核心是邏輯學,但也包括認識論和論辯術等內容,與政治和倫理也有十分密切的關系。邏輯學是名辯學的核心,并非名辯學就是中國古代邏輯。名辯學在中國古代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備的體系,而中國古代邏輯卻沒有得到很好發展,也沒有形成完備的體系”(11)劉培育:《名辯學與中國古代邏輯》,《哲學研究》1998年增刊,第12—14頁。。此“名辯學”是邏輯加認識論、論辯術。
5.“邏輯(邏輯學)”,如沈有鼎寫作《墨經的邏輯學》,以概念論、判斷論、演繹和類比推論、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等內容為線索,逐一比較《墨經》相關內容的異同。汪奠基對中國邏輯類型進行總結,大體上認為孔子等儒家邏輯的主流屬于社會政治的邏輯,名家邏輯稱為名辯邏輯,墨家邏輯歸屬于普通邏輯,老子的無名論邏輯歸屬于辯證邏輯,并寫作了《老子樸素辯證的邏輯思想——無名論》《中國邏輯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輯)《中國邏輯思想史》等著作。溫公頤在《〈先秦邏輯史〉編寫中的幾個問題》一文里講:“先秦邏輯我把它分為兩篇,第一篇寫辯者的邏輯思想;第二篇寫正名的邏輯思想。辯者的邏輯思想屬于正宗的邏輯……比較傾向于純邏輯的研究。至于正名的邏輯卻是從政治倫理出發,可以稱為政治倫理的邏輯。”(12)溫公頤:《溫公頤文集》,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6年,第262頁。
6.“符號學”,如李先焜以符號學理論寫出《〈周易〉中的符號學思想》《先秦名家鄧析、尹文、惠施的符號學思想》《公孫龍〈名實論〉中的符號學理論》《公孫龍〈指物論〉中的符號學思想》《公孫龍〈白馬論〉中的符號學思想》《〈墨經〉中的符號學思想》《中國古代醫學中的符號學》《中國古代的禮儀符號學》等論文。他認為中國古代邏輯是符號學,包括語用學、語義學和語形學,加上古漢語特點(13)參見李先焜:《語言、符號與邏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陳宗明、林銘鈞、曾祥云等學者亦持此說,但思想有差異。
7.“名學與辯學”,是崔清田對“中國邏輯”的稱謂,其中國古代邏輯觀念可以參見《中國邏輯史研究“五范疇”: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一文(14)曾昭式:《中國邏輯史研究“五范疇”: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這里的名學與辯學的關系尚有待研究的空間。
中國邏輯的稱謂還有諸多種,這些稱謂下的中國邏輯內容大體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以西方傳統邏輯演繹、歸納理論框架提煉中國文本中的部分內容,剩余部分置之不顧;第二類,西方傳統邏輯(含符號學)+中國的哲學、科學、倫理學等;第三類,中國邏輯是西方傳統邏輯之名學+中國的政治倫理的名學;第四類,著力構建中國邏輯獨立體系。其中,前兩類顯然是將中國邏輯置于西方傳統邏輯里,第三類將中國名學割裂成西方邏輯+中國哲學,第四類需要進一步厘清中國哲學方法與中國邏輯、名學與辯學關系。
筆者認為,從稱謂看,在當下學術史研究中國邏輯、印度邏輯等,既然將它們歸于邏輯學科,統一用“邏輯”稱謂,可以凸顯邏輯史研究的明確性和學科歸屬,只是需要將邏輯學的內涵與外延確立為包含中、西、印等邏輯的內容與范圍。從內容看,如果把邏輯學定義為關于論證結構與規則之學,則可稱亞氏邏輯討論的論證結構為三段論,佛教邏輯討論的是三支論式,中國邏輯則為“正名-用名”論證類型,“正名”是確定名之所指,“用名”是在說、辯中正確使用已正之名,說、辯既呈現論證結構及規則,又涉及說辯者及說辯目的(15)參見曾昭式:《先秦邏輯新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從特征看,三段論討論的是基于不同邏輯常項里的邏輯變項外延間關系,此真假概念純為形式的;三支論式與“正名-用名”論證是一種帶有信仰與價值的論式,自然引出論證者、論證目的的討論,如三支論式的“極成”規則等。
二、《正名》之“正名-用名”理論:正心與圣人、君子之辨說
“正名”與“正心”。《荀子·正名》開篇講君王如何制名,“刑名”“爵名”“文名”是不需要改變的(如《正名》講“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只需要正“散名”,散名指萬物之名,正散名的總原則是“從諸夏之成俗曲期”(同上)。荀子只選擇萬物中人之名來加以討論,形成“正名-正散名-正人名-正心名-正道名”這樣一個《正名》文本結構,其核心內容是從“正人名”到“正心名”。從文本看,“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16)“偽”即今“為”字。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12頁。。慮積焉、能習焉而后成謂之偽。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同上)。引文中“人”之特性包括“性”“情”“慮”“為”“事”“行”“知”“智”“能”“病”“命”等。在這些“人”的特性里,可以分為人性本能和后天習得兩類,只要是人,都具有人之性,包括五官和心的功能等,“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心有征知”(同上),此為本能之人性。后天習得之“人”的特性關鍵在“心”,所以文本接著講,今亂世圣王不得不正名。荀子提出了“正名”原則,列舉、分析了違反原則的“三惑”,提出去“三惑”的辦法——“正心”,“正心”就是“正道”,今摘引《正名》文本內容,以佐證之:
今圣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圣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此惑于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于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于道,說合于心,辭合于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
荀子在討論人之“心”時,包括本能之心和后天習得之心,“正名”重在“正心”,就是正后天習得之心,讓心符合荀子之道,因為心左右“情”“慮”“為”“事”“行”“知”“智”等方面,只有“正心”,方能“語治”,方能治“欲”,文本自“凡語治而待去欲者”(《正名》)以后便是討論這一論題,如所謂“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以己為物役”“重己役物”(同上)。可見,《正名》篇的主題還是通過“正名”來正人心的,所以《解蔽》篇之后便有《正名》篇。《解蔽》是要去蔽,是要去心之弊而求道,故說“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正名》與此一脈相承。如果說《解蔽》重在批評思想上的“弊”,《正名》則在于“語治”,通過“正心”,在“正名”和“說”“辨”中避免以名亂名、用實亂名、以名亂實之“三惑”情況。
再看“用名”與圣人、君子之辨說。在《正名》里,荀子的“用名”理論表現于其對“說”“辨”的研究。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荀子關于“說”“辨”“辯”的理解,從先秦邏輯視角看,考察《荀子》諸篇,只有《正名》有“說”“辨”研究,其它篇用“辯”來指“辨說”。如《荀子·修身》言:“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荀子·非相》言:“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正名》篇里“說”“辨”有合成“辨說”一詞的情況,也有分開使用的情況。“辨說”合用情況如:“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同上)“說”“辨”分開使用情況如:“實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說,說不喻,然后辨。”(同上)從此引文并結合整個文本內容看,“說”有解說義,“辨”有論證義,二者都是“喻動靜之道”(同上),即給出理由以論證思想觀念的,所以合起來稱“辨說”,是心對道的認知后的言說。至于“辨”與“辯”的差別,從《非相》分“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圣人之辯者”和《正名》分“圣人之辨說”“士君子之辨說”的內容看,《非相》之“辯”等同于《正名》之“辨說”。下引文即表明“圣人之辯者”同于“圣人之辨說”,“士君子之辯者”同于“士君子之辨說”:
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圣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圣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卻之屬,夫是之謂奸人之雄。(《荀子·非相》)
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圣人之辨說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襖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不動乎眾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埶,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正名》)
接著,據文本討論荀子是如何講“說”“辯”的。荀子講“說”“辯”的目的是“用名”,并且是從“辨說者”來討論辨說。《正名》里講“圣人之辨說”和“士君子之辨說”之后,便是比較君子與愚者之言: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茍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于其志義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
通過“君子之言”與“愚者之言”的比較,明確荀子所贊揚的“君子之言”是服務于言說的,這也是荀子思想的目的,即“以正道而辨奸,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同上)。從引文可以引申出,荀子之“說”“辨”討論的是“君子之言”,此“君子之言”就是荀子認為應該采取的“說”與“辨”,即無論是批評別人觀點還是闡發自己的主張,都要給出理由,此理由必須是“正道”,即“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奸說”(《荀子·非十二子》)。正如馮友蘭所說:“心的認識跟‘道’相合(‘心合于道’)。所立的‘說’跟心的認識相合(‘說合于心’)。所有的命題跟主題相合,為主題服務(‘辭合于說’)。所用的名詞都能正確地表示事物(‘正名而期’),能反映實際情況并且易于了解(‘質請(情)而喻’)。分析和類推都合乎規律(‘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取別人的話,能夠吸取它的合理的一部分(‘聽則合文’)。發表自己的主張,要把原因和根據都講出來(‘辨則盡故’)。這是荀況對于一個正確的合乎邏輯的思考和辯論的總的要求。”(17)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8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08頁。
最后,比較荀子“辨說”與墨家“說”“辯”的不同。《說文解字》對“說”與“辯”二詞從多種意義來說明。在先秦邏輯里,“說”“辯”是兩個核心概念。伍非百對二者有區分:“辯者,指正負兩方而言。說者,指正負之一方而言。謂其立敵對諍者曰‘辯’,謂其各自立量者曰‘說’。”(18)伍非百:《中國古名家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5頁。此釋是以《墨辯》文本內容為參照的,《墨辯》將“說”“辯”區分得十分清楚,“辯”有當下學科的意義,“說”歸屬于“辯”學科下的內容之一。關于“說”,我們將《墨經》六篇中與“說”相關的論說聯系起來,便可確立其涵義。“說,所以明也。”(《經上》)“以說出故”(《小取》)“夫辭,以故生……立辭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大取》)“故,所得而后成也。”(《經上》)“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經說上》)用沈有鼎的話概括,“說”的含義是:“‘說’就是把一個‘辭’所以能成立的理由、論據闡述出來的論證……有時舉例來說明一個一般性的規律或定義,也名為‘說’。”(19)沈有鼎:《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2頁。“辯”,《小取》開篇就從“辯”的作用、方法、內容、規則等角度予以論說:“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墨子·小取》)由此可見,墨家“說”“辯”不同而且范圍更為廣泛,它適用于任何內容的“說”“辯”,成就了中國邏輯學科;荀子的“說”“辨”意義相近且只適用荀子的“正道”論證。二者相同之處在于:其一,都有己是他非的說辯目的,莊子批評儒墨之辯就是基于此,“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莊子·齊物論》);其二,都是以“道理”闡發來展開論證的,如《中國思想通史》言“由于將‘類’與‘禮’及‘法’相結合,荀子使‘類’概念成了儒家君子立場上‘聽斷’的工具……是以‘隆禮’為‘明故’的前提……荀子是以邏輯從屬于儒家道德的體系的”(20)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58—559頁。。
三、結語:“正名-用名”論證類型與中國邏輯文獻
筆者不主張將“荀子的正名邏輯”單獨挑出來,寫成接近西方邏輯部分內容的理論,忽略《正名》篇里的其它內容,如言“荀子名學之核心乃是名或概念之理論。荀子對于辭或命題之探討較為簡略,雖然,荀子對于命題作過分析,且亦有合于有效推論形式之論述之實例,然而,荀子并未能抽象地提出有效之推論形式。因之,根據邏輯學之定義,可知,荀子之名學并不等同于邏輯”(21)李哲賢:《荀子之名學析論》,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第224—225頁。;不主張將先秦名學分為政治倫理的名學和邏輯學的名學,如溫公頤、虞愚等;也不主張用因明立、破來講“說”“辯”,如欒調甫用因明立、破來說“明是之說”與“爭非之辯”,“明是之說。案《經上》云:‘說,所以明也,’即謂‘說’為用以說明其所立之‘故’。蓋立者其‘故’必真,若其不真,則‘故’不立。不立之立,因明謂之似能立,能立之立,因明謂之真能立……爭非之辯……即謂‘辯’為用以爭正彼方所立之非,為因明之破”(22)任繼愈、李廣星主編:《墨子大全》第5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512—513頁。。這三種邏輯傳統差異甚大,其差異筆者已從多方面有所比較(23)參見曾昭式:《先秦邏輯新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這里僅說明“正名-用名”是中國傳統邏輯的論證類型,其中“用名”表現于說辯中,說辯也呈現出一種論證結構,即從理由到主張的結構,并包括理由規則、從理由到主張的規則。這些規則的基礎是已正之名,即理由一定是基于自己學派已正之名的述說,從理由到主張的規則不是形式規則,而是價值取向等(先秦大多派別認為生活常識不需要論證,也不屑于論證)。不像三段論講的是形式規則,檢驗用三段論論證的結論正確與否是按照三段論規則進行的;也不似用因明展開的論證,因明論證也是從宗、因、喻三支定的規則展開的,批評別人論證有問題,是從違反因明的什么規則來講的。中國傳統邏輯則是從具體內容上說理,如儒、墨等學派都不接受“白馬非馬”論證,是因為公孫龍的論證違反了人們的具體認知,其《名實論》中的“正位”理論是“白馬非馬”不好言說的,所正“白馬”“馬”名在“用名”(“白馬非馬”論證)中內容變異。即便是《大取》所講“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中的“故”“理”“類”也是由已正之名來確立的,所以我們用符號“-”表達“用名”與“正名”不可分。這里還有一個“說”“辯”的形式“推類”問題,此問題將另文討論。
中國古代邏輯也是研究論證結構與規則之學。這里需要處理兩組關系:一是哲學方法與邏輯關系,二是邏輯理論與邏輯應用。前者如經典解釋為中國古代哲學方法,經典解釋結構與規則為中國古代邏輯關注的對象;后者的中國古代邏輯理論與應用是兩個方面,本文認為只有中國先哲提出了中國邏輯理論方稱得上中國古代的邏輯。這種邏輯的素材選擇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中國古代經典的邏輯文獻,如先秦經典中的《公孫龍子》《墨辯》等就是中國古代邏輯的文獻,《公孫龍子》中的《名實論》《指物論》是討論“正名”問題,是基于“位”下的“彼”“此”“彼此”名實關系問題;《白馬論》《通變論》《堅白論》是討論“用名”問題。《墨辯》中的《經》《說》講“正名”,《大取》基于《經》《說》中的哲學、科學、政治學等已正之名,總結論證結構與規則,《小取》則在不同的“說”“辯”形式中講如何“用名”的問題。第二類是中國古代哲學文獻中的邏輯討論,如《正名》篇的主題是“語治”,破三惑,正人心,使之合于“士君子辨說”而服務于君王治國之道。在“正人名”中討論了名的由來、制名的原則、名的分類(如單名、兼名、大共名、大別名)、辭、說、辨等。對于這兩類邏輯問題的研究,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從名稱看,不同文化的邏輯都可以稱為“邏輯”;從論證類型看,包括亞里士多德三段論論證、佛學論證、“正名-用名”論證等。中國古代邏輯的研究基于如上兩種文獻,在比較不同文獻中邏輯問題差異的基礎上,求得中國古代邏輯的一般性特點,然后開展邏輯史比較研究。此研究或許是崔清田的討論問題的深化(24)崔清田:《“中國邏輯”名稱困難的辨析:“唯一的邏輯”引發的困惑與質疑》,《邏輯學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