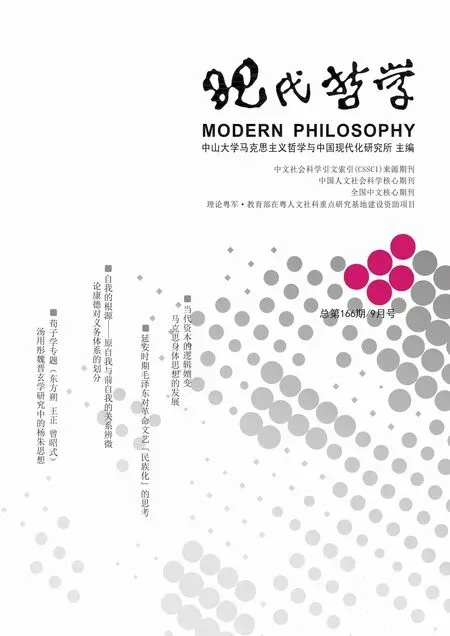Called:存在的命名和物的出場
——試論《舊約·創世記》命名神話的概念化思維及其問題
何光順
“called”一般翻譯為“稱為”或“稱名”,“named”則譯為“命名”。《圣經·創世記》開篇就有神在語詞的言說(said)中創造世界,又在稱名或命名(called/named)中區分世界,并在某種具有實踐的造物(made)上讓一種語詞的言說和區分實現為世界。關于“said”和“made”這兩個關鍵詞,筆者曾著文論述。本文將著重探討“called”所隱含的稱名/命名得以令世界和萬物出場的召喚和呼告意義,以及其在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命名神話構建中所隱藏的烏托邦的陷阱,以期借助某種具有比較性的分析,找到克服西方文明根柢性弊端的可能途徑。
一、Called/Named(稱名/命名),存在的命名:概念、秩序和區分
《圣經》英譯本有“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 And there was evening, and there was morning——the first day”(1)《圣經·中英對照》,中文:和合本,英文:新國際版,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7年。本文所涉《圣經》中、英文引用皆出自該版本。,而中譯本將“called”翻譯為“稱”,其詞組形式就是稱為、稱之為。“稱”是一種口語化的表達方法,是對事物的具體化命名和再次確認。比如,《創世記》說:“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said),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在神的最初道說(said)中,神說出了“光”,有關“光”的語詞又區分于此前的“暗”(黑暗)。只是這“光”和“暗”還比較抽象,缺乏規定性。當某個詞語還未得到規定時,它就只能是“純存在”,就還未曾被賦予本質,就還只是抽象的無規定物,它必須在被賦予本質中得到具體化地展開。這種賦予本質的“稱”,就是具體化的言說,是進行規定,是那作為質料的純存在或抽象物從其自然混沌狀態中顯現出來,或者說與他物區分開來。這就是“命名”,是“這是什么”的概念思維的進行和完成。因此,“稱”(called)就是“命名”(named),是個體從集體中的出場,是召喚事物進入語詞之中,是讓“這(物)”從“類名”的無規定狀態被確切地賦予規定性的“單名”,例如“恒星”是類名,“太陽”就是“單名”。單名在具體化的稱名中被規定,如“這個(孩子)”被“稱”為“張三”,“張三”就是單名。單名的具體存在讓其從更大的抽象的類存在中被凸顯出來,我們可以通過這樣一次具體規定性的“稱”或“命名”而實現海德格爾所言的“召喚”(das nennenruft),即“召喚者當然有所喚而來。它于是把先前未被召喚者的在場帶入某個切近處。但由于召喚有所喚來,它就已經向被召喚者召喚了”(2)[德]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2頁。。
因此,口語化的“稱”(called)或“稱之為”從書面語來說就是“命名”(named),“稱”的單字就可以轉化為“命名”的動賓式合成詞。《說文》釋“命”:“使也,從口從令。”朱駿聲按:“在事為令,在言為命,散文則通,對文則別。”“命,道也,命名也。”(3)[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845頁。這些解釋表明“命”是即將對事物進行具體化規定的過程或行為。又《說文》釋“名”:“名,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4)同上,第872頁。這里的“名”就是已經被具體化規定的事物的“單名”,并且在言“名”的時候,說明 “命名”或“自名”就是因為傍晚是光明趨于消逝而黑夜即將到來之時,當作為具體事物標記的“單名”被“說出”,那即將沉入自然混沌無法區分狀態的個體在這“命名”或“稱名”中就得以再次顯現與出場。可見,“稱”或“命名”就是人對其存在的確證,是存在者之存在得到召喚和出場。
在猶太-基督教奠基的西方文明的開端處,上帝(God)使用語詞(word)的道說(said),就是邏各斯(λογοσ/Logos)語詞中心主義的神話敘事的建構和確立,是世界的創造(created),是詞語word的肉身化,是存在之抽象到本質之具象的展開,是《創世記》開篇上帝為萬物的命名/稱名(named/called)。這命名包含著概念的三個環節:普遍性、特殊性、個體性(5)[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31頁。。作為概念思維的運作,命名同它自身的否定的統一,“作為自在自為的特定存在,就是個體性,構成它(概念)自身的聯系和普遍性”(6)同上,第334頁。。從《創世記》到《約翰福音》的突出問題就是對“語詞”之“命名”的“概念”思維的關注。這種“概念”思維就是從自然的直接世界進入理性的間接世界,就是為存在著的具體事物賦予具有標記性的符號或名稱,從而得到普遍性、特殊性與個體性的統一。命名作為概念就是一種綜合著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思維運動,就是在一種形象的故事中抽象出名稱而后上升為精神的理念。在《圣經》開篇《創世記》中,就有著這種從形象世界走出,而開始自我規定的“概念”萌芽。這種萌芽是在神和人都同樣運用“語詞”的“稱名/命名”(called/named)中實現的: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called)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創1:5)
“概念”的萌芽就是“秩序”的分化,是普遍性中出現了規定性和特殊性。在上帝的第一次概念的命名(called/named)中,“時間”秩序出現。“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光”(light)是在上帝的“道說”(said)中被創造,這種光明顯現的可被看視的“感官化”的“空間”狀態必須得到“精神”的命名,從而得著一種規定性和特殊性的符號化確認,進入“非感官化”的“時間性”維度,這種被“道說”的“光”便被“命名”(called/named)為“晝”(day),以區別于“光”被“道說”創造“前”的“黑暗”(darkness)。當然,基督教神學家不會承認這“光”被“道說”之“前”,因為“前”是一個時間性表述,在基督教神學家看來,不存在創世之前的時間,時間只是在上帝創世的那一刻開始。無疑,基督教神學的時間意識是非常現代的,即否定物理時間,否定亞里士多德的古典客觀時間,時間只有從創造和做工的視域中來觀照才能顯示其意義,如果依照費爾巴哈所說“上帝就是人的本質”,那么這“神”的“時間”實際就是“人”的時間,不存在“神-人”關系之外的時間。
在海德格爾看來,時間性是源始的、自在自為的“出離自身”本身。將來、曾在、當前等現象是時間性的綻出(ekstase),時間性的本質即是在諸種綻出的統一中到時(7)[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第375頁。。在《時間的政治》中,英國學者彼得·奧斯本談到了利科對于時間問題的理解,即“歷史時間是以三重敘事模擬的形式‘把生活時間(live time)(重新)刻印在宇宙時間之上’”,這三重敘述模式包括“預塑(prefiguration)歷史時間的敘事結構”“通過敘事結構塑造(configuration)歷史時間”“在‘讀者’經驗的基礎上重塑(refiguration)生活時間”(8)[英]彼得·奧斯本:《時間的政治:現代性與先鋒》,王志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83頁。。借此,彼得·奧斯本認為敘述時間是聯系歷史時間和生活時間的媒介,而這三重時間的統一,就構成了有機的宇宙時間圖景。《圣經·創世記》開篇的上帝創造宇宙,就確立了宇宙時間作為具有創生性質的源始時間就同時具有其綻出性質,具有歷史時間、敘述時間和生活時間的統一性。首先,這里的神創宇宙時間是一種明確的敘述時間,是借助神話和宗教確立其敘述的權威,但這種神圣敘述時間又構成西方基督教神學歷史或文明史的基礎,因而成為西方歷史時間的內在脈絡,支配著西方歷史的敘述,同時決定著歐洲基督徒的生活,構成生活時間的內在神圣性的依據。這種在時間性綻出中的敘述時間、歷史時間和生活時間的統一,也使基督教神學時間迥異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所確立的物理時間和客觀時間,成為從此在出發的生存時間或生活時間的基礎。這種神創時間的綻出性也道明了海德格爾所說的“無”對于此在的“不”,此在的“不”即是“超越”,這就指向了此在生存之根底的空空如也。正是這一空空如也的“無”構成了此在生存的無限可能性的“不”之背景,是源始的生存“尺度”。因此,海德格爾重視從“有-無”之辨出發,特別是從他的“無”論方面來把握“時間性”的意義,進而來把握“時間”的意義。此在是時間性的,也建基于無的基礎,它使無成為一種超越性的意向對應物。
《圣經》的神創宇宙時間觀念就與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哲學有著其內在呼應,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實際上,時間現象——如果從一種更為本源的意義加以理解——是同世界概念,因而也就同此在結構自身聯系在一起的。”(9)[德]海德格爾:《現象學的基本問題》,丁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376頁。歷史和世界從本質上就是在關于此在的時間敘述和時間視域中開展的,因此,西方文化中關于空間的思想也是后于時間的。這也體現在《創世記》開篇的敘述中:
神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事情就這樣成了。神稱空氣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創1:7,1:8)
神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神看著是好的。(創1:10)
如果說在上帝的第一次創造,“時間”秩序被顯現,那么在神秘“語詞”的后續耕作中,“空間”秩序也得到區分:“神稱空氣為天”(God called expanse “sky”),“神稱旱地為地”(God called the dry ground “land”),“稱水的聚處為海”(and the gathered waters he called “seas”)。相較于最初的直接創造事物的道說(said),上帝的概念化的“命名”(called)是另一次更為巨大的裂變。“天”(sky)“地”(land)“海”(seas)的概念化“命名”,就是這三種存在者進入到“神-人”的主體性世界,就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絕對精神”“絕對理念”的顯現。隨后,最重要的“命名”即“人”的命名被重點記述: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創2:7)
在《圣經》英譯本中,只有小標題處有“Adam and Eve”,這句的正文是“the LORD God formed the man from the dust of the ground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and the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正文雖沒有“名叫亞當”(Adam)的明確命名,但男人(man)和亞當(Adam)都來自象征絕對精神和絕對主體的上帝,這個“人”(man)是一個活人(living being),先天性地秉有上帝吹來的那一口“生氣”(the breath of life),這意味著一個半獨立的“人”出現了,有和上帝相通的“靈”,還有屬于自己的“名”。精神、身體、名稱第一次獲得統一形式,人的存在(being)得到昭顯。而這個“人”的完全獨立則有待于他自己獲得獨立和自主“命名”世界和萬物的權力。
二、Called/Named(稱名/命名),物的到來:自由意志的概念化彰顯
在《圣經》文本中,上帝首先以祂的語詞的“道說”(said)創造了這個世界,隨后以語詞的“命名/稱名”(called)對世界作出區分,讓萬物得以在命名中出場和顯現,并被帶到人的近旁。上帝還同時將這“稱/命名”的權力授予了人: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么。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創2:19-20)
“稱/叫/命名”就是文明的肇始,是在注重概念、秩序和區分中指向存在者的存在之出場。在《耶拿講稿》中,黑格爾分析了亞當“命名”神話所展現的精神的主權問題:“這是什么?我們答道,它是一頭獅子,一只猴子,等等。這即是說,它是[成為什么]……確切說,它是一個名字,由我的聲音而造成的一種音響,某種與其看上去完全不同的東西——而這[作為被命名者]是其真正的存在……不過,由于這名字,對象已經成為自我而出生[并已經呈現為]存在(seyend)。這是由精神(Spirit)所實現的首要創造性。亞當給予所有事物一個名字。這是[精神]的主權,其對于全部自然的首次把握——或者說出自精神[自身]的自然創造……人向作為他的所有物的事物講話。”(10)Hegel and the Human Spirit: 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 (1805-6) with Commentary, pp.89-90.中文翻譯參考耿幼壯:《文學的沉默——論布朗肖的文學思想》,《外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5期。這種作為“存在者”之出場的“命名”,意味著精神因符號化的表達而獲得自由和獨立的過程,也是“精神主權”或曰“自由意志”的彰顯過程。在《創世記》中,當“人”(man/Adam)被命名后,上帝把“命名”的“權力/能力”賦予人,實際就是人從自在狀態走向自為狀態的過程。無疑,上帝讓人為萬物“命名”,具有深刻的宗教神話的隱喻意味,那就是“語詞”之“命名”讓萬物作為存在者的“存在”(being)顯現和出場。這響應于最初上帝的“語詞”的“道說”讓萬物“存在”起來,“命名”則讓萬物的“存在”顯現到人之前來。
在《創世記》中,因“道說”(said)而創造世界,因“稱名”(called)而規范世界,“名”便具有了標示事物起源與出生的神圣性。“神”的“稱名”,就是世界最初的概念化,是世界的“初名”。初名是神圣的。據人類學家研究,重視初名幾乎是每個民族文明初始期就有的一種神秘身份區分意識的自覺,如印第安人極重視初名,一般情況下既不能說自己和他人的名,更不能說死者的名。在原始民族那里,神圣的“名”既是個體生命的標識,又是某種身份確認,具有自然、社會和歷史的淵源,能保護或危害它的擁有者。列維·布留爾指出:“名字從來就不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名字意味著一種親族關系,因而意味著一種庇護關系;恩惠和襄助取決于名字的來源,看這名字是不是來源于氏族或者在睡夢中道出了這名字的幻象。’”(11)[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丁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3頁。“名”從誕生始就意味著人與自然、家族、宗教聯系的神秘力量,并可能決定預示著人的命運。
“名”在古代社會雖普遍具有神圣性,但“名”從附屬于生命的自然關系擺脫出來,形成能指符號的清晰概念體系,卻主要是在希臘希伯來文明傳承下的西方文化體系。實際上,側重概念中的命名世界和令萬物出場,并不是世界文明發端的唯一方式;側重行動中的身體自覺和實踐經驗,同樣是實現人與世界的區分而開啟文明的另一種重要方式。比如,在屬于東方文明的中國神話中,無論“盤古神話”還是“女媧造人”,神的“行動”都先于“語言”,甚至看不到“語言”,盤古的肉身化成這個世界,女媧摶黃土造人,但沒有“說”(said),也沒有對世界進行“稱名”(called)。“盤古”“女媧”等創世神或救世神都是“沉默的神族”而非“言說者”,似乎有一種“無言的沉默”和“行動著的力量”。如《太平御覽》卷二引三國人徐整《三五歷紀》載: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后乃有三皇。(12)[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第8頁。
《繹史》卷一引徐整《五運歷年紀》云:
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云,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岳,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理,肌肉為田土,髮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氓。(13)[清]馬骕:《繹史》,王利器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頁。
盤古的創世是一種自然緩慢的生長和演進過程,缺少創世過程的清晰性,這種清晰性的缺乏主要源于主客體的未曾分離,缺少作為創造者的神給這世界的概念化命名。盤古始終內在于這世界,他最初在天地中,在世界創造完成以后,他又融入這世界。這種從上古神話中奠定的“無言”根基從根本上塑造著中國文化注重“得意忘言”“言不盡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悠久歷史傳統,與西方文化注重語詞和概念的清晰性、規范性,注重言說和命名的傳統明確區分開來。正如手冢富雄指出的:“我們的語言缺少一種規范力量,不能在一種明確的秩序中把相關的對象表象為相互包涵和隸屬的對象。”“我們受到歐洲語言精神所具有的豐富概念的誘惑……”(14)[德]海德格爾:《從一次關于語言的對話而來》,《海德格爾選集》,孫周興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1006—1007頁。這種歐洲語言的豐富概念在古希臘哲學尤其亞理士多德那里已經備受關注,但以《圣經》為基礎的基督教在后來的充分發展中才將希伯來文明的抽象思維與古典哲學關于語言的思考結合起來。歐洲以符號的清晰性概念語言進行“命名”寫作的傳統,使其明顯區別于中國自先秦以來以形象的模糊性的行為語詞進行“非概念化”寫作的傳統。因此,《創世記》的上帝以“語詞”“道說”(said)“命名”(called)這個世界,和中國神話以“身體”演化出這世界,存在著“語言中心主義”與“身體中心主義”、“概念化”與“非概念化”的分歧。
歐洲人的概念化思維和中國人的非概念化思維的分野,造成了中西方思想在書寫方式上的不同發展道路。當《圣經》在明確的概念命名中,確立了對于世界和萬物的區分時,我們的思想史具有一種強烈逆反概念命名的努力。在中國先秦思想中,道家明確反對“名”的確立,如《老子》在其開篇中就明確指出“可名也,非恒名也”“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帛書本第1章)“尋尋呵,不可名也,復歸于無物”(帛書本第14章)“道恒無名,樸,雖小而天下弗敢臣”“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帛書本第32章)。先秦儒家則有條件地承認“名”的作用,如《論語·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從禮樂政治的角度承認名的作用。但從形上層次看,儒家同樣認為“天”或“道”是“無名”或“無言”的,如《論語·陽貨》“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他如名家也有“離堅白”“白馬非馬”等關于“名”難符“實”的論說,雜家《呂氏春秋·古樂》也認為“道”是“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在先秦各家思想中,萬物之母或難言之道都是無法完全被命名的。秦漢以后,這種思想仍舊得到延續,如董仲舒同樣提出“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則圣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萬物載名而生”(《春秋繁露·天道施》)。
中國思想文化雖也有著“命名”觀念,但從根柢上是和“身體化”的現世踐行密切聯系的。美籍華裔學者孫隆基認為,“中國文化是把單個的‘個體’設計成為一個‘身’……在中國文化里,既然沒有個體‘靈魂’的設計,因此,將‘個人’只當作是一個沒有精神性的肉體”“中國人的精神形態卻是由這個‘身’散發出去的‘心’之活動,亦即是克服人我界限的‘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意感通”(15)[美]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5—16頁。“中國人的精神形態既然必須透過集體關系才能去完成”“所謂‘身體化’的存在,就是指整個生活的意向都導向滿足‘身’之需要”(16)同上,第25頁。。且不論孫隆基對中國文化“身體化”的褒貶傾向,應當承認中西文化在“身體化”和“概念化”方向上有重大差異,而這種差異預示了對于認識人之存在處境的分歧,即究竟是“語言”“概念”讓人成為人,亦或“行動”“實踐”讓人成為人?如果中國神話預示了只有行動和身體是人的存在之維,那么《舊約·創世記》就展示了西方文化的一個認識論維度,即“語言”“概念”構成了人之存在的地平線和生存處境,“語詞”之“命名”讓“人”成為“人”而有別于“物”。人就是在上帝的“語詞”之“道說”和“命名”中被創造。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詞”獲得一種超越普通“人言”的神圣性,即日常的“人言”通乎創世的“圣言”,通乎上帝之“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將上帝的“說”(said)和“稱”(called)名之為“道說”(sage),即“與讓顯現和讓閃亮(erscheinen-und scheinen-lassen)意義上的顯示(zeigen)相同”(17)[德]海德格爾:《從一次關于語言的對話而來》,《海德格爾選集》,第1052頁。。這神圣的“道說”(sage)有別于沾染各種偏見功利的“人說”(sprechen),成為“大道”(ereignis)的顯示運作。
三、Called/Named(稱名/命名),烏托邦的向往:命名的神圣和危險
在《創世記》的后續篇章和《約翰福音》的繼續書寫中,道說、命名的概念化思維得到進一步強化。然而,其隱藏的邏各斯語詞中心主義的神話敘事危機也逐漸被顯露。在《圣經》文本中,源自上帝而來的命名問題主要從兩個方向得到體現:一是命名指向上帝之存在而得到肯定,這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不斷尋求根源性的動力所在;二是命名指向世俗的存在者而被否定,這可以被視作西方文明難以解決現世生活困境的原因所在。如《創世記》載亞當后代子孫造巴別塔傳揚世俗的名,在進入世俗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這導致了神圣之名的被遮蔽,從而引來上帝干預(隱喻堅守神圣文化根基)的故事:
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后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里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于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里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注:就是“變亂”的意思〕(創11:4-9)
這段宗教神話似乎隱喻著指向“上帝”之“名”的神圣與指向“人類”之“名”的僭妄。“塔頂通天”隱喻著人類妄圖以有形的工具或階梯走近上帝,而忘記人應當通過內心的悔罪和對上帝的虔信以獲得救贖。“傳揚我們的名”意味著世人只知道傳揚世俗的名,而忘記上帝的名。上帝/我們,構成了神圣/世俗的二元區分,一種無法逾越也不應當被逾越的界限不斷被強調。“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這就是我們(世人)公然對抗在亞當夏娃犯罪以后上帝(神圣)施予人的流散命運的懲罰。這則宗教神話就是關于“命名”的故事,就是喻指著人可能在“成名”或“命名”中僭越神圣,從而造成“圣言”或“神道”的失落,同時也隱喻著西方文明中的絕對精神主宰的歷史,那就是超越“身體”的物質性關注以實現對于終極存在的超越。正如伽達默爾所指出的,巴別塔的故事表明了語言對人類生活的根本意義(18)[德]加達默爾:《哲學解釋學》,夏鎮平、宋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61頁。。這種語言的根本性意義,實際上更屬于西方文明。相較而言,“語言”之于西方,“身體”之于東方,二者具有同樣的本源性意義:從“語言”出發,猶太-基督教的宗教神學系統構造了西方的“命名”神話和彼岸超越;從“身體”出發,西周-春秋的禮樂文明系統構造了東方的“實踐”話語和人間生活。
《創世記》的“命名”神話在《約翰福音》中再次被強化。《約翰福音》的作者認為,凡是被確認并需要被銘記的“名”只能來自“上帝”。上帝乃是那最高的絕對的存在,是絕對的理念和精神,也是萬物之名所從出的恒名和絕對之名,亦或說是“圣名”: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1: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明確將耶穌基督向我們在現世顯示的“存在”和祂的“圣名”融合為一,因為信祂的“在”和“名”,基督就賜予世人以權柄,讓世人曉得上帝,并能重新成為神的兒女,以擺脫自己被魔鬼劫持的命運。耶穌基督就是上帝語詞之“道說”和“命名”的肉身化。“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1:14)在人的信上帝的“名”中,“語詞”“命名”“存在”的神力就像一道光,劃破黑暗。摩西的律法就是憑藉上帝的圣名而成就的,基督則將這神的律法顯示給人:“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里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1:17;18)
對于西方文化中貫穿始終的“語詞”的“命名”問題,福柯在其名著《詞與物》中作過深度詮釋。福柯認為,詞與物的不同關系配置形成不同時期的知識以及各時期知識都要遵循的一種“知識型”(episteme)話語規則(19)這種“知識型”也類似于科學哲學家庫恩(T·Kuhn, 1922-)提出的“范式”,即都是一種可以實證的具有認識論意義的結構型式。。這主要有三個時代的知識型:“相似”(resemblance)時代的知識型(從中世紀晚期到16世紀末),注重事物的相似性;“表征”(representation)時代(17-18世紀)的知識型,注重事物的差異性;現代(19世紀)知識型,注重事物的歷時性。“語詞”就是標記著世界的相似性、萬物的差異性及其歷時性變遷的符號印記,當“語詞”成為知識的獨立對象時,分析語言就和分析其他事物處于同一層次。在傳統《圣經》研究中,神學家常常誤入歧途,誤將《圣經》神話和宗教敘事看作是一種關于起源的真實歷史敘事,總是試圖“在不相稱的事件之間建立什么樣的聯系”,而未能看到《創世記》作為一種“語詞”存在提供給我們的只是摻雜著各種斷裂、變化而非連續的知識型話語,沒有看到我們應當避免“時代”“世紀”等宏大分類單位,以注意到在歷史連續性理論背后有一個主體在操縱、涂改著歷史。
區別于傳統歷史研究在事件之外的社會、文化、制度中尋找問題答案,福柯在“考古學”所著手的任務注重把事物看成是一套符號體系,認為歷史的各個事件本身是一些獨立的不受外部影響的運行規則和話語系統。歷史就是這些話語系統的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在什么秩序空間內知識被構造出來,在什么歷史前提并按照何種確實性原則,觀念得以顯現……”(20)姚大志:《現代之后》,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353頁。正如同羅蘭·巴特所指出的,寫作就是構建“語言的烏托邦”(21)[法]羅蘭·巴爾特:《寫作的零度》,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2頁。。在《圣經》的命名神話中,一種獨立的作為語詞敘述的烏托邦的秩序逐漸得到確立,借耶穌基督之名所創建的以羅馬為中心的基督教會,成為人類建造在世間的一座“新巴別塔”。它曾團結著歐洲的基督徒,形成對于他種文明和社會的自認為中心的優越感,但傲慢和自負成為其假托上帝之名的僭越性的精神元素,歐洲人在自詡為上帝子民的矜夸中墮入世俗之名而遠離圣名,世俗的道德也從此遠離了神圣道德。
或許,從歷史來看,《圣經》從《創世記》開始,就是一部關于“烏托邦”的文學經典與寫作示范,我們不必糾纏其中的每個事件和細節,而是應當關注敘述者在向我們指引的語詞符號、上帝命名、存在顯現的同一中去發現西方文明掙脫自然身體以進入精神概念的歷史軌跡與內在秘密。正是在這個語詞替代真實的神話或宗教歷史敘說中,神的“道說”(said)創造世界,神和人的“命名”(called)共同聯系和區分著歷史。這“命名”(called)的概念升華讓“道說”(said)的神圣蹤跡漸行顯露,并讓西方的歷史進入到對象化、概念化與規范化的運作。這也是近代以來東方人“受到歐洲語言精神所具有的豐富概念的誘惑……”(22)[德]海德格爾:《從一次關于語言的對話而來》,《海德格爾選集》,第1007頁。向西方學習的根源所在。當然,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當歐洲人以“圣名”構建起其在世俗生活中的烏托邦時,他們就將其宗教教規桎梏著的世俗生活美化成天國的生活,神圣/世俗的二元區分既在固化著一種疆界,形成對于人間感性生活與藝術的蔑視,又往往在借上帝之名為世俗生活命名時混淆了圣名與俗名的界限,禁忌與僭越已然構成歐洲文化元素的難分難解的極具沖突性的主題。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逐漸發現其純概念化思維的弊端,也在學習東方的非概念化思維的緣發性思想。一種“身體化”注重現世“生存體驗”的東方思想及其實踐,或許可以為西方文明提供某種突破困境的出路。當然,這是另一個層面需要探討的問題了。
四、命名與自由意志:精神的出場和身體的隱沒
上文指出,上帝將“命名”(called/named)的權力賦予亞當,意味著人的“自由意志”和“精神主權”的確立。正是在called/named確立的命名傳統中,才有了concept(概念)的區分。當神道說(said)時,有了“光”。但這“光”只是一個語詞,是一個沒有得到規定的純存在,這就必須有稱名/命名。只有命名,純存在才會得到規定,才會有萬物(世界)的出場。當神稱(called)光為晝、暗為夜時,一種亞里士多德式的關于“種+屬差”的概念定義法得到明確。比如,我們定義晝就是一種可見的有光的狀態,也可以將光定義為能夠讓我們看見外物的白晝狀態;還可以同樣的方式來規定“暗”或“夜”這兩個語詞。因為這種規定,概念思維就產生了。亞里士多德從一般的概念思維角度來談語詞的命名問題,只是經由奧古斯丁的“自由意志”概念,才得彰顯人的本質甚至上帝的本質。
因此,何謂上帝?何謂人?這樣的發問不能從作為物的角度來看待上帝和人,而當從《創世記》的“道說/言說”(said)“稱名/命名”(called/named)“做工/踐行”(made)所隱藏和貫通的“自由意志”來讓上帝和人出場,亦或上帝與人將在“道說”“命名”“踐行”所貫通的“自由意志”中自動顯現,上帝和人都是自由自在者。當上帝在造人之初為人吹了一口氣時,神之靈和人之靈就相通了。這種相通體現在自由意志所貫通的“道說”“命名”“踐行”。上帝道說,上帝稱名,上帝做工,這完全是自由自主的決斷,上帝不同于人的地方只在于祂的自由自在超越了時空限制,不受時空限制,不受阻擋和誘惑,是全能和絕對的善的根由。人卻受到時空的限制,人的自由意志只能在具體的時空條件中言說、命名和踐行。上帝給予人的最重要能力,其實既不是言說(said),也不是做工或踐行(made),而是called(稱名/命名)。這三種能力是上帝造人之初就賜予了人的,但言說(said)、做工或踐行(made)似乎沒有引起上帝特別關注,而“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創2:19),因為“稱名”(called)而有“名字”(name),充分體現了人從上帝那里獲得的命名權。這種命名權是一種獨立自主的權力,它的根據只能在“自由意志”那里。
從《創世記》的“命名”(called)神話出發,不但能夠界定自由意志,而且能夠再次界定上帝和人。自由意志就是人所本有的一種命名的能力,包括為自我命名、為萬物命名。這種命名讓言說得到區分,并必然帶向具體的實踐,我們也由此可以界定人。人就是憑借其自由意志能在言說中以命名的方式來自我立法并付諸實踐者。在言說、稱名、做工中,稱名是與自由意志更直接相關的,體現了一種立法者的自覺和自我規定,這就是黑格爾所強調的人的“精神主權”。正是在命名中,人將自己和萬物和他人區分開來,并明確自己的權利和責任,人從自然的產兒而成為他的自由意志的規定者、自我權能賦予者和對應責任的承擔者。只有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才具有命名的能力,也就是概念思維的能力,也才有“我知道些什么,我應該做些什么,我期待些什么,人是什么”的逐層問題的推進。康德的這四個問題都圍繞著“人是什么”的命名和概念來展開,都內含著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和自我規定,而最后一個問題是導出前三個問題的基礎和根據,人在自我命名中真正出場。
相對于“命名”的就是未被命名的“無名”,或雖有名卻不將名示于他人的“匿名”狀態。“無名”是事物還未曾得到語言的符號界定的混沌,它必然造成“有名”的人文理性的恐慌。古希臘神話中的混沌神卡俄斯(Chaos),在羅馬詩人奧維德《變形記》中就被描述為“一團亂糟糟、沒有秩序的物體”,它必須被突破;在《莊子·應帝王》中,中央之帝混沌就被代表著文明理性的南海之帝倏與北海之帝忽要強行鑿出“七竅”,形成一種由命名所帶來的概念和秩序的清晰。無法歸屬于“人”或“獸”的斯芬克斯在古希臘神話中也必須死,因為這種人獸不分的混沌無法見容于理性。“匿名”則是已自我命名或被命名者的一種自我隱藏狀態,這種隱藏不是作為身體的物的隱藏,而是作為概念的名的隱匿,是使自己處于不可見之中,有助于讓自己成為監視者而他人卻處于被監視狀態。在網絡化社會或現實社會,“無名”或“匿名”就是使自己處于對話和交流中的上帝一方,使自己在公開場合的任何出格言行,都不會帶來現實的不好的后果,因為他(她/它)是匿名或無名的,你無法規定和確認他,他只有空泛地說、無法被確認、也無法承擔責任,或者說只有虛擬的假名所承受的虛假責任。因此,公共權力不能匿名,平等的權力主體也不當匿名,因為匿名或無名狀態顯然會降低公共權力和自由主體的可見度,并導致公共社會的信任基礎瓦解。但對于那些相對于強大公共權力或強大力量的弱者,卻應當允許其有匿名的權利,這種匿名將有助于弱者的自我生命的有限保護。
這樣,“命名”就具有秩序和法則的規定性與明確性,因而也必然具備著自我必須承擔責任或強者施加于弱者的強制性。更強大者總是具有更大的命名權,人類享有為萬物的命名權,文明社會享有為被視作野蠻社會的命名權。命名就是黑格爾所強調的“精神主權”。這種精神主權具有否定中的肯定,就是“黑格爾所描繪的語言的否定性其實仍然是對精神性的肯定,即肯定精神是一種較之單純的接受而更高的活動。這也就是說,否定事物作為一種現存的存在同時也就意味著否認其只是以純粹的感知直覺而進入我,從而使全部意義向我展開”(23)耿幼壯:《文學的沉默——論布朗肖的文學思想》,《外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5期。。這種命名也將極可能導致某種同質化的傾向,喪失被命名者的豐富的血肉。因此,以古希臘、古希伯萊為導源的西方“命名”文化隱藏著其極大危險。正如布朗肖(Blanchot)在談到亞當與夏娃的故事時所指出的,“這個女人”失去了其活生生的存在,因為“對于我來說,夠說出‘這個女人’,我必須以某種方式奪走其血肉的現實性,使其變成一種不在場,使其消失”(24)See Macurice Blanchot, The Work of Fire, tran. by Charlotte Mandell,Stanford California, 1995, p.322.。這樣,以文學的方式來持留一種未被文明理性所壓制的“無名”或“匿名”狀態便又有了必要,也就是布朗肖所強調的文學空間以一種“無名的無處”(25)[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學空間》,顧嘉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60頁。的方式召喚被隱蔽的血肉的身體的出場和顯現,神的語詞之說和命名到人之說和命名,“是一種榮耀的透明”,“是歡慶,而歡慶就是頌揚”,是“光芒四射的純粹的消耗”,這也是布朗肖所說的“絕無僅有的語言”“黑夜和寂靜在其中表現出來而不中斷也不顯露”(26)同上。,對于文學作品的體驗就是對于幽晦和夜晚的體驗,“是夜的體驗本身”(27)同上,第162頁。。
文學是抵抗而上學哲學對于生命的血肉豐富性進行同質化掠奪的對手。《創世記》的“命名”神話實際寓藏了哲學概念思維中的文學張力場。如果說概念思維是對于混沌物質世界的否定,那么文學的神話式感性化言說,再次形成對于這種形而上學概念化思維的否定式表達,構成語言之身體即語言的物質性的復活。語言有其本身的物質性,有其詞語、字母、音素、聲音、形狀等。在布朗肖看來,這種物質性正是可以將事物重新從概念中補救出來的良方。西方現代詩歌的發展就是詞語的聲音、語詞的聯結形式,甚至詩的排版形式都被給予高度關注并被構造為詩的“物質”的過程。(28)王嘉軍:《“il y a”與文學空間:布朗肖和列維納斯的文論互動》,《中國比較文學》2017年第2期。文學藝術的語言構造了一條通向“匿名”的隱蔽道路,它通過語言的否定性而不斷使語詞與實物分離,同時又具有肯定的面向,是對現實性的關注;它致力于通過恢復語言的無形式的物質性,將現實中這些無法進入語言之意義秩序的在場,即列維納斯所說的“陰影”打撈出來。正如洛雷特阿蒙或薩德這樣的散文家或小說家”采用的“非人的語言、物質的語言、通向匿名的語言、追求晦義的語言”,從而達到對于文學語言的根本特征的把握,即對于“晦暗深遠而不能用理性所把握”世界的進入和體察。(29)同上。
五、余 論
在對《創世記》“命名/稱名”(called)一詞的讀解中,語言、神話、宗教、哲學、文學關于它的多層次意義得到彰顯。“命名”關乎從自然到文明、從混沌到秩序、從無名到有名、從隱蔽到顯現之路,也是一條召喚和出場的路,人的“精神主權”和“自由意志”于此確立。《圣經》從《創世記》到《約翰福音》的“命名”故事,昭顯著某種獨特的概念思維能力,它以這種能力來自上帝恩賜的神話或宗教神圣宣示,表明命名所具有的超越性維度;它讓人得以超越大地,進入蒼穹的神圣,意味著人從自然的必然束縛中獲得自由的解放;它把無名的混沌源初帶向了清晰可辨的秩序。
然而,這種“命名”在否定“物”而肯定“人”之中,又必須實現對于“人”的再次否定,人的概念化形而上學化的言說,可能建構出一個虛擬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王國。這是自由的逾越界限,就是“命名”權的濫用,就是“巴別塔”的建造。《創世記》以神的重新降臨和變亂人的語言來為人的“命名”或“精神主權”的濫用設置障礙和邊界。“讀解‘圣言’(word of god)的實質,既在于質疑‘人言’(word of man)及其價值系統的有限性,也在于看護‘意義’本身。”(30)楊慧林:《讀解“圣言”——神學解釋學向現代解釋學過渡的問題種種》,《外國文學評論》2002年第1期。維特根斯坦指出:“凡是不能說的事情,就應該沉默。”(31)[奧]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序》,郭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0頁。人當敬畏神,就是自覺到人之自由的有限,就是對于“命名”的權利和責任的雙重確認。《創世記》中神“稱名/命名”(called)世界到人“稱名/命名”(called)萬物,就是宗教的“神創世”向人文的“人創世”演繹。加達默爾指出:“在《舊約·創世記》中,上帝讓人類的始祖按照自己的意愿命名世界上所有的存在物,以此賦予他對世界的統治權,這一點意義十分重大。”(32)[德]加達默爾:《哲學解釋學》,第61頁。“人”是“神”的最偉大的“圣物”,很大程度體現在神將“言說”(said)與“命名”(called)的權能賜予了人。
西方形而上學哲學的理性概念化思維,造就了強大的“主體”之人,也抹殺了人的感覺、知覺豐富性,表明某種形而下的感性的文學想象必須被保存和持納。這既為《創世記》這一綜合文本所展現,也為當代西方的文學實踐與批評所重新提出。羅蘭·巴特在《寫作的零度》中曾經指出“文學的寫作仍然是對語言至善(bonheur des mots)的一種熱切的想象……借助某種理想的預期作用,象征了一個新亞當世界的完美”“文學應成為語言的烏托邦”(33)[法]羅蘭·巴爾特:《寫作的零度》,第55頁。。這也是謝文郁所強調的語言、情感和生存的關系中所隱含的真理的道路的問題,是語言在個體心靈中構造一種情感對象和信仰對象的方法(34)謝文郁:《語言、情感與生存——宗教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宗教與哲學》2014年第3輯。。只是謝教授未曾指出這種語言的命名所帶來的構造烏托邦的陷阱和危險。應當說,歐洲中世紀的文學長期籠罩在宗教神話的烏托邦的夢中,既有教會權力的現世影響,也可視作《圣經》神化“語言”的持久影響的證明。舊亞當在伊甸園犯了罪、被驅逐,而對未犯罪以前的純潔始祖的回歸構成歐洲人不斷前進的動力源泉,文學的語言就是要在宗教烏托邦之外去續寫這個文學烏托邦的夢。
因而,人類的歷史就不單純是行動史,更是語言的敘述史。真實的歷史永遠蔽而不彰,我們只能從語言的碎片中去尋找話語權力構建的歷史圖像。這樣,亞當“怎樣叫(called)各樣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創2:19),便不僅是隨意和偶然,而是人因其言說、稱名而創世的必然。歷史不過是人在言說、命名中的行動之展開。沒有確定和絕對的本質,精神主權只有自由意志在語詞的道說、命名中,在現實的做工中才能獲得實現。沒有離開語詞命名的抽象和絕對的自由意志。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思與詩的對話旨在把語言之本質召喚出來,以便終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學會在語言中棲居。”(35)[德]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第31頁。詩人的天職就是替神說話,呼喚人之失落的神性,就是在語詞的命名中確立精神主權的勞作,以將人引向終極棲居,找到回歸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