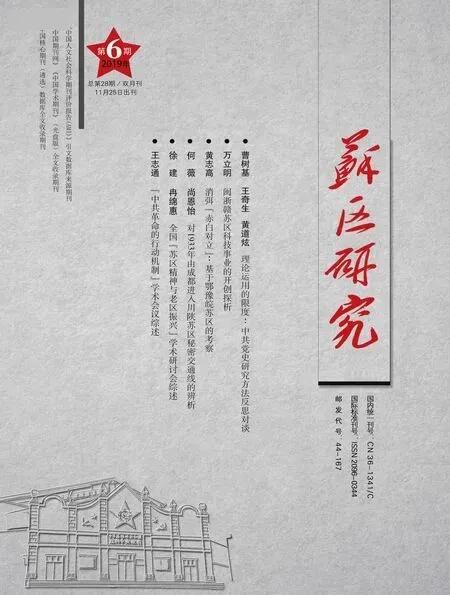理論運用的限度:中共黨史研究方法反思對談
一、為何研究中共黨史
曹樹基:為什么我開始介入黨史研究?大家都知道我研究明清史,但是我突然研究黨史了。中國共產黨的復雜性在哪里?80多年前,一個十幾人的小黨在上海的弄堂里開會,幾十年后他們發展成一個黨員人數達8000余萬的超級大黨,且領導一個人口多達14億的新中國。這里面有太多問題值得研究,世界上還有哪個組織可以讓我們去做這樣的研究?我覺得我以前的研究對象都比不上它。這一研究領域的拓展,對于歷史學將有廣闊的貢獻。這并不是倡導加強專業意識,邊界問題才是真正的挑戰。
王奇生: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開始學習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最初選擇的是民國史。為何選擇研究民國史?當時民國史研究剛剛開始,一個新的領域很容易吸引年輕人的投入。那時官方規定民國史的研究對象是民國時期統治階級的歷史。在同一時段,民國史要與革命史分工,前者研究統治階級的歷史,后者研究反抗統治階級的歷史。至90年代左右才逐漸打破這一界限,民國史開始轉變為研究民國時期的歷史,其研究對象包括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也包括這一時期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某種意義上民國史成為了一個斷代史。我開始側重國民黨史研究,但由于國共兩黨關系太過密切,研究國民黨史勢必要關注中共黨史。所以我研究中共黨史是水到渠成的事,不象曹樹基教授那樣跳躍式前進。
黃道炫:我記得考研究生的時候,報考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為什么考革命史?當時立志寫一本《毛澤東傳》,抱著對毛澤東的無限崇拜去學革命史。理想主義者容易有這種崇拜情緒。后來三年研究生的讀書時間,不斷的閱讀,慢慢擺脫盲目的崇拜,更理性地認知歷史人物。對各方面書籍的閱讀,開啟了另一扇窗戶,讓我反思之前對歷史的了解。這個反思不是簡單地顛覆既有認知,而是不斷地接近理性,接近歷史現場。
徐 進:時下的大部分研究者研究的范圍越來越固定,但各位老師則是分別從明清史、民國史研究轉作中共黨史,你們感覺之前的研究對黨史研究有何影響?兩個領域研究有什么差別?
曹樹基:十幾年前我由明清史轉到黨史。當時中共黨史研究者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解讀資料上,較古代史研究者偏弱。古代史的史料比較有限,秦漢、南北朝及隋唐史料,研究者花一生時間可以讀完;宋代資料則需要看個人情況——有人說能讀完,有人說不能讀完。而明清時期主要資料可讀完,但是涉及地方志仍無法遍覽一遍。總的來說,中國古代史研究者閱讀的資料比較有限,在有限的資料里做研究,就需要在資料上下功夫。也就是說,一份資料,第一個人讀成A,第二個人讀成B,第三個人讀成A加B。這是古代史讀史料的一個訓練——我要讀出其它研究者讀不出的史料信息。如果以此為古代史學者讀史料的方法,那么當年的中共黨史研究完全無此傳統。在西方似乎也僅有周錫瑞教授等少數學者解讀中共黨史方面的史料比較細致,而國內學者則沒有這類讀史料的方法訓練。古代史學者自認為解讀史料乃至考證功夫很強,但我現在認為,當年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有太不“意識形態化”的問題,就是太不理論化。這一趨向雖有所改變,但仍然存在。
黃道炫:我學中共黨史出身,因此我轉向中共黨史研究應稱為回歸。曾經“叛變”革命,研究蔣介石;現在回到革命,可謂“棄暗投明”。為什么會“叛變”?其實是因為導師所命。當時我對思想文化史感興趣,碩士論文打算研究王國維,后來老師讓我研究蔣介石,我只好遵師命。研究對象從王國維變為蔣介石,落差太大了!王國維是一個學術造詣很高的人,蔣介石怎能與之相比?當然這種研究方向的偶然性,如果聯系當時中共黨史的境遇,未必是壞事。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八九十年代研究中共黨史,因資料不足恐怕無法提出新的問題。民國史作為新興學科,史料比較多,研究空間相對大,對年輕人而言,能夠發揮的空間也就大。那時民國史是一個最好的研究訓練場,很多民國史論文可以給人以啟發。楊天石老師的《“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就是一例。既有的研究皆認為此事件是蔣介石主動打壓中共,但楊文通過史料的解讀梳理,發現此事件其實有很多的偶然性。這樣的研究路徑讓我有豁然開朗之感,為我打開了一道門,發現歷史研究還可以這樣做。
后來選擇回歸中共黨史研究,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個人認為國民黨歷史研究的挑戰性無法與共產黨研究相比。如果把國民黨比作端莊的大家閨秀,一舉一動皆循規蹈矩,共產黨則富于變化,你永遠不知道他的下一步將如何走。這種變化對研究者而言極具吸引力。當然我過去對國民黨的研究為我的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一個背景,當研究共產黨歷史時始終把這兩個放到一起看。這是有了民國史背景后自然而然就會有的視野,因為當你具備一種知識背景時,即使你不去刻意使用,它也會時時涌現,成為一種不自覺的資源。
二、社會科學理論的運用
徐 進:楊天石的“中山艦事件”研究是這一時期國共關系研究一個很好的范例。與此同時,楊奎松也有一系列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比如陳獨秀是否右傾及皖南事變等等。這些都標志著中共黨史研究開始走出意識形態的藩籬,學術化進程大大加快。但是,歷史研究也并不僅僅是對事件真相的把握,還要考慮事件內在的因果以及事件之外的運動、組織網絡等的發生機制。這一切似乎就需要引入社會科學的視角和方法。而近年來這樣的研究越來越多,似乎已經成為一種趨勢。這是不是反映出黨史研究在汲取社會科學理論方面存在一種過度理論化現象?
曹樹基:在讀史料的時候,我們會發現與原來說法不同的地方,就開始研究。我們把研究的各種事實整合起來后,就開始理論建構。以統購統銷研究為例,之前有沒有理論呢?有,經濟學有工業化趕超戰略理論。我們發現,這一理論并不能說明問題,我就提出一個糧食立國的理論,來解釋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十多年間國家經濟建設的方針變化。其實,沒有一個西方理論來告訴我們這一切。我們一點一點地在研究中構造這個體系,解釋逐漸完整。在研究當中,我并沒有覺得需要刻意地汲取哪種社會科學理論。我們對西方理論有誤解。西方學術訓練要求學者在個案的實證研究中都要進行理論化的歸納。這樣更有解釋力,從而形成理論。我們本來就應該這樣做。西方在博士生的訓練中就能做到。我們做不到。在聽完我們的個案討論時,總有人問我能不能歸納一下、概念化一下?概念化就是理論化。很多理論就是個案研究中抽象、概括的成果。早期我們比較缺乏這方面的訓練,今天應該加強。這樣我們也能為西方提供我們的理論資源。概括來說,實證抽象等于理論,理論碰撞形成勾聯,形成大的理論。我總結一下,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理論重要吧?重要。但是你要從一個工具性的方面來理解它。理論是什么?理論是工具,是你解決問題的手段或方法。我曾經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概念,幫助我分析傳統中國的地權結構。我也曾用人口學及數據庫方法,處理歷史上及當代人口史的問題。這些都是社會科學的方法,都可以用來幫助我們處理問題。這樣,當我們在接觸史料時,可以選擇用什么方法來解讀。
王奇生:我年輕時候喜歡讀一些社會科學理論方法方面的書,政治學、社會學都會看看。這些閱讀對我研究歷史到底有沒有幫助?很難說。這是潛移默化的東西。我個人的研究興趣,不大關注事件與個別人物,很少做事件史研究。我做政治史比較關注組織、制度、機制,關注政治參與、政治控制、政治動員以及政治文化。社會史也有所涉及,比較關注社會群體、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眼光朝下看得多一點,對基層的關注比對高層的關注更多一些。研究中共的群眾運動,也是側重其運動機制,而不是運動過程。我覺得在視野方法上適當借鑒社會科學并非壞事,關鍵要看如何運用。不能簡單地借用某一個西方理論概念,套在自己的歷史研究中。我非常認同曹老師說的,從史實中綜合、提煉你的觀點、理論,以及概念。從史實閱讀中產生你的問題意識,而不是先驗的。我們在研究中解決各層次的問題,不必刻意追求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宏大理論。在求真的基礎上,繼續求解,搞清楚它背后的深層機制。在我看來,不必排斥任何學科的理論方法,只要對研究解析歷史有幫助都可以借鑒。
黃道炫:黃宗智2017年撰文反對社會科學理論對歷史的凌駕。在海外中國史領域,黃宗智應該是非常早倡導引入社會科學視野的,而且身體力行。到了晚年,他開始這么強烈批評社會科學對歷史的侵入。后來我有一個學生,他去聽黃宗智講課。回來我問他,黃宗智對社會科學在歷史中的地位怎樣看?他說還是原來的看法。他可能在長年研究中覺察到社會科學對歷史研究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但是這種路徑依賴,或者說要改變使他曾經獲得成功,給他自信的研究理路,真的是難。不過,說實在的,社會科學的引入,對于歷史學的成長還是有幫助。比如黃宗智研究華北社會就是借用社會學的方法提供一種模型,不管這個模型是不是有繼續討論和商榷的空間,但起碼引起大家的注意,形成大的討論框架。
我和王老師一樣,什么書都讀。讀書不一定要追求立刻用得上,更多時候是潛移默化。除了社會理論,人文學科理論對我們研究歷史也有幫助。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書都可以讀。歷史就是生活的寫作版。每個人親身經歷的生活世界其實都非常有限,即便是那些所謂生活經歷豐富的人,也只是經歷相對多那么一點點而已。而文學可以提供各種深刻的人生描繪,文學家呈現的生活世界,其廣大蓬勃與細致幽微之處,很可能是絕大多數人一輩子都體會不到的。講生活經驗,不能簡單理解為就是親身經歷,實際上,對于愛讀書的人來說,從讀書中獲得的社會認知和生活經驗很可能遠遠超過親身經歷。這些生活經驗都有可能轉化為我們觀察歷史的有效資源。
三、解讀史料的心得
徐 進:澄清真相式的研究自然有其價值,我自己的學習與研究也是從這一路徑入手的,但其局限似乎也需要研究者自覺去認識。之前對史料的解讀往往都帶有意識形態化的色彩,因而導致在閱讀史料之前便對事實有一個先入為主的看法。然而在已經摒棄了這種明顯的價值判斷干擾后,我們又該如何對史料有一個深入的把握呢?
曹樹基:研究黨史的人注重意識形態化,而我們用我們解讀史料的方法來講歷史。我們原本就是講故事的人。我們用我們講故事的本領介入這個領域。什么叫講故事呢?一份材料,按照意識形態讀,讀成A;按照我的方法讀,從史料本身入手,讀成B。也就是說,同樣一份材料,全國黨史工作者都讀成A,某某讀成了B,某某某讀成C,這就是講故事。我提倡這樣的訓練方法,一群人坐在一起,一字一句地解讀原始檔案。有時連續讀三天,從早上讀到晚上,一天讀九個小時。這樣,你會發現,同樣一份材料,每個人讀出的差異在哪里——你們會讀出什么,而我會讀出什么,為什么會不一樣。為什么你想不到這一點,而他能夠想到這一點?這就是解讀史料的能力的差別。讀史料的能力要從哪里學?上課可以學,讀別人的文章也可以學。
要注意運用不同學科的方法來解讀史料。我以前是做明清史的,但實際上是做明清時期的專門史,包括人口史、疾病史等等,所用的方法是近代史和黨史的研究里所沒有的。把研究人口學的方法、研究流行病學的方法跟歷史學方法結合,就可能很快地切入黨史領域。在我們看來,中共黨史的研究與明清史相比,只是史料不同。在幾位做近代史的教授們的幫助下,我們很快熟悉并進入中共黨史研究領域。此外,還要注意史料與以往說法之間的張力。張力如何體現呢?在我看來,張力就是史料體現出來的反常識與反邏輯之處。
王奇生:史料解讀的張力體現一種復雜性。閱讀史料過程中,發現跟自己或跟學界既有的認知不一致的地方,要特別留意;遇到有悖于常識、常理、常情之處,要特別留意;與當今的價值觀念、概念表達不相同之處,也要特別留意。歷史學更多關注“變”,關注“突變”,關注“劇變”,關注重要的歷史“轉折點”;而社會科學更多關注“常”,關注“不變”的一面。其實歷史學也應該關注“常”,關注“不變”、“漸變”。不過史料的留存,往往是“變態”史料多,“常態”史料少。一個人寫日記,天天重復做的事情很少記,偶爾為之的事情反而會記下來。報紙記載,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歷史事件多半是偶發性、突發性和非常態的。歷史學者要擅長從“變態”史料中發現歷史的“常態”。
四、打通的重要性
徐 進:中國當代史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尤其需要與民國史乃至明清史貫通起來。我們上一代研究當代史的優秀者大多是從民國史乃至明清史領域轉來,所以多還具備貫通看問題的眼光,而我們年輕學者則需要有意識地培養。我個人認為,借助研究著作可以較好地建立貫通的問題意識。研究中國當代的農村問題與社會經濟問題,必須將民國乃至明清的歷史貫通起來審視。比如研究新中國農村問題,如通讀黃宗智、鉑金斯等人著作,即可了解自18世紀以來中國鄉村基本處于“糊口經濟”狀態,即通常所謂“瓜菜半年糧”。而1949年的中國仍在這一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中。了解上述前提,研究者就可了解新中國所面對的歷史實際難題究竟為何,不會被檔案材料中的政策論調所迷惑。再舉一例,孔飛力在其著作中關注現代國家的基層政權建設問題,其研究從清末稅收中間人包攬問題,一直延伸到新中國成立合作社問題。這提示我們,雖然時代各異,但國家都是要處理如何在基層政權降低中間人的“政權成本”問題。
王奇生:一個歷史學者既要有自己專長的“立足點”,又不可過于劃地為牢,應適度跨界、越界。學科之間分工越來越細,學科內部的分工也越來越細。現在做學術研究不僅跨學科不容易,學科內部每個人的研究領域也越來越窄,跳躍式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中國近現代史不過一百多年,卻一分為三:晚清、民國、共和國,或近代、現代、當代。很少有學者兼治兼通。最近30多年,很少有學者以一人之力寫出一部晚清史、民國史和共和國史,更不要說以一人之力寫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像金沖及先生那樣寫出一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者沒有第二人。也很少有學者兼治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等。即使研究抗日戰爭史,也很少兼顧戰爭雙方。中日戰爭史包括兩個方面:中國的抗日戰爭史和日本的侵華戰爭史。就算只研究一方面,也要關注另一方面。同樣研究中國國民黨史的學者很少研究中國共產黨史;研究中國共產黨史的學者很少研究中國國民黨史。晚清史與民國史也很少有人通做。近年來,共和國史興起,一大批年輕學者直接進入共和國史的研究,他們大多將自己的研究起點定在1949年。其實從中共黨史、中共革命史的角度看,1949年的轉折意義并沒有那么大。研究中共黨史和共和國史的年輕學者一定要打破1949年的界限。現在學界有人呼吁建立“中國當代史”學科,我是不大贊成的。一旦強調“中國當代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會強化這個學科的邊界。邊界意識太強并非好事。研究近代社會經濟史,不像曹老師一樣從明清往后做是很難做好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必須是長時段、中時段視野,相對而言,政治史在一個短時段里考察還能勉強為之。
黃道炫:我們需要這種縱向打通,擁有更廣闊的知識跨度,其意義在于提供了更多的背景知識,讓你在一個更縱深的環境、時空里,一個大的關注之下看具體研究的點。除了縱向打通,橫向打通也很重要,即各個領域之間的打通。現在歷史研究總是分成獨立的模塊,比如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等。但是生活難道可以被分成一塊塊的嗎?生活總是一個整體,歷史當然也一樣。我們研究歷史時,既要分解,又要綜合,需要從各個角度探究,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還要有俯瞰的視野,所謂一覽眾山小。這些,當然做起來都很難。相比之下,橫的打通或許還容易一些,因為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問題,有完全不同的現場,要了解這些不同的現場和問題,可能需要花費許多的時間。而同一時代的橫向打通,只要拓展自己的知識背景就可以了。
徐 進:中國當代史研究的每個主題皆有大量未刊檔案,因此如欲開展深入研究,搜集檔案必不可少。但我們需要注意以下兩點:首先在開展研究之前,我們必須通讀基礎史料,尤其需要注意與既有研究論述相異的信息。比如既有研究通常以薄一波的重大事件決策與回顧的論述為依據,認為1952年農村口糧消費量增大,尤其是細糧的消費量增多。但新出《鄧小平文選》和《鄧小平年譜》則屢次提到鄧對此時農民生活到底是好是壞頗有疑問。
由此我們就可循此路徑重新思考這一問題,農民的口糧是否得到增加。再進一步聯想到18世紀以來中國農民始終處于“糊口經濟”之中,并且1950年代的中國農業耕作技術和肥料等條件并未有根本性變化,那么糧食產量怎會飛躍式提高?而農業稅又大幅度提高。由上面論述可知,農民的消費量是否增加大成疑問。這樣的例子也特別提示我們,研究者要注意常見史料中不一致乃至矛盾的史料信息,這或可稱作“從史料中讀出問題”。
再舉一例。研究者還需要特別注意今人不太容易理解的論述。比如前舉薄一波書中就提到鄧子恢曾講:查田定產否定了土改偉大成果。這一與既有研究相異的邏輯,研究者要特別關注并可循此問題搜尋檔案,打開這一“相異的意義體系”。可見關注相異的邏輯亦會產生問題,由問題導引我們搜尋檔案,就相當于研究者在檔案史料叢林中佩帶了一枚指南針。
其次,現今中國當代史研究因為大多依賴基層檔案,因此研究者也群趨基層社會史。由此帶來的問題,正如有論者所謂“細節了解的越來越多,背景卻越來越模糊”。這也需要我們更加注意高層政治和政策的基礎文獻。
五、 革命史研究如何推進
王奇生:20世紀中國接連發生了三場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三場革命中,第一場是國民黨(前身同盟會)領導的,第三場是共產黨領導的,中間一場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過去學界習慣將這三場革命“分而治之”。其實這三場革命之間有內在的連續性和共同性。三場革命實際上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三部曲。前一場革命為后一場革命“預留”了空間,后一場革命在前一場革命的基礎上推進。只有將三場革命綜合貫通考察,才能把握“20世紀中國革命”的總體特征。
由于革命與當下現實之間還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革命尚未完全冷卻。作為歷史研究者,既要將革命放回到20世紀中國的歷史情境中去“設身處地”地理解,又要使自己與這場革命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冷眼旁觀”;既要客觀平實地解讀“過去”,又不可能完全擺脫現實關懷的干擾。這是當下思考和研究革命史的兩難。
另一方面,也因為革命尚未完全冷卻,親身參與、體驗過這場革命的還大有人在。革命史研究除了利用檔案等文書資料外,有必要加緊口述史的工作,讓親身參與和體驗過這場革命的人留下自己的歷史記憶。這項工作可以說是當下最急迫需要做的。檔案即使暫不開放,但總歸留存著,總有一天可以看到,而當事者一旦逝去,則無法追補。有必要發起一場群眾性的口述歷史運動,讓盡量多的革命當事者、參與者將自己的親身經歷說出來,寫下來。在這方面,有部分非專業人士在做,而歷史學者反而做得很不夠。在現有科研考核體制下,專業學者都忙于論文寫作,很難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但搶救革命歷史記憶,是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義務。
革命并非中國所獨有。中國革命與世界各國革命有密切的關聯。有必要將中國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視野下予以審視,從相似中歸納“共性”,從相異中發現“特性”,并尋找其相互影響的因子與關系網絡。與此同時,廣泛收集世界各地所留存的與中國革命相關的資料,期待建立全球性的革命史資料數據庫。
曹樹基:最近十多年來,我一直利用縣級檔案從事1950年代研究,形成自己的論述風格與解釋路徑。我與我的研究團隊至少在土地改革、統購統銷、反右與大躍進等幾個領域,貢獻了一批有份量的學術成果。欲輕松超越,并不容易。我想,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仍然可以達成超越的目標。
其一,關于資料。縣級檔案的內容極其豐富,從中搜集更多更好的資料,是一項永無止境的任務。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應更多地注重“過程文件”而不是“結果文件”。以土地改革為例,縣委、區委會議記錄、各區委分階段的情況報告及工作匯報、各區鄉各種統計表及工作總結,均為“過程文件”。縣級政府對于土改總結報告,則為“結果文件”。除此之外,還應當著力搜集這一時期的各種調解檔案與司法檔案。這兩類檔案也是標準的“過程文件”。當然,我們還應當將中共高層文件與基層檔案中的過程文件對照閱讀。
其二,關于方法。有了更多的過程文件,才有可能更多地關注細節,才有可能達成對于事件的突破性理解,才有可能實現理論的創新。最近一段時間,學界出現對于歷史研究及中共黨史研究碎片化的擔憂,其實大可不必。碎片化現象的產生,源自于學者對于新發掘的史實缺乏歸納與抽象的能力。提高中共黨史研究者們的思辨能力與歸納能力,就可能使似乎“碎片”化的史實,成為新概念或新理論的基石。
其三,關于理論。我一直認為,最好的理論是以實證為基礎,在實證基礎上建構理論。過去是這樣,將來也還是這樣。例如,在過去的十多年間,我證明了明清以降中國土地市場的性質,從而對土地改革的性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現在我一方面從事傳統中國商業史與金融史的研究,另一方面,這一思路也會成為我對中國革命史的思考線索之一。
黃道炫:這些年,我比較關注政治文化的研究。因為這樣的研究興趣,越來越感覺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崛起的新文化史的重要性。政治文化的寫作很容易被套到一個既有的政治敘述的框架中,成為確定性的政治講述的注腳。不這么寫,又好像無從下手。事件史可以通過歷史材料的復雜性,展現歷史的多個層次。政治文化的講述當然也要使用材料,但更多依賴邏輯演進,這就很難避免單一化和確定性的講述。新文化史把注意力更多放到歷史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當中,通過材料的解讀,打開歷史的多重世界,形成放射狀的通向歷史的多條解說路徑,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這樣,政治文化敘述的多面向就打開了。從對文本的再解讀中突破文本的局限,這是20世紀人類意識到自身講述空間的局限后,自我突圍嘗試的一部分,可以說,真的是觸到了人類自我認知的痛處。因為我們觀察到的歷史總是放射狀的,指向多個方向,可是寫作的邏輯迫使我們放棄很多,只能集中到自己選擇的角度當中。在新文化史的視野中,多個角度被納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當然,新文化史在展現歷史過程多歧的同時,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相對忽視對歷史中有可能存在的趨勢的尋找,否定確定性價值的追求,有相對主義的傾向,也容易導致碎片化。文本的解讀固然可以釋放歷史敘述的多面性,但解讀者意志的過多介入有時會使歷史研究成為游戲。歷史研究存在的價值畢竟還是尋真,不管這個“真”有多少不確定的因素在里面,這事實上是歷史學科存在的根據,也是歷史學科區別于其他學科的關鍵。整個歷史學科如此,革命史學科當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