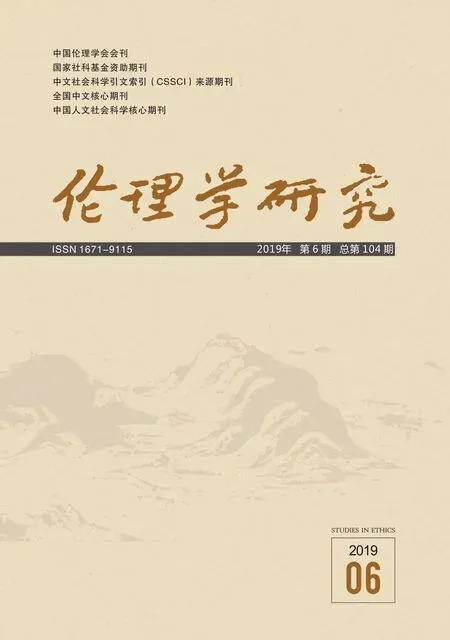羞恥的本質及其倫理價值
曾振宇,李富強
儒家和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都是圍繞著德性而展開的,通常被學者們稱為中西德性倫理學的典范。“恥”是儒家德性概念群中一個極重要的觀念,它是儒家“八德”之一。以倫理為本位的儒家自孔子以降,都很重視羞恥德性在人的道德生活與社會倫理秩序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盡管金耀基肯定“恥”概念在儒家倫理學中有特殊的位置,但是學者們在儒家“恥”觀念研究的規模與深度上,遠遠落后于儒家思想中的其他重要概念。如陳少明所言:“但與仁、義、禮、智、信等德性范疇相比,恥并沒有得到現代哲學家們足夠的重視。”[1]倪梁康也認為儒家的“恥”觀念與道德有內在聯系,尤其是孟子提出“羞惡之心”這一具有道德奠基地位的問題時,儒家“恥”觀念的形而上學性質已經凸顯出來。和孟子同處于人類“軸心時代”的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倫理學的集大成者,他開創的德性倫理學至今影響著西方倫理學家。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等倫理學著作中,他具體探討了很多德性概念,諸如勇敢、節制、正義、羞恥等,盡管他不否認羞恥具有導向善行的社會意義與倫理價值,但他對羞恥的德性屬性則有著模棱兩可的評價。羞恥感作為與同情感、正義感同等重要的人類道德感,始終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正如社會學家埃利亞斯所言,羞恥感像行為合理化一樣是人類文明進程的特征之一[2](P496)。但在現代社會中,羞恥感的衰弱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甚至被當作一種需要克服的負面情緒,羞恥的道德引導與倫理教育功能受到沖擊。有鑒于此,筆者力圖在孟子與亞里士多德思想互詮的理論視域下,澄清以下幾個基本問題:羞恥的本質是什么?亞里士多德的羞恥是不是徹底的德性概念?羞恥的倫理價值以及它對重建現代社會倫理秩序的啟示是什么?
一、羞恥的本質:內在而先天的自然德性與外在而后天的社會情感
先秦時期的“恥”字基本寫作“恥”,甲骨文中沒有出現過“恥”字,“恥”字的字形最早出現在金文中,金文“恥”字“”,由“”和“”兩部分構成。自漢代起,又寫作我們現在通用的“恥”,即《譙敏碑》里出現的“恥”字。《說文解字·心部》記載:“恥,辱也,從心,耳聲。”“恥”字左邊是“耳”,右邊是“心”。“耳”代表官能上的生理感受,不具有理性反思能力,這是動物也具備的官能。“心”則代表道德內省、反思等理性能力,人之所以異于禽獸,正在于人有能思的“心”。從字源上即可看出,“恥”由“耳”入“心”,是一種人類所獨具的道德意識,標識著心靈的某種品格狀態。它是一種具有特殊規定的用來規范人類內心生活的法,類似于黑格爾所謂“主觀意志的法”。盡管羞恥、羞辱、羞愧、羞惡、愧恥、恥辱等詞組在內涵與外延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性,但基于它們在語義上的家族相似性,本文在一般情況下,將它們作為整體上的道德感受來對待,故多用“羞恥”一詞來統括其余。
我們首先來看孟子有關羞恥概念的論述,在孟子心性論的思想視域下,作為“四端”之一的“羞惡之心”即是羞恥心,它是人所固有的、先天的道德意識①,亦是積極的道德情感。與羞恥相對的是“無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上》)人不可以沒有羞恥心,沒有羞恥心的那種羞恥,可謂是無恥至極了。“無恥”儼然是一個嚴厲的道德譴責詞語,孟子通過對無恥的極力批判來確證人與非人的區別,這可能是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獨有現象。孟子又曰:“恥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盡心上》)朱熹注曰: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于圣賢,失之則入于禽獸,故所系為甚大。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3](P358)
朱熹直截了當地指出“恥”就是孟子所謂的“羞惡之心”,而且它是人生而固有的,內在于人性之中的,亦即是說羞恥心是先天的道德意識,而非后天經驗化的、約定性的社會規范。這種先天的道德意識是人所具有的個體道德的真正來源,其特點是強調道德的自然性與自律性,而非人為性與他律性,它是人在生存處境中由低級的感性價值通往高級的生命與精神價值之間的橋梁,對其存養,則進達于圣賢,放失則淪落為禽獸。所謂“機變之巧”“機械變詐之巧”,用康德的話說是“機智”,莊子稱之為“機心”(《莊子·天地》)。概而言之,它指代選擇有關自己最大福利或利益的工具性技巧,是假言的機智指示,其行動并非出自本身而是作為實現另外目的的工具或手段,以其計謀實現自己的私人利益為最終目的。自私用智的人所施展的機智詐巧皆出于滿足個體的私欲與偏好,這是被人所深以為恥的,私欲與偏好滿足愈多,羞恥感便會消退愈多。沒有恥辱的人是君子式的道德典范,遠離恥辱甚至做到沒有恥辱是檢驗個人修身是否圓滿的重要準繩。
孟子從道德意識出發,建構他的性善論。牟宗三認為在孟子那里,道德意識就是道德的心(Moral mind)[4](P72),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對羞恥意識的強調在其“四端”說中得到了理論上的深化,孟子曰: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上》)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對孔子思想的進一步推進之一就是由“仁”到“義”的觀念變革,“仁義”并舉。孟子將“羞惡”連用,視為“義之端”,但他并沒有明確界說恥與“羞惡之心”有何關聯。朱熹道出了恥與“羞惡之心”的內在關系,他說:“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5](P241)又說:“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3](P239)“羞”是“恥己之不善”,“惡”是“憎人之不善”,羞惡皆指向“不善”,便自然于心中生發一種要求止于善的道德意識,這種個體化的自律性的道德意識便是羞恥意識。“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的活動,從心向上提升就是性,從心向下落便是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在善良之心的統攝下便成為四種積極的道德情感。龐樸對“羞惡之心”與“惻隱之心”之間相互關系的論述很有啟發意義,他說:“‘義’被說成是‘羞惡之心’的道德表現,它同‘惻隱之心’的‘仁’相對,并且是對后者的一個節制。”[6](P546)龐樸認為“羞惡”使“惻隱”的發用有一個界限,對其構成一定的節制,不至于濫發慈悲,從另一個方面說,“羞惡”是以否定性方式表達的“惻隱”,它基于“惻隱”而起。但在孟子的文本中,并沒有明確的“惻隱之心”是“羞惡之心”的必要條件這種說法,兩者都是獨立存在的。孟子將羞恥視為人的先天本性,類似于休謨的自然德性,這種起源于內心的道德意識很難給出令人滿意的合法性證明,而常常陷于自然主義進化論的窠臼,因為如果我們將可以為人類道德奠基的東西訴諸于人的自然本性,那么我們就不得不將這個理由追溯到宇宙演化的進程上:人類的道德法則起源于自然進化過程中偶然形成的某種物種之上。
我們再來看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及其關于羞恥的論述。在希臘語中,“倫理的”與“道德的”是同一個詞,指個體通過習慣而獲得的品質,以善的實現為理想。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著作有三種:《尼各馬可倫理學》《歐臺謨倫理學》《大倫理學》,他的德性(aretē)在廣泛意義上是指一切事物的優越特質,有倫理德性與理智德性之分,前者源于社會風俗習慣,后者源于理智自身的思考。倫理德性的價值在于生活中優良習慣的培育,理智德性的價值在于思維能力的訓練。基于沉思的理智德性是惟一的、靜止的,不存在過度和不及,而倫理德性或道德德性則是有條件而相互依存的。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關于“人事的哲學”,主要研究人的品格、品性或品質問題,即我們應該培養和贊賞或者譴責和避免哪些靈魂的品格。在倫理學意義上,德性特指人的實現活動,德性是一種主動選擇的品質而非被動的感情,行為的德性是值得稱贊的品格,過度與不及是兩種惡,居于中間狀態的適度是德性,這種適度的中道或中庸原則是由理性的邏各斯規定的,是一個明智的人做出的正確行動,欲望和感情的牽制往往使人喪失適度原則。居于中間的需要培養和實踐的品格狀態是德性的狀態,是值得稱贊的,另一些被廣泛認為是缺陷或惡性的狀態,則必須予以譴責和避免。例如,恐懼與信心方面的適度原則是勇敢,恐懼的不及是無懼,信心的過度是魯莽,恐懼的過度和信心的不足是怯懦。
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所開列的德性清單以及關于每種德性的討論包含某些不規則、不一貫或矛盾的地方,不符合其關于德性論述的總體框架,尤其是關于羞恥德性的探討表現得比較突出。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歐臺謨倫理學》《大倫理學》的德性表中,將羞恥視為一種具體的德性,它是羞怯、恐懼與無恥之間的中道狀態,但在《尼各馬可倫理學》若干章節的文字表述上又否認羞恥是一種德性。如《尼各馬可倫理學》的第二卷第7 章與第四卷第9 章分別談論了羞恥是不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而且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在第二卷第7 章,亞里士多德把羞恥當作羞怯與無恥之間的適度來探討,亞里士多德說:“因為盡管羞恥不是一種德性,一個知羞恥的人卻受人稱贊。在這些事情上,我們也說一個人是適度的,或者另一個人是過度的。例如,羞怯的人對什么事情都覺得驚恐,而在羞恥上不足的人則對什么事情都不覺羞恥,具有適度品質的人則是有羞恥心的。”[7](P55)譯注者萊克漢姆認為這段話出現了語句順序上的誤置,應該將“因為盡管羞恥不是一種德性,一個知羞恥的人卻受人稱贊”放在“具有適度品質的人則是有羞恥心的”之后。在第四卷第9 章,他卻沒有十分確定地把羞恥當作適度狀態進行探討,羞恥僅僅被視為一種假言意義上的道德德性。亞里士多德認為:“羞恥不能算是一種德性。因為,它似乎是一種感情而不是一種品質。至少是,它一般被定義為對恥辱的恐懼。它實際上類似于對危險的恐懼。”[7](P135-136)亞里士多德認為感情、能力與品質是靈魂的三種不同狀態,德性是區別于感情與能力的品質,感情是一種被動的感受性,德性則具有自愿選擇的主動性。如此一來,作為情感狀態的羞恥本質上是對后天經驗的社會壓力的恐懼,而不再是一種像勇敢那樣純粹的倫理德性。感到羞恥或恥辱時,會出現身體上的變化,如面紅耳赤等,這些變化是身體感受以及感情的特點,羞恥雖然不是倫理德性,但就其作為一種近似于他律性的社會道德而言,在依然可以提升個體過高尚的道德生活這一點上,它也有使人向善的倫理價值。
亞里士多德不僅否認羞恥的德性屬性,而且他的羞恥觀還有另一個特點,即盡管羞恥有積極的倫理價值,但羞恥的倫理作用不是普遍的,羞恥感僅僅適用于年輕人。因為年輕人時常不能理智地做出正確的行為選擇,而是聽憑感情的支配常常做出錯誤的決定,保持羞恥感有助于減少他們的錯誤行為。所以應該對一個表現出羞恥的年輕人大加稱贊,但不能去稱贊一個感到羞恥的年長者。亞里士多德進而認為,羞恥是由卑劣或惡的行為引起的,它是壞人的特點,一個人做了壞事之后感到羞恥是不能被視為有德性的,因為任何引起羞恥的行為必定是出于自身意愿的行為,而一個有德性的人是不可能出于意愿去做不好的事情。亞里士多德又強調羞恥只有在一種虛擬語氣的條件下才是德性:“如若他會做壞事情,他就會感到羞恥。然而德性的行為則不是有條件的。”[7](P136)其表達的真實意思是好人不會做壞事情,所以不會有羞恥的感受性體驗。亞里士多德的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其邏輯是做了錯事而不知羞恥的無恥之人與做了錯事而感到羞恥的人都同樣是不道德的人,兩者之間并沒有嚴格的區分。然而經驗事實告訴我們,即使是一個好人有時候也會有出于不公正的意愿的行為,這種行為一旦暴露在他人的視野中,便會使他產生羞恥的社會情感,這種羞恥感的外在譴責性作用可以促使行為者在以后的生活中減少甚至杜絕類似行為的出現。
由以上論述可知,孟子是性本善論者,他認為羞恥是先天的天賦能力與內在的自然德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性規定,它是一種原初性的道德情感或內在的道德感受。與孟子思想透顯出的道德理想主義傾向相比,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性格具有很強的經驗主義色彩,他認為德性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接受習慣訓練的結果。德性既不源于自然本性,也不違背自然本性,自然賦予人接受德性的潛在能力,并通過后天的實踐習慣而得以完善。但亞里士多德的羞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種由后天的人為訓練所塑造的倫理德性,而是一種在社會壓力下呈現出來的情感上的恐懼狀態,這種社會情感的德性屬性偏弱,甚至不能算是一種德性。孟子的德性倫理學更加強調道德情感的本然地位,而亞里士多德則將情感排除在德性之外,對羞恥這種原初性的道德情感沒有進行深度剖析,所以謝文郁認為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在說服力上不及孟子[8](P56)。在這種互詮的思想視域下,我們發現孟子和亞里士多德分別看到了羞恥本質的不同側面,即內在的、先天的自然德性與外在的、后天的以暴露恐懼為標識的社會情感,這是構成羞恥本質的兩個要件,而且這兩個要件在羞恥德性的倫理價值上得到了體現。
二、羞恥的倫理價值:積極的倫理建構與消極的道德譴責
學者們通常將羞恥與罪責放在一起進行討論,如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從文化模式的角度,將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文化類型判別為“恥感文化”,受基督教原罪觀念主導的文化類型判別為“罪感文化”。但有學者指出“恥感文化”并非是日本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專利品”,威廉斯在《羞恥與必然性》中談及古希臘文化時,提到荷馬的世界具有羞恥文化(a shame culture)的特征,而且羞恥的核心倫理價值被之后的道德罪責(moral guilt)所取代[9](P5)。由此可見,中西文化都重視羞恥本身所具有的倫理價值,根據上文對羞恥本質的分析,我們知道羞恥的本質是內在而先天的自然德性與外在而后天的社會情感的統一,道德自律與道德他律的統一,個體道德與社會道德的統一。羞恥的倫理價值與羞恥的本質也是辯證統一的,羞恥感是人的精神人格中心的“良知動蕩”,一方面具有否定的譴責性作用,亦即對不道德行為的羞惡之情,另一方面又具有肯定的解放性的建構作用,使人“知恥而后勇”,由低層次的價值序列超拔挺進高層次的價值序列,以此成就完善的道德人格和自我價值的實現。
首先,羞恥的倫理價值表現在消極的社會道德譴責方面,所謂消極是指這種羞恥感是由外在的社會壓力臨界觸發而出現的,這是羞恥發生的社會根源。這種社會性羞恥的觸發機制所包含的要素是自我意識、缺陷的暴露與“他者”的在場。這個“他者”可以是具體的個人或想象中的“他者”,也可以是抽象與形式化的社會規范。羞恥作為一種道德現象,與其相關聯的基本人類經驗是不當行為的暴露,不體面行為的“被觀看”及其被觀看的行為相關項,如偷竊、奸淫、穢語等。羞恥感的實質屬于自我感覺的范圍,更確切地說是自我保護的感覺,所以任何羞恥現象中都必須伴隨的一個意識活動被舍勒稱之為“轉回自我”。具備上述條件的羞恥事件,都會使行為主體或與行為主體有親密關系的人產生有失人格尊嚴的羞恥感。行為主體因自我缺陷與不足的暴露而產生羞恥感的情況比較常見,如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孟子·萬章下》)在朝廷出仕為官,自己的道義主張卻無法實行,這是君子應該引以為恥的,因為君子沒有承擔與其身份相當的社會道義,這與君子對擔當道義之形象的自我期許相背離,故而君子必然要經受自我良知中所確證的社會道義的責難。行為主體的不當或不體面行為被與其具有親密關系的人看見也會使后者產生同樣的羞恥感,父母會因子女的行為而羞恥,丈夫會因妻子的行為而羞恥,反之亦然。孟子就講過一個“齊人有一妻一妾”的小故事,來說明齊人的妻妾因齊人的撒謊行為被發現而產生的羞恥情感,孟子曰:“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離婁下》)齊人乞求升官發財的卑劣方法及其虛榮心,使他的妻妾于內心中生出一種憎惡之情并深以為恥。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與倫理學之間有著內在關聯,或者說他是以倫理的方式來理解政治的。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一卷后半部分對開篇進行了總結,他說:“我們在那里說,政治學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貴行為的人。”[7](P26)對亞里士多德而言,人天生是政治動物,人生來就屬于城邦,他敏銳地意識到一個事實,即只有當一個人在理想的城邦中被培養起來,這個人才能真正形成關于什么是高貴、什么是可恥的正確觀念。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政治生活是個體之間約定的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德性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遵循由習慣積累而來的德性是人的生活方式的一個本質方面,德性的欠缺與匱乏則意味著對約定的社會道德的違背。一個理智而成熟的成年人不會去做令人羞恥的事情,只有不能運用理智的年輕人才會做出違背社會道德的羞恥之事,并因其不理智行為的外在暴露以及隨后的社會譴責而產生一種類似于恐懼的心理情感。所以無論亞里士多德是將羞恥視為德性或排除出德性清單,羞恥都有很強的外在的社會屬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羞恥是主體間性的,它以社會譴責與規訓的方式使個人對不道德行為產生被動的羞恥感,警示個人不要做違背社會道德或倫理規范的事情,而要去做一個有德性的人。
其次,羞恥的倫理價值表現在積極的倫理建構方面,它植根于人之為人的自然本性,確證著人是有良知的道德存在,它是個體完善自我道德人格與實現自我價值的內在驅動力。結合前文分析可知,亞里士多德的德性作為一種道德概念是由習慣訓練得來的,他的羞恥概念揭示了人類道德意識來源有經驗性、后天性與社會性的一面,而儒家孟子則將羞恥視為人與生俱來的自然德性,比亞里士多德更深刻地闡釋了羞恥的本質及人類道德意識的原初起源。作為道德意識的羞恥感與人的自我尊嚴或人格具有內在關聯,是人之所以為人而區別于禽獸的內在價值根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儒家一直重視羞恥觀念探討。“羞惡之心”同“惻隱之心”一樣是“人皆有之”的,都是人類道德意識的最初來源,揭示了人類良知的存在。孟子用“嗟來之食”的故事解釋了“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的道理。孟子曰: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
面臨死亡的威脅,路人與乞丐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嗟來之食,表現出大義凜然的浩然正氣,是因為這類人沒有“失其本心”,朱熹點出了這里的“本心”所指為何。朱熹曰:“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于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于晏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于斯焉。”[3](P340)朱熹的解釋是符合孟子本意的,就道德主體而言,作為“本心”之直接當下呈現的“羞惡之心”具有明顯的情感性,而且是一種主動的道德情感,是道德主體主動承擔道德責任的內在道德動機。
“羞惡之心”也就是人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它是人天生的道德本能,源于人的自然本性。孟子、陸九淵、王陽明代表儒家的心學傳統,王氏門人有個小故事,即講為何是羞恥心點出了良知是人的道德本能。故事大概是說,王氏門人夜間捉住一個盜賊,他對盜賊大講良知之學,此盜賊不以為然。因為天氣過熱,于是王氏門人讓盜賊脫掉褲子,盜賊面露羞澀,認為這樣不太雅觀,羞恥感油然而生,王氏門人告訴盜賊這個羞恥感就是他有良知的證明。總而言之,“羞惡之心”作為人的本心、良知、良能,是一種主動的道德情感,只要“擴而充之”(《孟子·公孫丑上》),就可以提升個體主動地去完善自我的道德人格,所以羞恥具有積極的建構性倫理價值。
三、培植與提升羞恥感:重建現代社會倫理秩序
后現代理論家利奧塔認為現代道德只具有審美的意義,因為現代社會的生活節奏急劇加速,生活使所有的道德化為烏有。羞恥感的薄弱與衰退往往意味著人的道德力量的衰減,這是人的類型的退化,退化到與禽獸無異時,人便不復成其為人,所以現象學倫理學家舍勒強調:“在近代史上,羞感的明顯衰減絕不像人們膚淺斷言的那樣,是更高級和上升的文化發展的結果,而是種族退化的一種確鑿的心靈標志。”[10](P257)由于現代社會中個體主義自我價值的過度膨脹,羞恥感的衰減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羞恥感這一道德力量的普遍衰減削弱了個體自身從道德上對其自身價值所做的反省,重建嶄新的社會道德秩序,應該以培植與提升個體自我的羞恥感為基礎,因為羞恥是道德世界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古典文化中的道德資源是否能夠培育一種現代道德人格,以抵御與挽救現代社會中個體羞恥感不斷弱化的世界性問題,儒家孟子與亞里士多德的羞恥觀或許可以提供一些積極的、值得借鑒的價值資源。基于孟子和亞里士多德倫理思想的互詮,我們發現羞恥感可以為道德秩序奠基,對重建現代社會倫理秩序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其一,現代社會倫理秩序的失序究其根源在于人的心靈的失序,重整人心秩序意味著參與社會活動的主體需要具備完善的道德人格。現代社會的倫理學主要是強調規則及其普遍有效性的規范倫理學,一個人只要不違反倫理規則,也就意味著他盡到了作為道德存在的人之本分,服從倫理規則是這種現代式道德觀的第一原理,基于道德修養與實踐德性的道德人格培育則不在其任務之內。以儒家孟子和亞里士多德為標識的古典時代的德性倫理學,其道德管轄的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用規則來調節的個人利益沖突的場合,而是更進一步地以個體道德人格的培養與精神的提升為目的。培植與提升羞恥感在養成理想的道德人格時具有重要意義,孟子理想中的道德人格是君子,亞里士多德理想中的道德人格是有教養人士。德性是儒家倫理的基石,正如蒙培元所言:“儒家倫理是建立在德性之上的。”[11](P383)如何實現德性及成就理想人格是儒家倫理學最為核心的部分。在孟子性善論的思想視域下,人生而具足的羞恥心是道德意識的重要來源,保持個體的羞恥心或羞恥感,在培養道德人格時具有重要意義。孟子曰:“圣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圣人是社會中道德完善的人,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理想人格。培養君子式的道德人格則是可期的,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于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君子持守“四端之心”,落實為踐履工夫上的善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不是對柏拉圖式的“哲人”講話,他的倫理學有一定的言說對象,特西托勒將這類人統稱為希臘古典文學中的“君子”(gentlemen)[12](P24)。他各種倫理學著作中列舉的德性清單不是基于個人的偏好選擇與評價之上的,而是反映了當時希臘社會“有教養人士”[13](P104)階層的普遍行為準則。我們可以把亞里士多德的言說對象統稱為高尚的好人、正派的人或道德嚴肅的人。羞恥感雖然不是一種德性,而是由惡的行為引起的社會情感反應,但羞恥感可以幫助人少犯錯誤,亦可導向正確的行為,成為城邦里的有教養人士。
其二,重建現代倫理秩序需要找到真正可以為道德奠基的基質,通過對孟子與亞里士多德羞恥德性的互詮,我們發現孟子與亞里士多德關于羞恥本質的認識能夠承擔得起道德奠基任務,并且兩者具有互補性。為道德奠基不是制定一些道德準則或倫理規范,而是為道德之所以為何能夠存在提供某種合理性論證,就是要為道德找到一個先于任何人類經驗生活而又使之獨立于人類經驗生活的根據。這實質上涉及到對人類道德意識起源的考察,因為道德意識是道德概念與道德行為的前提條件,找到為道德奠基的基質就要探究道德意識的來源問題,即我們的道德意識究竟來自何處?明確了道德意識的來源,我們就可以知道哪些道德意識是可激發不可教化或可教化而不能激發的,這將有助于倫理教育的改善與現代社會倫理秩序的重建。羅爾斯與羅素等西方哲學家提到過道德秩序或倫理信念的來源問題,倪梁康深入探究了中西哲學家對這一問題提供的解答,他將道德意識的來源一分為三:良知本能的內心起源;社會主體間約定的外在起源;宗教道德信念的超越起源。因為孟子和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不涉及超越性的宗教問題,所以我們立足于從內心起源與外在起源探究道德意識的來源問題。就這兩個起源而言,良知本能是道德意識最基本、最穩固的來源,因為它不因社會、文化、歷史與民族的變化而變化,后者則呈現出一定的不穩定性,不同的社會形態、歷史時期、文化背景及民族差異都可能使人們對社會主體間約定的社會道德產生非道德化的價值判斷。
法國哲學家于連認為與宣揚人世苦難的佛教以及張揚原罪意識的基督教傳統相比,儒家思想以人性本來之底蘊為根基,在現存的世界幾大文化傳統中,當是最可能完成道德奠基的古典思想資源[14](P85),他具體分析了孟子的“不忍之心”“惻隱之心”為道德奠基的可能性。筆者以為孟子的“羞惡之心”與“惻隱之心”具有同樣的原初性,都是植根于人之自然本性的先天道德意識。羞恥的自發性與主動性是人類道德生活與社會倫理秩序的根本保障,是觸發道德行為的出發點,具有同樣的道德奠基功能。美國學者博姆持有類似的看法,他更是將人因羞恥而臉紅視為道德起源的真正標志。在孟子那里,羞恥作為先天的道德本能,在理智反思之前就相當活躍,是不可以通過教化和傳授來獲得的,但是需要有意識地去激發它。亞里士多德認為成就德性也就是德性的實現活動,德性不出于人的自然本性,自然則賦予人接受凝聚這種本性的能力,接受活動的實踐性使德性由潛在的能力變現為現實的品質狀態。行為正義才能成為擁有正義德性的人,行為勇敢才能成為擁有勇敢德性的人,行為節制才能成為擁有節制德性的人,亞里士多德顯然不會認為行為羞恥才能成為擁有羞恥德性的人,因為羞恥是心智成熟的人要堅決杜絕的惡的品質。他認為羞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由惡行或不體面的事情暴露于外所引發的恐懼情感,亦即意味著行為主體在做出違背社會道德的行為之后,經過理智思考與反省,會于心理上產生一種恐懼情感,這是外在的社會壓力導致的結果。人類的幸福生活需要良好的倫理秩序,而良好的倫理秩序不僅建基于人性本身,而且是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中相互依存的需要。所以這種社會化的羞恥情感雖然是道德來源的次要方面,但它亦是不可或缺的,這也是后天的倫理教育能大有作為的地方,對現代社會倫理秩序的重建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注 釋]
①倪梁康認為“惻隱之心”和“羞惡之心”構成內在道德意識的兩個重要來源,它們是在排除了各種外在的、約定的、社會化的道德替代品之后,仍然牢固保存下來的人的自然本性之殘余,這兩種并行不悖的道德意識構成人類一切道德生活的基礎。參見倪梁康:《心的秩序——一種現象學心學研究的可能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