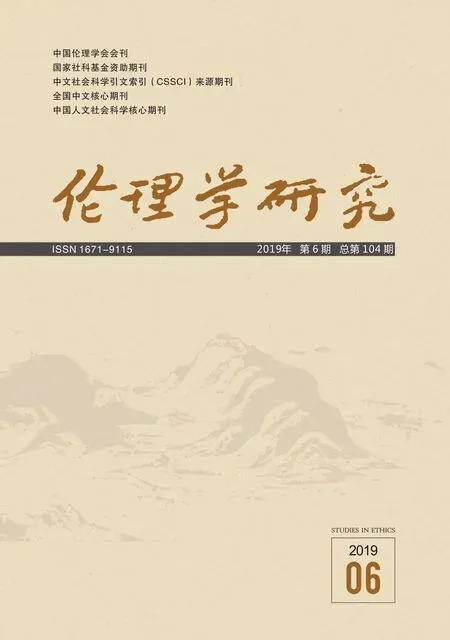人工智能輔助醫療決策并未挑戰尊重自主原則
孫保學
在醫學倫理中,尊重患者的自主權是一項最基本的倫理原則。它要求醫護人員、患者家屬“幫助患者做出自己的決定(比如通過提供重要的信息)并尊重和遵從那些決定(即使健康方面的專職人員認為患者的決定是錯的)”[1](P63)。隨著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智能化醫療決策支持系統(med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MDSS)的引入創造出新形式的道德選擇問題,人工智能代理決策成為醫學倫理的熱點話題。從對病患的最佳利益出發,醫護人員采用MDSS 提高醫療決策的精準度,但也可能被它誘導。最近,《自然-醫學》期刊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使用4 萬余幅肺癌患者CT 掃描圖像訓練的深度學習模型預測肺部腫瘤的準確率高達94%,而且在對比實驗中,全部優于樣本組平均擁有8 年臨床經驗的6 名放射科醫生[2]。有不少人擔憂,隨著MDSS 在醫療決策中被越來越多地采用,不僅醫生的權威會被削弱,患者的自主選擇權也可能受到侵蝕,使他們都更信賴人工智能。
一、醫療決定:從醫生的權威到患者的自主
在西方醫學史上,患者要遵照醫囑,醫療決定基本上都由醫生做出。當患者到了醫院或診所,醫生就是權威,患者對于醫生的醫療決定要言聽計從。“醫生不會問病人希望怎么樣;也不會去了解病人優先考慮的是什么;有時還會對病人隱瞞一些重要資料,比如吃的是什么藥、接受的是什么治療以及診斷的依據;甚至會禁止病人翻閱自己的病歷記錄。醫生說,病歷并不屬于病人。醫生把病人當成一個孩子,認為病人過于脆弱而且頭腦簡單,不能直接面對事實,更不要說自己做決定了。”[3](P194)然而,這種看法在近幾十年來已經發生明顯轉變。
1.從最小化傷害到保護自主選擇
傳統上,醫生代表著權威,醫療決定權牢牢把控在醫生手里,患者只好聽之任之。然而,20 世紀50 年代后期,“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提出打破了“一切聽從醫生決定”的做法。在紐倫堡審判中,納粹在很多猶太人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人體實驗的行徑被披露,激起了人們對于知情同意的高度重視。1957 年,“知情同意”這個詞在美國法院的一次醫療事故案例中第一次出現,到70 年代初學術界已經展開了詳細討論。
現在,醫療決定權已經從醫生移交到患者手中。無論是醫生還是醫學研究者在對病患或受試者進行任何實質性干預前,都必須征得他們的同意,這已經被確立為一項基本的醫學準則。起初,設立知情同意準則是為了將潛在傷害最小化,同時避免不公平地對待病患或受試者。不過,近年來知情同意“關注的焦點已經從強調醫生或研究者告知信息的義務,轉移到強調病人或受試者理解和同意的質量。促使重點轉移的動力是自主”[4](P77)。從20 世紀70 年代中期開始,學者們論證知情同意的必要性時更多地是圍繞保護患者和受試者的自主選擇權展開。尤其,杰伊·凱茨(Jay Katz)在1984 年出版的《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沉默世界》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他列舉了大量案例有力地論證了患者不僅可以而且應該自己來做醫療決定[5]。
此后,越來越多的醫學院開始接受這種觀念,并在將其貫徹到教學過程,要求學生樹立尊重患者自主權并為患者服務的意識。“老師教導我們要把病人當作有自主權,能自己做決定的人。”[3](P196)與此同時,患者賦權(patient empowerment)革命使越來越多的患者在醫療活動中的自主選擇意識開始覺醒,不再對醫生的建議言聽計從。于是,“大部分醫生都認真地把決定權交到了病人手里,把所有可選擇的治療方法和可能發生的風險通通告訴了病人;有些醫生甚至拒絕給病人任何建議,就是擔心給出的建議會影響病人做決定”[3](P196)。在患者明顯做出錯誤決定時,醫生會陳述利弊試圖說服患者,但往往也不能過度干預。“目前為止,醫學的正規說法是,他們怎么決定,你就怎么做。無論怎樣,身體的所有權是屬于病人自己的。”[3](P196)
2.患者放棄自主決定權的情況
患者擁有自主權并不意味著他必須行使這項權利。患者希望能有好的結果,無論醫療決定是由誰做出的。卡爾·施耐德(Carl Schneider)的實證研究揭示:“雖然病人基本上都希望知悉醫療情況,但其中有相當數量的病人(尤其是老年病人和危重病人)不想做出自己的醫療決定,甚至可能不想以任何非常顯著的方式參與這些決定。”[4](P63)如果患者認為他的自主選擇很可能不會導致好的結果,那么患者就有可能放棄自己的這個權利,將其轉交給其他更有能力或資格做出決定的人,或者聽天由命。在很多情況下,患者會選擇放棄自己的自主決策權,希望醫生、家人或朋友代替他們做決定。一項被廣泛引用的調查研究同樣表明,“大多數(59%)確診初期的患者希望醫生代表他們做出治療決定。患者們最常說的是:‘我希望由我的醫生來決定采用哪種治療方法,而不是認真考慮我的意見。’只有12%的確診初期患者愿意積極地參與決策”[6](P945-946)。在具體的醫療情景中,患者可能因為身體狀況、精神焦慮或其他原因難以做出正確決定,他們可能會為了緩解身體或心靈的巨大痛苦而不假思索地做出決定。
在上述情形中,患者希望醫生和家人能在其病情嚴重而無法理性地權衡選擇的利弊時,分擔做決定的責任。由于未知的醫療風險的普遍存在,面對生死攸關的重大決策,其實醫生、患者和家人都不太愿意主動做出選擇,更不用說需要面對隨之而來的責任承擔。但是,總得有人做出選擇并為此承擔責任。醫生作為有著良好的職業訓練和豐富的臨床經驗的專業人士,被認為要比患者冷靜得多,能夠更客觀地看待患者的病情,盡可能地減少情緒的干擾,還可以通過集體商討的方式做出正確的決策。當然,醫生除了要對決策失誤承擔責任,內心也會有對生命的愧疚;對于家人,錯誤的決定也會給他們帶來深深的自責。
“誰決策,誰負責”的模式將醫療決策權更多地賦予患者,但這也給患者帶來巨大的壓力。面臨可能涉及生死決策時,患者往往會受到無意識和非理性壓力的影響。而且,醫生作為關鍵的信息提供者,其行為方式不同可能導致患者做出完全相反的決定,而最終的責任都由患者來承擔。“當決策的過程變復雜時,很多人傾向干脆不做選擇……(如果)決定困難得多,后果也嚴重許多,患者想當然會逃避做決定的責任。”[7](P6)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生真的尊重患者自己做出醫療決定的自主權的話,是否也應該尊重他們將決定權再次交給醫生的權利呢?
二、數據驅動的智能醫療決策
上述令醫生和患者同感糾結的選擇難題是否可以交給智能機器來完成,使他們都能從壓力中解脫出來呢?事實上,醫生的工作(從病情分析到手術治療)現在越來越多地被MDSS 所接管;同時,患者為了確診病癥,往往也更信賴具有更先進的MDSS設備的醫院。但是,即便確診,患者仍然要面對“該不該手術?該不該放化療?哪種治療方案是更好的?”等選擇困境。對于這些選擇,人工智能輔助醫療決策系統會做得比醫生更好嗎?
1.數據驅動的輔助醫療決策
人工智能輔助醫療決策系統被寄予厚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能夠將醫生和科研人員從繁瑣的數據處理和分析工作中解放出來。確診工作是醫療決策的前提,很多患者因為誤診而錯過治療的最佳時機,甚至付出生命代價。隨著人們對于精確性要求的提高,完成這項工作所需的勞動量也成倍上升。現在,醫生和醫學研究者已經開始利用人工智能系統分析患者的基因數據,通過對比癌癥基因數據庫和已發表的癌癥遺傳學文獻來診斷疾病。以前,這項工作需要專家團隊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完成,現在智能診斷系統可在幾分鐘內完成,大大提高了效率。
現階段,高效的智能化診療系統是由數據驅動的,這與傳統的診斷和治療依賴醫生的臨床經驗和直覺判斷形成鮮明對比。機器學習算法對于疾病的診療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具有較為完備的醫療大數據是智能輔助醫療決策的前提。目前,基因數據庫、臨床治療數據庫、醫療影像數據庫等都在不斷完善。據報道,“在過去的十年中,超過90%的美國醫院已經實現了計算機化,超過一半的美國人在Epic 系統(注:Epic 公司是美國醫院最大的電子病歷供應商)中擁有自己的健康信息”[8]。如今,大多數電子病歷系統都具備決策支持功能。在會診和檢查時,智能系統會為醫生提供指導和建議,通過屏幕上顯示清單和提示的方式直接呈現給醫生。
基于電子病歷系統提供的案例數據和最新研究成果,人工智能輔助決策系統可以實現推理、學習和交互等功能。據報道,IBM 的沃森“醫生”可以對乳腺癌、肺癌等13 個癌種提供治療方案建議,這些建議甚至已經可以做到與世界頂級腫瘤專家的建議高度吻合。IBM 在其官網上宣稱,沃森“醫生”能夠做到提前數小時預知患者某些疾病的發病時間,為患者制定相應的醫護方案;“能夠幫助癌癥晚期患者選擇更具療效的全新治療方案。通過分析復雜的基因數據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沃森可以幫助醫生發現原本可能失之交臂的治療方案”[9]。這些技術進步使很多人樂觀地認為,人工智能系統的疾病診斷能力遲早會全面超越人類醫生,尤其在依靠醫療影像和檢驗檢測方面。
2.大數據算法重塑醫療生態
在未來,大數據算法可能比我們自己更了解我們的身體狀況和內心感受。醫療大數據是海量的,不只是人類群體疾病的橫向數據,還包括個體從小到大的縱向數據。智能可穿戴設備可以實時監測我們每天的運動量、心跳速率、血壓和血脂等各項身體指標,這些數據可以被實時地存儲到醫院或數據平臺的云端。如果異常值出現,它立刻會發出警報,提醒個體,甚至代替他們啟動急救方案。
近年來,生物技術與信息技術的交疊融合顯著增強,智能化醫療正在加速發展。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預測:“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醫療決定,并不是取決于我們自己是否覺得健康,甚至也不是看醫生做出什么判斷,而是要看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身體的計算機得出怎樣的運算結果。再過幾十年,大數據算法就能通過持續的生物統計數據流,24 小時監測我們的健康狀況。早在我們出現任何感覺之前,算法就能監測到流感病毒、癌細胞或阿爾茨海默病的蠢蠢欲動,接著就能針對每個人的體質、DNA(脫氧核糖核酸)和性格,量身推薦適合的治療方案、飲食和養生之道。”[10](P45)實際上,這種極端觀點認為未來我們是被大數據算法統治,生活在數據主義的陰霾下,我們終將成為聽命于大數據算法的傀儡。
按照赫拉利的分析,過去幾千年人類一直奉神靈為最大權威,直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幾個世紀,人逐漸取代神靈,成為新的權威。自此,人們追求平等,信仰自由,人本主義開始興盛。赫拉利預測,就在我們生活的當下時代,正在發生一場權威再次轉移的革命——從人類轉移到大數據算法。以前,宗教神話為神靈確立權威,人本主義為人樹立權威;如今,大數據算法正在智能社會建立自己的權威。新權威的確立意味著人本主義信念的瓦解,人類將對新權威言聽計從。
那么,我們憑什么甘愿聽信大數據算法?赫拉利指出,“你會發現自己老得面對一個又一個‘病癥’,得遵守這個或那個算法建議。不想聽算法的?那么醫療保險就有可能被取消,或者被公司解雇”[10](P46)。如果這種預測是一種極有可能發生的情形,那么不聽從算法的指引而固執己見將會付出慘痛的代價。赫拉利認為,我們已經被以大數據算法為核心的技術綁架,不得不聽命于它,我們在未來可能將毫無自主可言。在下文,我將論證或許我們不用如此悲觀。
三、尊重自主原則不會受到挑戰
尊重自主權的問題之所以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可歸因于人們對醫學權威的質疑和挑戰。在普通人缺乏醫學知識的時代,醫生確實能夠做出比普通人更加可靠的判斷,因此絕大多數人自然愿意聽命于醫生。但是,隨著整體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們能夠越來越多地了解自己的身體和疾病,并且關心醫生的診治過程,甚至質疑他們的某些做法。一些患者、律師、倫理學家等一起掀起患者賦權革命,“開始反對這種傳統醫療決定方式,認為醫生做決定時,患者的意見應該也要更積極地加入”[7](P2)。在人工智能時代,醫生的知識權威角色被進一步弱化,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將會被MDSS 接管。隨著系統可靠性的不斷提高,患者有可能更愿意相信大數據算法而不是醫生的建議。但是,這種相信是否會發展成高度信賴仍然是存疑的。實際上,存在多重因素會削弱人們對MDSS 的信賴,患者仍然保有自主決策權。
第一,智能診療系統并不總是做出優于醫生的決策。現代醫學給很多人一種錯誤印象:醫學已足夠發達,能夠治愈絕大多數疾病。近幾十年來,醫學的確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并不是所有疾病都能治愈。智能診療系統是基于過往的病例數據進行預測和決策,難以應對普遍存在的“醫學無法解釋癥狀”(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MUS)。2011 年,《身心醫學》雜志發表的一項針對620 名德國患者的統計研究發現,MUS 足足占了所有已報告癥狀的三分之二[11](P263)。況且,人體作為一種復雜系統,選擇治療方案要因情況而異。智能診療系統擅長分析已經有成熟應對方案的病癥,但面對未知病癥,專業醫護人員可能更有優勢。據報道,目前即使是最先進的MDSS 也經常給出不靠譜的醫療建議,在醫院中并沒有發揮太大的實際作用。[12]在未來較長時間內,MDSS 完全取代醫生的工作還很難實現。
第二,從社會經濟的角度考慮問題,很多患者可能不會選擇使用MDSS。有時,人們對技術的發展可能過于樂觀。以電子病歷系統為例,它的普及恰恰帶來一些意料之外的副作用,甚至與我們的預期完全相反:“同安裝軟件之前相比,采用電子病歷后,醫生給病人開出的賬單越來越貴。”[13](P110)研究表明,如果醫生更容易調取患者的X 射線記錄和其他診斷圖像,他反而更可能要求患者進行新的影像檢查[13](P111)。診斷提示雖然有助于防止醫生忽視某些細微病癥,但卻刺激醫生為患者做了很多不必要的檢查,這大大提高了醫療成本,這將使很多患者不堪重負。醫院以高昂成本采購的MDSS 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能服務少數人,因此在推廣應用上存在普惠難題。
第三,輔助醫療決策技術的先天限制因素可能導致患者并不信任它們。電子病歷系統的引入分散了醫生的注意力,提高了他們職業倦怠感。“在檢查室里,醫生把病人一半的時間花在面對屏幕做電子工作上。”[8]醫生不得不把大部分時間花費在屏幕上,而不是和患者面對面地溝通。“超過90%的接受調查的以色列醫生表示,電子病歷‘妨礙’了他們同患者的溝通。”[13](P115)作為醫生,在屏幕前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通過“復制+粘貼”的慣性動作來填寫問診報告。這些生搬硬套拼湊起來的病歷記錄恰恰又降低了病歷數據的精準性,冗余樣本增多和數據失真會導致機器學習出現診斷誤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智能診療系統可能導致醫生被過度引導,離患者越來越遠,喪失獲得直接經驗的機會,從而削弱或限制醫生的專業技能。這可能成為醫療決策失誤的某種隱秘根源,這些因素所導致的決策失誤會降低人們對智能診療系統的信任度。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患者依然擁有自主決定權。雖然智能系統在某些方面具有優勢,但其難以克服的自身局限使得理性的患者不會因為它的突出優點而對其言聽計從。
四、放大患者的自主權民主化醫療
隨著智能醫療時代的到來,家長式的(paternalistic)醫療模式將逐漸被淘汰,而醫療民主化的進程將逐步實現。事實上,患者正在獲得更多的主導權,成為醫學進步不可忽視的力量,開始積極地參與到臨床醫療決策。他們會對自己的病情提出問題,到網絡上查找資料,研讀教材和最新論文,與專家商討治療方案,最后自己做出決定。“患者正在從根本上變得越來越聰明:他們了解自己的身體以及生活情況,并且比任何人都關注自己的健康。然而,這并不代表他們會堅持做有益健康的事情,只是一旦出現問題,他們則相當擅長發現。”[14](P9)傳統上,患者服從醫生的權威是因為患者和醫生之間存在知識鴻溝。如今,隨著全民教育水平的提升,每個人都能夠通過閱讀和學習掌握一些基本的醫療知識,甚至緊跟醫學前沿。患者與醫生之間的知識鴻溝已經不像以前那樣不可跨越。
人人參與的民主式醫療時代正在到來。對于一些疑難雜癥,患者本人及其家人會通過書籍和網絡上最新科研成果的學習成為某種“專家”。正如《柳葉刀》雜志的編輯埃瑪·希爾所說:“每個患者在自己選擇的領域里都是專家,這個領域就是自己的生命。”[14](P3)在未來,患者可直接面對智能醫療系統做診斷和治療,這其實是對患者的重新賦權。托普用古登堡印刷機與輔助醫療系統進行類比。古登堡印刷機使閱讀不再是教父、權貴和社會精英的某種特權,平民百姓同樣能夠閱讀。類似地,智能設備讓醫療不再是醫生的特權,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到針對自己的醫療決策中,我們正在步入個體化的精準醫療時代。當然,目前的智能醫療決策系統在有效性和穩定性上還有待大幅提升。
尊重患者的自主權是技術應用的一個必然后果。個體化的精準醫療必須考慮患者自身的具體病情,而且智能系統給出的治療方案很可能并不是經過充分的臨床檢驗的。因此,醫療決定的做出應該根據智能系統提供的診斷結果,由醫生、患者和家屬等通過協商共同做出,既不能完全交給患者,也不能完全由醫生或家屬代理。從這個意義上講,患者有權利要求醫生的診療符合規程并詳細了解醫生的治療方案;醫療機構要履行職責,“確保病人有選擇的權利,以及有接受或拒絕信息的權利,是一項基本義務。強制提供信息、強迫選擇和含糊其辭地提供信息,都有悖于這一義務”[4](P64)。當然,如果患者并沒有相關的基本知識,卻仍然任意地行使自主決策權可能就不是恰當的。如果患者有條件使用智能診療系統,實際上他將減少對醫療專業人員的依賴性,從而獲得更多的主動選擇權與自主決策權。
不過,智能化醫療放大了患者的自主權,但這并不意味著醫生的地位和意義被嚴重削弱。首先,輔助醫療決策技術改變的是數據和信息的流向,能夠大大減弱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醫療決定的做出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單向模式。但是,過度依賴信息的醫療決策是有陷阱的。醫學的實質性進步不是只靠大數據算法就能推動的,還依賴于醫護人員的直覺和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復制思維的產物并不等同于復制思維。圖靈強調,算法永遠也不能完全替代人類的直覺。有意識的推理無法得出‘直覺判斷’,這種無意識的判斷不會消失。”[13](P134)醫護人員在臨床實踐中養成的無意識的直覺判斷力是快速應對復雜情況的關鍵要素,是他們建立權威的核心競爭力。智能決策系統獲得信任,需要將它的計算結果與醫生或專家委員會的判斷進行長期的對照比較,只有在明顯優于后者的情況下,醫學界才會接受它。然而,醫學實踐充滿各種不確定性和不可控因素,很難有一套固定程式對所有疾病提供一攬子的解決方案。人工智能輔助診療系統可能會接管醫生的大部分工作,但不可能提出完美的治療方案。
其次,親密度是塑造良好醫患關系的關鍵,尊重患者的自主權是它的前提。“最佳醫患關系的核心是‘親密度’,即患者可以吐露他們難以啟齒的秘密和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恐懼,并且醫生的體觸安撫可以讓患者提升自信,促進患者康復,這一點是不可能被取代的,也永遠不會消失。”[14](P12-13)表面上看,患者是希望獲得自主選擇的權利,其實患者更愿意希望得到專業能力過硬并且值得信賴的醫生的救治。態度親切的醫生能夠讓患者在做出醫療決定時感受到自主權得到了尊重,醫生是在為他著想。對于患者做出的決定,醫生有提出建議的義務,消除患者對醫療手段的恐懼,讓他們放棄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現代醫學不斷發展,技術日新月異,真正的考驗已不再單單是祛除病人的病痛,而是醫生能否以將心比心的態度提供熱情親切的服務。”[3](P207)如果患者在做決定方面猶豫不決,或者干脆愿意放棄自己的自主權,那么醫生應該挺身而出,提供引導或按照合規程序代替他們做正確決定。
最好的醫療決定是醫生和患者都認同的決定,這離不開他們密切的溝通、互動與合作。醫療系統存在的目的是治病救人,應該始終以患者為本,為患者服務。未來醫生的角色是為病患提供更好的決策支持,而不是僅僅作為高高在上的專家或權威對患者發號施令,更不是做一個冷漠的理性旁觀者。輔助決策系統分擔了醫生一部分工作,是作為助手而存在,不是以替代者的姿態出現。
結語
在人工智能時代,醫學倫理面臨這樣的新挑戰:隨著醫療技術越來越智能,我們迫切需要一套醫護人員和患者相互信任、親密協作、共同決策的機制,盡可能地幫助我們擺脫令人進退維谷的境況。這不僅是對醫療體制提出的要求,也是對患者自主決定權的高度尊重。“尊重自主不是醫療領域的純粹理想,而是專業義務。自主選擇是病人的權利,而不是病人的義務。”[4](P64)在生病時,患者要盡可能地了解醫療過程的細節,明白哪些情況下要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愿,也要清楚在哪些情況下需要聽取他者的建議。如果患者放棄自主決策的權利,醫護人員和家屬應該詳細地審查這個過程。只有醫生與患者彼此充分地了解,才能共同做出最有力的醫療決定。從這種意義上講,強調醫患合作比強調權責更貼近醫療新革命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