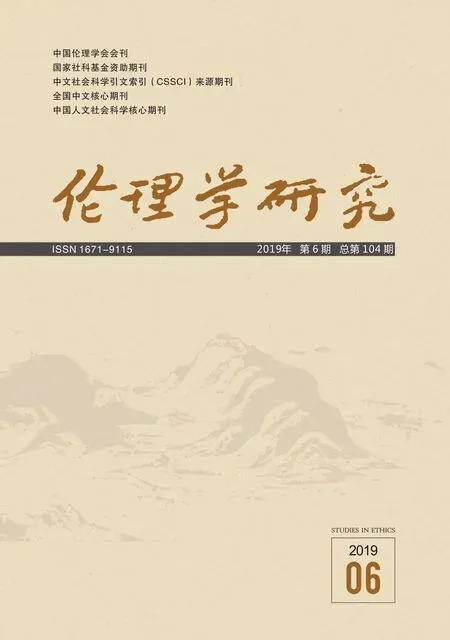論正義的空間性與空間的正義性
袁 超
正義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永恒的價值理想和目標,在人類的社會生活當中發揮著重要的價值引導作用;空間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條件,是人類所有活動的重要載體;現代社會當中空間與正義的互動日趨明顯,正義具有空間性,與此同時空間也具有正義性,兩者共同成為“空間正義”的兩個極為重要的維度。“空間正義就是一種符合倫理精神的空間形態與空間關系,也就是不同社會主體能夠相對平等、動態地享有空間權利,相對自由地進行空間生產和空間消費的理想狀態。”[1](P40-46)正義的空間性指的是正義具有空間維度,正義價值規范的構建與創造需要引入空間維度;空間的正義性也就是指現代社會的空間生產需要符合正義的邏輯,這是由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決定的。正義與空間兩者是相互建構的,“空間正義”的提出正是正義與空間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
一、正義與空間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總括,公正是最主要的,它比星辰更加光輝”[2](P103),作為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價值存在,正義一直以來都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永恒的價值理想和目標。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更多注重的是分配正義,是如何實現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公平配置。自由平等原則以及機會的公平平等和差別原則是羅爾斯提出來的正義的兩大基本原則,也是社會財富分配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指導原則。作為“經濟人”存在的個人來說,趨利避害是每個人的本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是個人存在的重要目標。然而作為個體存在的人由于多方面因素(如性別、職業、社會地位等等先天以及后天因素)的影響其獲取利益的能力是存在一定差異的,每個人的利益訴求也是不盡相同的,因此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利益的沖突也就在社會發展過程當中不可避免。此時我們自然就需要一套科學合理的理論來指導社會利益的分配,而正義原則就是社會發展過程中保證社會利益分配公平、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
現代城市的不斷發展帶來的是城市空間生產的不斷推進,空間的力量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之一。空間生產的不斷擴大使得空間的屬性也逐漸發生了改變,空間已經不再單純具有自然屬性,是一種自然的存在,不再僅僅是一種場所,其具有了更為豐富的意義。“空間是行為的場所,也是行為的基礎”[3](P70),這也就是說空間已經不再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存在,其已經逐步成為人類行為的基礎,具有社會屬性。現代空間生產從“空間中的生產”轉變為“空間的生產”,為了滿足資本增值的需求,空間自身成為一種生產資料或者是一種商品,空間除了物理屬性之外還具備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成為政治和權力運行的基本載體,空間關系直接反映了社會關系,空間結構的調整、空間生產方式的改變影響著整個社會的發展。空間屬性變化的同時,我們對于空間的認識也需要做出調整,“完整的空間認識論應是自然(物質)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一,它們兩者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4](P340-345)。空間具有社會屬性也就意味著空間與社會聯系更為緊密,這其中“空間正義”的提出就是最為明顯的例子。
正義是人類社會追求的永恒目標,空間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場所、載體以及基礎所在,空間具備社會屬性也就代表空間與社會正義已經緊密聯系在一起,無法分割。對于正義理論來說,傳統的正義理論是建立在時間的基礎之上的,隨著現代空間生產的發展,其解釋力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的需求,因此需要在理論的建構過程中引入空間的維度;對于空間自身來說,空間生產的發展帶來了社會的巨大進步,但是與此同時空間出現的種種不正義問題直接影響到空間生產的進一步擴大以及社會的基本穩定,以此需要用正義理論的邏輯來規范現有的空間生產。空間與正義相互需求、相互構建,“空間正義”理論也就應運而生,其實是空間生產的價值核心,是規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價值準則。
二、正義的空間性
正義的空間性指的是正義具有空間維度,正義價值規范的構建與創造需要引入空間維度,這是正義理論發展的必然趨勢。“哪里有空間,哪里就有存在”[5](P22),空間是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最為基本的維度,人們的所有活動都需要在空間當中進行。空間要素是正義理論自身的建構過程中的核心要素,空間維度的引入使得傳統的正義理論被解構和重構,同時作為一種價值規范的正義作用社會的過程中也需要空間的參與。
空間要素是正義理論自身建構過程的中核心要素,人們通過空間去認識和把握世界,空間是構成社會理論的核心要素和范疇,“社會系統的時空構成恰恰是社會理論的核心”[6](P196),在社會理論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用列斐伏爾的話來說,“空間在當今構成了我們所關注的理論和體系的范圍”[7](P18-19),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空間是社會理論構建的基本維度,任何一種社會理論體系的構建都需要以空間為基礎。正義作為一種社會理論,再其建構的過程中也就必然有空間的參與。現代社會正義理論的發展過程中,空間扮演了雙重角色——解構和重構。空間維度的引入對原有的正義理論具有解構作用。“至少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時間和歷史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社會科學的實踐意識和理論意識中,已占據了寵兒的地位”[8](P1),傳統正義理論是在時間和歷史的基礎之上構建起來的,其強調的也是正義的歷史性。然而隨著社會科學的研究的空間轉向發展,空間逐步受到重視,也開始逐步引入正義理論。然而隨著空間維度的引入,原有的正義理論體系遭到破壞,正義理論框架的重構成為必然的趨勢和要求。將空間維度引入到正義理論的建構過程中是對正義理論合法性認識的再思考和論證,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義理論本身就應當是暗含著空間維度的。無論是正義理論的建立還是正義理論的實施其都應當是在空間和時間的場域當中布展開來的,正義是不可能獨立于空間而存在的。空間語境是現代正義理論的構建與創造的核心要素。列斐伏爾極為重視空間在社會理論架構重構過程中的作用,甚至認為空間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在“某種總體性、某種邏輯、某種系統的過程中可能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9](P23-24)。現代“空間正義”理論的提出就是空間維度引入正義理論的重要表現,是對正義理論發展的重要創新。現代“空間正義”理論的提出打破了建立在時間性、歷史性以及社會性基礎上的正義理論,開拓了現代正義理論的空間維度,是對正義理論的有效拓展。將空間與正義結合起來也就意味著正義理論的建構和作用的發揮已經不僅僅是局限于單純的社會領域或者時間領域,其已經延伸到了空間領域,正義的理論內涵更為豐富,其對于社會現實的解釋力也進一步提高。空間正義是一種微觀正義,是對原有建構在時間和歷史基礎上的傳統正義理論的深刻反思,其改變了傳統正義理論宏大的敘事方式,將關注點回歸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更加注重對于個體生存狀況的揭示。空間維度的引入是正義理論進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是開拓正義研究新視域、豐富正義理論內涵的重要途徑,這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正義理論本身的建構過程當中空間要素是極為核心的存在,而作為一種價值規范而存在的正義理論在作用社會的過程中同樣少不了空間基本作用的發揮。從正義價值規范作用于社會需要空間場域作為載體來看,作為一種價值規范而言,正義的構成本身就是包含了空間維度的,而在其作用于社會的過程中也需要空間作為場域和支撐。這是由空間的基本性質所決定的,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沒有辦法脫離空間而存在,價值規范作用于社會也是一樣。也就是說任何一種價值規范作用的發揮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間當中進行,空間為價值規范的作用創造了最為基本的條件,其作用的結果也是通過空間結果反映出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價值規范和社會空間的作用和運動是雙向的,二者相互影響。社會空間的變化可能引起社會價值規范的變革,而社會價值規范的變化同樣可能導致社會空間的調整。作為價值規范存在的正義作用于社會,需要空間作為支撐和載體,而與此同時不同的空間場域影響之下的價值規范也不盡相同。從現實社會發展的情況來看,其實每一種價值規范作用的發揮都是具有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背景的,不同時代背景、不同空間場域的價值規范必然存在一定的差異,這是由社會發展現實所決定的。“空間正義”的提出是建立在空間生產的基礎之上的,空間生產的過程其實就是正義作用于社會的過程,空間生產的過程也可能看成對于社會空間結構的調整過程,而不同形式的空間生產可能會帶來不同形式的正義價值規范,空間場域的差異也就使得正義的表現形式及其發揮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差異。“時空性的生產既是一般社會過程的構造性和根本性環節,又是創造價值的根本性環節;這個原則跨越了文化限制,適用于完全不同的生產模式和顯著不同的社會構型。”[10](P281)作為價值規范存在的正義在作用于社會的過程中,由于空間場域的不同,正義的形態和作用必然不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其空間生產是由資本主導的,資本主導下的空間生產帶來的是社會空間發展的差序格局,可能會加劇空間的不正義,帶來的是正義理論的異化以及社會價值的淪喪。“空間正義”理論的提出就是要改變這樣一種差序格局的狀態,改變現有不合理的空間格局,構建一種更為和諧的社會空間體系,使得空間正義價值規范能夠更好地發揮其作用。從這一方面來看,作為一種價值規范而存在的正義理論在作用社會的過程中,空間因素和空間維度是極為重要的,空間作用的發揮直接影響到正義理論作用的發揮。
總而言之,無論是正義理論自身的建構還是正義理論作用于社會,其都需要空間的參與,正義自身包含了空間的維度,正義與空間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正義具有空間性,不同的空間生產形式、不同的空間形態、不同的空間組織結構會導致正義形態的發生變化,同時也會使得正義理論作用于社會的形式和效果出現差異。“正義的地理性或者空間性是正義自身內在的構成要素,是一直以來正義與非正義如何被社會地建構與演化的決定因素。”[11](P1)傳統的正義理論是建立在歷史和社會的基礎之上,空間維度被忽視,然而正義的多重屬性注定空間是正義理論建構和正義理論作用過程中的重要環節,這也就是現代社會科學需要進行空間轉向的重要原因。
三、空間的正義性
正義自身包含了空間的維度,正義具有空間性,正義價值規范的構建與創造需要引入空間維度;而正義與空間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空間具有正義性,空間的變遷同樣需要引入正義維度,空間生產需要正義邏輯的規范。空間的正義性也就是指現代社會的空間生產需要符合正義的邏輯,這是由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決定的,是空間邏輯演進的必然走向。如果說正義的空間性是站在正義的角度考察正義理論的建構以及作用的發揮受到空間維度的影響的話,那么空間的正義性就是站在空間的角度考察空間生產的實踐需要正義邏輯的規范和指導。隨著現代社會多元發展趨勢的日益明顯,正義問題已經逐步成為人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之一。正如同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一樣,正義問題的表現和形成原因也變得更加復雜。現代社會正義問題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今天成為不平等形成原因的多元化因素,包括:階級、種族、民族、性別、興趣、年齡、居住區域、移民狀況、住房、環境正義以及文化認同,等等”[12](P360)。面對如此復雜的問題,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將其歸結于某一種或者幾種因素來進行分析,也沒有辦法通過一種或者幾種政策的調節就將其全方位解決,但是我們可以抓住其中的關鍵點進行深入研究,解決其中的主要矛盾。正如同前文分析,正義問題產生的關鍵因素就是空間要素,空間問題是正義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之一,正義問題的解決首先就要重視空間因素的作用。“空間正義”理論就是針對現代社會空間生產由“空間中的生產”轉變為“空間的生產”而提出來的。空間生產的集聚帶來了一系列社會不平等問題并使得這些不平等被合法化,隨著空間生產的進一步推進,這樣的不平等甚至有加劇的現象,此時自然需要正義邏輯對空間生產進行規范。
資本力量是推動空間生產的第一動力,在資本邏輯之下空間生產將會出現一個差序格局,一系列的不平等隨之產生并逐步加劇。空間生產作為社會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成為現代城市發展的重要內容,甚至于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現代城市的擴張其實就是空間生產的擴張。但是現代社會的空間生產由“空間中的生產”逐步轉變為“空間的生產”,這個過程當中資本的邏輯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使得空間生產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不平等并將這些不平等在空間生產的過程當中進一步強化。在資本邏輯和權力邏輯的主導之下,空間物化、空間資本化、空間政治化以及空間權力化等空間問題的出現和加劇使得現代空間生產中的不正義問題越來越嚴重,社會矛盾趨向于尖銳。現代城市的快速發展極大改善了人類的生活,開拓和發展了人類生存和生活的空間,但與此同時也使得空間逐漸脫離了人類的掌控成為限制人類自由的存在,人的發展單向地被社會空間決定,空間物化情況日益嚴重;而隨著空間生產的不斷推進,為了實現資本的增值,空間自身被看成是一種資本的形式并被生產、消費和流通,空間資本化的傾向不斷加強;與此同時由于空間生產過程當中政治權力的干預,空間成為權力的象征,成為其運行的載體,權力的不平等可以通過空間的不平等來體現,空間逐步淪為政治統治的工具,空間政治化和權力化的趨勢也是更加明顯。這樣一系列的空間問題都是由于空間生產過程中缺乏正義邏輯的規范而導致的,因此我們需要利用正義邏輯重塑現代空間生產,保證社會的公平發展,維護社會正義。傳統的正義價值規范是建立在時間維度上的,對于空間的關注度不夠,其解釋力已經不足以滿足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特別是現代空間生產的需要。建立在時間基礎上的正義理論觀點不能夠直接照搬到空間的使用當中,因此面對現代空間生產帶來的空間物化、空間資本化、空間政治化以及空間權力化等問題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新的理論分析框架,將空間維度納入到正義的理論分析框架當中。“空間正義”理論的提出正是對資本主導下的空間生產的批判,是對現代空間生產帶來的諸多不正義問題的深刻反思。現代中國的城市發展是建立在高消耗的基礎之上,其對弱勢群體空間權益侵害日益嚴重,這與缺乏科學的價值規范的指導具有深層次的聯系。因此用正義的邏輯規范現代空間生產,建立科學合理的空間生產體系,是現代城市發展的必然要求。
空間生產掩蓋了社會的不平等并使其合法化。空間生產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不平等,由于空間物化、空間資本化、空間政治化以及空間權力化等空間問題的出現和影響,這些不平等在空間生產的過程當中進一步強化,與此同時空間又將這樣的不平等掩蓋起來甚至使其合法化。空間結構和空間組織形式的轉變都是在資本邏輯的作用之下開展的;空間具有政治性,是政治運行的基本載體,同時空間也是權力的象征,權力的不平等體現在空間的不平等之上,因此空間與資本、政治以及權力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空間與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社會資源的配置、社會地位的確定具有內在的聯系。而社會財富、社會資源以及社會地位是決定社會公平與否的重要影響因素,換一句話說,空間與社會的公平有著無法斬斷的聯系,可以說空間直接決定了社會不公平的生產和再生產。其實空間不僅僅是決定了社會不公平的生產和再生產,更是進一步將社會的不平等合法化了,空間的存在將這樣一系列的不平等掩蓋或者使其成為人們在潛移默化的影響之下自然接受這樣的不平等。空間的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以及經濟不平等不同,其表現并沒有那么明顯,或者說在空間的遮蓋下很難被察覺。現代空間生產過程中,特別是在“空間中的生產”轉變為“空間的生產”之后空間背后存在的不平等關系(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等)被隱藏得更深了,加上人們空間意識的淡薄以及空間意識形態的存在,現實中的空間不平等完全被忽略,甚至在某些時候這樣的不平等被視為習以為常。隨著現代空間生產的進一步發展,我們需要對空間以及隱藏在空間背后的社會關系進行深刻地研究和反思,“消除空間性的神秘色彩并揭示其披著面紗的工具性力量,這是從實踐、政治及理論角度認清當今時代的關鍵之所在”[13](P94)。
總之,空間的變遷需要引入正義維度,空間生產需要正義邏輯的規范,這是現代空間生產發展的現實需求,是空間邏輯演進的必然走向。由于空間生產過程中資本、政治以及權力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可能帶來一系列的不平等并在空間生產推進的過程中進一步加劇。而這樣一系列的不平等在空間的掩蓋之下被人們所忽視甚至習以為常。“空間正義”理論的提出是對現代空間生產的深刻反思,是對空間不正義問題的深刻批判,是改變不合理空間生產方式以及空間組織形式的重要指導理論,是減少由于空間生產所造成不平等的重要手段。空間正義的提出并非為了建構一套新的正義理論,而是在傳統正義理論的基礎之上引入空間維度用于指導空間生產的實踐活動,使得現代城市空間生產體現平等性、屬人性等價值導向,這是現代空間生產的現實需求,同時也是空間邏輯演進的必然走向。
結論
正義具有空間性,正義具有空間維度,空間要素是正義理論自身建構過程中的核心要素,空間維度的引入使得傳統的正義理論被解構和重構,同時作為一種價值規范的正義,作用社會的過程中也需要空間的參與,空間具有正義性,資本、政治以及權力等因素導致了不平等并使其空間生產推進的過程中進一步加劇。而這樣一系列的不平等在空間的掩蓋之下被人們所忽視,因此現代社會的空間生產需要符合正義的邏輯,這是由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決定的,也是空間邏輯演進的必然走向。
就目前而言,空間正義的缺失促使城市的發展向“物的城市化”轉變,城市發展不再是“人的城市化”,資本具有逐利性,城市的發展在資本的作用之下更多的也是偏重于利益,而忽視了人的發展。
要實現城市化的持續發展,就要從人的角度來矯正城市化過程中的急躁冒進、只求業績不顧市民真正的利益等問題。各城市政府應該確定合理的利益分享方式和制度,來實現社會的公平、公正、合理,應該讓各個城市主體都能享受城市化帶來的成果,讓城市化朝著利益差距不斷縮小方向而不是相反的方向發展。無論是內城改造還是外城擴張,城市化的建設和發展始終要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它的建設應是在和諧的氛圍中既保證讓城市居民住有所居,也可以讓廣大農民和外來務工人員等社會階層共享其發展的成果,通過城市的現代化帶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從而推動城鄉一體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