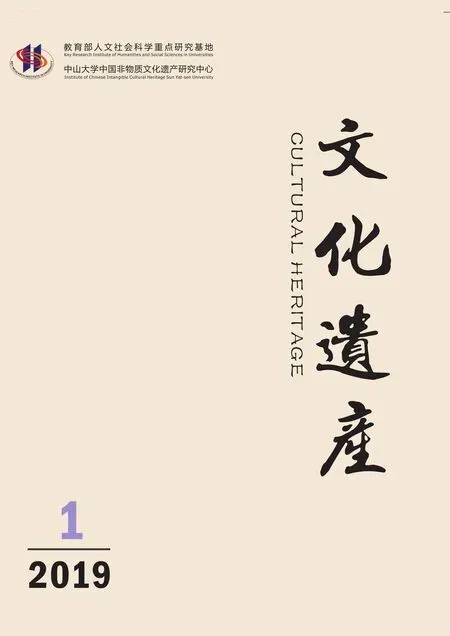媒介變遷與民間敘事的現代傳承
——以木蘭傳說為例
朱婧薇
如今,人們已然置身于“技術的世界”(technische Welt)*德國學者赫爾曼·鮑辛格(Hermann Bausinger)使用的術語,參見赫爾曼·鮑辛格:《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戶曉輝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媒介的變遷對民間敘事的傳承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最初單純依靠口耳相傳到書面傳統的發生,再到電子媒介的參與,現代技術的進步讓民間敘事得到更為豐富的表達。同時,在民間敘事的現代傳承過程中,口頭與書面、講述者與聽眾、集體與個人、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之間的關系在動態發展中呈現出相互交融的態勢。那么,媒介與人究竟是怎樣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如何看待它與民間敘事的現代傳承之間的互動?民間文化傳統如何通過媒介進入公眾的視野?又是如何實現文化的多樣化表達?這些都是擺在學者面前的課題。
20世紀中后期,學者們圍繞著“在口頭傳統與書寫傳統之間是否橫亙著人類認知與現代心智的‘大分野’的問題”*巴莫曲布嫫:《口頭傳統·書寫文化·電子媒介——兼談文化多樣性討論中的民俗學視界》,《廣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展開辯論。“書寫論”的倡導者埃瑞克·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沃爾特·翁(Walter J.Ong)對口頭傳統與書寫傳統之間存在“大分野”持肯定態度。沃爾特·翁在《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一書中概括出口頭傳統與口語文化的九大特征,認為書寫傳統的出現對人類的思維方式、語言習慣的轉換產生了重大影響,并指出書寫轉換了傳統的表達方式。與之相對,持“連續論”的學者則認為將口承與書寫割裂開來的二分法存在嚴重的漏洞,這種二元對立的觀點與具體的文化傳播語境相抵牾,并指出口承與書寫之間的關系并非對立而是呈連續、共生和互動的狀態。反觀“書寫論”與“連續論”的分歧,我們可以發現前者的立論依據在于將希臘字母的使用作為人類文化和思維方式進步的普遍原因,這顯然站不住腳。學者們對口承與書寫之間關系的不同看法反映出媒介與人類文化表達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以及媒介自身具有的復雜性和多面性。同時,隨著影視媒介、電子媒介的產生和普及,媒介變得日趨多元。那么,媒介的變遷究竟與人類的文化表達和認知方式之間保有怎樣的聯系,文化傳統又是如何在媒介中得以多樣化地表達,這些問題為學者進一步的探究預留了空間。
在大眾媒介與人類創造、傳播藝術作品的過程之間是否存在良性互動的問題上,法蘭克福學派持消極態度。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論將民間文化放在現代性的語境下討論,聚焦于批判以大眾媒介(電視、廣播、電影等)為主體的文化工業對社會的總體性控制,反思媒介的日益擴張對人的主體性進行侵蝕的現象。因此,他們對大眾媒介與文化傳播之間的關系持消極態度,認為整齊劃一的批量生產模式不僅會使人類的思維模式走向扁平化,也會使作品喪失“光韻”[注]德國學者瓦爾特·本雅明(W.Benjamin)使用的術語,參見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王才勇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現代性改變了民俗學原有的發展軌跡,一方面,技術沖擊了人們已有的社會生活,民俗學成為學者們心中一片岌岌可危又富有浪漫情愫的理想之地,成為現代性的他者;另一方面,在這一“他者”的鏡像中,民俗學得以認識自身的特殊性,從而催生了民俗學學科的誕生。在“向下看”和“向后看”的民間文學觀看來,技術與民間文化陷入了二元對立的狀態,民間文化被視為傳統、原始、封閉而又純凈的象征,而大眾媒介作為技術進步的產物自然被視作破壞民間文化的力量。
但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民俗學的專業認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出現了新的研究取向。圖賓根學派聚焦在社會、文化和歷史三者重合閾限內的日常生活,當赫爾曼·鮑辛格(Hermann Bausinger)這一代民俗學者將本學科的對象定位于普通人日常生活時,他們發覺自己必須告別本學科舊有的名稱“民俗學”(Volkskunde),將眼光轉向當下。在《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一書中,鮑辛格表明民俗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活的文化,現代技術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并大大拓展了民間文化的生存空間。在鮑辛格眼中,民間文化與大眾文化、民間傳承與大眾傳播之間并非涇渭分明,傳統也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繼承與創新的過程中不斷碰撞,煥發出新的光彩。可見,鮑辛格是以動態的民俗學觀來看待技術與民間文化的互動,以當下為時間節點,既能夠追溯傳統,又可以預期未來。
以動態的民俗學觀為前提,電子媒介中的民間文學走進了學者們的視線。戶曉輝在《民間文學的自由敘事》中,以網絡民間文學為例,討論了在電子媒介中民間文學全新的傳承形態,指出網絡不僅沒有使民間文學走向消亡,反而增強了民間文學的生命力,具備新形態的民間敘事同樣在體現人的實踐理性和自由意志。無論是鮑辛格還是后來的學者,對新媒介的使用所持的態度日趨客觀,既認為技術的進步和民間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又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特別是在電子媒介中,民間敘事的表達形式不但沒有走向貧乏,反而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豐富。
學者們的不同觀點反映了媒介與人、媒介與民間敘事的傳承之間關系的復雜性。在當代技術不斷進步的時代浪潮下,媒介變遷與人類自身發揮的能動作用,究竟是讓民間敘事形態走入了快節奏、單一化、模式化的“死胡同”還是促進了多樣化表達的形成?這一問題還需要放入具體的語境中去考察。本文以木蘭傳說為例,探討多元媒介下民間敘事的現代傳承中出現的問題。文章選取木蘭傳說作為討論的核心內容,基于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木蘭傳說的傳播過程具有代表性,國家、社會和個人的意志在其中均得以體現,并且這三個層面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另一方面,木蘭傳說傳播的媒介豐富多樣,其中媒介的變遷過程具有連貫性,并且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木蘭傳說文本眾多,民間口頭文本、書面文本、影視劇作品、網絡段子、電子游戲中均有涉及,本文以《木蘭詩》的經典化過程、迪士尼電影《Mulan》的成功上映和游戲《花木蘭》的制作為核心事件展開論述。
一、 書面文本經典化對民間敘事的反哺
在木蘭傳說的書面文本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民間敘事長詩《木蘭詩》,其中完整地記載了木蘭代父從軍、凱旋歸來不受賞、重新回歸家族的歷程。它為之后人們了解木蘭傳說,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復述、改編和再創作提供了范本。《木蘭詩》作為民歌,在被正式搜集、整理進入書面傳統之前必然經歷了長期口耳相傳的播散過程。而《木蘭詩》由口頭傳統進入書面傳統,直至之后被收入義務教育七年級的語文教材,對木蘭傳說的現代傳承產生了巨大影響。
書面傳統中的《木蘭詩》語言質樸而凝練,富有美感。通過將口承文本整理、記錄下來,使木蘭傳說超越了在言語媒介下具有的時效性和極強的變異性,傳說的主干情節和行文邏輯也得以固定,即:(1)描繪木蘭的閨中生活;(2)說明木蘭女扮男裝從軍的緣由;(3)木蘭投軍的過程;(4)木蘭的從軍經歷;(5)軍隊得勝歸來后,木蘭不慕名利,回到故鄉;(6)回鄉團聚,恢復女兒身。傳說的核心——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在書面文本中得以凸顯,木蘭這位集忠、孝、勇、義于一身的女英雄也被刻畫得栩栩如生,成為備受民眾喜愛的傳說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還留有許多空白,比如缺乏對木蘭的外貌、木蘭出征前的心理活動、木蘭的婚姻狀況等方面的描寫,空白地帶的存在表現了文本雖然進入了書面傳統,但仍然具有口語性。麥克盧漢(M. McLuhan)按照人的參與度和信息傳達的清晰度將媒介分為“冷”媒介和“熱”媒介,其中言語“是一種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因為它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憐,大量的信息還得由聽話人自己去填補”[注][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51頁。,人在其中的參與程度高,接受者自身完善的信息多;而印刷則是熱媒介,提供的信息不僅清晰度高,且相對完整。在現實語境中,口承與書面的界線并非十分清晰,其間存在交融互動的情況,正如《木蘭詩》原為北朝民歌,即使經過了整理,文本中依舊保有許多空白的信息,這為其日后生發出多種形態的敘事奠定了基礎。
《木蘭詩》由口承歌謠進入書面傳統,使文本跨越了時間設下的界限,與人成功“會面”。“口頭文本是活的,其核心形態是聲音,對聲音進行‘文本化’后的文字文檔,不過是通過這樣那樣的方式對聲音文本的固化。然而,恰恰是這種對口傳形態的禁錮和定型,又在另外一個層面上擴大了聲音文本的傳播范圍,使其超越時空,并得以永久保存。”[注]朝戈金:《“回到聲音”的口頭詩學:以口傳史詩的文本研究為起點》,《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木蘭詩》的文本化為其經典化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同時,國家力量的介入對《木蘭詩》作為經典文本為人們所傳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木蘭詩》與《孔雀東南飛》一道被譽為“樂府雙璧”,雙雙入選人教版中學語文教材,走入了中學語文教育的課堂。《木蘭詩》入選中學語文教材,代表了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對木蘭這樣一位傳說中的女英雄的認可,她具有的品質與國家和民族所接受和倡導的價值觀相契合,“木蘭”也成為一個符號,成為“巾幗不讓須眉”的代表人物。
《木蘭詩》進入書面傳統的經典化過程不僅沒有讓木蘭傳說陷入只見此文、不見其他的境地,反而讓它在傳說的現代傳承過程中發揮了強大的反哺功能。最直接的功能在于通過書面對木蘭傳說的留存,讓更多潛在的受眾知曉木蘭傳說,無形中擴大了木蘭傳說的傳播范圍,促成了傳說傳承機制的完善,增強了傳說的存續力。民間敘事經典化的過程伴隨著人對文本的篩選,《木蘭詩》能夠在眾多流傳下來的傳說文本中脫穎而出,除了因為它是木蘭傳說早期的書面文本,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之外,還在于詩歌本身具有朗朗上口、便于記誦和講述的特征。相較于口承,書寫更便于實現傳播內容的統一,《木蘭詩》的經典化可以迅速讓所有使用人教版語文教材的少年加入了解、記誦和傳承木蘭傳說的陣營,加快了傳說的擴散速度,讓人們清晰地了解木蘭傳說的基干情節。同時,受眾的數目大量增多意味著潛在的講述者的數量也在增加,使實際達到的傳播范圍超出了課堂。在這一過程中,口頭與書面兩種媒介在不斷地發生交融,且不存在一方替代另一方的關系。如此循環往復,《木蘭詩》的傳承不僅沒有在時間的維度上出現斷層,從空間的角度看,也沒有出現萎縮,經典化對木蘭傳說的現代傳承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木蘭詩》的經典化在更深層次上的功能是刺激了傳說的多樣化表達。誠然,經典化的過程具有“排他性”,即人們認定其中一個文本為經典的版本,而其他的文本就可能被排除在外。但即使國家層面認定了《木蘭詩》為經典,也不可能真正將木蘭傳說束縛在《木蘭詩》這一片小天地中,因為民間敘事無論是通過口承還是通過書面實現傳承過程,都不能忽略人的主體性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要讓每一位受眾都認定《木蘭詩》為木蘭傳說中的經典之作并背誦下來加以傳承,這是不現實的,而但凡有不同于《木蘭詩》的表達出現,就意味著《木蘭詩》的經典化與木蘭傳說的多樣化表達之間并非簡單的對立關系。歸根結底,傳說的多樣化表達根植于人之根本訴求的多樣性上,而人對于多樣化表達的追求,蘊藏于人自身之中。《木蘭詩》的經典化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都對木蘭傳說的現代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詩歌為更多的講述者提供了底本,對實現傳說的多樣化表達提供了現實條件。當受眾接收到《木蘭詩》的文字文本后,不會止步于機械地背誦和復述詩歌的內容,而是會加入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來對它賦予全新的解讀后,再進行傳播。比如電子媒介中出現了以《木蘭詩》中的句子為底本的網絡段子:“女生開始長胸后,擁有傲人的胸部就等于擁有了一筆可觀的財富,這就是古人說的:長胸如富。神回復:所以花木蘭是古今第一女屌絲,有詩為證,木蘭無長胸。”[注]文本發表于2017年10月11日,筆者于2018年8月10日下載。網址為: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80954104957791930&wfr=spider&for=pc網絡段子手作為通過電子媒介表達自我的講述者,以戲謔、調侃的口吻對《木蘭詩》中的語句進行了再創造,生發出了新的文本形態。
《木蘭詩》經歷了先文本化后經典化的過程,在媒介由口承轉向書面時,木蘭傳說發生了三個明顯的變化。首先,傳說在傳播中使用的語言發生了變化。口承中的傳說文本“是一系列聲音符號串”[注]朝戈金:《“回到聲音”的口頭詩學:以口傳史詩的文本研究為起點》,《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轉瞬即逝且不可重復,僅限于即時交流的群體內部才能捕捉到信息。通過書面文字將傳說整理和固定后,便有了具象的、固定的符號串,口承中個人當下的言語通過書面文字轉換為可以跨越時空限制的語言。其次,在木蘭傳說的口承時期,傳說的“經典版本”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同一位講述者面對同樣的聽眾講同一個傳說,也會根據當時自身的狀態對傳說的細節有所調整,每一次講述都是獨一無二的,更沒有哪一版更為經典的分別。但當傳說進入書面后,就有了固定的文本可供人們比對和品評,文本自身具有獨立性,《木蘭詩》的經典化也是在此基礎上才得以完成。最后,在文本的創作過程中,人的參與方式發生了變化。在口承中,人的講述過程即是對文本的再創作,聽眾與講述者之間可以即時互動,兩者之間的身份也可以隨時發生轉換。相較之下,面對書面文本的讀者是單向地接受書面文本傳達的信息,無法直接介入傳說的講述,文本的講述過程與再創作的過程相分離。總之,木蘭傳說進入書面,特別是《木蘭詩》的經典化,使傳說的核心情節得以固定,在迪斯尼將傳說改編為動畫電影時,也保留了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情節,并在此基礎上對傳說賦予了全新的內涵。
二、現代媒介與民間敘事傳統的碰撞
木蘭傳說的書面化,促使傳說中倡導的價值觀由地方認同進入國家認同的層面,而影視媒介的加盟,則讓木蘭傳說走出了國門,在文化的交融與互動中尋求國際認同。迪斯尼公司于1998年推出他們根據中國民間敘事長詩《木蘭詩》打造的動畫電影《木蘭》(Mulan),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主人公花木蘭更是和影星成龍、香港首位奧運金牌獲得者關穎珊等全球著名的華人一起,登上了美國、亞洲雜志的年度亞裔風云人物榜,且位居榜首。在電影《木蘭》大獲成功的時候,“迷茫的中國創作者還在苦苦探尋中國動畫的出路”[注]陳建憲:《民俗文化與創意產業》,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5頁。,電影和其中的花木蘭形象也引起了觀眾的熱議。在中國流傳已久的民間傳說,為何經過迪斯尼的重塑之后便大放異彩?《木蘭》究竟是在講“中國故事”還是在講“美國故事”?這些問題需要學者認真思考。
《木蘭》大獲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電影呈現出了精美的藝術效果,展現了中國文化獨特的韻味。影視媒介在麥克盧漢的分類體系中同樣屬于“熱”媒介,但與書寫相比,影視傳播信息的清晰度更高,對觀眾參與度的要求更低,除了付諸視覺外,還可以調動聽覺來完成傳播過程。《木蘭》的制作者將小橋流水、大紅燈籠、書法等視覺符號融入其中,同時將中國民間小調加入電影配樂,為影片賦予了濃郁的中式味道,通過視聽結合的立體式表達抓住了觀眾的胃口。同時,影視媒介需要體現影片的形式和功能是統一體的感覺,敘事具有很強的序列性。[注][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第40頁。電影《木蘭》與《木蘭詩》相比,情節更為連貫,增添了許多細節,比如在電影的開頭,通過木蘭失敗的相親經歷對木蘭機智活潑、率性灑脫的性格進行了生動刻畫,為木蘭從軍后表現出不輸男兒的勇氣和智謀奠定了基礎。
除了藝術效果的高水平呈現,電影《木蘭》能夠受到現代觀眾喜愛的根本原因是“其創作者在動畫改編的過程中對故事主題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現代性的重構”[注]陳建憲:《民俗文化與創意產業》,第46頁。。中國的《木蘭詩》意在傳達忠孝兩全的價值取向,其中的木蘭形象也十分符合中國封建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木蘭為國出征是對君主的忠誠,代父參軍是對父親的孝順,立功后婉拒功名是淡泊名利的氣節,回歸女兒身是儒家思想對婦女的要求”[注]陳建憲:《民俗文化與創意產業》,第46頁。,似乎木蘭的宿命理應如此。而電影制作者則打破了傳統的桎梏,將木蘭塑造成了一個性格豐滿,不懼他人眼光,堅守本心的女性形象,影片的主題也定位于個體的自我審視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全新價值觀的注入在讓木蘭傳說煥發出生機的同時,也引發了爭議。李婉在文章《穿著比基尼的“花木蘭”》中直言電影《木蘭》“僅僅是借助于中國的符號而編織出來的美國童話”[注]李婉:《穿比基尼的“花木蘭”——從敘事學角度看迪斯尼影片〈木蘭〉》對中國〈木蘭詩〉》的改編》,《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8期。。陳韜文則在《文化轉換:中國花木蘭傳說的迪斯尼化與全球化》一文中指出:“Mulan既不是純中國的文化,也不是純美國的文化,它已經成為了一個跨文化的文本”。[注]《傳播學論文選粹》編委會編:《傳播學論文選粹》,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3頁。學者面對他者對中國民間文化傳統的表達,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而爭論的焦點在于電影《木蘭》是否正確地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的價值觀。
電影媒介迅速而直接地將木蘭傳說由中國拉入了“環球村”(Global Village)[注]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M.Mcluhan)使用的術語,參見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木蘭》的全球化傳播迅速引發了國人對自身傳統的關注。從空間的角度看,“人們在生活世界中總是試圖維護引起認同的視域:‘全球化’這個口號表達的意思以及毫不留情地闖入所有人日常生活的東西,常常導致家鄉和家鄉文化的升值。”[注][德]赫爾曼·鮑辛格:《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第11頁。學者認為《木蘭》具有跨文化的特點,是基于他們認定電影中所傳達的觀念與中國的木蘭傳說表達的價值取向不同,中國人認同的木蘭形象也不是電影中出現的那位“花木蘭”。從時間的角度看,《木蘭詩》創作的年代在先,電影《木蘭》在后,人們往往會以前者作為傳統的標準,并以此來衡量電影在制作過程中對原有文本做出的改動是否合理。由此可見,學者界定《木蘭》是否表達了傳統的標準在兩個維度上展開:在空間的維度上具有地方性,在時間的維度上具有延續性。
當地方性遭遇全球化、時間在先的文本遭遇時間在后的文本時,問題自然就落在了傳統與現代性的爭論上。兩者之間的悖論關系從民間文學作為獨立學科的誕生之初便已然存在,現代性只有擺脫傳統的藩籬,傳統才能不斷地求新求變,保持與歷史和社會的發展步調一致;但現代性又需要將傳統確立為自身的來源和出處,并且在與傳統的比較中認識自身。[注]戶曉輝:《現代性與民間文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正是基于現代性與傳統之間的內在關聯,一方面,電影中所呈現的木蘭傳說被學者們描述為被現代技術拆解得面目全非的東西;另一方面,《木蘭詩》里體現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又被罩上了遠離世界現代文明且具有獨特性的純潔光環。但若將民間敘事放進時間軸去考察,民間敘事文本之所以能夠打破空間和時間的阻隔,除了依靠民間文學自身的發生、發展外,還有賴于人對民間敘事的傳承和重述,不斷地調和現代性與傳統之間的沖突。“在民間文化的早期階段,傳統并非通過漫長的流傳時間跨度才保持著強制力,不如說反過來,通過一再被重新傳承的東西的強制力才出現了漫長的流傳過程。”[注][德]赫爾曼·鮑辛格:《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第142頁。每一次媒介的變遷都會為木蘭傳說帶來新的表達方式,除了傳說的情節之外,也需要注入當下民眾提倡的價值觀,傳說只有與社會生活真正發生了聯結,才能夠成為“活水”,而不是一具干癟的軀殼。因此,敘事傳統不是僵死的,而是立體的、多棱的,是包含了民間敘事多樣化表達的有機體。
“當傳統真的是規定生活的力量時,它就能夠允許用最新穎的成分來增加自己的活動余地。”[注][德]赫爾曼·鮑辛格:《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第171頁。若從“規定生活的力量”再去審視電影媒介與人的關系,電影《木蘭》無疑喚起了當下人們對個體價值的關注。新技術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使人步入了信息爆炸、物質資料極為豐富和生活節奏迅速加快的生活模式中,當此之時,電影《木蘭》和其中女主人公“花木蘭”傳達的價值取向對每一位深陷精神泥沼中的人發出了信號,提示人們進行自我審視和自我啟蒙。片中木蘭在身份被識破后說出的那一句話:“也許我并不是為了我爹,我這么做,也許我只想證明自己的能力,這樣每當我看見鏡子,就會覺得對得起自己”,是每一個尋求自我價值的人內心的寫照。值得學者深思的是,電影《木蘭》所傳達的價值觀的確受西方現代思想的影響,《木蘭詩》中的木蘭傳說著重強調的主題也并非是實現個體價值,但傳統是多棱的、立體的。在中國民間敘事傳統中,木蘭不僅可以出落成一位不思功名的孝賢女,也可以成長為一名追尋自身理想的勇士。在徐渭的作品《雌木蘭替父從軍》中,木蘭從軍后說道:“兀的不你我一般,趁著青年,靠著蒼天,不憚艱難,不愛金錢,倒有個閣上凌煙。”[注](明)徐渭:《四聲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8頁。這一番話表明了木蘭心中的志向和抱負,也讓一個肯定自我、高揚個性的少女形象躍然紙上。長久以來,《木蘭詩》中刻畫的木蘭形象為國家所倡導,而民間敘事極具包容性,《木蘭詩》的經典化并不意味著其他敘事形態的消失。當社會環境和人類心理狀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敘事傳統的另一面便會顯現出來。電影《木蘭》以新的表現形式和敘事方式促成了民間敘事傳統與現代社會的對接,也激活了潛藏在敘事傳統中多元的因子,電影傳達出的價值取向與敘事傳統中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部分相呼應,傳統與現代通過電影媒介實現了超越時空的對話。電影媒介為木蘭傳說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同時,人也在通過新的媒介形式尋求對自身更為深刻的表達方式。
電影媒介中的木蘭傳說保留了《木蘭詩》中的核心情節——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但其中的細節處理得更為靈活。電影通過對人視覺和聽覺的延伸填補了許多《木蘭詩》中的空白之處,比如在電影的開篇,生動、詳細地交代了木蘭決定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心理活動。同時,電影也對《木蘭詩》中的情節進行了一些刪減。例如在《木蘭詩》中木蘭家中還有其他兄弟姐妹,而在電影中,木蘭是作為獨生女出現的,這樣的處理使木蘭與父親之間的互動真摯感人,木蘭代父從軍的行為也顯得合乎情理。相較于書面,木蘭傳說在電影媒介中的內容表達更為連貫,傳播速度更快,范圍更廣,電影對傳說的呈現也更為直觀。不過隨之而來的是,電影媒介的介入也將敘事過程中人的參與度大大降低。
麥克盧漢認為,在地球已經成為“環球村”的背景下,“任何發明或技術都是人體的延伸或自我截除”[注][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第78頁。,人利用技術可以達到人的感官所不能及之處,但技術也會反過來束縛人的感知能力。如果將木蘭傳說在電影媒介中的傳播視為一個獨立的過程,電影媒介的確限制了民間敘事傳播過程中人之主體性的發揮。但正如口承和書面會不斷進行互動一樣,電影媒介的加入使原有的傳播系統更加豐富,電影媒介與書面和口承之間的界限并非涇渭分明,而是呈現出相互交融的狀態,民間敘事最終還是會在人的交流過程中獲得新生。在傳統與現代媒介的碰撞中,多元的媒介共同促成了民間敘事傳統的多樣化表達,至此,媒介自身的多棱性和復雜性已經可見一斑,而在之后興起的電子媒介中,各種媒介的包容與互動使木蘭傳說的表達再度生發出了新的形態。
三、多重媒介的交融與個體表達的回歸
電子媒介的廣泛使用為木蘭傳說的現代傳承增添了一抹亮色。它巨大的包容性不僅為媒介帶來了變革,使多重媒介在同一個文化空間中的并存得以實現,同時也揚棄了口承民間敘事中民與官、口頭性與書面性、講述者與聽眾、集體性與書面和各種體裁形式之間的外在對立,打破了書面和電影文本中潛在的“‘創作高臺’和傳播壁壘”[注]方彧:《民間文學現代傳播新形態初議》,《民族文學研究》2009年第2期。,使網民們的感官在新穎的媒介形式中得到更大程度的延伸。
2005年斯普公司以木蘭傳說為題材發行了一款動作角色扮演游戲(Action Role Playing Game,簡稱APRG)《花木蘭》,以《木蘭詩》奠定的基調展開敘事,花木蘭為游戲主角,講述女主人公代父從軍,建功立業,班師回朝的故事。APRG的特點在于玩家在游戲中的角色扮演,即在游戲的過程中,玩家需要將自己全情投入角色之中,達到“我就是木蘭”的效果。《花木蘭》的結局也不是唯一的,游戲會根據玩家在游戲過程中的表現,使玩家走向不同的結局。游戲本身的設計極具個人化,在玩家參與游戲的同時,還可以通過網絡評論和回復已有評論的方式來交流感想。
以下是在電驢大全中游戲的下載頁面下游戲玩家們的部分評論和交流:
swq713swq:木蘭的頭像看著很不舒服啊(2011年7月6日)(6人點贊)
ChanSeven:做得不美感一點啊。。倒(2011年7月29日)(1人點贊)
Shikui1234:不錯!支持下!(2011年8月11日)
Wugs132:畫面明明挺好的,非要把花木蘭的頭像畫得那么挫,是不是腦子壞掉了啊,頭像畫那么難看誰還愿意玩啊。玩一個游戲至少豬腳頭像要看著養眼才愿意玩吧。(2012年1月10日)
龍海莊莊主:看起來不錯呢。(2014年3月21日)[注]以上評論參見電驢大全,下載時間為2018年8月10日,網址為:http://www.verycd.com/entries/634/comments/
Liubo0405:這花木蘭太妖艷了。有點像妲己。(88個人選擇支持,6個人選擇反對)
Wqyj8482:還沒下,不知道有沒有源,話說這木蘭長的真有點慘不忍睹,好歹也是巾幗英雄又是主角,這下真成豬腳了,趕著最近花木蘭劇組到處為這個電影造勢做宣傳,這游戲發的很有審時度勢的感覺啊(2009年12月5日)[注]以上兩條評論參見電驢大全,下載時間為2018年8月10日,網址為:http://www.verycd.com/topics/2785087/
玩家們在評論區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游戲體驗,就游戲中木蘭的形象設計而言,玩家就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木蘭”在玩家心中已經成為一個符號,其中凝聚著玩家對這位巾幗英雄的喜愛和尊敬,但從電驢大全網站評論區的240條留言來看,認為游戲中的木蘭形象不符合心中期待的玩家占絕大多數。游戲中的木蘭形象收獲如此的評價與電子媒介中玩家與角色的心理距離有很大關系,在APRG中更需要玩家與游戲中的主角“合二為一”,因此,當玩家認為游戲中的角色無法讓自己的情感全部投射在主角身上時,便會對游戲產生失望的感覺。而喜愛這款游戲的玩家會在游戲過程中將自己代入到該角色當中,激發對木蘭這一角色的認同,并且通過自己的切身體驗去感受木蘭傳說的溫度。雖然麥克盧漢沒有操作電子游戲的體驗,但他將游戲作為一種媒介,稱其為“心靈生活的戲劇模式”[注][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周憲、許鈞主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第293頁。的解讀是貼切的。
如此看來,電子媒介與口承雖然有一定區別,但也具有相似性和同一性。兩者的區別在于,口承建立在現實的人際關系網中,人與人互動時還可以通過雙方的肢體動作和面部表情來實現情感的傳達,但溝通的過程具有即時性,人對民間敘事的復述和創編過程與言語行為同步,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嚴格限制。而在電子游戲中,隨著玩家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一起被隱去的還有交流雙方鮮活的表情和動作,“網民”的身份讓玩家單純地根據網絡評論的內容來表達自己的感想。同時,電子媒介中木蘭傳說的特殊之處在于,它不僅實現了人與媒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且超越了時空的限制。生活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的玩家以游戲為紐帶形成了一個網絡團體,表達自身的體驗。針對其中電子游戲而言,它可以使玩家達到比口承更為強烈的代入感,使玩家通過操作完成對帶有游戲規則的敘事過程,并且可以在評論版面中隨時留言。以前文引述的玩家評論為例,從2009年12月5日至2014年3月21日的留言都有,并在游戲規則之外進行自由發揮,生發出新的敘事情節。
但若將口承和電子媒介放入人類社會媒介變遷與民間敘事的互動之中來考量,兩者的相似性和同一性便顯現出來。媒介既是人的交流方式,也是民間敘事的表達方式。口承和電子媒介實現了人與人的直接對話和情感交流。正如周福巖所指出,民間傳承這種以言語為媒介的傳播方式更具“人格性”[注]周福巖:《民間傳承與大眾傳播》,《民俗研究》1998年第3期。,而在大眾傳播中,“媒介組織‘隔斷了’信息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人際聯系,同時也取消了兩者人格參照和判斷的可能性”[注]周福巖:《民間傳承與大眾傳播》,《民俗研究》1998年第3期。,后果是受眾的道德、審美等判斷力的退化。在單純的書面和電影媒介中,人與人的直接交流與信息傳播的過程不同步,會帶有“非人格性”的特點。可一旦電子媒介加入了民間敘事的傳播過程,網民的交流不僅具有“人格性”,相較于口承,實現交流的群體規模更大。例如觀眾在愛奇藝網站點擊播放電影《Mulan》時,隨著電影一起出現在觀眾面前的,還有其他觀眾打出的彈幕——“外國人畫下的中華”、“《木蘭詩》”[注]參見愛奇藝網站,下載時間為2018年8月10日,網址為:http://www.iqiyi.com/v-19rrifmf77.html等等,有趣的是,當有觀眾打出《木蘭詩》的第一句“唧唧復唧唧”時,屏幕上彈出了其他觀眾接上的下文來表示對《木蘭詩》的喜愛和認同,以電影為紐帶,在電子媒介中同一個觀看電影的小團體內實現了即時交流。電子媒介中的觀眾具有雙重身份,在接收電影媒介傳達的消息時,也可以發揮網民的身份,對他人的觀點表明自己的態度。在電子游戲中,游戲玩家親身參與敘事過程,進入評論板塊之后,玩家交流的不再是文本的內容,而是自身參與游戲的體驗。玩家們即使面對同樣的評論,也會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人格性”在電子媒介中得到了延伸。
口承中講述者對自身的言語行為負有責任,同樣,電子媒介使人的交流回歸到了個體的表達當中,民間敘事行為的發生需要具備公共倫理條件。在網絡公共空間中,網民的道德和審美的判斷力不僅不會呈退化狀態,反而會保持敏銳。在游戲《花木蘭》的評論板塊,有三條評論,內容如下:
新褲子-:雞雞復唧唧 木蘭襠褲濕……(2009年12月4日)(171人選擇支持,49人選擇反對)
csz614: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胸”(2009年12月5日)
非如此不可:我不是什么文人雅士,但看到以上2位的留言,我的悲哀(93人表示支持,5人表示反對)[注]以上兩條評論參見電驢大全,下載時間為2018年8月10日,網址為:http://www.verycd.com/topics/2785087/
道德和審美的判斷力是每一個作為實踐主體的人都具有的能力,并且不會隨著媒介的變遷而消失,網友在發起言語行為時,就意味著具有接受網絡空間內其他網友品評的義務,同時也擔負著監督其他網友言論的權力。以三位網友的留言為例,“非如此不可”看到兩位網友對《木蘭詩》進行戲謔和調侃,便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直言他不認同另外兩位網友的言論。在評論中,其他網友也對幾位評論人的留言保有不同姿態,例如支持“非如此不可”的網友不會因為支持“新褲子-”的網友數量更多而放棄自己的立場。人不僅會受到媒介的影響,其自身具有的主體性也得以彰顯。
電子媒介中的木蘭傳說文本相較于書面和電影媒介中的文本更為雜多,表現力也更強。游戲媒介讓人的多重感官在其中得到了極大的延伸,讓玩家在講傳說的同時有了身臨其境的體驗。網絡文本的篇幅可長可短,內容不一,反映的主題也不受限,個人化的表達更為凸顯,口承文本進入書面時,文字由言語轉化為語言,而在進入網絡空間時又回歸為言語。網絡中的木蘭傳說看似毫無拘束,但與口承文本相同,文本在講述者的責任與聽眾的義務中得以規訓。這其中包含了游戲的設計者有設計規則的權力,玩家有遵守游戲規則的義務,而評論者有發表言論的權力,也承擔著監督與被監督的義務。因此,木蘭傳說在多元媒介中實現了自身的多樣化表達,極大地拓展了傳說的生存空間,而且在走向現代的同時勾連著深厚的敘事傳統,在看似紛繁的表達中蘊含著內在的規則。
四、結論
總之,學者對媒介的關注和討論也是建立在現代技術與民間敘事已經發生緊密聯系的前提下,現代性問題伴隨著民間敘事發展過程的始終。現代技術已經讓人類社會駛向了高速運行的軌道,媒介的變遷極大地加速了民間敘事現代傳承的進程,促進了民間文化的多樣化表達。其中,無論是對媒介本身還是對媒介與民間敘事之間的關系,學者都應該以動態的眼光去考察。首先,媒介是一個動態的研究對象,[注]參見崔寶國的文章《媒介變革論》,收錄于《傳播學論文選粹》編委會編《傳播學論文選粹》,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33頁。新型媒介的出現不代表先前存在的媒介就必然會走向消亡,相反,它可能會與先前已有的媒介形式發生互動,共同形成一個有機的系統,促成民間敘事的現代傳承。
新型媒介的出現不代表民間敘事走進經典化、單一化、平面化的死胡同,也不意味著傳統本身會不復存在。媒介變遷與民間敘事之間是互動的關系,一方面,媒介的日益豐富為民間敘事的產生和傳播創造了條件,為敘事形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敘事體裁的變化和豐富也得益于媒介的變遷。[注]孫正國:《媒介形態與故事建構》,上海大學2001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5頁。技術使民間敘事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展現在人們面前,借助于多重媒介的力量,激發了人們對民間文化更為真切的感受,使傳播的過程更富有想象的溫度。同時,新的表達形式含有傳統的因素,引導人們去關注、去回溯傳統。通過技術,可以讓人們認識到傳統本身就具有多樣性、立體性的特質。
在媒介與民間敘事的互動關系中,人的主體性發揮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民俗學范疇要尋找的首要問題,不是文化財富的社會基礎或母題史的關聯,而是特定的文化財富在特定的社會基礎上生成出來的精神互動的特殊形式。”[注][德] 赫爾曼·鮑辛格:《技術世界中的民間文化》,第20頁。媒介是人的交流方式,作為實踐主體的“民”,其道德和審美的判斷力規訓著媒介變遷與民間敘事現代傳承的內在走向。周福巖在《民間傳承與大眾傳播》中表示,“民俗(民間文化)與其傳播方式(民間傳承)存在本質的聯系”[注]周福巖:《民間傳承與大眾傳播》,《民俗研究》1998年第3期。,同時“民俗的這種在日常生活中展開的傳承方式本身對民俗的意義必有特殊的規定性”[注]周福巖:《民間傳承與大眾傳播》,《民俗研究》1998年第3期。,因而要準確傳達民間文化的意義,還需要選擇相應的媒介。誠然,民間傳承即口承的方式是民間敘事歷史最為悠久的傳承方式,即使有了其他媒介的加盟,依舊不能撼動口承的基礎性地位。但歸根到底,媒介溝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民間敘事的創編、傳承方式代表著人在當下表達自我的方式。每一次媒介的變遷與民間敘事的全新表達,都是深廣的社會意蘊和人之心理狀態極大動蕩的外顯,民間敘事也正是在這樣的更迭中得以煥發出無窮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