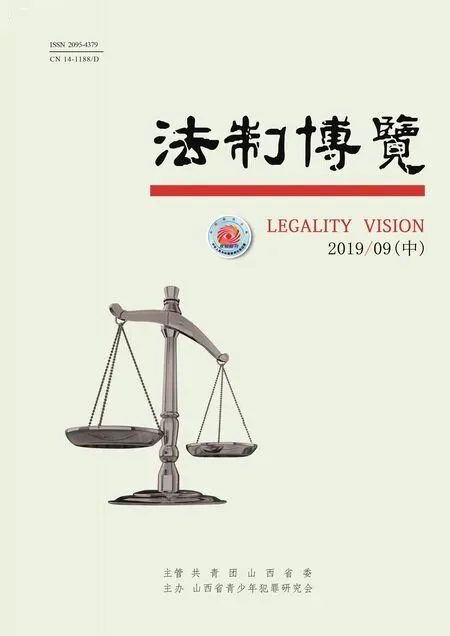理性人標準在知識產權法中的規范性適用
付亞超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北京 100088
從傳統法律的分析角度,似乎商標法與受理專利法的技術人員符合理性人標準,并且在知識產權法和學術領域中往往是相同概念。在這種情況下,理性人標準在知識產權法中應該被執行和審查,同時在規范和實踐背景下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一、理性人標準的內涵
(一)廣義上的理性人標準
對于一般的理性人來說,廣義的標準是作為英美侵權法合理人員的法律依據,判斷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一保護自己私權利的標準,會出現不同的情況,這些類似的行為會因個人的理性思維產生不同的效果,再者就是可能也不會產生其他理性人所做的行為。即使說,這個標準的基本特征和定義的水平和角度存在差異,涉及的理性人的范圍正在進一步擴展,目前來說,已被刪除的侵權法就是例子,還包括行政法以及其他方面。就法律層面來講,憲法就是一個合理的理性人的標準,明確地制定了行為規范。但是,實際上的情況總有例外,理性人的標準范圍遠不止法律法規的規定,有的時候會超出合同法律中明確反映的習慣法范圍。因此,與一般的合同法相比,還沒有表達理性人的標準相關的民事文件。
(二)狹義上的理性人標準
從微觀層面分析,理性人在基礎法律上可以用法人來進行詮釋,也就是特定組織團體的活動代表。可以說,這項法律是理性人的關鍵標準之一。從實際生活這個角度來看,存在于法律中的理性人,是進行客觀的定義無法面對自己內心世界,無法理解和控制行為。同時,也不是說這個過程需要與社會進行分離,只注重自己的主流價值觀。當然,由于知識產品有具體和抽象的內容,具有不確定的特征,因此,產權的定義,范圍以及能夠解釋的權利就會受到許多不確定的因素的影響。
二、理性人標準在知識產權法中的司法實踐適用
(一)所屬侵權行為的認定
與其他一般的產品不同,知識產品沒有具體的物象可言,僅具有抽象的基本特征。如果說,僅僅是保護這些外部的知識產品,那么依舊是無法保護所有者的權益和勞動成果。對知識產權有指定的應用標準的話,其使用范圍被界定,就可以有效的避免這些爭議。一般情況下,知識產權的定義中會對相應的侵權進行具體的評估,還包括索賠內容。就現階段而言,中國知識產權侵權的標準已經很規范了,而且識別較為準確。因此,如果僅涵蓋外部知識產品,則絕對不可能體現出作者的所有工作。出于公平,在版權商標法和競爭性專利法等基礎上,我們正在采取開放式方法來確定權益比率。代表相同或類似技術產品的知識產品的使用由專利法管理。法律不能完全概括實際情況,并且無法要求都按照“規則”進行,但是可以明確的是:無論是最好的,還是失敗的知識產權法典都是“標準+型號”或只有“標準”。在知識產品部門引入“標準”意味著立法者不能事先完全確定對知識產權進行限制,只能在會議決定的情況下確定。換句話說,限制知識產權的過程包括確定舉報侵犯知識產權所必需的權力。相關標準包含在知識產權文件或判例法中,以明確規定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就一般情況而言,盜版就是利用與其產品的相似之處進行商業活動,然而這種違規行為的相關處罰標準可能不夠清楚,會令人困惑。在沒有確切的應用標準下,人們常規的認知會對侵權調查造成直接的影響。
(二)理性人標準介入權利闡釋
通常情況下,理性人在分析知識產權標準的時候,特別是在知識產權的許可方面具有極為重要的積極作用。對于產品識別,包括物理和化學方法,同時,在力和美學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差異。由于知識產品具有不確定性和差異性,這就增加了表達創新的難度。然而,作為書面語言的“符號”只是現實的近似表象,表象和現實之間總會存在鴻溝或所謂的“符號空間”。專利權要求的表達與專利申請者的真實意圖之間存在著難以克服的“鴻溝”,在不同的解釋框架或參照框架內,同樣的權利要求被賦予的價值和意義將會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偏差。當通過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等方法仍不能確定權利要求的含義時,究竟以誰的解釋為準至關重要。各種不同的表達組成了知識產權的主要部分。相同的,技術的創新和獨特的表達都有相似的情況發生,比如說,在申請知識產權注冊時,專利的申請人的意圖和該項專利的表達完全不同。對此,專利實踐中也同樣采取了理性人標準,即根據“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的通常理解”進行解釋。理性人不但可以發揮對權利要求內容進行調控的功能,而且也可以調控知識產權許可合同中債權的范圍。當知識產權擁有者授權他人對知識產品進行利用時,被許可人所獲得的債權范圍有時會出現不清晰情形,此時就涉及到對合同的解釋,尤其涉及到被許可人能否獲得許可人的默示授權。所以說,在專利申請的過程中,實施理性人的標準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該方式對知識產權的各個方面進行合理的解釋和保護,這樣可以避免由于模糊解釋以及差異性造成的不必要影響。
(三)界定法律客體的適格問題
可以說,知識產品就是其基本形式中極為重要的核心精神產品,當然,也會受知識產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科學、技術和文化等相關精神領域。這種知識產權具有很高的內在價值,同時還有很高的潛在價值,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實際上僅僅存在物理形式的價值,主要包括相關的表達和形式,如發明,文學創作,藝術創作等。在專利法的實踐中作為一個理智的人對技術解決方案起著重要的作用,以專利性條件:按照中國的“專利法”的規定,指導方針從專利申請開始就由作品的創作人員提交材料,完整地描述本發明的實用性、創新性。在這項事例中可以明顯看出,識別的內容包括獨立的創意和有意義的差異。人們對于這些常規的標準的認知理解有偏差,尤其是對涉及的范圍和差異方面,從而導致保護知識產品的規范要么過高要么過低,都是由不同的標準所決定的。當前的“重要性”應該從公眾的角度來判斷,根據一個法律文件的期限,消費者和該技術的技術人員充分披露了理性人基本的另一種方式。在中國標準的理性人對于傳統版權文章作品的獨創性評估并沒有實際定義,“創意”是這項工作的一個關鍵要素,“獨立”要求具備明確標識的事實證據,“創造”過程中會帶來很多著作的版權保護標準,主觀因素則是為了防止標準過高或過低,版權法必須從理性人的角度清楚地判斷原創性。這項產品沒有具體的物理界限,僅僅是一個簡單且易于識別操作的實施方案,不過卻可以降低管理和檢測的難度,能表現地更加清晰,還能有效的進行交流溝通。
三、結論
在現代社會中,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私權在各國普遍獲得確認和保護,知識產權制度作為劃分知識產品公共屬性與私人屬性界限并調整知識創造、利用和傳播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的工具在各國普遍確立,并隨著科學技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地拓展、豐富和完善。同時,還為各個行業的合法權益進行有效的保護,而且和理性人許多標準有相似的地方,然而,公共形式的標準更為容易,需要提供相協調的方式。最后希望通過本文的研究,對今后的專家學者研究相關的課題有一定的借鑒與幫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