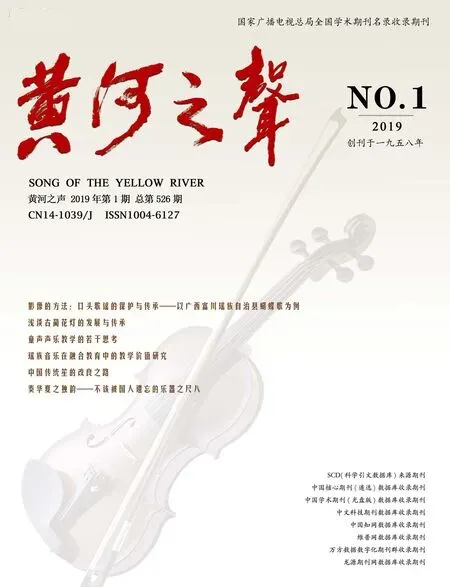論中國古代箏的音樂文化
陳雨嫣
(沈陽音樂學院,遼寧 沈陽 110818)
一、中國古代音樂文化概述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音樂與音樂文化是藝術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文化的定義可謂是多種多樣,陳華文在《文化學概論新編》中通過綜合各種關于文化的論述后給文化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所謂文化,就是人類在存在中為了維護人類有序的生存和持續(xù)的發(fā)展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關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各種關系的有形無形的成果”。在古代,“文化”一詞見于《易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見文化不是一種物質(zhì)現(xiàn)象,而是一種精神現(xiàn)象,而音樂從抽象的角度更具有一種文化的精神。音樂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原始社會音樂就伴隨著人類生產(chǎn)勞動和生活而產(chǎn)生和發(fā)展,在遠古社會中詩樂舞三者緊密結(jié)合,音樂占據(jù)了主導地位。“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①,不難看出音樂起源于人類的思想感情變化。
其次,“音樂文化”的概念目前雖沒有明確的定義,但凡是與音樂有關的范疇都可稱其為音樂文化,它包含了兩個層面內(nèi)容。一是音樂本體文化:通常是與音樂有直接關系的內(nèi)容,如音樂體裁形式、音樂作品、音樂家、樂器及其器樂的發(fā)展、樂律等;二是音樂外延文化:是指與音樂互相聯(lián)系、相互制約的內(nèi)容,例如音樂制度、音樂審美趨向等。
再者,中國音樂文化是歷史上各名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且與人類生存環(huán)境密切相關。從整體上來看,中國的音樂文化具有復雜性、完整性、發(fā)展性。
二、箏的發(fā)展歷程
中國古代的音樂文化可謂是豐富多彩,在先秦的“六代樂舞”中度過了奴隸制社會;在漢魏“樂府”、“相和歌”,隋唐“梨園”、“教坊”和“燕樂”中度過了封建社會由產(chǎn)生到繁榮階段;在宋元的說唱和戲曲,明清“四大聲腔”和京劇中度過了封建社會后期階段。
箏,又稱“古箏”,史稱為“秦箏”,是中國傳統(tǒng)的古老彈撥樂器之一,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究其根源,詳細產(chǎn)生于何時何地,目前尚不能做定論。有關于箏的史料記載,最早見于《史記·李斯列傳·諫逐客書》中:“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可見在戰(zhàn)國時期,箏就在秦地流行了。關于箏的形制,漢晉以前的箏有十二弦,演奏技法比較原始,主要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來撥彈琴弦,左手的滑音或者顫弦非常少;到了唐朝,箏的音域擴大,琴弦增至十三弦,但在演奏技法上仍無很大的變化;直到二十世紀古箏出現(xiàn)了大變革、大發(fā)展,逐漸出現(xiàn)了十八弦、二十一、二十五弦等多種形制,在技法上也有了很大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
中國古箏在發(fā)展中逐漸形成了南北兩大箏派的局面。北派有河南箏派、山東箏派等;南派主要以浙江派與客家派為代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曹正先生率先統(tǒng)一規(guī)范使用了古箏演奏技法中的符號,為古箏音樂的發(fā)展做出了貢獻;趙玉齋先生創(chuàng)作箏曲《慶豐年》,打破了單手彈奏古箏的局面,開辟了雙手演奏箏的新紀元。90年代以來,古箏音樂出現(xiàn)了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世。
三、箏樂的審美文化
(一)箏樂體現(xiàn)了古代的道家思想
白居易在詩中寫道“弦凝指咽聲停處,別有深情一萬重”②,這里的“弦凝”和“指咽”并不同于真的無聲,而是一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境,這與道家“大音希聲”的音樂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音樂雖然停止了,卻產(chǎn)生了比有聲時還要強烈的情感效果。
(二)箏樂體現(xiàn)了包容美
知名作曲家王建民創(chuàng)作的《幻想曲》、《西域隨想》中,不再采用傳統(tǒng)的定弦方式,而是加入了變音,使中原音調(diào)和西域音調(diào)相結(jié)合;在技法上也加入了叩、擊、拍弦等手法。這不僅僅使古箏演奏的表現(xiàn)力和演奏技巧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而且很好地結(jié)合了西方優(yōu)秀音樂的演奏技巧與作曲的技巧。由此可以看出,古箏藝術在傳播和創(chuàng)新發(fā)展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步與變化,體現(xiàn)了其包容美。
(三)箏樂體現(xiàn)了民族美
《高山流水》《蘇武思鄉(xiāng)》等古箏樂曲都是以我國的傳統(tǒng)故事改編而成的著名箏曲,可見箏樂不僅扎根于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而且還融合民族的文化精髓。從記載了西南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文化特色的《黔中吟》中也能看出,箏樂在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過程當中融入了民族特色,體現(xiàn)了民族美。
四、結(jié)語
中華傳統(tǒng)文化始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其中的古代音樂文化更是通過多年的積淀,得到了較為顯著的修改和完善。如今,中國古代音樂文化不僅對當時的文化傳承和發(fā)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還對現(xiàn)當代音樂作品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也就是說,中國古代音樂文化對于現(xiàn)當代音樂的發(fā)展同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理,中國古代音樂中的儒道佛等思想和箏樂中的包容性、民族性的文化特點,都對現(xiàn)代箏曲的創(chuàng)作有著極大的影響。
古箏是我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中的瑰寶,是民族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國人來說,古箏不僅是一件民族樂器,更是代表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民族文化招牌。而面對當今“古箏熱”現(xiàn)象,我們要積極培養(yǎng)文化覺意識,理解古箏中的審美思想。作為箏樂文化的繼承者,要大力弘揚箏樂傳統(tǒng)文化,推動傳統(tǒng)流派和箏曲發(fā)展的同時也要積極創(chuàng)作順應當今時代潮流的新曲目。
注釋:
① 荀子,《禮記·樂記》
② 白居易,《夜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