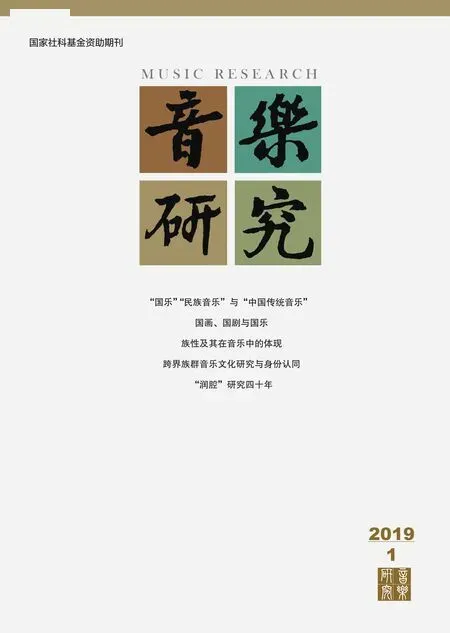傳統的建構與理解
——岷江上游地區的音樂民俗與文化認同研究
文◎楊曦帆
西南高山高原區域在文化上存在著自身的特殊性。岷江上游在地理環境上屬于西南地區,也是費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的重要區域,是歷史民族文化走廊,系漢、藏、羌文化的連接地區。特殊的高原環境和多民族的存在使得該區域文化具有多樣性特點,不同的族群、信仰、變遷、傳統交織著互動與認同的內在心理結構,形成自己的文化特點。本文擬針對這一具有“復雜結構”區域,從建構、理解和文化認同角度進行深入研究。
一、岷江上游地區的區域文化特點
岷江上游地區泛指岷江流域都江堰以上至岷江發源地松潘一帶,以及岷江上游所納支流黑水河、雜谷腦河、草坡河等河流;行政區劃涉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黑水、茂縣、理縣、汶川五縣,生活著藏族、羌族、漢族和回族等民族。明清“改土歸流”以來,漢人逐漸進入該地區生產生活,由于生產的差異,在這一區域基本上是漢族住河壩,少數民族住高山。因居住環境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不同族群的習俗和文化傳統。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在相對狹窄的地域空間,漢、藏、羌等民族之間相互通婚,在血緣、文化上相互交融。宗教信仰主要有藏傳佛教本教、寧瑪、格魯等教派以及原始宗教信仰。土司文化對該區域人們生活也有著較大影響。音樂舞蹈種類中較有特點的包括:多聲部民歌、鎧甲舞(兵舞)、鍋莊(藏)、沙朗(羌)、端公跳羊皮鼓舞等。從它們存在的方式來看,少數民族的“音樂舞蹈”無法和“民俗文化”相隔離,文化不是外在的與附加的,文化就是音樂本身。比如,白馬藏族有“跳曹蓋”傳統,舞者戴面具,隨著巫師“白莫”的鼓聲即興起舞,其意圖在于為村寨“驅邪除害”。從文化認同角度看,這些音樂舞蹈文化不僅是娛樂和情感表達的方式,也是族群身份認同的標志與族群精神氣質的呈現。文化的多樣性也表現出岷江上游地區文化的“復雜結構”,即多民族、多文化、多信仰交融地帶,其文化既有來自古老歷史積淀的“藝術”表達,也有當今多民族文化相融交匯而成的“新文化”。岷江上游地區各族文化既是歷史傳承,也是在不同族群的交往互動中逐漸形成。不同民族的音樂在不同文化的流動與變遷、交流與互動中互相影響并形成自己的風格。不同民族的音樂在其形成過程中都會受到包括歷史、民俗、宗教、社會結構、族群心理、經濟發展等若干因素影響,這些因素也會使音樂的影響力不斷發生變化。
信仰習俗在該區域表現出相當的重要性。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本地區存在著兩種或多種信仰的情況,一些民族雜居區和文化多元地區也表現出信仰的多重性,比如在嘉絨藏族區域,不少人“在家信原始宗教,在外信藏傳佛教”;在白馬藏族生活地區,一些受到漢文化影響的家庭,也設有祖先神位,供奉祖先畫像。另一方面,在受到信仰影響的習俗活動中,由于有宗教/信仰的“教義”所牽制,其習俗變化相對較小,呈現出同一區域內不同民族各自特點的明確性;但如果沒有或者是缺乏宗教/信仰的控制,不同民族之間的習俗活動則互動性較大。比如,“在藏、羌、漢民族為主雜居的理縣,各民族喪葬的葬俗、葬儀是與其各自的宗教信仰密切相聯系。由于各民族間長期相處,相互交往,在習俗上,不可避免的會互為影響。但在喪葬中,至今保留有自己民族的特有習俗。”①理縣民族宗教局編《理縣民風民俗》,開明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頁。當然,也要指出,岷江上游地區的信仰和其他地區,比如和歷史上佛教僧侶勢力更大的藏區相比還有所區別。這里的信仰在歷史上受到諸如“土司制度”等影響沒有形成絕對權威,而是表現出和世俗更為緊密的聯系,在世俗世界中的信仰所產生的儀式化內容,也影響著音樂舞蹈的發展。
二、文化認同的角度
文化認同與區域音樂文化研究之間存在密切關系,區域文化源自區域內人們對于文化的態度以及趨向于認同的心理。認同是一種心理機制也是一種主體判斷,其通過建構象征識別體系來體現“自我”與“他者”的差異。而象征體系并不是客觀對象化的“物”,而是觀察者/研究者的判斷,認同與否不是既定的,而是充滿著偶然性。因此,區域文化的特點在于其是以在歷史中逐漸形成的民俗為主線來進行劃分,對于歷史形成的民俗要素只能是通過文化闡釋才能讓人們有更深入的理解。但是,只有貫穿以人的社會活動所形成的區域民俗特征的歷史才是有意義的。在這個層面上,“岷江上游地區”自然地理屬性盡管是重要的,但在此基礎上,對這一區域的文化理解與闡釋更是不可或缺的。
學術研究是以學術理論與學者經驗相結合為基礎,對于文化的理解也是學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知識投射的雙向互動過程。文化認同與音樂研究的特點包括:“第一,從文化認同角度進行研究會更加強調現實性,‘認同’的產生都是在現實的作用下形成的;第二,認同研究更強調了主體性的觀念,關注于‘音樂觀念’問題。”②楊曦帆《一種新的視角:文化認同與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以川西高原“鎧甲舞”為例》,《中國音樂》2018年第1期,第46——54頁。從學術研究轉型特點來看,認同不是簡單的單向度發展而是在多重因素的互動中完成。“沒有一種身份是本質性的,也沒有一種認同本身可以不根據其歷史脈絡就具備進步或壓迫性的價值。”③〔美〕曼紐爾·卡斯特著,曹榮湘譯《認同的力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認同是一種歷史性的動態發展過程,它以“自我認同”為基礎,并在認同的過程中獲得更多的以民俗行為建構的文化自信。如果相反,那么,“喪失自信的核心就是歷史感的喪失。”④〔英〕 E.霍布斯鮑姆、 T.蘭格著,顧杭、龐冠群譯《傳統的發明》,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頁。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西方世界文化變革的時代,我們今天所接受的很多來自西方的學術理論大多定型于這個時期,比如,受到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1902--1994)認同理論影響,人類學界也開始廣泛重視文化認同研究。又如,這個時期由德國美學家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等學者提出的接受美學理論;強調研究對象不再是“作品本身”,而是將研究視角轉向讀者,看重作品被讀者如何接受以及接受后的效果。這一理論提出讀者的“期待視野”和“客觀存在”的作品之間的關系說明了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更注重具有活態的互動關系,而不是簡單的將作品作為一個“客觀對象”看待。⑤參見〔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在后現代思維影響下,學術的興趣從客觀化、對象化轉向主體感受,研究者擁有什么樣的視角已成為解釋對象的重要原因。對一個區域的音樂舞蹈研究已經不再局限于其作為“對象”的身份,而是其作為被研究者所觀察與體驗的視角。在這個語境中,文化認同更主要的意義在于其是被局外人的觀察所建構的。“岷江上游地區”這一概念本身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這是一個自然地理屬性;另一方面,這也是學術建構的一個概念,是作為局外人的學者以及大眾需要認識和理解一個特定區域文化含義的一種通途和一個闡釋的道路。簡而言之,“岷江上游地區”這一概念是代表著學術分析的學者和地方性知識與情感的族群、是局內人和局外人共同建構的。這一區域是存在的,但在文化上更多是“發明的”“想象的”“建構的”。這有點像當人們提及“江南地區”時,盡管“江南地區”在自然地理屬性上有著自己的特指,但“江南”這個詞本身已經在歷史中逐漸積淀出較為豐富的文化含義并被廣為傳播。這種想象性的建構在文化上影響著人們對藝術的態度和對生活的品位,在多民族地區也平衡著不同族群在相同地理環境中生存的文化需求。
文化認同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個涉及族群情感、歷史文化以及個人身份認同的話題,包含著人們對自身社會生活價值的判斷,對于人們的社會行為有著潛在但卻是根本的影響。文化認同擴大了傳統研究視野,將研究的目光投向人,使學術研究在結合實際中保持了活力,當音樂被視為人類情感與生活的一種表達時,音樂的經驗就不可能脫離于社會、歷史語境而孤立存在,在這個層面上,音樂與文化認同的關聯就是有效的和必要的,從這一角度就能進行更深層次的文化闡釋。有學者指出“作為一種自身的主觀定位(subjective position),‘認同’是一種對所謂‘歸屬’(belongingness)的情感。學者們把‘認同’從一個行為科學的術語帶入社會人文科學領域,所尋求的是某種群體的歸屬儀式的形成過程。”⑥范可《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認同與文化自覺》,《世界民族》2008年第2期,第1——8頁。在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研究中借用人文學科的“文化認同理論”并不是簡單的跨學科套用,而是說這一理論本身為學術研究開啟了新的視角,同時,在這一視角研究中,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所關注的人類情感的需要、情緒的宣泄等環節也可以為人文學科的研究提供重要個案;畢竟,情感因素不僅是認同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人類生活的“本真”狀態。很大程度上,人們不是通過理性思考,而是依據情感體驗來實現內心的認同傾向。
從文化認同角度切入對岷江上游地區音樂舞蹈文化的研究,可能改變了過去將具體音樂事象當做固定對象的學術方式,而是將其看作是具有復雜結構的、流動的,并在歷史中不斷建構的、其建構主體不僅包含當地的地方性知識擁有者,同時也包含著作為“局外人”的學術研究者。認同也并不是有某個“標桿”等待著需要獲得認同感的人或族群向其靠攏,認同也是在發生中不斷建構的。比如,今天通過音樂事象所要表達的對于“岷江上游地區”的認同就完全可能不同于一百年前,因此,人們對于這一地區的理解、情感、認識也都可能因為時間的長度而具有很大差異。在這個層面上,文化認同理論有利于結合現實深入理解該地區的信仰、民俗行為等,將音樂視為社會文化行為,能夠豐富對音樂的理解,更深地理解當地人的音樂行為,理解人們通過音樂舞蹈這一樂舞行為所要表達的內在情感以及不同民族對自身文化身份的認同。
三、歷史語境中的文化認同
能夠成為“區域文化”研究對象的,往往都具有著較為深厚的文化傳統與歷史積淀,這是所謂“區域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學術特征。岷江上游地區是因自然環境而成的區域,漢、藏、羌多民族聚居于此,在歷史中逐漸形成獨特的多民族混雜居住和文化區域,具有的傳統文化在其形成過程中多會伴有認同的諸多環節,如族群認同、身份認同、信仰認同、音樂認同、習俗認同和政治認同等。認同是傳統在社會生活中的必要條件,沒有認同,傳統就不可能穿行于現代社會。
文化認同和區域文化研究之間有著緊密的學術關聯,特定區域中的傳統在不同時期的認同中不斷豐富、變化和成長;這很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頁。觀念的變化就是認同的變化。認同本身也具有多樣性,一方面,認同是“當事人”自身的情感歸屬;另一方面,認同代表著學者的視野以及社會大眾對具體民俗文化的承認。有學者指出:“承認與認同是個體或群體身份建構過程中,對建構者而言客體意識和主體意識產生作用的具體表現。客體或他者的認知及承認與主體或自我的認同相互影響、互相交織,共同推動主體的身份建構。”⑧王文光、朱映占《承認與認同:民國西南少數民族的身份建構》,《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第84——92頁。建構需要象征性符號的支撐,象征性符號可以來自信仰、神話、儀式、樂舞文化等族群生活環節,這些象征性符號之間也是充滿交叉互動并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形成新的文化符號。
岷江上游地區有著深厚的文化歷史發展脈絡,針對這一地區的現代學術研究起步見于民國時期,美國人類學家葛維漢在“民國22——37年間,多次到羌族地區調查,……形成了《羌族的習俗與宗教》《川西調查記》等著述。”⑨耿少將《羌族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0頁。專門的音樂專業研究相對晚一些,比如,阿爾麥多聲部民歌的研究,始于在1985年《音樂探索》發表的由張光榮和江國榮撰寫的論文《知木林地區阿爾泰人(藏族)二聲部民歌概述》。此文第一次向大家介紹了阿爾麥多聲部民歌,主要涉及阿爾麥人二聲部民歌的演唱原則、演唱形式及其分類。此后樊祖蔭先生在《中國多聲部民歌概述》中將其作為23個民族的多聲部民歌中藏族(阿爾麥人)多聲部民歌做了進一步的梳理。
田野工作不僅僅是做靜態研究,而是要思考如何進入“歷史語境”,通過深入的田野工作與深度的訪談,從而建立對“音樂——情緒——集體意識”的梳理。田野工作與口述史的要點是對個案的把握,這其中也包括對于民間傳說的理解。人類學家王明珂《羌在藏漢之間》一書中,對流傳于羌族中的兄弟定居傳說進行解讀,這種傳說已成為相關族群的文化思維并演變為儀式中的樂舞。也就是說,“親近——沖突”成為這一地區的特殊親屬關系和社會文化結構。而這一內在的族群結構是類似“鎧甲舞”存在的文化前提。“鎧甲舞”(又稱“兵舞”)的出現是受到自然、歷史、習俗的多方面影響;同時也可視為岷江上游地區“弟兄故事”傳說的樂舞表達方式。過去的研究對此缺乏重視,特別是內地學者沒有注意到“弟兄故事”在岷江上游地區的意義,沒有注意到其中所反映的認同和不認同之間的關系問題。這類似于人類學家王銘銘所講的“青蛙爭鳴”理論,即在一片蛙鳴中,我們可能只關注到了鳴叫聲最大的一只耳忽略了其他青蛙。我們的研究也可能存在類似問題——對“主流”的重視而忽視了“邊緣”。在學術上存在著“典范歷史——邊緣歷史”的關系,口述史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解讀了邊緣歷史。口述史不是簡單的“事實”和“非事實”的考辨,而是反思當事人“言說”的意義。
在“文化變遷”理論看來,今天的很多文化,特別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常常是不同文化認同在歷史中互動形成。人的個體音樂思想和行為、情感和體驗與其他個體或社會群體進行交流和融合,同時包括個體對于宗族、族群,甚至國家的歸屬、凝聚和認同的歷史過程。音樂是發生在具體時空中的系列文化事件,音樂對現實的反映與影響乃至作用也都帶有歷史語境的意義。歷史材料不是簡單證明當下,而是反思當下。當然,反思并不是要簡單的推翻客觀存在的事實,而是說,主觀和客觀之間存在某種勾連,不是分離的,而是一體化的。不存在分離的客觀和主觀,只有以主體體驗方式進入到現場的理解。
四、認同的音樂體驗
生活在山區的少數民族對于外界的觀察,除了視覺之外,聽覺也是他們理解外界的重要途徑,“阿爾麥多聲部”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在歌唱中模仿自然,他們對外界的經驗包含著敏銳的聽覺思考,而不是如漢族和學術界所習以為常的“眼見為實”的思路。“多聲部”這一知識,特別是關于“多聲部”的“珍貴”概念,都是在文化互動中獲得的,是外來的文化給予了“多聲部”概念,并在現代社會中賦予其文化意義。
聽覺是生命的情感體驗和對世界的意義理解的重要環節,在這個意義上,“對音樂的研究”才能轉渡為“對聲音的研究”,才能夠把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學術追求引入為一種合理的語境,如此,“把音樂放在文化中研究”之“文化”的含義才能夠顯得飽滿而不蒼白。音樂中的文化認同首先是對他們所生存土地的認同,這樣的認同也隱含著一種音樂文化生態的學術闡釋角度。在這個層面上,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學術意圖才能夠真正得到彰顯;如此,我們的研究才能不僅僅是一種以知識為對象的,而是在文化互動中不斷建構和理解的。
從聽覺所闡發的學術認識,意圖還原山地民族對聲音的感受以及通過聲音對世界的文化表達,或者說,這是山地民族音樂不同于平原地區的一個特點,從對聲音理解的角度也是對在歷史中發展的傳統的新的理解。我們過去對傳統的看法是基于類似教材的統一化知識,而缺少來自于個人對于自然區域環境和民俗文化體驗的理解。當我們以個人的體驗為視角來理解這一地區的傳統時,我們會發現,所謂傳統并不是如教材那樣按照某種既定程序完成的,而是在歷史發展中充滿著豐富的不同元素和無法預測的偶然性。這一現象也使得學術研究從表面上看增加了難度,因為我們通常會認為對“不確定性”的研究要難于對既定的、確定的對象。這涉及學術研究的觀念問題,同樣也關系田野工作的有效性。如果缺乏深入思考和反思的精神,我們就很可能用我們自己的眼光看待、改變著研究對象,或者說,我們用我們的文化觀念投射于對象,使其受到我們的影響并發生變化。
在聆聽中體驗世界,這是少數民族音樂生活的一個重要體現。如果說在歷史的發展中沒有不變的傳統,那么從聲音的角度體驗世界就更具有“真實性”。在聆聽中,傳統沒有程式化,而是以當下的活力貫穿歷史。岷江上游地區的“阿爾麥多聲部”之所以能夠伴隨歷史傳唱至今,這種對聲音的想象和追求包含了當地族群的娛樂生活和他們對神圣性的理解以及對世界的體驗。文化認同解釋了多聲部這一社會(音樂)活動存在的原因,多聲部表達了人們對他們所居住世界的熟悉與認同并形成山地音樂的特點。另外,文化認同對于在文化上具有復雜結構的岷江上游地區音樂舞蹈文化研究來說是一個重要窗口,認同不是一種表象的言說方式,而是一種情感的隱喻表達。從文化認同角度研究有利于揭示真實情感,理解音樂對于人類生活的意義。通過音樂來揭示岷江上游地區不同民族的內在情感和族群性格,從文化認同理論角度來解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和信仰儀式中的音樂行為是關鍵;在這個意義上,每個民族都會在歷史中逐漸形成屬于自己的音樂舞蹈表達方式,因此,音樂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民族心理和文化認同的表現。
五、認同與不認同
有認同,就可能會有不認同的現象,就像有圖騰就會有禁忌一樣。現在學者們更多關注的是認同,較少談及“不認同”;談的少的原因或許是因為習慣,我們看待世界的眼光大多數時候都比較“正能量”,主要看到其積極的方面,較少論及其反面。但是,“不認同”在現實中是存在的。總的來說,在現實中處于瀕危狀態的文化就意味著其正在面對著現實中的不認同。這說明,文化認同的要點就在于學術研究要緊扣現實,認同與否不是一個固定的知識,而是必須在現實中實踐。比如在岷江上游地區歷史上就和其他地區一樣已有流傳久遠的傳統鍋莊,現在人們把主要是老年人,以自唱自跳方式的鍋莊稱為“老鍋莊”,而把運用藏族、羌族音樂元素改編的“藏羌鍋莊”稱為現代鍋莊或者是青年鍋莊。從現實中看,年輕人基本上都是跳帶有典型現代專業音樂編創風格的新鍋莊,新鍋莊不需要舞者自唱,聽不懂播放的音樂中唱的歌詞也不要緊,經過編配的音樂已具有某種獨立性質。通常講,只要能夠跟上節拍就可以學著跳,至于音樂所要表達的意義已經可以越過歌詞這一環節而直接從音樂的旋律、節拍中感受到。歌詞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之積淀已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這就是時代的變化。自唱自跳的老鍋莊越來越少人會跳,盡管老鍋莊已是“非遺”項目,但其面臨“失傳”的危險卻越來越大。年輕一代人沒有接受老一代人的鍋莊而是選擇了更具現代風格、更具活力的新鍋莊,這一選擇說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品位,并不是所有的“藝術”都能夠千年流傳。就現代鍋莊而言,一方面,輕快的節奏突出了健身的功效,擺脫了傳統拘泥的規矩;另一方面,老鍋莊所唱內容諸如歌頌草地、雪山、活佛等傳統農牧生產生活方式脫離于當下社會的城鎮化浪潮,老年人的情感寄托在現代社會生活已不占有主要地位,或者說,人們的情感需要和文化品位已發生了變化,和傳統社會已有差異。由是,“背景”的變化會直接影響著人們對于音樂本身的選擇,這從學術上也說明,背景研究并不能因為我們語言上的習慣,覺得“背景”是某種可有可無之物,實際上,對背景的理解是學術研究的起點。認同不是一個固定的對象,而是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從認同角度始發的學術研究,強調了其學術視野不能脫離于現實和人,認同與否不僅有歷史的建構,更關聯于現實中的精神需要和文化品位。
從歷史角度看,認同與不認同之間也是相互轉換的。對于岷江上游而言,自然崇拜、大禹文化、祭山會、母系血緣、藏文化、鎧甲舞、羊皮鼓、本波教和鍋莊等已成為區域民族文化符號,在今天已成為區域族群精神凝聚力的象征。但是在歷史上,在少數民族身份未獲得國家認同之前,岷江上游地區的少數民族在相當大的層面上被漢族視為“蠻子”;“聽到羌族唱山歌,就說‘蠻子狂了’”。⑩同注⑧。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少數民族文化只能在本族本地區內認同并傳承,但在更大的文化區域中,特別是在與漢族的交往中未獲得承認。在現代社會中,由于其民族身份獲得國家認同,其文化符號也就在更大范圍內被承認,大量民間藝術成為了有著“國家在場”意味的非遺項目。從“蠻子狂了”到由國家承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其中音樂文化身份的轉變——從不認同到認同——在文化語境中建構了當今岷江上游地區的少數民族音樂形象。而這種形象的文化意義則通過信仰、習俗、音樂予以表達,這些文化符號從意義層面呈現了“岷江上游地區”的文化內涵。
在這個層面上,認同或不認同不是以標準答案的方式呈現。局外人愿意看到一個認同與否的明晰結果,但就局內人的歷史發展來看,很多時候認同與不認同之間往往是逐漸形成的。筆者一再強調了認同不是固定的對象,而是在發展中不斷獲得認同的支點,對認同的獲得本身也就意味著其在不斷擺脫著不認同。從哲學上說,認同包含著不認同。這就像黑格爾講的:“有之為有并非固定之物,也非至極之物,而是有辯證法性質,要過渡到它的對方的。”?〔德〕黑格爾,賀麟譯《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92頁。一種音樂在一種文化中被認同,有可能在另一種文化中則不被認同;在這個語境中,有可能是音樂本身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是文化背景的改變決定了認同與否。
六、特殊自然環境與區域音樂文化認同
突出“岷江上游地區”的文化認同,其基礎首先來自于相似的自然地理特征,包括相似的自然災害。由于種種原因,在一次次自然災害過后,并沒有出現大規模移民以逃離這一危險地區,人們以各種方式繼續生存于這一片狹窄的土地之上。這種回蕩在漫長歷史中的記憶成為這一區域族群共同體心理上的彼此慰藉與認同情感,是不同族群間彼此認同的一個因素。在災后重建的規劃中,突出表現地域民族特色也是重建中的一種文化認同與象征。這一點,無論是地處理縣的甘堡藏寨還是桃坪羌寨等重建村寨都有很明確的表達。如果說,文化在社會中是有功能作用的,那么,在災后重建十年中,當地的傳統文化/樂舞文化對于撫慰傷者心靈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人們有沒有通過樂舞文化重振對家鄉的情感認同?這些問題都亟待學術界認真思考。事實上,沒有文化上的認同,就不可能有有效的傳承與保護。文化認同研究是岷江上游地區災后重建的一個重要要素,重建不僅是城鎮的、物質文化的重建,同樣包括了精神與文化的重建和認同。傳統文化作為“看不見的手”,作為一種隱藏于人們心中的慣習,其力量對于今天的社會生活而言依然有著影響力。
文化認同依靠于信仰、習俗等堅實的社會結構而存在,認同還表現為多種層面。一方面,認同似乎是作為外界的自然環境強加給當地人的;另一方面,普遍的宗教信仰緩解了外界壓力,使得認同作為安撫心理作用而得到接受。同時,伴隨于生活、儀式中的音樂則使得人們的精神得到釋放,從生活的壓抑中獲得愉悅感并從日常狀態中形成新的集體記憶,因此,記憶也因為對生活的認同而不斷重構。很可能,在心理上是文化重構撫平了創傷;因此,盡管音樂是認同的一種表象,但認同在本質上有著心理的“趨利避害”之功能。這說明,“岷江上游地區”不僅是一個自然地理概念,同時也是在歷史中不斷形成的文化認同概念,是包括自然地理和文化認同等多種因素使得認同不是單一的,而是成體系的,是必須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的。
區域文化研究的學術特點一方面要注重其區域內文化的歷史脈絡,另一方面也要關注區域內文化的互動機制。少數民族音樂都是以民俗、信仰為基礎,脫離了民俗、信仰則很難把這類音樂的意義說清楚;少數民族音樂的這種特點,以及學術上的線索也是文化認同作為一種學術理念切入對少數民族地區音樂研究的前提。由于岷江上游地區存活著豐富的民俗信仰文化,包括神話傳說、民間傳說等,豐富的文化成為理解該區域音樂觀念的重要基礎和線索。“把音樂放在文化中研究”的意圖在于如何在文化中理解音樂。也就是說,只有對于習俗、信仰、神話、傳說等文化內涵有著深入認識和理解,才可能找到理解這一地區音樂觀念的鑰匙。比如,岷江上游地區嘉絨藏族/羌族的多聲部、羌族的“沙朗”、嘉絨藏族的鍋莊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樂舞形式,有喜事和憂事之分而有不同的社會文化功能;本地區普遍有原始宗教信仰,羌族“端公跳神”的羊皮鼓舞和白馬藏族的巫儺樂舞“跳曹蓋”代表了人們對于神靈的崇拜;嘉絨藏族和羌族都有分布的“鎧甲舞”,或稱“兵舞”則屬于典型的祭祀儀式樂舞。通過具體音樂事象理解人們的生活與情感,音樂舞蹈個案研究為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等研究領域拓展特殊的研究視角;岷江上游地區的民間音樂大多都是無樂譜的,對于沒有樂譜的族群,研究的視角就應當圍繞著他們的生活、習俗、信仰,以及音樂如何運用于儀式之中等。因此,關注于被忽視的與歷史語境/日常生活相關聯的音樂,這樣的學術思路使得研究工作更注重個人生命體驗和身體感受以及對歷史的記憶和音樂的社會文化認同。把音樂放在文化中研究,揭示了樂舞行為與信仰、民俗社會文化行為之間的內在關聯,這樣的音樂與文化的“雙向循環結構”有利于促進學術的深入研究,抓住了研究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關鍵。
就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的學術方法而言,深入、扎實的田野工作以挖掘具有深描意義的個案是不斷理解不同文化中關于認同的學術研究基本方法,它能夠使學術研究不斷獲得新的角度,能夠使研究視野更貼近包括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民間藝人”。這也是為什么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視田野工作為其事業的靈魂。甚至于,通過田野工作所建立的以口述史為基礎的歷史資料不僅補充已有歷史材料,而是獲得理解的視角。這樣的理解,不是憑空無端的想象,而是時間與空間,局內人與局外人視野匯聚于因深度田野工作所帶來的具有深描意義的個案之中,并從中不斷闡發著有效的學術理論。這就提醒我們,田野工作不是簡單的記錄,還要關注研究者的學術理念與進入的角色。這樣看來,正是因為文化的發展有“不確定性”,就會要求研究者與當地人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主客觀對立的關系,而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互動中共同建構著音樂的文化意義,這些學術理念與方法都使得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這一專業對于其從業人員來說充滿了挑戰和誘惑。
從文化認同角度來看,岷江上游地區不同民族互相交織融合,同時又各自努力保持自己的傳統。該地區的音樂并不僅僅保留著傳統的樣式,而是在現代社會中發展著屬于現代社會的音樂。比如,進行了專業配器改編的“現代藏羌鍋莊”就是容納了藏族和羌族鍋莊音樂中在同一文化區域中被不同族群都接受的因素進行了再創作,其明快的節奏和更富有時代氣息的旋律都讓其被大眾和城市所接受。因此,不僅有族群本身的音樂文化認同,還包括著岷江上游地區的音樂文化認同。認同存在不同層級,認同不僅是單向度的單一性認同,也存在不同文化在差異性中所求得的認同。認同在差異中所形成的力量不僅因為作為客觀因素的自然環境而成,同時是不同族群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盡管從自然和文化較大層面上看,岷江上游地區有著相對具有特點的文化,但在這一特定區域文化內部,也還是存在著不同的音樂舞蹈風格。這說明,文化本身的結構是復雜的。在復雜結構中理解音樂的意義,需要一種更為有效的學術方法。文化認同理論在音樂研究中的實踐,就是一種落實“把音樂放在文化中”研究的學術思路。
結 語
岷江上游地區作為區域音樂文化呈現出多民族多種音樂舞蹈文化聚集與綻放,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情感表達方式;該地區音樂大多表現出較強烈的社會文化功能性,扮演著族群意識、信仰習俗、情緒感應等功用;盡管這一地域的民族主要包括藏、羌、漢,但從更廣泛的局面來看,羌族作為存在于岷江上游地區的少數民族,在這一區域具有著無可替代的代表性和重要性。作為“羌在漢藏之間”的族群分布格局,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著漢藏文化。
岷江上游地區多族群文化元素在社會文化層面上表現為“復雜結構”,融合、邊界、分離、變遷等文化現象同時共生,實際上,傳統是人們立足于當下而對歷史的想象和文化的結構,傳統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流變與建構。認同不僅是簡單的“聚攏”,而是具有文化上的互動與多種表現形式。相關樂舞的文化背景也可能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對于“背景”的解讀需要結合于當下的需要,需要理解“當下”人們的情感/情緒的表達。因此,“岷江上游”文化含義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比如,民國時期有學者把和漢族地區相連的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稱為“內地邊疆”,其意指文化的差異性;今天沒有人會對類似于岷江上游這樣的少數民族地區產生“邊疆”的概念,這里已經不再是內地漢人遙不可及的地方,這里是旅游者的天堂。作為學術研究而言,這種“背景”的轉換直接關聯了我們對于當地樂舞文化的理解。音樂已經不再僅局限于神秘的祭拜儀式,而是面向旅游者的表演;音樂也不再僅限于家族或者是村寨內或文化區之內的民間傳承,而是作為有國家在場意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對象。
無論是歷史地看,還是整體地看,文化認同語境中的學術研究是研究者識別研究對象心理認識的一種學術方法。既包括“當事人”界定“自我”區別“他者”的重要手段,也是研究者歸納同一文化特征的主要途徑。認同是與在他者的互動關系中形成的,認同的視角也不是恒定不變的。對于學術研究而言,認同由研究者在研究中和被研究對象之間于互動中建構,并在文化的流動與互動中理解文化的意義。總體上看,文化認同理論作為一個更為宏觀、更為切中不同族群文化意義的學術理念,在相當程度上具有打通并貫穿區域音樂文化研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