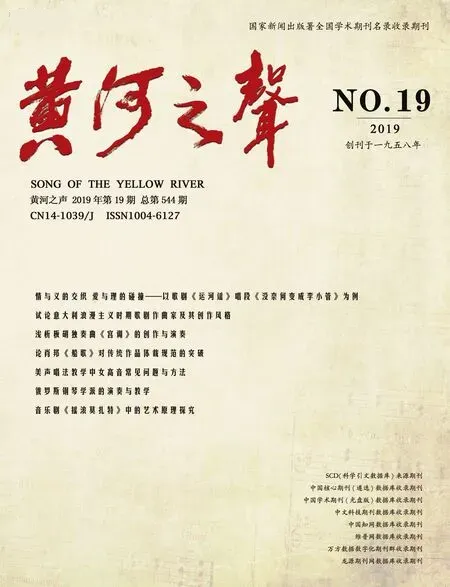分析舞蹈劇目《逍遙》的編創(chuàng)手法
馬 靜
(江南大學(xué),江蘇無錫214122)
該舞蹈作品由史博編創(chuàng),張列作曲:杜尚武、羅天、王文虎等表演,曾獲第七屆全國電視舞蹈大獎賽,古典舞組作品銀獎!
一、背景介紹
2013年舉辦的第七屆CCTV全國電視舞蹈大賽中,北京舞蹈學(xué)院史博以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為人物基礎(chǔ)創(chuàng)作的中國古典舞《逍遙》,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依據(jù)編導(dǎo)所說,古典舞《逍遙》取“竹林七賢”的人物形象,但舞蹈主題內(nèi)容并非是為了刻畫“竹林七賢”的形象。而是因有感于道家思想中“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這句玄妙之言,并借用漢唐古典舞的舞蹈語匯,取“竹林七賢”這一形象為古代文人雅士的形象代表,來表現(xiàn)中國文人的淡泊名利、堅持自我的氣質(zhì)豪放不羈、灑脫自在的情懷。因此,整個舞蹈作品無論從內(nèi)容、語言還是意境營造上看,都是給人以瀟灑自由、飄然世外之感!
另外,該舞蹈中編導(dǎo)選用“古典舞”作為舞蹈語言,正是由于“古典舞”本身所具有的圓潤有度、氣韻流暢、頓挫有致的風(fēng)格特點。通過古典舞行云流水般的動作表現(xiàn),更是與古代文人雅士逍遙灑脫、內(nèi)斂含蓄的性格特征巧妙的融合為一體,將人文雅士的氣度情懷同古典舞一起徐徐展開……此外,古典舞本身就是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下的產(chǎn)物,“竹林七賢”是古代文人雅士的代表,更是淡泊名利、憂國憂民之品格的典范,編導(dǎo)通過古典舞與“竹林七賢”的融合,更是體現(xiàn)出了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相互融合與相互滲透,以及對優(yōu)秀傳統(tǒng)品格的追求與發(fā)揚。因此,舞蹈《逍遙》不論是從作品取材、舞蹈語言方面,還是從有感于道家思想與文人情懷方面來看,古典舞《逍遙》都處處滲透著古代文人雅士的含蓄內(nèi)斂,處處滲透著中國古典舞的審美要求,處處滲透出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保留,并且體現(xiàn)出編導(dǎo)嘗試著將古典文化與現(xiàn)代的審美需求的結(jié)合,使人觀賞過后,意味深長。
二、作品內(nèi)容
該作品不以表現(xiàn)戲劇情節(jié)為主要目的,而是通過塑造七位著寬衣博袖的文人風(fēng)貌,以行云流水般的肢體動作來予以展現(xiàn)古代文人群體獨有的精神世界,表現(xiàn)的是一種不為功名利祿所羈絆,逍遙灑脫的理想追求。
舞蹈開始便是一個靈活分散的畫面,甚至這七人的朝向都是不同的,各自分散在舞臺之間。在看似沒有章法的布局中,卻絲毫沒有不協(xié)調(diào)之感,可能正是這種“不同”才更好的營造出了文人任自然的“逍遙”意味。
接著由一位舞者引帶,一傳二,二傳四,四傳七,舞蹈動作與調(diào)度變化富有層次感,靈活多變而又彼此呼應(yīng),時而動作各異,但畫面依舊和諧完整,風(fēng)格統(tǒng)一。主舞段時而七人同步,時而二人舞動,四人駐足,時而六人駐足,一人舞動,舞蹈情緒起伏變化,調(diào)度流動連綿不斷,無時無刻都在傳達(dá)心靈自由,無拘無束的逍遙境界。
在酣暢淋漓的集體舞動之后,在眾人運用博袖組成的呼吸造型之后,各自又回到了獨立的空間位置,在看似無序的排列中,透露著的是任自然的道家思想,沒有了庸俗,沒有了沽譽(yù),留有的只是文人理想的精神世界。
三、意境營造
該作品是沒有情節(jié)的舞蹈作品,與其說編導(dǎo)是在刻畫古代文人的藝術(shù)形象,不如說是在借用文人形象來營造出了文人內(nèi)心逍遙脫俗的飄然意境。因此,該作品意境的營造是其重要內(nèi)容。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現(xiàn)的那種情景交融、虛實相生、活躍著生命律動的韻味無窮的詩意空間。《逍遙》之所以這么引人入勝,原因就在于編導(dǎo)對于舞蹈本身的意境營造有著獨特而又深刻的認(rèn)識,在看似簡單的舞蹈表演中透露著濃濃的氛圍感。
首先,在舞蹈結(jié)構(gòu)安排上,開始影子部分,以及末尾部分,都為作品的意境營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開始的影子部分,長達(dá)一分鐘的舒緩清麗的琴聲中,有坐有站的散落著七位舞者,怡然自得,配以悠然的呼吸韻律,將觀者從凡世拉回到了古代文人的詩意世界。這一分鐘對于該作品而言,是一個氛圍孕育的過程,沒有繁雜的音樂,沒有過多的動作,在至簡中營造逍遙的氛圍。而在結(jié)尾處,六人散去,只一人以逍遙步態(tài)繼續(xù)漫游,此時音樂已經(jīng)結(jié)束,而這一人持續(xù)的漫步,卻使得觀者依舊漫游在這濃濃的意境當(dāng)中,而這正體現(xiàn)了編導(dǎo)對作品意境的把握的深厚功力。
其次,在音樂選擇上,以清麗高雅的琴聲為主,伴以中國民族打擊樂器為節(jié)奏,配器簡單,音樂風(fēng)格性統(tǒng)一,整體節(jié)奏,起伏婉轉(zhuǎn),是營造逍遙意境的重要推手。
再次,在舞臺調(diào)度方面,舞蹈調(diào)度富有流動飄逸之感,多以圓形、弧形、斜線為主,且步法輕盈飄逸,這些特點對于逍遙的意境營造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在舞蹈表演中造型往往適合塑造人物形象,而連綿不斷的舞臺流動則更適合于營造輕盈飄逸之感。
并且舞者在舞蹈調(diào)度,空間變化上都有著巧妙呼應(yīng),看似隨意的布局,飽含著編導(dǎo)對于逍遙之美的理解,身體不受羈絆,心靈自由放逸。舞臺調(diào)度和空間運用靈活多變,暗含著這七位文人墨客的逍遙任自由,而舞者之間的呼應(yīng),則又暗含著彼此心境的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這些虛實相生的調(diào)度運用,是建構(gòu)舞蹈意境感的重要手段,搭配以怡然自得“氣若浮云,志若秋霜”的表演,共同營造出了飄逸逍遙的文人心境。
四、舞蹈語言方面
中國古典舞代表著中國舞蹈的傳統(tǒng)和經(jīng)典,遵循著中國古典藝術(shù)的審美原則,而這些特點無疑為中國古典舞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諸多的特殊性。中國古典舞的動作語言不僅要符合作品本身需要內(nèi)容需要,更重要的是自身的民族屬性不能夠丟失,因此,對于中國古典舞的創(chuàng)作,首先要在傳統(tǒng)審美的規(guī)范之下進(jìn)行創(chuàng)作。
正如該作品的編導(dǎo)史博所說,古典舞的創(chuàng)作是“帶著枷鎖在跳舞”,這里的“枷鎖”并非是對古典藝術(shù)的貶低,而是說中國古典舞的編創(chuàng)要扎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土壤之中,要在中國古典的審美原則之下進(jìn)行創(chuàng)作,而非跳出古典舞的屬性,隨意主觀的追求新意。
舞蹈《逍遙》的舞蹈語言完全符合于中國古典舞的形式風(fēng)格和審美特色,并沒有因為新的舞蹈內(nèi)容而依據(jù)個人喜好隨意創(chuàng)造。在整個作品中漢唐舞中的“斜塔”重心,“流動連接”的氣韻,“頓挫”的發(fā)力,“虎頭蛇尾”的氣息,這些漢唐舞典型的動作元素貫穿于作品之中,應(yīng)該說這是一支典型的漢唐舞蹈作品,繼承了漢唐舞蹈的語言原型,符合于中國古典舞蹈的審美原則。
如果說編導(dǎo)在舞蹈語言的創(chuàng)造上堅守住了中國古典舞的文化高地,那么真正的困難則來自于怎樣才能創(chuàng)作出符合作品的內(nèi)容,為我所用的個性化的舞蹈語言。
編導(dǎo)所選擇了以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形象為藍(lán)本進(jìn)行創(chuàng)作,當(dāng)時的文人墨客崇尚寬衣博帶式的著裝,以此來彰顯自己飄逸玄妙的風(fēng)貌。編導(dǎo)充分領(lǐng)會了南北朝時期的文化風(fēng)格,以及對古代文人理想追求的深刻理解,抓住了服裝寬衣博袖的服裝特點,將漢唐舞的“斜塔”重心再夸張化,并與闊步流動的步法相搭配,飄渺不定,甚至有種飛翔之感。同時博袖不單能營造輕飄之感,編導(dǎo)還創(chuàng)造了較為豐富的舞袖動作,揚袖,饒袖,飛袖,甩袖這些動作的開發(fā),都是編導(dǎo)根據(jù)南北朝時期的文化環(huán)境和文人的出世氣質(zhì)進(jìn)行的再創(chuàng)造。不同的舞袖方式給予觀者不同的心理感受,雙袖飛揚,配以流動的步法,是飄逸之感,而有力的甩袖動作,配以上身的隨動甩頭,則體現(xiàn)出的是放浪形骸,豪邁瀟灑的風(fēng)貌氣質(zhì)。
豐富的袖舞動作,傾倒的重心和流動的舞步,都是編導(dǎo)在對古典舞蹈的深刻把握之后的個性化再創(chuàng)造,除此之外,該作品還有很多個性化的舞蹈語言,但這些都是在中國古典舞蹈的審美原則之下的合理再創(chuàng)造,即便是一個燕式的吸腿跳躍,都不再是照搬芭蕾的動作,沒有過分的肢體逞能,沒有雜技般的技巧嫁接,留有的是中國式的審美情趣和人文特征。
啟示:古典舞《逍遙》通過古典舞的方式,取“竹林七賢”的文人形象,來展示古代文人淡泊名利、逍遙灑脫的氣度與情懷,更展現(xiàn)出編導(dǎo)繼承傳統(tǒng)與融合創(chuàng)新的理念。因此,可以說,中國古典舞的創(chuàng)作是有原則的創(chuàng)作,其原則便是繼承傳統(tǒng)文化。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是中國古典舞創(chuàng)作的母體,它所展現(xiàn)的不單單是編者個人的審美觀點,更代表著中華民族公認(rèn)的審美觀。因此對于古典舞的創(chuàng)作,我們應(yīng)該扎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中,對文化理論多做研究和思考,對中國古典舞蹈的素材進(jìn)行不斷的豐富和補(bǔ)充,了解中國歷史不同時期的文化風(fēng)貌,并且根據(jù)不同創(chuàng)作內(nèi)容,創(chuàng)造出個性化的舞蹈語匯,只有這樣中國古典舞的語言原型才能不斷豐富,逐漸形成中華民族公認(rèn)的古典舞蹈語匯,從而創(chuàng)作出更多富有深層精神與寓意的優(yōu)秀舞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