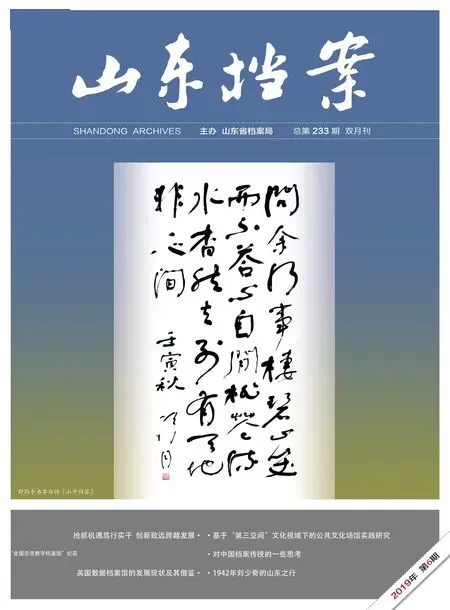基于“第三空間”文化視域下的公共文化場館實踐研究
——以檔案館和圖書館為例
文·崔玉珍
適應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緊跟經濟社會信息化進程,推動檔案文獻、圖書資料管理利用電子化、網絡化、社會化、多元化,是檔案圖書事業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推動文化事業改革發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務能力的重要內容。探索構建城市檔案館和圖書館的“第三空間”體系,促進用好用活檔案圖書資源,吸引更多市民走進檔案館、圖書館,讓廣大公眾真正有收獲、受啟迪,是非常有意義的嘗試。
一、何為“第三空間”?
作為一個學術用語,“第三空間”一詞最早見諸于美國都市社會學家雷.奧登伯格在1999年出版的名著《絕好的去處:咖啡館、書店、酒吧、理發沙龍和其他位于社區中心的聚會場所》。在文獻研究和實證觀察的基礎上,奧登伯格為美國中產階層的非正式的公共生活提出了“第一空間”“第二空間”與“第三空間”的概念。他認為,僅僅滿足于往返于職場和住所之間的“兩頭跑”模式絕不是一種令人滿意的社會黏合方式。而且這種兩站式的日常模型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共或公開的放松的機會。結果是,中產階層只好專注于工作及家庭生活中,美國工業為此支付了更多的醫療費用并承受了更低的勞動生產率,人民對生活方式的滿意度和期望值大幅下降。
在奧登伯格的話語體系中,“第三空間”的提出是與美國人非正式的公共生活的匱乏與缺位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第三空間”正是重構美國人多樣化的生活方式及非正式公共生活的需要及著眼點,它有效地平衡了廉價性與滿意度的關系,使以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咖啡館、書店、酒吧、理發沙龍等為代表的社區中心場所成為維系個體與社區、個體與周邊環境以及家庭與社會之間情感交流和休閑放松的臍帶。正是基于以上的邏輯和分析,奧登伯格為當時的美國中產階層開出了一劑解決非正式生活場所問題的藥方,即“第三空間”的概念。他認為,“第三空間”可以代表當地居民非正式生活的整個譜系,覆蓋最廣泛的人群。“三個空間”的劃分較好地平衡了住所、職場與社交場之間的關系,使人類經驗建構在聯系、區別以及自治性的基礎之上。可見,“第三空間”概念與生俱來就有著豐富的情感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的,這應該是我們應用于檔案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場館的實踐中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此外,許多專家學者也對“第三空間”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奧地利的克里斯蒂娜·米昆達就視之為住所和職場之外的“情感精神”的場所。美國學者愛德華·索亞認為“第三空間”是超越了物理與精神二元對立關系的第三種樣式,是一個城市最具活力和人文多樣性的場所,它甚至于可以視作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標。由于它基于人本主義的理念與公共文化場館著力為市民和利益相關者服務的理念以及公共空間的自我定位不謀而合,因此“第三空間”逐漸成為公共文化建設的努力方向和業界的普遍共識。比如,第18屆國際檔案大會的主題是“檔案、和諧與友誼”,還組織了“檔案文化和社會多樣性與和諧”專題論壇,運用“第三空間”理論拓展檔案機構的社會功能。再比如,2009年召開的國際圖聯會議就鄭重地以“作為第三空間的圖書館”作為討論話題,深入探討了公共圖書館在當地文化建設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作為“第三空間”最重要的有效載體,公共文化場館理應成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第三空間”。這個概念也成為了當今公共文化場館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二、移動互聯網時代公共檔案館、圖書館的機遇與挑戰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層出不窮的科技創新,我們已經步入了移動互聯網的時代。一方面,互聯網帶來的巨大便利性極大地沖擊了檔案館、圖書館傳統的查詢、借閱業務,來館訪問量、借閱量連年縮減,使其地區信息資源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極大地挑戰。人們的信息獲取方式迅速地從“讀紙”躍升為“讀屏”,從平面到立體,從單向到交互。人們的文化消費趨向于碎片化、快餐化、淺層化,傳統的現場查詢查閱迅速被搜索引擎的網上查閱所替代。互聯網上有海量的、多種形式的、富于個性化的文化消費的產品,除了快速發展的網上圖書館、網上檔案館,還有類似網上公開課等視頻課程、邏輯思維、知識類的微信公眾號、簡書、今日頭條等付費訂閱專欄等等。可以說,移動互聯網的技術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現代社會高節奏、快餐式的文化消費,進而消解或弱化了檔案館、圖書館等傳統機構原來擁有的信息資源、知識資源的優勢地位。另一方面,人們對于公共文化場館數字化的虛擬資源的需求有增無減,大型公共圖書館附設的數字圖書館,各級檔案館開通的網上資料庫等的網絡訪問量、資料下載量等均呈現大幅增長的趨勢。同時,公共文化場館特有的寬闊空間、安靜舒適的環境布局、豐富的館藏資料、濃厚的文化氛圍、經常性的專家講座和實物展覽等仍然對許多市民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快餐式、蜻蜓點水的文化消費方式并不能增進人們的思維能力、對世界和事物的認識深度以及知識體系的建構。因此,這也有必要在“第三空間”的文化視域下加以審視和利用。當我們將一個城市的檔案館、圖書館視作文化“第三空間”時,其中的言外之意是公共文化場館可以成為一個人們了解歷史、獲取知識、交流思想、豐富文化娛樂生活和終身學習的平臺。
三、公共文化場館服務理念的轉變與文化“第三空間”
城市檔案館和圖書館最主要的資源是歷史檔案文獻和圖書報刊資源,但是傳統檔案館、圖書館把過多的關注放在了館藏數量和自身的內部建設上,而對外部的讀者群體乃至各類的利益攸關者的實際需求反應不夠靈敏,從而沒有很好地形成知識正向流動的閉環。這導致的結果是檔案館、圖書館對服務對象的吸引力下降,現場訪問量、紙質圖書借閱量不斷減少。從本質上講,這類傳統公共機構由于自身的理念及傳統實踐問題而未能走出“為藏而藏”“為書而書”的“收藏”模式。所以,往往出現“世外桃源”“鬧市凈土”“門可羅雀”的蕭然景象。
但是,從國內外一些的創新實踐來看,只要公共文化場館實現“以藏為本”到“以人為本”的觀念變化,通過自我定位的改變和品牌重新塑造是可以實現華麗轉身的,從而煥發出新的活力和生機,承擔起更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功能。
根據特勞特的定位理論,應對變化和適應變化的最佳方法是重新定位。因此,公共文化場館應當采取實際措施調整和改變利益攸關方的認知,以應對變化帶來的各種危險。我國的公共文化場館由各級政府出資建設,屬于社會公益性質,服務對象主要是當地的市民以及范圍更廣的利益攸關方。在這里,利益攸關方主要是指與公共文化場館有各種利益關系或者聯系的群體或團體,比如市民、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各類學校、文化機構從業人員等等。所以城市檔案館要從原來的征、入、存、保、研、用的工作鏈條上做好拓展創新,書館要從原有的采、編、流、存、借的傳統功能和路徑中升級、整合和融通,形成一個基于更新社會功能的有機整體。因此,公共文化場館要改變在人們心目中“鐵柜子”“書架子”和“空房子”的刻板印象,以“尊重人、關懷人、滿足人”作為自身工作的基點,讓檔案館、圖書館更加充滿想象力、時尚感和價值,實現與現實生活、用戶需求等的有效鏈接。這一點得到了廣大業界人士的一致認同,文化“第三空間”正在成為公共文化場館實現轉變的重要戰略指導思想和進化路徑之一。
四、公共文化場館的“第三空間”的體系構建
公共文化場館非營利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它具備“第三空間”的典型特點,比如自由交流、平等對話與分享、易獲得性、資源共享、多元化和尊重人性。
首先,公共文化場館要充分利用自身優勢,通過整合和提供信息查詢、電子文獻、音視頻資料、學科講座、在線課程、各類展覽、下載與閱讀、專題庫、社交性共享等形式吸引市民和各類潛在用戶“走進檔案館”“親近圖書館”,引導公眾更充分地了解館藏資料,更有針對性獲取潛在需求方向,激發他們學習和交流的興趣,倡導社會公眾從網絡上的“快瀏覽”“淺閱讀”轉變為來現場的“坐下來”“靜思考”“深閱讀”,構建精神港灣,涵養城市氣質,進而為文化強國和文化自信做出重要貢獻。
其次,公共文化場館要以“引進來,走出去,攜起手”的方式,加強與美術館、博物館、藝術團體、文化工作室等的協作與合作關系,把其他形式的“第三空間”引入到城市檔案館、圖書館系統的文化“第三空間”之中,形成一種共融共榮的文化共同體。
第三,公共文化場館要設計好、配置好和使用好自己良好的空間體系結構,以良好的環境為用戶營造出一個自由、平等、多元、愜意和個性化的文化空間,使得用戶能夠得到充分的人文關懷。
第四,公共文化場館要凸顯服務理念和用戶需求至上的思路,提供對孤兒、留守兒童、務工人員、老年人、殘障人士等的特殊群體的特殊關懷,滿足他們個性化的需求。
第五,檔案館、圖書館管理員要更新服務理念,提高業務技能,優化知識結構,樹立“以用戶需求”為導向的服務理念,建立“二線業務”為“一線業務”服務、全體職員為用戶服務的工作流程,構建起有效的文化“第三空間”,為用戶放飛心靈和自我提高提高一片文化的沃土。
最后,公共文化場館要與時代同步進化,成為親民的檔案館、溫馨的圖書館和聯結人與社會關系的文化沙龍,成為一個社區、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知識中心、信息中心、學習中心、休閑娛樂中心和文化中心,成為一個人們工作、生活之外的不可缺少的文化空間和生活的一部分。
五、公共文化場館構建“第三空間”實踐探索
在構建文化“第三空間”的熱潮中,國內外的專業機構本著“以人為本”“重新定位”和“重塑品牌”的思路進行了多樣化、基于自身實際情況的有益實踐探索,取得絢麗的成果。
(一)英國的“思想屋”(Idea Store)
“思想屋”模式是通過政府投入巨額資金,把英國東部地區的社區圖書館改造成一個集圖書館服務、成人學習課程、系列活動和事件的匯聚之所。“思想屋”在線打造24小時不打烊,為用戶提供各類知識查詢、電影欣賞、音樂下載、報刊閱讀、在線課程、電子書及音視頻、流媒體等綜合性的服務項目。讀者還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在線學習種類繁多、學科覆蓋面廣的視頻課程。“思想屋”舉辦的各類活動分為不定期的畫展、假日活動、作家節、最新科技展示等和全年性質的固定欄目(故事時間、朗讀、商業工作室和研討會等)兩種。在注冊成為會員之后,用戶還可以享受電子書下載和閱讀的服務。此外,“思想屋”還提供社區信息,比如參加當地的社團或俱樂部、醫療服務信息等。正可謂無所不包,充分滿足了社區居民及其他利益攸關方的實際需要,以公共圖書館自身各種資源的整合為用戶提供最優化的服務。“思想屋”也由此成為了當地社區文化活動的心臟。
(二)中國的“皇史宬”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是專門保管利用明清兩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檔案的中央級國家檔案館,保管的歷史檔案約1000萬件(冊),在信息化、數字化迅猛發展的新時代,為滿足社會各界檔案利用需求,更好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主動地走向社會、走向世界,向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向廣大人民群眾生動形象地展現明清檔案背后的歷史故事,精心組織了一系列特展、專展,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熱烈反響。并積極開發利用新媒體資源,開通運行“皇史宬”微信公眾號,關注人數和閱讀總量都大幅攀升。還采取多種形式與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檔案機構、學術單位、社會團體開展豐富多彩的合作交流活動,擴大國際影響力。
(三)城市檔案館、圖書館“第三空間”的實踐
城市檔案館、圖書館擁有豐富的館藏資源及各類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資源,擁有相對充足的財政支持以及潛在的巨量用戶數量。因此,在構建文化“第三空間”時,如果能注入超前管理理念和市場意識,引進更多具有時代特色的創新型文化資源和市場力量,找準所在城市的社會公共文化需求切入點,常常能夠先行一步。德州市檔案館積極探索依托資源服務社會的新模式新路徑,大力推動“征進來、走出去”,把大量有地方特色的明清時期史志、族譜、蘇祿王墓史料等珍貴文獻檔案征集進館,并挖掘利用館藏資料,積極組織系列專題展覽,與媒體合作拍攝系列專題片、出版專題書籍、開辦網上展廳,開通德州檔案微信公眾號、門戶網站等多種形式,積極擴大檔案工作社會影響力,參觀人數、進館參訪人數、檔案利用人次均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檔案館已經成為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重要場所。這些公共文化場館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共同性:實現與市民和其他用戶的良好互動,鼓勵他們參與到搜集征集、采購流通、開發利用等決策環節;針對青少年、專業技能人員、老年人、外來務工者等特殊群體展開有針對性的服務,形成本館的特有品牌;組織地方特展、讀書沙龍、專家講座等,實現市民之間的交流分享和專家與公眾之間面對面的對話溝通,構建終身學習、文化休閑的空間;提供良好的人文環境,設立“創客空間”等項目,整合實體資源與虛擬資源,做到對用戶的全媒體資源服務。
六、結語
曾經有人說過,如果想和認識的人聊天,咖啡館是個不錯的選擇;如果想和古人神游或者和不認識的對話,也許檔案館、圖書館算得上是個好去處。當公共文化場館成為了以人為本、以用戶需求為導向、以品牌重塑為抓手的文化“第三空間”時,城市檔案館、圖書館一定會煥發出魅力四射的活力,擔當起社會文化建設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