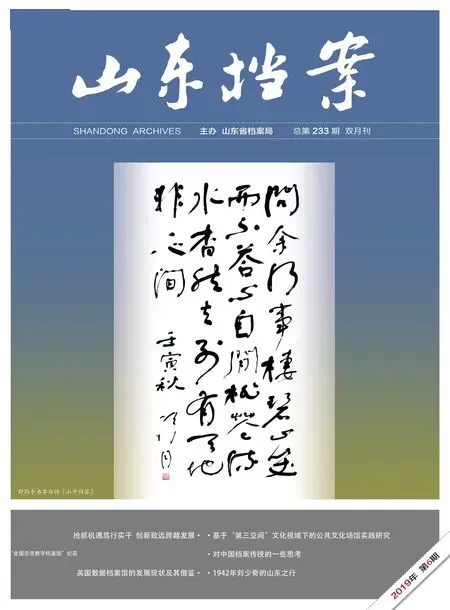對中國檔案傳統的一些思考
文·朱鵬瞻
《現代漢語辭典》對“傳統”一詞的解釋為:傳統是世代相傳、具有特點的社會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現象都能夠連接成傳統,有的文化現象只不過是一時的時尚,它不能傳之久遠,當然不可能成為傳統。”可見,文化不一定都是傳統。那么,檔案文化是傳統嗎?中國存在檔案傳統嗎? 檔案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文化的定義有多種,在《現代漢語詞典》上的解釋為: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而檔案是組織或個人在以往的社會實踐活動中直接形成的清晰的、確定的、具有完整記錄作用的固化信息,它既是人類的物質財富更是精神財富,所以檔案是文化無疑。中國的檔案文化,具體而言,應該是中國國人有意識地保管檔案、利用檔案的現象。這樣,中國檔案文化可否成為中國檔案傳統的關鍵就在于,國人有意識地保管檔案、利用檔案的現象是否是世代傳承的。
一、中國檔案古來有之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古代的檔案在各個朝代有著不同的稱謂。商代稱為“冊”,周代叫做“中”,秦漢稱作“典籍”,漢魏以后謂之“文書”“文案”“案牘”“案卷”“簿書”,清代以后多用“檔案”,今天統一稱作“檔案”。中國的檔案古來有之,檔案歷史可謂源遠流長,檔案實體的傳承性是顯而易見的。比如,中華民族是世界上較早使用“結繩”等檔案的民族,也是較早具有檔案意識的民族。近代發現了甲骨檔案大量集中的遺跡,比如河南的安陽,表明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國先民就有意識地集中保存甲骨檔案,形成了巨大的甲骨檔案庫。周代出現了金文檔案,后來又有了石刻、帛書、竹簡、木牘等形式的檔案,如近代發現的湖北曾侯乙墓竹簡、云夢睡虎地秦代法律簡、山東銀雀山兵法簡、湖南馬王堆竹簡、帛書、居延漢簡以及長期傳留的石鼓文、秦皇刻石等等。東漢發明了造紙術之后,紙質檔案登上歷史舞臺,由于其輕便性和低廉的價格而得到廣泛應用,成為中國檔案的主體,歷經后來的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千多年再到民國,最后一直到今天,經久不衰。其中中國近代發現最早、最重要的古代紙質檔案文書當屬甘肅敦煌和新疆吐魯番出土的經卷和各種寫本,其中敦煌文書形成于公元5~11世紀,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是敦煌文獻中最有史料價值的第一手資料。而現存最豐富和完整的檔案當屬明清檔案,尤其是清代檔案。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的明清檔案共計一千萬件,分成77個全宗,世界罕見。
今天,國人對于檔案早已是司空見慣,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檔案,每個部門都有部門的檔案,檔案分類更加細化,比如文書檔案、科技檔案、專門檔案等,檔案的載體更加多樣,比如紙質檔案、聲像檔案,電子檔案等,傳統載體檔案受到挑戰,但是檔案家族始終存在,并且不斷發展壯大。相信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檔案實體將會更加細化和先進,作用更加廣泛和重要。
二、檔案保管一脈相承
在中國的歷史上,歷朝歷代無論如何更替,都十分重視保管檔案,并且幾乎都設有專門保管檔案的機構,建造了檔案保管庫房,建立了檔案保管制度,盡管名稱各異,但在檔案保管方面的作用是一脈相承的。
檔案保管機構方面,秦始皇統一全國后實行三公九卿制,設諸曹掾屬、少府等職掌文書檔案,西漢初期中央丞相府是收貯王朝重要檔案的機關,東漢為尚書臺,唐代三省為文書檔案工作的最高管理機關,再到宋代的中書門下、金耀門文書庫,明代的中央架閣庫,清代的內閣、軍機處,民國時期的總統府秘書處文牘科,直到新中國的國家檔案局,這些機構雖然在各個時代名稱各異,但均具有檔案管理的職能,對國家政治體制的正常運行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檔案保管庫房方面,封建社會的文書檔案是封建王朝的核心機密,是維系封建王朝生死存亡的命脈,故歷朝歷代統治者無不高度重視檔案工作,這種重視在檔案保管庫房上便可以明顯看出。著名的保管庫房有漢代的石渠閣,宋代的皇帝檔案庫,明代的后湖黃冊庫和沿用明清兩朝的皇史宬等,規模宏大,建筑技術精湛,令人嘆為觀止。到了今天,我們的檔案保管庫房著名的如中央檔案館,館址在北京西郊溫泉白家疃,環境優美,擁有自動化空調、監視、報警、消毒和保護技術設施,負責管理黨和國家中央機關的重要檔案與資料。許多省市也建立了現代化的檔案新館,檔案保管條件大大改善。例如山東省檔案館新館總投資2.65億元,建筑面積4.7萬平方米,集檔案保管、開發、休閑于一身,是泉城濟南的重要文化景觀之一。
檔案保管制度方面,我國歷代的檔案保管制度經歷了一個由不健全到健全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不斷改革創新的過程。富有特色和創新性的檔案保管制度很多,如唐朝的“三年一揀除”制度、宋朝的逐級報送制度和置冊匯抄編錄檔案制度、元朝照刷磨勘文卷制度,清朝的一案一卷制度,其中宋朝的置冊匯抄編錄檔案制度成為我國古代重要的檔案管理制度,宋王朝規定“諸路——州——司條制,各置冊編寫,仍別錄連粘,元本架閣”。可知各級機關文書除原件都要求架閣保管外,還置策抄錄。這種檔案匯抄的制度,同樣也在中央機關實行,如三省也編錄制敕文書和其他重要文書,為以后歷朝歷代所沿襲。到了20世紀初,北洋政府外交部、司法部曾制定《編檔規則》《文件保存細則》,在20~30年代,國民黨政府行政院、考試院、內務部、交通部等曾頒布《保存機關舊有檔案令》《文卷管理規則》《檔案室辦事規則》等檔案保管法規。新中國成立后,檔案保管的法律和制度則更為健全和完善,比如《科學技術檔案工作條例》(1980年),《機關檔案工作條例》(1983年),《檔案館工作通則》(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1987年)等。
三、檔案利用源遠流長
保管檔案的目的是為了利用檔案,為現實需要服務。古代社會利用檔案的表現主要為利用檔案文獻從事編纂活動,包括編纂史書,纂修譜牒和地方志等。
(一)編纂史書
中國歷朝歷代長期地有意識地大量收集和保存前朝及本朝檔案,所產生的直接結果就是為撰寫前代和本朝歷史提供了大量翔實的史料。我國國人在“立德、立功、立言”以及“盛世修書”等思想的影響下,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編書修史的工作中,歷久彌新,久盛不衰,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傳承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假如沒有這一檔案文化,那么中華文明的歷史記錄必將是一個個的片段,至少不可能如此的連續,中華文化明珠的光芒必將不再耀眼。
孔子首先對檔案典籍進行整理和匯編,他“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即刪定六經,六經實際上就是對檔案的整理和編纂。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 其中《尚書》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檔案文件的匯編,是真實嚴肅的正式文書,在世界古老文獻中價值地位重要。漢代杰出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繼父業任太史令,憑借自己豐富的游歷經歷、史官職務可以接觸大量史籍檔案之便以及自己頑強的毅力,前后經過十八年,完成了歷史巨著《史記》。唐太宗李世民時代,我國歷史上正式設館修史制度,此制度從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建立一直沿襲到清朝,直到民國未變。史館征集了大量歷史檔案,在史書編纂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二十四史”中的《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和《北史》都成書于唐朝的史館。宋代利用檔案編修各種史書有顯著的發展,編纂檔案文件機構增多,利用檔案編纂史書的范圍更加廣泛,官修史書成就巨大。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上起春秋下至五代,是我國歷史上重要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其史料的真實性駕于許多正史之上。明清時期則重視利用檔案編纂皇帝實錄以及典章制度。明代編纂《元史》的速度很快,這和明統治者對元朝檔案的收集有關,史評“古今成書之速未有如元史者”。清代修史機構較多,所修國史分作本紀、傳、志、表四種,修有《明史》336卷、《明史紀事本末》80卷、《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等,清朝無論是從修史的次數、成書的數量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民國時期雖然社會動蕩,但是修史同樣沒有間斷,由特設的清史館編修的、倉促問世的《清史稿》雖然存在許多缺陷,但仍然是今日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價值的史書。2004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文化工程——《清史》編纂工程的主體工程正式啟動,可以說是我國這一檔案文化的延續。
(二)纂修譜牒
譜牒亦叫家譜,是一種特色檔案,修譜之風的盛行是我國檔案文化的一大特色,“自商代至民國,上至帝王,下至庶民,從城市到鄉村,從漢族到眾多少數民族,都十分重視編修譜牒,并且多對譜牒懷有一種極其崇敬的心情。”可見,譜牒在我國漫長歷史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國譜牒檔案源遠流長,有確切證據的譜牒要屬商代的甲骨譜牒,從目前的考古發現得知,我國先人發明文字之后,中國出現了現存最早的一種以文字記載為形式的譜牒——距今4000年前商代的甲骨譜牒,這種譜牒被刻在了龜甲和獸骨之上,記載了殷王世系以及祭祀祖先的祭祀譜,雖然它只記世系和人名,沒有事跡,但這已經足以證明這是譜牒無疑,之后又出現了青銅譜牒、碑譜、紙譜等。周、秦、漢朝是中國譜牒檔案的發展階段,國家設立專官專司“掌譜牒、定世系、辨昭穆”之職,還出現了西漢的《帝王年譜》和東漢的《鄧氏官譜》兩部譜書。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譜牒的黃金時代,譜牒數量激增,譜諜種類繁多,譜學名家相銜而出。到了唐宋,中國譜牒檔案繼續發展但由盛轉衰,明清時期中國譜牒檔案再度興盛。直到今天,家譜對于大多數國人也并不陌生,修譜和續修譜牒的活動在一些地區仍然存在。譜牒促使以家庭家族為核心的宗族社會成為古代中國社會的基礎,無論朝代如何更替也改變不了宗族社會的存在,宗族社會的源頭是原始氏族,而譜牒檔案及譜牒檔案文化則是維系宗族社會最強大的支柱。
(三) 編修地方志
我國現存地方志文獻為10000種左右,地方志相當于地方百科全書。撰寫國家歷史必須利用檔案為資料基礎,方志作為地方性史地之書,其撰寫同樣需要利用檔案。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編修地方志的活動歷傳不輟。先秦時期,方志尚處于萌芽狀態,清代學者章學誠認為先秦時期的晉國的《乘》、魯國《春秋》、楚國《梼杌》是方志的源頭,但目前所知最早的方志是《禹貢》《周禮》和《山海經》。漢朝為有效控制全國,開始編纂各地的方志,著名的有《越絕書》和《吳越春秋》,二書開創專史體例,成為地方志書的先導。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豪族勢力擴大,相繼產生了大量內容和體例不同的方志。隋唐時期,官修全國性區域志開始,地方志走向成熟,門類詳備,有圖有經,現存最早的地方志《沙州圖經》和《西州圖經》就是撰修于此時。宋代是我國方志發展的重要時期,方志內容、體例、名稱、編撰宗旨等都發生變化,出現創新。修志到了明清進入全盛時期,明初僅全國性區域志的編修前后就達四次之多,清代中央政府下令撰修一統志,是中國方志史發展的里程碑。新中國成立后,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倡議,全國各地要修地方志,編修地方志被列入國家議事日程,修志之風方興未艾。
總之,中國的檔案古來有之,中國歷來注重保管檔案,歷來重視利用檔案,中國的檔案文化是一脈相承的,并且形成了中國檔案傳統。這是一個偉大的傳統,因為這一傳統,我們的國家留下了歷史,地方有了志書,家族有了譜牒,中華民族有了清晰的記憶,這一傳統在傳承中華文化、維護社會穩定、增強民族凝聚力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歷史不容忘卻,它為我們面對現實,迎接未來提供了一面可供借鑒的鏡子;檔案傳統不容丟棄,它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我們要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改革其中的保守和落后因素,科學地保管和利用檔案,提高社會檔案意識,加快檔案開放步伐,迎接科技革命的挑戰,滿懷信心地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