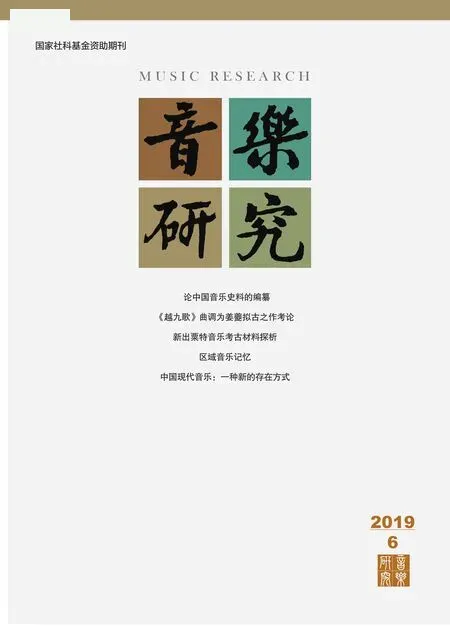中國現代音樂:一種新的存在方式—井岡山“中國當代音樂創作研討會”的啟示
文◎李詩原
2019 年8 月24—27 日,策劃、籌備已久的“中國當代音樂創作研討會”在井岡山市茨坪鎮召開。研討會開了兩天兩夜,分六個單元集中研討了六部作品:代博的管弦樂《看不見的山》(2014);許舒亞的管弦樂《百川歸海》(2019);姚晨的《牧云圖》(為笛、二胡、中阮和古琴而作,2016);秦文琛的《對話山水》(為錄音帶和管弦樂隊而作,2010);郭文景的《川崖懸葬》(為兩架鋼琴與管弦樂隊而作,1983);溫德清的弦樂四重奏《潑墨二》(2017)。與會者除上述六位作曲家外,還有全國部分院校從事作曲技術理論及當代音樂教學、研究的教師:王旭青(缺席但有論文宣讀)、石磊、朱赫、安魯新、熊小玉、紀德綱、鄒彥、張寶華、周杏、鄭艷、班麗霞、夏滟洲、黃宗權、蒲方和魏明,特邀嘉賓李吉提、劉康華和蔡喬中(缺席)。會議主辦單位是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江西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策劃者是向民、任方冰、熊小玉;主持人是向民、任方冰和筆者。本次研討會不拘形式、不走套路,特別集中、特別純粹,問題探討極深、學術含量極高,頗有“沙龍”氣息。透過此次研討會,筆者似乎看到了當下中國現代音樂的存在方式,洞察到了一種新的學術動態,領略到了一種新的學風,聞到了一種新的“學院派”味道。
一、有現代音樂,無現代音樂思潮
自有現代音樂以來,“現代音樂終結論”就不絕于耳。但現代音樂卻是只“不死鳥”,至今還活著,且還飛得很高。阿多諾《現代音樂的哲學》(1948)曾將現代音樂比作一艘即將沉沒的“船”所發出的“浮瓶信息”,并認為現代音樂“否定了自身對美的幻覺”,以致“絕望地被忘卻”,最終如同“一顆啞火的子彈”,“正無聲無息地死去,甚至連一聲回響也沒有”。①參見于潤洋《“浮瓶信息”引發的思考》,《人民音樂》1995 年第6 期,第18 頁。于是后來便有這樣的詮釋:“阿多諾在西方現代音樂的前途和命運面前”表現出“困惑和悲哀”②同注①,第19 頁。;“在他看來,20 世紀的現代音樂所面臨的卻是一場異常深刻的、真正的危機”③同注①,第18 頁。。但現代音樂并未像阿多諾預料的那樣“無聲無息地死去”(好在他內心并不情愿它死去),而自在地活著,不過是不再以“主義”和“流派”而存在。這支“浮瓶”仍漂在海面上。一個多世紀以來,仍在傳遞著“帝國主義”即將滅亡的信息——“浮瓶信息”。從第一首無調性音樂(勛伯格1909 年的《鋼琴曲三首》)算起,現代音樂在西方已有110 年的歷史,和它用“異在”方式所揭示的帝國主義一樣,垂而不死。前60 年可謂主義頻出、流派林立,標新立異,無奇不有;但自1969 年后的50 年,總體平靜,局部活躍,且仍是專業音樂發展成就的標識。從喧囂轉向平靜,作為一種發展狀態或規律,在中國也能找到其注腳。從1979 年算起,中國現代音樂,也有從喧囂轉向平靜的前后兩個發展階段之分。前20 年,有現代音樂,有現代音樂思潮,也有旨在推動“審美時空革命”的現代文藝思潮,還有支撐現代文藝思潮的思想解放運動。于是現代音樂的產生,現代音樂思潮的崛起,成為早期(1949 年以前)中國現代音樂的接續,成為針對現代音樂1949—1979 年發展中斷的“補課”。后20 年,現代音樂在經歷“新潮”和“后新潮”的激蕩和奔涌后,趨于平靜,歸于常態,雖然不再展現出“語不驚人死不休”“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三五天”的發展態勢,但也未呈現“一顆啞火的子彈”,“無聲無息地死去”,而給人“深潮動若寐”的跡象。的確,后20 年不但有現代音樂,且佳作頻出,技術更成熟,一些“體系性”作曲技法(如勛伯格的“十二音技法”④參見鄭英烈《十二音技法在中國音樂作品中的運用》,《音樂研究》1986 年第1 期。、興德米特“二部寫作技法”、巴托克“調式半音體系”⑤參見楊通八《調式半音體系與和聲的現代民族風格》,《中國音樂學》1986 年第3 期。)在中國得以延伸和發展;在現代音樂分析中較為奏效的阿倫·福特“音級集合理論”在中國更被用得出神入化。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后20 年有現代音樂,卻無現代音樂思潮,中國現代音樂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沒有“宣言”的時代。
當然,新世紀的現代音樂活動十分頻繁。旨在推介現代音樂作品的“北京現代音 樂 節”(Beijing Modern Music Festival)已辦17 屆;“上海當代音樂周”(Shanghai New Music Week)已辦12 屆;“中國—東盟音樂周”(China-ASEAN Music Festival)已辦8 屆。除這三個分別由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廣西藝術學院舉辦的常規性(一年一度)現代音樂節外,還有從20 世紀延伸至21 世紀的現代音樂活動,如“中青年作曲家新作品交流會”⑥天津國際現代音樂節暨全國中青年新作交流會,天津音樂學院,2001;成都國際現代音樂節暨中青年作曲家新作品交流會,四川音樂學院,2003;全國中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會,上海音樂學院,2015;全國中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會,西安音樂學院,2017。、“京、滬、閩現代音樂創作研討會”(第三屆至第七屆)。此外還有一些冠名“現代音樂”“當代音樂”“新音樂”的音樂節,如“武漢國際新音樂節”(2007)、“秋之韻——成都當代音樂節”(2012)及曾發布不少了現代音樂作品的“北京國際音樂節”(BMF,自1998 年起已舉辦22 屆)等。上述這些活動,雖然推出了一大批現代音樂作品,但卻不再具有“一石激起千層浪”⑦此為對1985 年4 月22 日“譚盾民族器樂作品音樂會”的評論,見《中國音樂學》記者《一石激起千層浪——“譚盾民族器樂作品音樂會”座談會簡述》,《中國音樂學》1985 年第1 期。,帶動一個潮流,掀起一道波瀾,引發一場爭論的效應,最終也只能是部分學院派作曲家的狂歡和盛宴,甚至就像此次研討會一樣,成為一種沙龍性音樂活動。這些現代音樂活動事后之所以悄無聲息,除舉辦方和參與者未能提出一些宣言或口號之外,⑧現代藝術是需要“宣言”的。在進入新世紀后的中國現代音樂發展中,不乏單個作曲家音樂思想和觀念的表達,但群體的“宣言”或“口號”并不多見,只有2008 年第一屆“上海當代音樂周”舉辦時曾提出一個“沒有當代,就沒有未來”(No Today,No Future)的口號。參見李鵬程《“上海當代音樂周”九年回眸》,《上海藝術評論》2017 年第3 期,第21 頁。音樂理論界的漠視和淺釋,也是其重要原因。這些都是后20 年“有現代音樂,無現代音樂思潮”的征兆。
2017 年,一篇回顧前9 屆“上海當代音樂周”的評論中曾有這樣一個小標題:“驚雷:于無聲處崛起的中國當代音樂”,旨在用“于無聲處動驚雷”的詩句暗示“上海當代音樂周”或能像1978 年上海的四幕話劇《于無聲處》和1991 年荷蘭的“中國現代音樂會”⑨這場音樂會于1991 年4 月2 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荷蘭新音樂團(Nieuw Ensemble)演奏了瞿小松的《寂I》、 譚盾的《圓》《距離》、陳其鋼的《水調歌頭》、莫五平的《凡I》《凡II》、許舒亞的《秋天的落葉》、何訓田的《幻聽》和郭文景的《社火》,后發行唱片(CD)《中國新音樂》(New Music of China,1992)。基于這場音樂會的影響,荷蘭導演菲利普斯(Eline Flipse)拍攝了80 分鐘的紀錄片《驚雷》(De oogst van de stilte,1995),記錄了莫五平、陳其鋼、譚盾、何訓田、瞿小松五位中國作曲家的生活和音樂。一樣,平地響起一聲“驚雷”,進而引發出一股文藝新潮,讓人們從內心發出一聲驚嘆。⑩李鵬程《“上海當代音樂周”九年回眸》,《上海藝術評論》2017 年第3 期,第20 頁。但事實并未像這位評論家期待的那樣,即便響起了“驚雷”,但也總是“干打雷,不下雨”,未能促成一波新的現代音樂思潮。其實,早在20 世紀末就已顯露“不打雷”或“干打雷,不下雨”的尷尬。1998 年11 月于武漢舉辦的“中青年作曲家新作品暨作曲教學經驗交流會”,本希望能像1985 年12 月的“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會”那樣,托舉一批青年作曲家,給中國樂壇帶來一股沖力,使剛剛進入市場經濟時代的現代音樂走出疲軟,并帶來一波跨世紀“行情”,但最后還是事與愿違,以致后來天津、四川、上海、西安的“新作品交流會”,都未見“驚雷”,或有“驚雷”,卻無“喜雨”。但愿今年10 月浙江音樂學院舉辦的第七屆“全國中青年作曲家新作品交流會”能借助錢塘江的潮汐,有所作為。其實,有現代藝術,無現代藝術思潮,也是整個中國現代藝術的發展狀態。朦朧詩、意識流小說、荒誕戲劇、新潮美術、探索電影,雖仍以各自的方式存在,但卻都展露出散兵游勇、單兵作戰、孤芳自賞的發展狀態。
為何有現代音樂,無現代音樂思潮?這里不妨從“潮”和“思潮”說起。第一個將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稱為“新潮”的王安國曾說:“‘潮’,可解釋為一定量的 動態。”?王安國《我國音樂創作“新潮”縱觀》,《中國音樂學》1986 年第1 期,第4 頁。但后20 年的現代音樂有“動態”,但其“量”卻明顯不足,或只有散點動態,而未能同頻共振,形成聯動效應。所謂思潮,就是“某一時期內在某一階級或階層中反映當時社會政治情況而有較大影響的思想潮流”?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6 版),商務印書館2014 年版,第1230 頁。。據此,前20 年的中國現代音樂思潮就可表述為:1979 年以來,中國作曲家在反傳統、創新精神驅動下,通過借鑒現代作曲技法回應思想解放運動的思想潮流。正是憑借解放思想的力量,德彪西“平反”了;現代音樂也不再是“形式主義”了,故而便有一股基于“反彈”的現代音樂思潮。這也就不難發現為何后20 年沒有現代音樂思潮了,因為在今天的中國,“日丹諾夫的幽靈”也過去了,中國作曲家可自由創作現代音樂且不受干涉、指責和批判,故無須借助解放思想、形成一股思潮進而去抵御、去反駁那種“異己”的力量。這在一定意義上也表明,中國現代音樂進步了,即便失去那種“反異化”語境,它仍能存在,并佳作頻出。當然,中國作曲家也可像阿多諾所推崇的勛伯格一樣,和西方作曲家一道,作為“進步”力量,用無調性音樂發出“浮瓶信息”,表現出基于“地球村”或國際視野的批判意識。此次研討會上的作品展露出的,正是這種意義上的批判意識。如秦文琛的《對話山水》和代博的《看不見的山》,就不再像郭文景的《川崖懸葬》那樣,只是一部針對中國的“現實主義作品”(郭文景語),而將視角指向了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其國際視野的批判意識顯而易見。由此可見,像前20 年一樣,后20 年“有現代音樂,無現代音樂思潮”首先是歷史的選擇。
后20 年沒有形成現代音樂思潮的另一個原因在于,現代音樂似乎未能得到理論界的深度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理論家的缺位。一股音樂思潮或一個音樂流派的形成,需要作曲家,也需要音樂理論家。或許有人會說,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極其通暢的網絡時代,所有現代音樂活動的信息都能在手機上搜索到,有報道、有樂評,關注度極高。但這些報道和樂評,也多為就事論事的個案,而非深度關注。故這些信息及其所指涉的音樂作品,最終都難以成為一個“互文本”(intertext),并讓讀者(手機持有者)獲得其“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進而就難以匯聚成一種對后20 年中國現代音樂的整體認識和把握。由于理論家的缺位,沒有宏觀理論家的總結、提煉和托舉,其與作曲家形成對話和互補更無從談起。當年提出“音樂新潮”這一概念并對其進行整體性、持續性深度觀測的王安國,將更多的精力投向了音樂教育;發起現代音樂“四人談”?李西安、譚盾、葉小綱、瞿小松《現代音樂思潮對話錄》,《人民音樂》1986 年第6 期。此文成為“現代音樂思潮”的最早表述。的李西安,其關注點也較多,盡管其中仍不乏學院派作曲家的創作;曾倡導“觀念更新”,為“新潮”一辯的居其宏,更關注歌劇了;建立“異化”和“反異化”這組二元對立的戴嘉枋也將視角轉向整個20 世紀中國音樂;曾密切關注海外華人現代音樂創作的梁茂春,則對“音樂史的邊角”產生了興趣。或許因為如此,面對后20 年的中國現代音樂,理論界更多是個案分析和研究,并無總體的觀測、總結和歸納,更無“觀潮”的高度和境界。在一定意義上說,理論家們再也無須現代音樂去為他們曾經的那些反思性理論構建提供注腳和依據了。此其一。其二,其中的這些并不是“學院派音樂批評”(academic music criticism)的樂評,而是放逐了旨在區分本質與現象、能指與所指的深度模式?這里所說的“深度模式”,即杰姆遜所說的“深度模式”——第一種深度模式基于“黑格爾或者馬克思的辯證法”,區分“現象與本質”的深度模式;第二種則是弗洛伊德區分“明顯”和“隱含”的深度模式;第三種是存在主義區分“確實性和非確實性”的深度模式;第四種為“所指和能指”構成的深度模式。,最終在“平面化”表述中成為一種缺乏思想深度的后現代敘事?關于這種批評“平面化”及其后現代性,參見李詩原《批評平面化形象的哲學反思》,載田可文編《那些年,我們一起走過——田可文與他音樂學的學生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這種缺乏深度模式的后現代敘事,難以形成關于中國現代音樂的總體值取向,也難以讓人們獲得關于現代音樂的共識,并引起他們對現代音樂的深度關注,進而讓其感覺到思潮的客觀存在。
不難發現,21 世紀以來,以現代音樂創作為研究對象的碩、博論文也多涉及后20 年的現代音樂創作。這些學位論文雖然都聚焦一部作品或一位作曲家,甚至集中在一種作曲技術手段上,體現出從“小”處著眼的選題原則,但卻未能做到“小題大做”“以小見大”。這種只注重內在性(immanence)而無超越性(transcendence),只注重小型敘事而無視元敘事,只注重零散性、差異性而無視整體性、同一性的分析和研究,也囿于平面化和內在性局限,成為后20 年未能形成現代音樂思潮的另一重要因素。總之,理論界的無深度關注是“有現代音樂,無現代音樂思潮”的重要原因。一股音樂思潮需要一個由作曲家和理論家組成的共同體。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一種有共識、有宣言的時代,進而使音樂創作呈現出一種基于宣言的價值取向和訴求。但當下的作曲家大多作而不述,這無疑也是缺乏宣言、難以形成思潮的重要原因。如果每位作曲家都能像朱踐耳那樣,每部作品都寫創作札記,最后形成一本厚厚的“創作回憶錄”?朱踐耳《朱踐耳創作回憶錄》,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 年版。,像王西麟那樣,既有音樂表達又不乏語言和情緒的表達,那么思潮在理論家缺位的前提下也是可以存在的。此次參會的作曲家們都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了較深入的闡述,并與理論家的分析、研究形成了對話和互補。那么,此次與會的作曲家和理論家會不會成為一個“群”,而不只是那個為開會而建立的“微信群”?
應當承認,有思潮或許就更有激情,更有推動力,更有群體意識,進而就能推動現代音樂創作的整體突進、集體沖鋒。但沒有現代音樂思潮、沒有群體意識、無須得到某種社會和文化力量的推動,仍有現代音樂,似乎更顯得進步和成熟。這種進步和成熟就在于,現代音樂創作已成為當下學院派作曲家的一種常態,或是當代專業音樂創作的一種常態。難怪“現代音樂”(modern music)在今天已多被“當代音樂”(contemporary music)替代。此次井岡山研討會的會標用的就是“當代音樂”。盡管在許多語境中,“現代音樂”和“當代音樂”的所指一致(在西方語境中,“modern music”與“contemporary music”可相互替代),但實際上也有不同(如范圍大小,時間先后),尤其是當“近代”“現代”“當代”三個詞置于同一語境時,就有時間上的先后之分。但根本區別在于,“modern music”與“現代性”(modernity)、“后現代性”(postmodernity)密切相關;“contemporary music”則更多是現時代(當下)所有音樂的總稱,而無關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換言之,“現代音樂”更主要是一個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相關的美學概念,“當代音樂”則更主要是一個著眼“當下”且較之“過去”的歷史概念。既然“當代音樂”已替代“現代音樂”,且二者可以互換,那么打破“共性寫作原則”的現代音樂,不過是現時代音樂中的一種常態化音樂;至于說它是否與“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相關,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對于學院派作曲家而言,現代音樂創作即便是一種特別的價值追求,也如同家常便飯,無須再去標榜為“新潮”,無須再以“先鋒派”自居。現代音樂既非“潮兒”,也非“怪胎”,一切似乎都常態化了。但也應看到,不再依托思潮的現代音樂,似乎永遠是“單數”的,或是一種“私人性”的東西,故仿佛放逐了一些意義和價值。這雖然是現代音樂的一種進步和成熟,但其“單數”或“私人性”都會導致許多作品最終難以成為一個“互文本”或“總體本文”(total text),進而使其指涉、隱喻及其批判精神大打折扣。總之,“有現代音樂,無現代音樂思潮”,其原因就在于后20 年的現代音樂作品,不能像前20 年的作品那樣,總是一個與其他文本形成“對話”、構成“間性”的“互文本”,并呈現出依托中國現代音樂思潮乃至中國現代文藝思潮、思想解放運動這一總體語境(context)的“互本文性”。
二、現代音樂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后20 年的中國現代音樂已呈現新的存在方式,不僅不再依托思潮而存在,還表現出不同的文化姿態,扮演著不同的文化角色,承載著不同的文化功能,呈現出不同的意義和價值。
(一)作為學院派作曲家文化身份的重要標識
如前所言,創作現代音樂作品,對于一位學院派作曲家而言,已不再是反傳統和標新立異,甚至不能說是一種創新,更不是彰顯主體意識的“反異化”行為,它與運用古典作曲技法一樣,都是作曲家的一種存在方式或生存狀態。在今天這樣一個市場經濟時代,學院派作曲家游走在現代音樂與大眾音樂之間,不可能總在寫現代音樂,而需要創作一些實用性、商業性較強的音樂,寫一些“命題作文”。但值得注意的是,學院派作曲家大多并沒有在學術性寫作和商業性寫作之間“搞折中”“搞變通”,而是涇渭分明。因為他們深知,過于學術的作品是沒有商業價值的,過于商業化的作品也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推向音樂學院講堂和國際音樂舞臺。當然,將學術性或現代技法滲透至商業性音樂并仍能達到商業目的,可能性也不大。在這種前提下,既接受商業性委約,又不放棄現代音樂,無疑是學院派作曲家的最佳選擇。這也是在商業時代現代音樂依然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對于一些作曲家而言,創作一些實用性、商業性作品,并非“為稻糧謀”,而旨在呈現其音樂風格多元化,故采取了與創作現代音樂同樣嚴肅的學術態度。比如,郭文景既寫《狂人日記》《夜宴》這樣的現代室內歌劇,又創作《駱駝祥子》這種較傳統的歌劇。他寫《駱駝祥子》用了三年時間,且在三年中沒有寫別的作品,可謂專心致志。故《駱駝祥子》贏得更多人的肯定,但也不失其學術性。這何樂而不為?總之,學院派作曲家與現代作曲家之間無須畫等號,其音樂創作是多元化的。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盡管任何技術或風格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如果一位學院派作曲家只是或只能“為稻糧謀”,那是會受到詬病的,就會被認為是有悖“學院派作曲家”這一文化身份而成為“笑柄”。因此,創作現代音樂作品,是當下“學院派作曲家”這一文化身份的重要標識。在一定意義上說,能否嫻熟掌握并運用現代作曲技術(即使掌握了但不用),在當下已成為檢驗學院派作曲家的試金石或“潛規則”。況且,當今世界一些重要的作曲比賽和重要的音樂節,仍是現代音樂的角逐或展示之地,并未因現代音樂“否定了自身對美的幻覺”而有所改變。換言之,現代音樂創作水平仍代表著一位作曲家(或一個國家、地區)的學術水平。現代音樂作為“學院派作曲家”這一位文化身份的重要標識,正是后20 年中國現代音樂存在的一種意義和價值;現代音樂探索和創新也仍是學院派作曲家一種重要的價值實現。當下中國的現代音樂也正借此而繼續存在。
(二)作為專業音樂院校作曲專業的一種技術訓練
將現代風格音樂創作作為專業音樂院校作曲專業學生的一種技術訓練,始于20世紀80 年代,它一直是催生和推出現代音樂作品的重要途徑。此次所研討的《川崖懸葬》就是郭文景大學時代的畢業作品,也是第一部在國外演出的中國現代音樂作品;譚盾在國際比賽中獲獎的弦樂四重奏《風·雅·頌》(1982)也是其大四時創作的作品。進入新世紀,現代音樂創作仍是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等專業音樂院校作曲專業常規的技術訓練手段。尤其在碩士、博士階段,現代音樂創作更是重要的教學內容。此次參加研討的《看不見的山》,即代博攻讀博士學位時創作的作品,于2014 年獲“貝多芬協會國際作曲比賽”第二名。
現代音樂從創意、構思到創作,往往對作曲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創作也往往因此受到更多的限制,故更能使一位作曲家受到歷練。將現代音樂創作作為一種技術訓練,其意義不只是在于創作現代音樂,也十分有利于傳統風格作品寫作,甚至對大眾音樂創作也不無裨益。那些曾經歷現代音樂訓練的作曲家,其傳統風格的作品往往也略勝一籌。相反,那些較少接受現代音樂訓練或根本不涉獵現代音樂的作曲家,創作的作品也都較為平庸,他們的交響樂和歌劇等大型作品在技術上更顯得捉襟見肘。郭文景的《駱駝祥子》之所以強于當下其他歌劇,與他長期的現代音樂實踐不無關系。張千一的歌劇《蘭花花》、民族管弦樂組曲《大河之北》、交響套曲《我的祖國》不僅廣受好評,而且技術上也可圈可點,就因為他曾創作許多現代音樂作品(如2019 年6 月23 日北京音樂廳演出的《大提琴協奏曲》),并受到嚴格的現代作曲技術訓練。推出高品位流行音樂(如《阿姐鼓》《央金瑪》)的何訓田,也曾發明了“R·D 作曲法”?關于何訓田的“R·D 作曲法”及《天籟》,參見思銳《實驗性·任意律·對應法及其他——析〈天籟〉》, 《人民音樂》1989 年第2 期。并創作了《天籟》《平仄》等現代音樂作品。同樣,劉健的《盤王之女》之所以是一張高品位、發燒級流行音樂唱片,也是因為這位已故作曲家長期的學院派電子音樂實踐。這些都是現代音樂歷練作曲家的例子。總之,現代音樂對于技法訓練的意義,也決定了現代音樂在當下的存在。
(三)作為滿足部分受眾審美口味的小眾藝術
絕大多數人并不真的喜歡聽現代音樂,中國如此,西方也如此;過去如此,現在更如此。現代音樂作為與生俱來的小眾藝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像阿多諾所說的,“現代音樂把絕望地被忘卻看作是自己的目的”?轉引自注①,第18 頁。。這也是現代音樂在世界各國都曾受到詬病、指責乃至批判的重要原因。中國現代音樂也自始至終沒有指望得到大多數人的喜歡和理解,甚至采取了一種“管你聽不聽”的態度,故一開始就不得不接受“可聽性”的拷問。當年譚盾《離騷》(1979—1980)序奏中的那個高疊和弦就曾引起非議。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聽眾的耳朵在經歷40 年的“挑戰”和“轟炸”后有了更多的適應性。今天許多看上去很常見、很實用、很通俗的音樂,都比譚盾的《離騷》要“現代”得多。
至20 世紀90 年代中后期,國人對現代音樂的接受已有了較大的提高,形成了一批知識界聽眾。這本應成為中國現代音樂得以發展的受眾基礎。但進入21 世紀后,一種新的音樂審美觀就悄然形成——“好聽”成為判斷一切音樂的價值標準。伴隨著中產階級迅猛崛起,感官享受(快感)越來越成為一種務實和流行的審美經驗和價值判斷,于是好聽、好看、有趣、易解逐漸成為市場經濟法則前提下的審美標準。同時,小說、詩歌越來越通俗,戲劇、舞蹈越來越市井,影視、繪畫則不斷制造所謂“視覺盛宴”和“饕餮大餐”。在這種境遇下,一些原本看好和支持現代音樂并能在其中找到“自我”的知識階層(甚至也包括一部分音樂家)的審美觀也悄然不再。許多人似乎猛然間發現,音樂原本即一種訴諸聽覺的藝術,“好聽”才是判斷音樂好壞的鐵理,才是最本質的音樂審美標準。更重要的是,對于許多聽眾而言,似乎再也沒有什么必要透過現代音樂那種艱澀、刺耳的音響,去發現一些什么,聯想一些什么,思考一些什么,反思一些什么,批判一些什么。物質豐富了,日子越來越好了,就沒有必要去體味那種“朱踐耳式的反思”和“王西麟式的痛苦”,更沒有“沒有義務”去“分食”現代音樂這顆“西方特定社會歷史文化結下”的“苦果”的“苦澀”。?參見注①,第20 頁。總之,現代音樂的聽眾群在“好聽”的審美價值認同中不斷減少,于是現代音樂就只能是一種小眾藝術。時至今日,現代音樂仍受到“可聽性”的嚴峻挑戰,并在“好聽”成為唯一審美追求的快餐文化時代,如同白酒中的瑯琊臺、雪茄中的玻利瓦爾(Bolivar)、咖啡中的埃斯普雷索(Espresso),只能是滿足少數人的“重口味”。但可貴的是,學院派作曲家們不怕被冷落,仍孜孜不倦地創作現代音樂,并不斷滿足著這一小部分聽眾的“重口味”。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進步和成熟。
(四)作為國際視野和文化自信的表征
中國現代音樂思潮的崛起曾有兩股推動力:歷史反思和走向世界。歷史反思得益于思想解放運動;走向世界則來自改革開放和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慣性。正是在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下,中國現代音樂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憂患意識和批判意識。如《川崖懸葬》作為一部創作于1983 年的作品,就充分表達出了一種基于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的憂患意識。郭文景曾說,《川崖懸葬》雖然是一部寫古代僰人“懸葬”的作品,但卻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創作時受到羅中立《父親》的影響。在那苦澀、尖厲的聲音中,我們仿佛看到了油畫刻畫的這位大巴山農民。在前20 年的現代音樂中,這種歷史反思得以充分表達。這即所謂“鐘信明式的思考”(《第二交響曲——獻給人類文明的開拓者》)?參見鐘信明《〈第二交響曲〉的創作思維及有關問題》,《黃鐘》1991 年第1 期。、“王西麟式的痛苦”(《第三交響曲》)?? 參見王西麟《從“云南音詩”到“第三交響樂”——我的美學歷程》,《現代樂風》(內部刊物)第18 期。? 同注?,第11 章。? 參見劉經樹《崛起的一群,迷惘的一群——評音樂新潮》,《人民音樂》1988 年第1 期,第11 頁。? 參見管建華《新音樂發展歷史的文化美學評估》,《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5 年第1 期,第23 頁。、“朱踐耳式的反思”(《第四交響曲——為竹笛和22 件弦樂器而作》)?? 參見王西麟《從“云南音詩”到“第三交響樂”——我的美學歷程》,《現代樂風》(內部刊物)第18 期。? 同注?,第11 章。? 參見劉經樹《崛起的一群,迷惘的一群——評音樂新潮》,《人民音樂》1988 年第1 期,第11 頁。? 參見管建華《新音樂發展歷史的文化美學評估》,《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5 年第1 期,第23 頁。。這種類似“鐘二、王三、朱四”的作品還有很多,都旨在進行基于中國的歷史反思,并非在“分食”西方“先鋒派音樂”這顆“苦果”的“苦澀”,而有著自身的切膚之痛。這也意味著,中國也具有產生現代音樂的文化土壤,中國也需要勛伯格那種用“異在”的方式揭示某種社會本質、“否定了自身對美的幻覺”以致“絕望地被忘卻”的現代音樂。在井岡山,筆者曾就這個問題試探性地問郭文景:“現代音樂是否不再需要那種歷史反思?”可他說:“這種反思很重要。”然而,在后20年的現代音樂中,這種歷史反思不多見了,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種基于“地球村”的國際視野——面對整個人類生存狀態的文化批判意識和社會責任擔當。這種諸如對戰爭、環境、倫理等全球化問題的思考,作為一種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關懷,似乎更為可取。例如,秦文琛的《對話山水》,其錄音帶中的聲音,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最真實的自然界的聲音”。正是這些自然之聲,與樂曲開始處的“警鐘”一起,反映出作曲家對當今世界共同面臨的環境問題的思考。這種基于“人與自然”古老二元關系的人文關懷,不僅是一種“胸懷祖國”的考慮,更是一種“放眼世界”的國際視野。
后20 年中國現代音樂的國際視野,還體現在在技術觀念和運作方式上,即對“國際慣例”的遵循。例如,一部音樂作品首演時往往都要注明“中國首演”或“世界首演”。這似乎是“國際慣例”。其中,“中國首演”意味著此作還將在世界其他地方首演;“世界首演”則表明在中國首演地(如北京、上海)也是世界的一角。二者皆為國際視野,更重要的是美學和文化意義上的國際視野。這主要在于,其民族性已逐漸被中國性替代的趨勢。所謂民族性,即基于中國傳統音樂和傳統文化的特性;所謂中國性(Chineseness),既包括民族性,又包括中國作曲家現代作曲技術運用的個性所建構的特性。如果說民族性更多體現為中國傳統音樂、傳統文化的特殊性,那么中國性則主要訴諸現代作曲技法的普遍性。一言蔽之,當下作曲家們已不滿足于用本土傳統音樂語言或傳統文化符號去證明自己作為“中國作曲家”的文化身份,而更希望依托現代作曲技法上的個性去構建作為“中國作曲家”的文化身份。這更是一種國際視野的體現。中國現代音樂思潮在20世紀80 年代的崛起,更是以走向世界為契機和動力的。曾幾何時,幾乎所有作曲家都希望得到世界的認同和肯定。難怪有人說,中國現代音樂不過是拾人牙慧,“解決不了它的文化歸屬”?? 參見王西麟《從“云南音詩”到“第三交響樂”——我的美學歷程》,《現代樂風》(內部刊物)第18 期。? 同注?,第11 章。? 參見劉經樹《崛起的一群,迷惘的一群——評音樂新潮》,《人民音樂》1988 年第1 期,第11 頁。? 參見管建華《新音樂發展歷史的文化美學評估》,《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5 年第1 期,第23 頁。;接著又有人說,中國現代音樂掉入西方預設后殖民“陷阱”?? 參見王西麟《從“云南音詩”到“第三交響樂”——我的美學歷程》,《現代樂風》(內部刊物)第18 期。? 同注?,第11 章。? 參見劉經樹《崛起的一群,迷惘的一群——評音樂新潮》,《人民音樂》1988 年第1 期,第11 頁。? 參見管建華《新音樂發展歷史的文化美學評估》,《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5 年第1 期,第23 頁。。 盡管這些批評(尤其是所謂“后殖民批評”)并不客觀且有理論上的缺陷,?? 參見李詩原《當代音樂批評中后殖民話語評析》,《黃鐘》2009 年第3 期。? 分別參見劉紅柱《紐約林肯藝術中心響起中國聲音——記2018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家新作品世界首演音樂會》,《人民音樂》2018 年第4 期;《2018 年中央音樂學院管弦樂新作品音樂會美國卡內基音樂廳首演》,《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8 年第4 期。? 這個英文表述來自姚亞平《于潤洋音樂學分析思想探討》,《音樂研究》2008 年第1 期,第56 頁。但另一方面也顯露出中國現代音樂在走向世界的價值認同中,的確受到了西方的牽引。但后20 年的情況就大不一樣。我們已看到,在經歷前20 年的現代音樂“補課”后,“第五代作曲家”不再是被人指指點點的“青年作曲家”,而都成為成熟、穩健的中老年作曲家,并在國際音樂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一些人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級作曲家。我們也能看到,自21 世紀初以來,北京、上海等城市已成為世界現代音樂的中心。“北京現代音樂節”“上海當代音樂周”等現代音樂節,都曾吸引許多現代音樂大師和一些頂級樂團的響應和參與,而不再是中國人的自娛自樂。第16 屆“北京現代音樂節”還有“國際現代音樂協會”的到訪和參與;剛剛結束的第12 屆“上海當代音樂周”(9 月13—18 日)也有馬克·安德烈(Mark Andre)等當今世界頂級現代作曲家的身影。我們還能看到,2018 年1 月和10 月,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家分別在紐約林肯藝術中心、卡內基音樂廳舉行新作品音樂會?? 參見李詩原《當代音樂批評中后殖民話語評析》,《黃鐘》2009 年第3 期。? 分別參見劉紅柱《紐約林肯藝術中心響起中國聲音——記2018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家新作品世界首演音樂會》,《人民音樂》2018 年第4 期;《2018 年中央音樂學院管弦樂新作品音樂會美國卡內基音樂廳首演》,《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8 年第4 期。? 這個英文表述來自姚亞平《于潤洋音樂學分析思想探討》,《音樂研究》2008 年第1 期,第56 頁。,已不再是到西方“朝圣”。音樂會上所發布的作品雖不失中國傳統音樂乃至傳統文化印跡,但也不再像那些曾在國際舞臺上展示的“國粹”,只是一種貼有中國標簽的“土特產”,而是具有國際性(普遍意義)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一種用國際化符號塑造出的“中國形象”。透過這些現象,我們似乎能揣度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文化心理——文化自信。顯而易見,中國現代音樂走向世界的價值認同,而成為一種文化自信的表征,成為一個用國際語言講“中國故事”,且著眼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文本。
三、關于現代音樂的分析和研究
此次井岡山“中國當代音樂創作研討會”是以音樂分析為話語中心的,尤其涉及音樂的音高組織和曲式結構。在現代音樂研究中,分析(analysis)至關重要,一些青年學者熟練掌握了分析這個有力“武器”,展露出年輕一代在技術上的優勢。怎樣才能充分發揮這種技術優勢?對于一部特定的音樂作品而言,這需要探討其語言形式的音樂結構功能和藝術表現功能;或不假其思想內容,通過音樂分析直接生成其人文意義。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卻是老生常談,而尚有一些問題似乎更值得思考。筆者在此次研討會濃重的學術氣氛感召下,進一步意識和領會到中國現代音樂分析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透過諸君的分析和研究,發現其方法或已/或當體現出以下三個方向的轉向。
第一,從“文本”轉向“話語”——打破音樂分析(musical analysis)與音樂學分析(musicological analysis?? 參見李詩原《當代音樂批評中后殖民話語評析》,《黃鐘》2009 年第3 期。? 分別參見劉紅柱《紐約林肯藝術中心響起中國聲音——記2018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家新作品世界首演音樂會》,《人民音樂》2018 年第4 期;《2018 年中央音樂學院管弦樂新作品音樂會美國卡內基音樂廳首演》,《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8 年第4 期。? 這個英文表述來自姚亞平《于潤洋音樂學分析思想探討》,《音樂研究》2008 年第1 期,第56 頁。)的學科壁壘,實現多學科、多方法的整合,使作品分析和研究成為綜合性、交叉性的“話語分析”。此次研討會已呈現出一些可喜的端倪:一些從事作曲技術理論研究的中青年學者開始向音樂分析以外的學科領域伸展,并觸摸到音樂美學、音樂史學、音樂哲學的邊緣;一些從事音樂史論研究的青年學者則表現出對音樂分析的稔熟。他們的分析和研究又一次使筆者看到,音樂分析與音樂學分析之間的界線在逐漸被打破,二者之間的分野和學科壁壘顯得多余。這就意味著,音樂分析已不再是一種封閉性的文本分析,而走向多方法、多維度的綜合性、交叉性話語分析已逐漸成為一種必然。另一方面,在那種重視社會學、歷史學維度的音樂學分析中,青年理論家們對作曲技術的認識和把握也顯得相當精當。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是,作曲系師生已“有文化”了,音樂學系師生已“很靠譜”了。上述這些端倪或跡象,或許能使我們達成一個共識:關于中國現代音樂作品的分析和研究本來就應是一種綜合性、交叉性的話語分析。這主要在于:(1)音樂分析應進一步打破其封閉性閱讀模式,實行開放性閱讀,不僅在結構主義范疇內探討語言形式的結構功能,而且還要在“結構詩學”?? 參見賈達群《音樂結構研究的詩學策略》,《藝術百家》2014 年第4 期。? 參見李詩原《音樂分析生成人文意義的獨立性》,《黃鐘》2017 年第1 期。? 這里所說的“外在因素”就是“生平事實,政治事件、社會條件、教育方式及所有那些組成這個現象的周圍環境的其他因素”,參見《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Stanley Sadi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1980)第1卷“音樂分析”條,第341 頁。? 參見李詩原《音樂學分析:從文本到話語——西方音樂作品研究方法的哲學背景》,《黃鐘》1999 年第2 期。、修辭學語境中探討形式的藝術表現功能,并將音樂分析的觸角伸向內容與形式關系的范疇。(2)通過分析直接生成音樂作品的人文意義。?? 參見賈達群《音樂結構研究的詩學策略》,《藝術百家》2014 年第4 期。? 參見李詩原《音樂分析生成人文意義的獨立性》,《黃鐘》2017 年第1 期。? 這里所說的“外在因素”就是“生平事實,政治事件、社會條件、教育方式及所有那些組成這個現象的周圍環境的其他因素”,參見《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Stanley Sadi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1980)第1卷“音樂分析”條,第341 頁。? 參見李詩原《音樂學分析:從文本到話語——西方音樂作品研究方法的哲學背景》,《黃鐘》1999 年第2 期。即注重文本的整體上下文(total context)和“互文本性”,探尋蘊含在結構中的“共性寫作原則”和“形式美法則”,進而不假其思想內涵和其他外在因素(external factors)?? 參見賈達群《音樂結構研究的詩學策略》,《藝術百家》2014 年第4 期。? 參見李詩原《音樂分析生成人文意義的獨立性》,《黃鐘》2017 年第1 期。? 這里所說的“外在因素”就是“生平事實,政治事件、社會條件、教育方式及所有那些組成這個現象的周圍環境的其他因素”,參見《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Stanley Sadi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1980)第1卷“音樂分析”條,第341 頁。? 參見李詩原《音樂學分析:從文本到話語——西方音樂作品研究方法的哲學背景》,《黃鐘》1999 年第2 期。,在形式范疇內直接生成其人文意義。(3)應使音樂作品研究進一步體現出對音樂分析的依賴,同時進一步擴大音樂學視域,不應囿于形式主義封閉、自足的“語言—結構”分析(文本分析),也不應在歷史主義及社會學派的“歷史—社會”分析那里駐足,應在新歷史主義話語分析中對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制度、階級等進行全面、綜合和交叉性研究。上述即所謂“從文本到話語”?? 參見賈達群《音樂結構研究的詩學策略》,《藝術百家》2014 年第4 期。? 參見李詩原《音樂分析生成人文意義的獨立性》,《黃鐘》2017 年第1 期。? 這里所說的“外在因素”就是“生平事實,政治事件、社會條件、教育方式及所有那些組成這個現象的周圍環境的其他因素”,參見《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Stanley Sadi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1980)第1卷“音樂分析”條,第341 頁。? 參見李詩原《音樂學分析:從文本到話語——西方音樂作品研究方法的哲學背景》,《黃鐘》1999 年第2 期。。
第二,從“分析”轉向“闡釋”——在與作曲家的“視界融合”中進行有邊界的“誤讀”(misreading)。筆者曾問郭文景:“如果一個理論家對您的作品做了一些與您先前構思或作品實際所不同的解釋,您會怎么看?”他回答說:“他所做的這些解釋將成為我的作品意義的一部分。”向民在會上也指出:“分析和研究者對一部作品的解釋,本來就是作品意義的一部分。巴赫、貝多芬的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來分析和研究者的解釋。”作曲家們的回答,完全符合現代解釋學原理。一部音樂作品的意義,既包括作曲家和表演者賦予它的意義,還包括聽眾和理論家對它的理解和解讀。就理論家而言,他們對一部音樂作品的理解和解讀,雖然基于音樂分析,但畢竟取決于其主體意識,有著自身的“視界”,故將對原作意義進行延伸和闡發,即現代解釋學的闡釋或“誤讀”。這也就是所謂從分析轉向闡釋。但有兩點需注意:其一,闡釋不能脫離分析,不能脫離文本,不能不靠譜。其二,闡釋雖然旨在凸顯理論家的主體意識,但這種主體意識也應受到一定的抑制。這種延伸和闡發一旦超越了邊界(“太離譜”),就是“過度闡釋”和“誤解”。故作為一個理論家,首先應與作曲家構建對話式的“視界融合”,即“初始的視界”與“現今的視界”的“視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進而根據文本(總譜和音響)做出有邊界的“誤讀”。回望40 年中國現代音樂研究可以看到,理論家們似乎一直都在試圖從分析轉向闡釋。這在從事作曲技術理論的理論家那里更為明顯。但這種轉向也產生了一個問題:過去的闡釋主要是對作品思想內容和精神內涵上的闡述,但現在的闡釋則大量出現在對作品的技術性解讀之中。那么,音樂分析中的“誤讀”是否合理?或者說怎樣才能適度?這無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在筆者看來,這種形式或技術范疇的闡述或“誤讀”與對作品思想內容和精神內涵的闡述或“誤讀”是有區別的。很顯然,后者能在音樂形象和意義的不確定性中獲得理論支撐,但前者卻難以找到一個解釋差異的理由。除作曲技術給音樂作品在結構上的規定性外,音樂形態的多解性也應有特定依據,而非空穴來風的任意想象。例如,郭文景《川崖懸葬》開始處高疊和弦(第6 小節)的內在結構邏輯究竟是什么?筆者認為,這個高疊和弦可以看成是兩個“減三聲”(#F—A—C、 G—bB—bD)和兩個“窄三聲”(G—bB—C、 bB—bD—bE)的疊合。也許作曲家當時并不是這樣考慮的。既然如此,筆者為什么又要這樣闡釋這個高疊和弦?因為這種“減三聲”和“窄三聲”正是川東、鄂西民間音樂中常見的音調模式,其中“窄三聲”或許就來自《尖尖山》中“la—sol—mi”這個音調模式。況且,音樂中的“懸葬”就在川東。這樣的闡釋或“誤讀”即使不符合作曲家原意,且有差異,但也不失依據或契機。總之,從分析轉向闡釋必須“靠譜”,在闡釋或“誤讀”時,不但要與作曲家形成“視界融合”,而且還必須找到某種內在依據和契機,“語言—結構”層面的闡釋和“誤讀”尤其如此。
第三,從“民族性”探尋轉向“中國性”構建——探討和構建中國現代音樂的獨創性。“民族性”探尋一直是中國現代音樂研究的重要選項,并成為一種固化的思維模式,進而在一定意義上阻礙了中國現代音樂獨創性的探索。這種思維模式即“本土與西方對話”或“中西結合”。“本土與西方”(the Native and the West)是近代中西文化比較中的一對理論范疇,旨在構建中西的二元對立和對立統一。在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中,這種“本土與西方”就演繹出“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民族與世界”等子范疇。其研究目標就在于構建中西音樂的二元對立,進而闡釋和論證二者的融合——“本土與西方對話”或“中西結合”。也正是在“本土與西方對話”中,“民族性”探尋成為中國現代音樂研究的重中之重,且成為一個“套路”。顯然,這種“民族性”探尋的背后,似乎始終都有這樣一個潛臺詞——中國現代音樂實現了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的融合,故具有鮮明的“民族性”,而不是對西方現代音樂的簡單模仿,更不是“后殖民文化”的產物。毋庸諱言,這段潛臺詞中隱藏著一些復雜的文化心理。眾所周知,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 年中,由于受到蘇聯批判現代音樂?? 參見馮燦文《蘇聯歷史上對音樂家的兩次批判》,《黃鐘》1989 年第1 期。的影響,故現代音樂一直受到禁錮。現代音樂被指為一種患了“貧血癥”的“形式主義音樂”,不符合中國人的審美情感。于是,既有中國現代音樂研究似乎總在證明:中國現代音樂雖然是一種運用西方現代作曲技法創作的音樂,但卻充分體現出了中西音樂的融合,故具有鮮明的“民族性”,進而在審美上就能與中國人的審美情趣和審美情感相吻合,為此表現出了與西方現代音樂的不同,故不是也不可能是依附西方的“殖民文化”。既有研究正是從“反駁”入手的。1979 年羅忠镕發表了歌曲《涉江采芙蓉》,作為“中國第一首公開發表的十二音作品”,此曲可視為新時期中國現代音樂的起點。于是鄭英烈在對此曲進行全面分析之后指出:“《涉江》的旋律雖然是用十二音方法寫成的,但由于包含有結構的方整性,基本節奏的貫穿性,旋律的流暢性,詞曲聲調的密切配合,明顯的五聲風格以及內容的調性因素等多種傳統因素,使得這首序列旋律聽起來既有現代風格的特征,又不失古色古香的風味;因而也就較接近中國聽眾的欣賞習慣。”?? 鄭英烈《歌曲〈涉江采芙蓉〉的創作手法》,《音樂藝術》1981 年第3 期,第82 頁。這正是其民族性探尋。這種民族性探尋已持續了40 年,并取得可喜成果,既有助于中國現代音樂技法體系的構建,又推動了中國現代音樂的發展,但尚不足以構成對既有“形式主義”論和“殖民文化”論的有力反駁,也不能足以證明中西現代音樂之間的不同。筆者認為,要完成這種反駁和證明,必須從民族性探尋轉向中國性構建。如前所言,中國性包括民族性,但主要是中國現代音樂的獨創性,訴諸中國作曲家那些特殊的思想觀念和作曲技法。但需說明的是,這種特殊無關乎中國作曲家的族性,而在于中國作曲家的個性。后20 年中,越來越多的中國作曲家,已不再依賴民族性而躋身國際舞臺,而是在尊重世界性(或國際性)前提下力圖展現自己的個性。此次研討會中討論的作品(如秦文琛《對話山水》、代博《看不見的山》等),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這種價值取向。可見從民族性探尋轉向中國性構建,不僅是反駁既有某些理論的需要,還是闡釋當下中國現代音樂更注重基于獨創性的中國性這一價值取向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中國性構建將有助于推進中國現代音樂的國際化,使其成為一種真正體現國際視野和文化自信的音樂文化,而不再是那種只依托民族性的“土特產”或“異國情調”。
今天,中國現代音樂,除上述作為學院派作曲家文化身份的重要標識、作為專業音樂院校作曲系的一種技術訓練、作為滿足部分聽眾審美口味的小眾藝術、作為國際視野的體現和文化自信的象征外,還是當代音樂和作曲技術理論研究者開展學術研究的文本。作為接通實踐與理論的橋梁,正是這個文本,使作曲家和理論家在新的語境中形成對話,并在“視界融合”中生成了新的意義,形成了技術和意義上的互補,最終構建出一個新的文本。現代音樂分析和研究成為一種“靠譜”的音樂分析和學術探討,旨在通過技術分析支撐其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或直接通過“語言—形式”的分析生成其人文意義,最終使現代音樂的意義和價值得以充分闡發,真正體現出一種基于學術意義的存在價值。既然如此,關于中國現代音樂的分析和研究就顯得至關重要,因為它是現代音樂意義得以生成的重要途徑。就這個意義上說,現代音樂分析和研究也是現代音樂的一種存在方式。
余 言
現代音樂在當下中國并非“昨日黃花”,盡管不再有思潮可依托,亦不能像時下的命題作文和委約作品那樣受關注,但卻以別一種“姿態”存在著:它揭掉了“新潮”的標簽,也不再以“先鋒派”自居,而是在不斷自我反省、自我更新,并仍以一種基于樂音結構和音響造型的象征和隱喻,表達出一種潛在、深邃的思想高度和批判精神,呈現出學院派作曲家的價值追求,并代表著中國當代音樂的發展水平。這無疑是中國現代音樂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但中國現代音樂要成為一種真正詮釋文化自信、實現自我價值的音樂文化,還必須思考并解決兩個問題:第一,關于中國性的構建。中國現代音樂何以成為一種依托民族性,但更依托中國作曲家個性或獨創性的音樂文化,進而立于國際舞臺?這就需要從民族性探尋轉向中國性構建。然而,中國性不僅僅訴諸特殊性的民族形式、民族風格,而將更得益于中國作曲家運用普遍性的作曲技法過程中的獨特創造。唯有如此,中國現代音樂才能真正脫離那種由“土特產”或“異國情調”建構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身份,進而成為一種以開放(“反本質主義”)的中國性,而非封閉(“本質主義”)的民族性為前提的音樂文化;也唯有如此,中國現代音樂才能真正用一種國際化音樂語言講“中國故事”,真正成為文化自信的一種表征,進而體現出從文化自覺到文化自強的價值追求。第二,關于可聽性的認同。這并不意味著現代音樂應做出一種折中或妥協,放逐現代技法、現代風格等本質屬性,回到旋律、回到調性,而是試圖在“反傳統”與“可接受性”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這就是要使現代音樂既呈現出其應有的“力度”,同時也不總是以那種“異在”方式或以否定“自身對美的幻覺”為代價來揭示社會本質,實現其文化批判,并在適當考慮大眾審美取向的前提下做出一種新的選擇。只有這樣,現代音樂才能真正實現其文化謀略,體現其文化功能;才不會“絕望地被忘卻”,最終真的成為“一顆啞火的子彈”;才能使聽眾領會其主旨和指涉,感受其思想、筋骨、力度、溫度和情懷,進而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高原”“高峰”,最終像貝多芬、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一樣,具有超時代的魅力和超國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