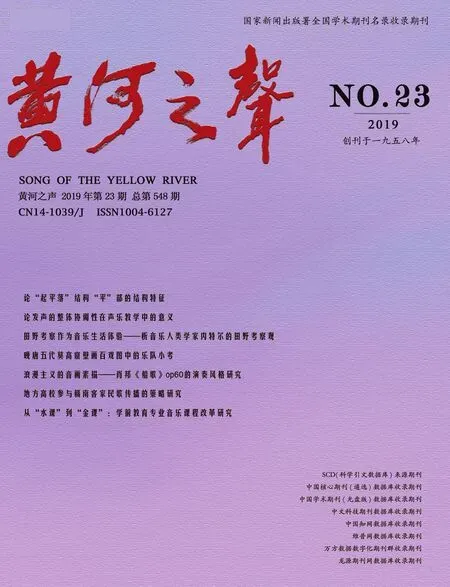不同視闕下的《關于島嶼》
楊 青
(西安外事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2017年,一直被譽為“臺灣之光”的林懷民,掌舵其云門舞集,歷時三年,創作出他退休前的收官之作——《關于島嶼》。
林懷民創作之初,欲將這部作品命名為《美麗島》,不料,2015年2月4日墜機事件,43人死亡,15人受傷;2016年2月6日高雄6.7級地震,117人罹難;2017年8月15日,臺灣爆發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無預警停電事件,時間長達5個小時,全臺共800多萬戶中的688萬戶居民受到影響。與此同時,林懷民本人在此期間,也由于遭遇車禍,導致右腳粉碎性骨折。這一連串的事件使得林懷民著實“美麗”不起來,于是乎便將“美麗”二字“退位”,將其作品名稱命名為《關于島嶼》。
蔣勛曾說:“人生就像一條河,從湍急繁華到寬闊平靜。”當林懷民由于車禍而導致其右腳粉碎性骨折的時候;當身為一名舞者的他躺在床上無法動彈的時候;當七十余歲的他經歷天災人禍一齊襲來的時候……當時的他將所想為何呢?也許王國維對于人生三個境界的言論可以很好的將其詮釋。第一個境界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彷佛詮釋了他在1988年“不得不”停掉云門舞集時的孤獨感悟;第二個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彷佛詮釋了他1991年復出,重新出現在人們視野,將云門舞集繼續下去的決心。他對舞蹈的愛,即使愛到極瘦無比,但卻仍不后悔,并且心甘情愿;第三個境界“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彷佛詮釋了他創團伊始直至今日,回望歷程,不論急流險灘,抑或繁華錦繡,臺灣這座島嶼其實一直都在。
一、幾何透視關照下的舞臺構造
在這部舞劇中,林懷民并非采用傳統舞臺構造形式,而是利用幕布將舞臺構建為一個舞臺與舞臺內側,兩面呈90°折角的立體造型,與此同時,舞臺全然采用純白底色,將簡約感達至極致。這一橫空出世的具有獨特造型的幕布,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投影幕布,于是乎在劇中時,純白底色上會不時投射出,由蔣勛等13位詩人所描寫臺灣的文字,而這些文字投影與舞者舞姿之間的交相輝映,便構成了舞臺上別具一格的視覺風景。
二、立象盡意之“留白”“余白”處理
全劇總籠觀之,林懷民彷佛在與觀眾進行“打翻調色盤”的調色游戲。純色有六種,第一種為白色,是純色之首,也是各色之本,而黑色則為第六種,是純色之末,代表各色皆無。[1]而林懷民則在白與黑之間有序“調和”舞臺整體色調,意味無窮。
伊始,呈現出干凈如新的白色投影幕布,而后背景幕布與燈光營造之效果,有如黑色顏料逐漸添加般,將其變為淺灰色——深灰色,繼而再加重色調終至黑色,隨后,幕布整體色調又如倒敘般,從黑色——深灰色——淺灰色,當最后一瞬,舞者轉身,幕布又變至“一片空白”,仿佛換了一個“人間”。
劇終,已被支離分解的文字慢慢被海浪沖刷,直至消失,就如林懷民曾經所敘述到的:“我們正處于文字大泛濫的一個時代,不斷低頭看手機看電腦,大部分是用文字所書寫,可是文字在這個時代也會漫漶掉,有時候是被改寫,被抹殺,變成一片空白。”這也許是他最后一幕如此這般設計的原由。而在我看來最后那一瞬而至的“一片空白”,一人獨獨矗立于舞臺還有另一層涵義,就如云門舞集的看板被林懷民任性的全然delete,等待另一個人的丹青妙筆在這片空白的畫布上再次繪制。
“言有盡而意無窮”,與此同時,這“一瞬空白”之我見,亦有結合于“余白”與“留白”二者之內涵。
“余白”在此含義有二,一為我們常言道“心有余白”,特指一個人沒有半點私心雜念,具有一種超然、豁達、寬容的心態。二為安藤忠雄在其著作《在建筑中發現夢想》中對京都庭園的代表龍安寺石庭的描述:“100坪大的長方形土地以低矮的筑地墻包圍、僅以大小不一的15塊石頭配置而成的這個庭園……這個庭園就像是為了襯托筑地墻身后的樹影、更后方的山巒而存在的舞臺裝置。在自然當中截取‘余白’、使得四周的環境更加一目了然,而也因此進一步增加‘余白’的深度。[2]
“留白”是以“空白”為載體進而渲染出美的意境的藝術,是一種極具中國美學特征的藝術作品創作手法。不論是體現在南宋馬遠的《寒江獨釣圖》中,雖無一絲江水,卻感煙波浩渺,滿幅皆水的繪畫藝術;或是“不著一字,而形神俱備”的文學藝術;抑或是“無聲勝有聲”的音樂藝術……
于筆者所見,林懷民最后一幕的“一瞬空白”,借助大片的“白”來凸顯舞臺中獨獨矗立的舞者,使觀眾透過其舞者之“形”窺探其純潔如水般超然、豁達之“境”。
三、群體舞段之個體“人”性
從早期林懷民的《行草》《屋漏痕》《水月》《竹夢》等作品中不難發現,舞者雖為人之肉身,但卻不為人之心靈,舞者只是成為藝術表現的一個物化載體而已,所有的“人”均一同“失性”——失去“人”性。
而近期的作品《稻禾》《關于島嶼》等中的舞者,均回歸日常生活世界,切近日常生活世界,所有的“人”均恢復了“人”性。在作品《關于島嶼》中,這種“人”性并非是一個個具有獨特個性的人物、獨特命運的人物,更甚是具有強烈的個體化的情感等方面表達的人物,而更多的是運用每個人物均保持著各自在自身狀態之中的群舞,繼而將其人物自身的狀態消融在眾人之中。
其中一幕,三名舞者矗立于舞臺,但高低錯落,正反相異,方向有別的設計,使得觀者強烈感受到他們雖同一在物理空間,但卻迥異于心理空間。這一有形看得見的物理空間與無形看不見的心理空間放置一處時,三名舞者的實際距離便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于是乎便產生了《關于島嶼》中群體舞段之個體“人”性對于觀者的撞擊感。而類似場景在作品中則頻頻出現。
四、內心呼喚之陰陽衡律
天災難測,人禍難避。《關于島嶼》一開篇便在幕布上投射出:“臺風,地震,內門,像世界許多地方,島嶼經常面臨災難與挑戰,但它的居民始終沒有喪失仰望星空,往前走的能力”,繼而又投射出:“編舞者以島嶼為隱喻,思忖《金剛經》的偈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易經·系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之,成之者性也。”[3]陰陽運動是萬事萬物的運動規律,而陰陽平衡是生命活力的根本。陰陽平衡就是陰陽雙方的消長轉化保持協調,既不過分也不偏衰,呈現著一種協調的狀態。陰陽平衡則人健康、有神;陰陽失衡人就會患病、早衰,甚至死亡。在這多災多難的島嶼上生活的林懷民,與其他民眾一樣,在經歷、在感受。以筆者觀之,林懷民欲將男指陽,女指陰,在作品的群舞部分,大部舞段不時出現的男女人數均等,興許并非巧合,而是暗喻林懷民在作品中所承載其內心的呼喚---陰陽平衡,繼而使得像母親一般養育了2300萬子民的“婆娑之洋,美麗之島”能夠“四季如春,國泰民安”。
從第一次出現一男一女的雙人舞便達至陰陽平衡之后,上場口前區跑來1女,繼而再跑來1女,增至2女,接下來再+2女,繼而再+4女,最后成至7女;繼而在下場口后區反側也逐漸+男,最后成至7男,又一次達至陰陽平衡。緊隨其后,7男齊步俯身跑向7女,并且一男一女組合成對,再一次達至陰陽平衡。
無獨有偶,同樣的陰陽平衡是在作品第二次出現一男一女的雙人舞之后,則通過上場1男1女——上場1女——下場1女,上場2男2女,達至4男4女的陰陽平衡。除此之外,還有一處則是,舞臺上只余2男——上場1女——上場1女,下場2男——上場2男,達至2男2女的陰陽平衡;另有一處則是當巨大的白字“麗”慢慢爬上全黑底的幕布時,舞臺上僅剩1男,隨后便是上場1女——上場1女——上場1男——上場1女——下場2女1男,上場2女1男——上場1男,達至3男3女的陰陽平衡,但此時,1女上場,若無其事走下場,其余6人也緊隨其后若無其事拍成一條直線走下場去,在隊伍的末端又上場1女,但這1女并未下場,留于舞臺之上抽泣不止,可隨著七名舞者的下場,舞臺便變為一片漆黑,只有一條白色的長長的線留在了幕布上。而這一切,未嘗不是陰陽失衡,物極必反的結果呢?可就像林懷民曾說:“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害怕,我們一定有很多事情是害怕的,從個人的事情到對萬物的發展,可是我們不要呆在那個害怕的情緒里。人生不設限制,除非你給自己制造障礙。”而那條細細長長的白色的線,正如萊昂納德·科恩在其《Anthem》中曾唱道“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五、內心情懷之《關于島嶼》
(一)對島嶼
從早期《白蛇傳》《薪傳》《紅樓夢》等作品中,我們在林懷民的舞蹈中可以窺探到其深切的歷史關切和傳統情懷。而后來的《我的鄉愁,我的歌》《九歌》《家族合唱》《關于島嶼》等作品,我們便可清晰看到,林懷民對于自己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來說,對于臺灣腳下這片土地的熱忱與關切,不言而喻。李翱曾請教惟演禪師:“什么是佛法大義?”惟演禪師指一指天,又指一指桌上的凈瓶。在創作《關于島嶼》時,想必林懷民定是深刻的參悟到了其中至奧妙,正如李翱所說:“我來問道無余說,云在青天水在瓶。”云在天上,水在瓶中,其實就是一個自然的狀況,是想告訴我們不要本末倒置了,每天念佛經,念佛法大義,可是卻已忘記腳下之事。而這也是一個機鋒,興許也是林懷民在創作《關于島嶼》時的初衷,意思是要讓我們回到人最基本的生命認知上。
在這部舞劇中,不論是從桑布伊那來自靈魂深處的吟唱中,抑或是那一個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字體中,再抑或是從極具特點的舞蹈語匯中,都能夠感受到林懷民那不自覺的焦慮與悲愴之感。對于島嶼,因為喜歡,所以熱愛;因為熱愛,所以堅持;因為堅持,所以傳遞。他想通過舞蹈,這個他從事了一生的藝術形式,直擊觀者心靈,發人深思,引人思考。
(二)對舞蹈
本雅明在其極具顛覆性的作品《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書中,曾指出“在大眾看來,藝術品是消遣的誘因,而在藝術愛好者看來,藝術品則是凝神專注的對象”。[4]這聽起來多多少少有些諷刺。而一身儒雅氣質的林懷民,對于藝術與藝術家的理解,表面聽來卑微至極,但深究便能發現其言語中所流露出的那份驕傲與自信。他曾說:“何謂藝術家?什么時候大家才會感覺到藝術?作為一個藝術家,就像在路邊唱小調要錢的乞丐,行人匆匆,只有在他有人事的時候,他放慢了腳步,終于聽到了那個乞丐的歌聲,但是,在每一個人的生命里頭跟生活里頭,如果需要聽到那歌聲,而沒有那個歌聲的時候,那是很大的悲哀”。
六、結語
《天堂電影院》中有一句臺詞“如果你不走出去,你就會以為這里是全世界”,而1973年創團至今已46年的林懷民,雖帶著他的舞團走遍了全世界,但始終,臺灣這座島嶼才是他最掛于心間的一片凈土。
正因如此,以《關于島嶼》結束自己傾其一生所打造的舞蹈王國再合適不過了。林懷民從其不同視闕下講述“關于島嶼”的種種,使其散發出與眾不同的美學張力與藝術清香。獨特簡潔的舞臺空間,給與觀者以不同的關照視角;中國美學中“余白”與“留白”之韻,另觀者“劇有盡而意無窮”;中國古代哲學中陰陽恒律之觀,使觀者不禁深之慮之;群體舞段中個體“人”性的顯現,讓觀者審視現實,真實之感仿佛歷歷在目;所有濃厚之情歸根到底皆因對舞蹈之情、對島嶼之愛。
將于今年“退休”,年以70余歲的林懷民,想必并非如《論語·為政篇》中所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規”,[5]也許,他的另一個人生篇章才就此拉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