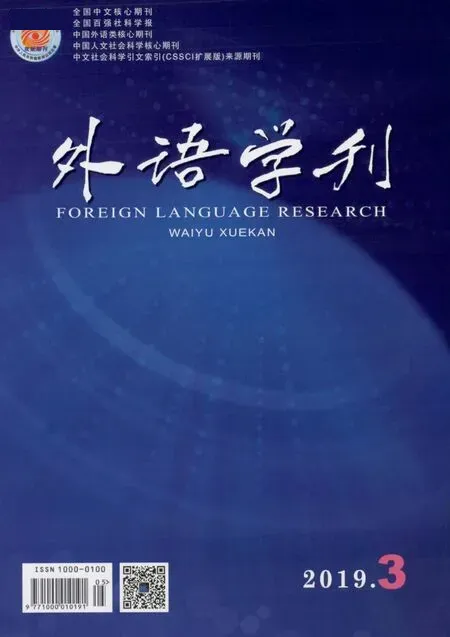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三副面孔*
——語言生產·欲望政治·生物權力
袁文彬
(深圳大學,深圳 508060)
提 要:盧卡奇開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道路為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智性動力,葛蘭西、阿爾杜塞、普蘭查斯、拉克勞和墨菲等將隱喻式的“基礎—建筑”詮釋為符號學意義上的語言生產模式。而法蘭克福學派的賴希、馬爾庫塞和弗洛姆則將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結合起來,展開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欲望政治研究。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命,語言與生命須臾不可分離,后馬克思主義者如阿甘本、哈特和奈格里等則將語言生產模式和欲望生產模式推進到生物生產模式,即考察后現代語境下人類社會的生命權力,甚至人體內部的生物權力。無論是語言生產還是欲望政治都是生命權力的外在表現形式,對身體從外到內或從身體到生命,即從生命權力到生物權力的范式轉換,才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終極關懷。
1 引言
正統/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對資本主義社會展開宏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上層建筑中的文化因素。為彌補這種宏大敘事的缺憾,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不斷補充、修正馬克思主義關于“基礎—建筑”這一二元互動的辯證關系。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提出“什么是正統馬克思主義”這一基始性問題。在盧卡奇開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道路上,葛蘭西在《獄中札記》(1971)中首次提出“文化領導權”,阿爾杜塞將結構主義思想融入馬克思主義形成結構馬克思主義,提出“多元決定”,普蘭查斯則順此提出“相互決定”,他們以不同方式理性而辯證地再思考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多元互動關系。在福柯“話語—譜系”這一知識考古學的認識論范式啟發下,拉克勞和墨菲則認為這一切都是由話語決定的①。而鮑德里亞則試圖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取代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法蘭克福學派在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展開了事關人類微觀精神層面的“文化批判”。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命,語言和生命兩者之間須臾不可分離。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也因此步入語言生命政治學階段。傳統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太過籠統,還不足以揭示人類社會存在的各種普遍性問題,包括性別、種族、生態、環境等,它也無法深入到人體內部來揭示當代人類的生物醫學權力。所以,對微觀精神分析、生命權力和生物權力等的分析似乎能補充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中沒有涉及到的層面,使得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能在新時代展現新面貌,使我們借此得以豐富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語義地平線。本文將從語言生產、欲望政治和生物權力3 個維度簡要地分析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在后現代狀況下對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語境化/再語境化等問題的思考。
2 語言生產
對于阿爾杜塞而言,“文化領導權”也未免粗枝大葉,失于籠統,他進一步將國家機器分為壓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認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已經取代暴力性國家機器。在這方面,他和葛蘭西不謀而合,不同之處在于其挪用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這一資源,形成其極富語言性、符號性的結構馬克思主義。阿爾杜塞將結構主義語言學原理運用到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分析中去,對他而言,語言結構就像意識形態的結構②。所以,阿爾杜塞說,“意識形態無歷史”,“意識形態不是歷時的,而是共時的” (Althusser 1971:159)。對阿爾杜塞而言,社會主體就如同索緒爾的符號一樣,個人與其社會地位緊密結合在一起。

索緒爾 符號=聲音形象(能指) +概念(所指)阿爾杜塞 主體=個人(能指) +社會位置(所指)
主體就如同符號一樣,其身份和自我認同來自于和其他符號人在系統中的結構位置,而這種符號人的總體就形成阿爾杜塞所言的社會結構。單個符號沒有意義,只有在符號關系網絡中才有意義;單個人也沒有意義,只有在社會關系系統中才有意義。阿爾杜塞借索緒爾之口,重申馬克思的“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人的社會屬性,人的語言性和社會性在此殊途同歸。阿爾杜塞區分大寫主體(“S”ubjects)和小寫主體(“s”ubjects),類似于語言和言語,與喬姆斯基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也不無內在的親和力。

結構 深層先天結構 表層后天結構索緒爾 語言:語言規則系統 言語:具體個人話語阿爾杜塞 大寫主體:意識形態范疇 小寫主體:個人具體行為
他反對經濟決定論將歷史簡化為一系列的結構因果論,起決定的經濟結構既非線性因果關系,亦非先驗精神本質的反映,而是結構關系互動中的各種要素以不同方式排列組合起來決定經濟基礎,也就是“多元決定”(over-determination)。多元決定深化了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用語言學模式來詮釋社會模式,否定經濟決定基礎的單向度線性關系,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語言性、符號性、結構性、科學性,使得馬克思主義思想實質性地進入到現代語言哲學層面,開啟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轉向的新局面。
在阿爾杜塞開辟的結構馬克思主義道路上,普蘭查斯提出經濟國家機器(Economic State Apparatus),以補充壓制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溝壑壁壘。這3 種國家機器具有相對獨立性,只有兩兩面對時才能實現國家統治。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并非僅僅是觀念、文化、信仰或價值觀,而是與社會物質生產關系緊密相連。不是上層建筑再生產經濟基礎,而毋寧是說,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須臾不可分離。這樣,政治、經濟、意識形態3 個領域合而為一,并簡化為3 個互相依存的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壓制性國家機器和經濟國家機器。對普蘭查斯而言,這3者相互決定。普蘭查斯將基礎和建筑融合在一起,否定各自的獨立存在,“國家再也不是擁有權力本質的容器”(Poulantzas 1978:108)。國家只是運作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關系的策略性產所。普蘭查斯將阿爾杜塞的多元決定改寫為相互決定(mutual determination)。
無論是葛蘭西的領導權,還是阿爾杜塞的多元決定,抑或普蘭查斯的相互決定,都圍繞“基礎—建筑”這一結構關系而拓展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基本思想。不同之處在于,只有阿爾杜塞受到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并明確將其和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聯姻在一起。馬克思主義的物質生產、社會勞動和階級關系等實體內容都被轉換為結構關系,物質性逐漸被轉換為語言性和結構性。如同索緒爾所言,語言是一種形式而非物質(Language is a form not a substance.);對于葛蘭西、阿爾杜塞、普蘭查斯而言,“基礎—建筑”之間的關系也僅僅是一種形式,而非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物質關系。
拉克勞和墨菲就表達這樣一種純粹依靠語言符號關系而建立起來的社會結構。社會及其階級關系已經變成符號要素,階級關系就是符號之間的關系,“系統中的組成成分不斷朝系統運動,但沒有最終的穩定系統……這是一種結構,意義是被結構建構出來的,這就是我所說的話語,話語說明了現存社會中一切事物都不具備穩定性”(Laclau 1988:254)。結構是穩定的;話語則是變動不居的。葛蘭西、阿爾杜塞、普蘭查斯所謂的結構關系在此不復存在,結構關系演變成話語關系。國家不再是實體,而是索緒爾意義上的符號運作,其身份/認同是在符號差異關系中被建構起來的,諸如生產力、生產關系、階級關系不過是符號之間的互動而已,“所有價值都是對立價值,由差異關系決定”(Laclau,Mouffe 2001:106)。在語言中只有差異,而無實體要素(positive terms)③,在社會中也是如此。須要注意的是,如果語言不能和外部的物質世界形成互動性紐帶,社會系統將會在時空中形成漂浮的能指,新的話語構型只能作為社會生產范式的替代品而已,但無法消融語言范式和生產范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
在符號化的道路上,鮑德里亞走得更遠。他從德波的“景觀社會”出發,深入符號帝國,以符號生產關系取代社會關系,以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取代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異形同構的特點:
1.政治經濟學:在有用性(需求、使用價值等,所有人類經濟的指涉)的遮蔽之下,它建立了邏輯一致的體系,以及可計算的生產率,所有生產都被分解為單一要素,所有產品在抽象性上都是等價的。這就是商品邏輯和交換價值系統。
2.符號政治經濟學:在功能性(客觀目的性,使用同質性)的遮蔽之下,它建立特定意指模式,其中,所有外圍的符號都在邏輯計算中充作簡單要素,在符號交換價值系統框架中互相指涉。
(Baudrillard 1981:191)
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符號價值建構人們在社會中的身份/認同,而符號是一種被抽空內容的空洞所指,它代表人類不斷走向異化這一事實,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拓展馬克思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豐富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批判內涵。當然,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是無法取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但它對當前虛擬經濟、虛擬世界、仿像與擬像充斥的商品符號拜物教的批判仍然顯示出激進的批判鋒芒。這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發展的第一階段,我將其稱為語言符號生產,簡稱為語言生產(linguistic production)。語言轉向之后,語言模式提供的智性動力已經滲透到所有人文學科領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研究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中的語言生產正是語言模式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領域滲透的結果,揭示出語言模式和社會生產模式的異形同構,闡明兩者的聯系節點,使我們能挖掘出傳統馬克思主義所忽略的語言因素對社會生產的構型塑造力。
3 欲望政治
語言中孕育著欲望,它是后結構主義者們的共同訴求,語言與欲望因此緊密聯系起來。結構主義興起,結構、規則、符碼取代所謂的存在主義/人本主義,結構主義巨人列維·斯特勞斯在紐約避難期間與雅各布森邂逅相逢,吸收其二手索緒爾思想,突然橫空出世,宣告存在主義巨星薩特的隕落,人的主體性或主觀訴求因此被懸隔。后結構主義者們則力圖沖破語言結構主義的牢籠,消解自啟蒙運動以來“大寫的人”對主體性的宰制,還原“小寫的人”,所以有了克莉絲蒂娃“詩學語言的革命”等,將人的微觀欲望之訴求浮出歷史地表。比后結構主義更早的要數法蘭克福學派的先驅們。賴希在1936年的《性革命》中將其思想體系稱為“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和微觀精神層面結合的始作俑者,他試圖用弗洛伊德的理論來填補馬克思主義空白,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馬爾庫塞的“欲望解放”、弗洛姆的“社會性格”進一步豐富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而德勒茲則掀起“精神分裂分析”革命,以“逃逸線”批判資本主義的非人境地。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與精神分析能夠聯系起來,就在于人既有“動物性”,也有“社會性”。人既受社會關系支配,又被生物本能控制;批判理論既包括社會批判,也包含心理批判;革命既有社會革命,也有心理革命。在人性理論、批判理論和革命理論這3 個維度中,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找到共同的阿基米德點。在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方面,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更是異形同構:

(Wolfenstein 1993:113)
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價值生產體系,后者是欲望生產體系。這樣,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研究對象就從語言生產范式過渡到欲望生產范式。馬克思主義忽視人類的微觀精神層面,而精神分析則忽視人的社會性,所以,兩者必須結合起來以彌補自身的不足。
對賴希而言,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有兩個缺陷:不能解釋經濟發展過程中意識形態形成的機制,也不能說明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賴希因此認為,“性格結構”理論可以解決馬克思主義的這兩個缺陷。精神分析應該跳出狹隘的圈子,投身于改變現存社會秩序之中去,精神分析家的任務不是“治療”,而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將革命動因歸結于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受壓迫、在經濟上受剝削,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決定了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目標也僅僅為無產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獲得解放。人類在性格方面的斗爭,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而是具有自由性格結構和獨裁主義性格結構兩種人之間的斗爭。在此基礎上,賴希提出了“性革命”。性革命能帶來性健康,成為新社會的助產婆,創造新的社會結構。所以,賴希用“性格結構”“性格盔甲”“性革命”等微觀層面的訴求來彌補馬克思主義對人類微觀精神層面的忽視。除此之外,賴希也用其理論分析了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就在于釋放出人性中的破壞性力量,與人的獨裁性格同流合污,賴希將其稱為“法西斯群眾心理學”。也就是福柯、德勒茲所言的“微型法西斯主義”(micro-fascism),它更隱蔽、更危險,且無所不在,根治起來也更困難。人類的未來在于性格結構的解決。
德勒茲系統地置換了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概念。(1)范疇轉換:符號、力比多流、編碼取代生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2)從歷史到地理:從時間到空間;(3)從勞動到欲望:即從勞動生產到欲望生產;(4)從意識形態到裝備:欲望從意識形態中脫離,形成群體話語裝備;(5)從政黨到群體:前者屬于被規訓的主體,后者屬于群體主體;(6)從克分子到分子:產生了弱勢語言/文學。在《千高原》中,德勒茲對占統治地位的語言哲學和語言學展開強烈批判。語言不是交流工具,它具有特定功能。語言是列寧意義上的命令詞,是實施權力、灌輸意識形態的工具,它不是個人話語,而是群體裝備下的話語,打上了社會性標簽。在這種意義上,語言就是歷史現象、物質現象、政治現象、歸根結底,語言的功能就是主體生產(Lecercle 2006:139)。語言經歷一個疆域化—去疆域化—再疆域化④的過程,人類社會也經歷了原始社會—專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3 種社會形態與之對應,這就是語言的褶子問題。原始社會疆域化的語言對應原始社會的大地身體,反生產模式為狂歡化慶典;專制社會解疆域化的語言對應于專制社會的帝王,反生產方式為帝王對民眾的恩澤;資本主義社會再疆域化的語言對應于流動的資本,反生產模式為“政治—軍事—工業情節”。3 種社會的書寫方式不盡相同:原始社會為大地書寫;專制社會為帝王書寫;資本主義社會為資本書寫。這標志人類社會的變遷:從對大地的依戀到對專制帝王的依賴,再到對資本的依賴。德勒茲以此方式改寫了馬克思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話語關系:
生產方式:
馬克思(生產方式):原始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摩爾根(《古代社會》):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
德勒茲:符碼化——超符碼化——(解符碼化)再符碼化
(詹明信1997:18)
因為欲望的流動性主體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一個“生成”(becoming)過程,生成也是逃逸的過程,這就是德勒茲“逃逸線”的意義。我們的人生由各種線組成,總是被各種線穿越,它們是:堅硬線、柔軟線、逃逸線(Deleuze,Guattari 2000:195-198)。堅硬線是質量線,無比堅硬,無法逃脫;柔軟線是分子線,擾亂線性和常態,沒有目的和意向;逃逸線則完全脫離質量線,從破裂到斷裂,主體在多變流中變成碎片,即解放之線,讓我們自由感受人生,它是危險之線,使我們能夠逃逸符號資本主義,逃逸線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言的“解放敘事”。
跨越地平線到另一個世界去。逃逸線是一條開放道路,通往未知的漫長人生旅途,目標只是旅行,是索緒爾組合段上無盡的指涉。對德勒茲而言,寫作就是:背叛、生成、逃逸。寫作就是追尋一條線路、多條線路、整個制圖學。卡夫卡的《城堡》代表官僚機器;《審判》代表法律機器;《美國》代表技術機器。卡夫卡的《變形記》中動物變成人,人變成動物這樣脫離領土的相互生成逃逸線,以逃脫官僚機器、法律機器、技術機器這樣僵硬的切割線。德勒茲用逃逸線重寫馬克思主義對未來歌德巴赫式猜想的浪漫主義情懷。
4 生物權力
阿甘本吸收維特根斯坦的“去想象一種語言形式,意味著去想象一種生命形式”,即通過語言來思考生命問題本身。僅有一種方式表達“我說話”的意義,就是“我生活”。生活就是語言存在的表達式。阿甘本就這樣從語言問題上升到生命問題。阿甘本不但延續福柯的生命政治學內涵,也吸收卡爾?施密特、本雅明、阿倫特、海德格爾以及巴塔耶的生命政治學內核。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阿甘本也因此將生命分為zoē 和bios,前者為生物存在,事關家庭、繁殖;后者為政治生命,事關城邦。他從羅馬法中發現了神圣人(homo sacer)。因神圣人自身有污點,所以不能作為祭品,任何其他人殺死神圣人都不觸犯刑律,神圣人不在任何政治—法律范圍之內,不受主權邏輯保護,只剩下自然存在,即“赤裸生命”。從古羅馬被驅逐者到中世紀被詛咒者,再到納粹集中營的囚犯,都如同神圣人一樣。即使是當代社會,赤裸生命仍然存在,如尋求庇護者、難民、腦死亡等。他們都具有一個共同點:其生命都被排斥在法律保護之外。
在福柯和阿甘本對人類未來無限悲觀之時,哈特和奈格里則顯示出樂觀的態度。他們借用福柯的生命政治學概念,但作出重要修正,提出“生命生產”(biological production)這一概念。生命政治生產,即社會生命本身的生產。他們批評福柯只關注規訓—權力這一“結構認識論范式”,是靜態的生命政治學。生命政治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化的兩種趨勢,即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的區別消失殆盡,生命不再屬于再生產范疇和生產程序;而毋寧是說,生命決定生產本身,生產和再生產之間的差別也消失了。
無論是福柯、阿甘本,還是哈特和奈格里,都僅僅關注作為完整身體的外部,而20世紀的生物醫學則關注人類的身體內部。腦部掃描、DNA 分析、移植醫學、生殖技術等表明我們與自然身體告別,身體將不再是有機體,而是一個可以被閱讀和被改寫的分子軟件。生物科技實踐將越來越把身體內部作為干預空間。生物政治學將創造新型的生死關系,消解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認識論界限。在生物醫學、生物技術和基因組學的時代,新的“生物公民”將會形成,不可避免會激起國家政治、優生學和種族衛生學等幽靈。一方面,生物技術及其衍生物如生物經濟、生物資本可能會促進人類福祉;另一方面,也會給人類帶來災難。所以,福山不斷警告生物科技時代的后果,需要全人類慎重考慮。生物科技時代,知識生產和主體生產涉及到3 個方面。首先,生命/生物政治學需要生物和生命體的系統知識,提供認知地形圖,打開生物政治學空間,重新定義主體及其形成;其次,生命/生物現象不能和政治脫離開來,權力如何傳播、生產知識都是不可忽略的問題;最后,主體化如何受到科學、醫學、道德、宗教或其他權威的影響,是如何接受社會認可的對身體和性別方面的改造的。
這樣,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問題就不斷從語言生產到欲望生產,并順次推進到對人體內部的生物政治學研究,體現出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對人類社會由外到內,即從身體到生命的關懷,再次說明,語言生產、欲望生產只不過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起點,對生命由外而內的關懷才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落腳點和最終關懷。
5 結束語
馬克思主義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在不同時代,需要不同詮釋,如同克羅齊所言,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或如同懷特海所言,整個西方哲學都只不過是柏拉圖的一個注腳而已,現代社會的各種批判理論也不過是馬克思批判哲學的一個注腳而已。各種迥然異質的詮釋也許才能更全面深入地促進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現象學還原,誤讀才是最穩定的閱讀。馬克思主義留下的空白為我們預留出無窮無盡的話語空間。我們得感謝他老人家沒有把話說盡說透,在語言哲學層面更是留下諸多盲點,為我們言說提供可能性,否則,我們將失語癥似地無可言說。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3 副面孔——語言生產、欲望政治、生物權力——也只是為了分析的方便而作出的粗線條勾勒,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比之更為紛繁復雜,遠不是這3 個關鍵詞所能涵蓋的,但這3 個關鍵詞背后蘊含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范式轉換,預示著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內涵和外延的多義性。但不可忽視的是,語言模式和生產模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決定語言模式無法真正取代生產模式,也決定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無法真正取代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生命而非身體,才是當代所有人文科學包括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的終極關懷。
注釋
①福柯只是作為現代生命政治學的始作俑者,但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柏拉圖在《理想國》《法律篇》中討論了“優生學”;亞里士多德在《尼格馬可倫理學》、《政治學》中討論了人口的質量和數量問題,此為生命政治學的真正開端。中古時期,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也持續了討論了相關問題,此后,生命政治學方面的論述不斷式微,直到福柯在《性史》(第1卷)提出這一概念,隨后在法蘭西學院講演錄中如《生命政治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必須保衛社會》(The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安全、領土、人口》(Security,Territory,Population)等作品中深化這一論題,“生命政治學”方始成為當代人文科學中的關鍵詞。
②對于后結構主義者拉康而言,語言的結構就像無意識的結構。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分歧在于,前者凸顯索緒爾的語言系統;后者強調語言的使用即話語。
③國內學界往往將positive terms 譯成“積極要素”,忽略了歐陸哲學和英美哲學之間的差異,前者強調先驗式的形式范疇,后者突出經驗主義的實證/實體成分,在此基礎之上,就不難理解其為“實證要素”“實體成分”或“實體要素”的意思了。
④愿意為“領土運動—脫離領土運動—再領土運動”,大多數譯為“轄域化—去轄域化—再轄域化”,與列斐伏爾(H.Lefebvre)、蘇賈(E.W.Soja)的空間概念不無關聯。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已經開始顯示從“靜止時間”到“空間運動”的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