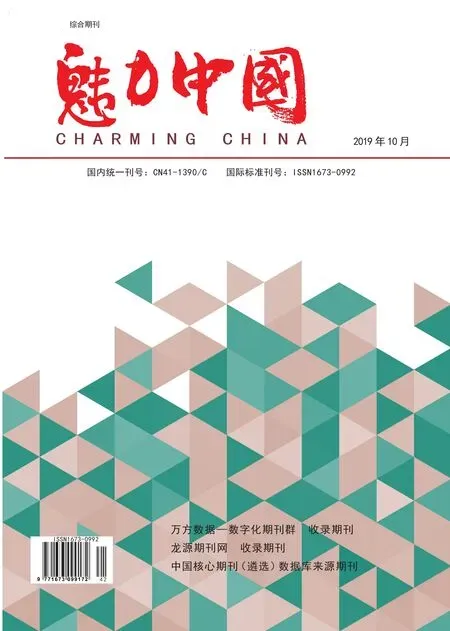以彝族畢摩為例探究少數(shù)民族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機制
邱作 宋強
(四川農(nóng)業(yè)大學法學系,四川 雅安 625014)
一、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含義與保護意義
(一)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含義
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對其定義為“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chǎn)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以及與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相關(guān)的實物和場所”。其包括(1)傳統(tǒng)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2)傳統(tǒng)美術(shù)、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3)傳統(tǒng)技藝、醫(yī)藥和歷法;(4)傳統(tǒng)禮儀、節(jié)慶等民俗;(5)傳統(tǒng)體育和游藝;(6)其他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二)非遺文化保護意義
非遺文化可直接作用于經(jīng)濟發(fā)展,也可是簡接反作用于經(jīng)濟。如畢摩繪畫可以直接利用于當?shù)厣唐飞希魍庥^裝飾的同時也可以給予商品特殊性質(zhì)促進商品銷售。但,非遺文化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無形精神物質(zhì)存在,而這種精神物質(zhì)可以作為研究該文化群體的歷史、心理等的研究。
二、現(xiàn)有保護機制
從法律理論和實際保護機制兩個方面來探討現(xiàn)有保護機制的缺失。
(一)缺少具體化的實施細則
法律理論層面,目前畢摩文化保護法律依據(jù)有《文物保護法》,《中國非物質(zhì)遺產(chǎn)法》,《四川省非物質(zhì)文化保護條例》。前一部法律調(diào)整范圍較大,加上中國56個民族文化多彩多樣,所以所規(guī)定的內(nèi)容也是概括性的條例,實踐性較低。后一部法律的內(nèi)容上相對于前一部法律較具體化,但大部分內(nèi)容都是對于前一部法律的重申,實踐指導(dǎo)性也沒有具體化。
(二)過度強調(diào)政府指導(dǎo),缺少監(jiān)督程序
我國非物質(zhì)文化的總原則是“政府主導(dǎo),群眾參與”,而這種非物質(zhì)文化保護的原則在實際文化保護工作中顯示出雙面性:既有利也有弊。“政府的參與會提升文化保護工作的便利性和效率性,但政府一旦限制文化保護工作的資金流,文化保護工作就陷入了癱瘓狀態(tài)。其次,政府層面缺失有效的監(jiān)督程序,以致政府在很多文化保護工作中缺乏積極性,大多是根據(jù)政府的財政預(yù)算情況進行階段性保護。過度的強調(diào)政府的指導(dǎo)地位,但是在文化保護工作中政府又受限于各種原因而不能更好的去分配更多的精力去了解文化保護的途徑。
(三)觀念意識淡薄,群眾真正的參與度不高
文化繼承人,在享受著外來文化帶來的新鮮感的同時也在逐漸降低對自己本身文化的關(guān)注度,造成很多年輕人不了解畢摩文化,即外來新鮮文化沖淡了年輕人對于自身文化的興趣度和對文化消逝的危機感的認知。畢摩文化,包括畢摩文字、音樂、繪畫、儀式,這些對實際生存沒有實質(zhì)性影響的情況下人們更愿意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花在能實際有利于未來發(fā)展的事情上。
三、新形勢下少數(shù)民族非物質(zhì)文化保護機制
(一)文化觀念的宣傳,提升群眾的參與度
1.發(fā)揮專家的權(quán)威性和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知識和經(jīng)驗。
專家在調(diào)研、研究、著書等方面經(jīng)驗比較豐富,可以在文化保護中做出更科學的理論指導(dǎo),而這些理論指導(dǎo)可以成為政府或者其他文化保護主體進行保護時的重要參考依據(jù)。
2.文化傳承進校園
教育比任何強制性措施都要有效持久。一方面發(fā)揮高校和學者的力量,高校雖不能直接參與彝族畢摩文化的保護,但是作為保護工作的積極參與者,高校所起的作用是任何結(jié)構(gòu)沒有辦法替代的。 高校可以增設(shè)有關(guān)這方面的專業(yè)學科,招收此類學生。再者,中小教育系統(tǒng)增加對畢摩文化的教育,從小建立對畢摩文化的認知可以解決文化得不到認同的問題。
3.政府結(jié)合新媒介、新需求,讓文化動態(tài)發(fā)展,緊跟時代步伐。
文化保護是為了守住我們民族的精神,民族之魂,而如果文化保護只是把文化列入保護項目,然后再把可視化的文物原封不動的封起來。這是對文化保護的曲解,保護文化的目的在于讓后代不遺忘,不迷失,所以在文化觀念的宣傳中政府在合理開發(fā)的范圍內(nèi)借用當下新趨勢,如借用新聞媒體進行文化節(jié)目宣傳、報道。
4.加強非遺文化保護的國際合作。
加強國際合作不僅可以學習和汲取他國優(yōu)秀的保護經(jīng)驗,而且可以擴展文化保護資源和范圍。畢摩文化研究者與美國教授的合作、交流;2009年,聯(lián)合國機構(gòu)和中國政府有關(guān)部門聯(lián)合開展的“中國文化與發(fā)展伙伴關(guān)系項目”;2010年,中國檔案局與新加坡合作開展“搶救保護少數(shù)民族歷史檔案項目”對少數(shù)民族文化進行試點搶救。
(二)法律保護措施的完善
1.立法原則
在注重發(fā)揮政府在文化保護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也激勵其他文化保護主體充分發(fā)揮作用,即政府不是全方位的主導(dǎo)文化保護的全方面,而是加強其他文化主體在某些方面的主導(dǎo)作用,明確傳承人、文化保護協(xié)會等其他主體的權(quán)益和責任。
2.完善法律內(nèi)容
(1)借鑒實踐個案彌補立法空白。
如2002年,黑龍江省饒河縣四排赫哲族鄉(xiāng)人民政府訴郭頌等案例。該案是首個少數(shù)民族保護文化權(quán)利的勝訴案件。第一,該案確認了少數(shù)民族非物質(zhì)文化的權(quán)利歸屬于與該文化有歷史和心理等聯(lián)系的特殊性區(qū)域群體。第二、該案明確了地方性政府在非物質(zhì)文化保護中文化代表的地位。因為非遺文化更多的是無形的,再加上非遺文化具有區(qū)域性,所以在制定統(tǒng)一的規(guī)范化法律中存在困難,而實踐案例可以很好的發(fā)現(xiàn)不足。
(2)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直接保護和特殊保護
知識產(chǎn)權(quán)是一個開放的制度,自身是包容的不斷發(fā)展創(chuàng)新的,文化保護中應(yīng)該把與知識產(chǎn)權(quán)相兼容的部分納入到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范圍中來。將畢摩文化、經(jīng)書歸作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的“知識”。知識在社會進步與生產(chǎn)財富中居于源泉與核心的地位,同時利用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來保護畢摩文化有利于實現(xiàn)經(jīng)濟效益,從而提高文化保護者的積極性。地方性法律的區(qū)域化保護。在區(qū)域性法律或地方性政府文件中具體化代表性傳承人的認定、文化遺產(chǎn)申報標準、流程和文化保護落實的措施。